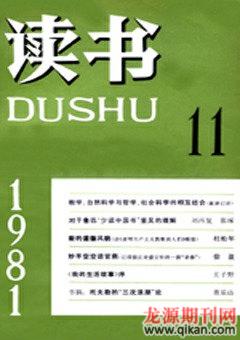是诗?是画?
凌 宇
是诗?是画?诗画里有的东西它有,诗画里没有的东西它也有。它不是一曲战歌,却非软性音乐;它真是一幅水彩,却不失于纤弱,秀丽其衣,健美其质。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充溢着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淖记事》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不是一般的爱情悲剧,没有一把泪,一滴血;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喜剧,三分幽默,七分笑料。它不落俗套,立意新奇。故事不能说不悲惨,但使人没有重压之感;描写的风俗决不是美玉无瑕,读了却让人神清气爽。
故事的主线是巧云与十一子的奇特遭遇。它是悲剧,又不是悲剧。我们同情人物的命运,也憎恶那些邪恶势力。但我们不能说同情,你要的“纯洁”、“贞操”与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不可同日而语。从表象上看,大淖也真有几分“风气不好”,但骨子里却充溢着美和力。真象莲花,虽身出污泥,却神骨不染。爱,钱买不到,强力抢不到。爱是心心相印,是灵魂的吸引。她们说不出这番道理,却真正领悟了人生爱情的真谛。那些流氓、强盗,那些仗势欺人的恶棍,当然该杀该剐。他们对女性的侮辱,是十足的野兽行为。巧云被人强行破了身,她痛恨那些恶棍,失悔“没有把自己交给了十一子!”但过去的不能挽回,未来的全靠自己。有什么理由要悲不欲生,要跳水,要自杀,要为那些恶棍殉身?执着地追求生,追求爱,追求自己的权利,这才合理。巧云就看破了人生的这一层老壳。她不要救世主,也不要人来怜悯,她自己救自己。在巧云的行为面前,封建主义的贞操观,岂不黯然失色?
人是环境的产物。巧云的行为植根于大淖的特殊社会环境。婚娶不用媒人,对所爱的人情愿在经济上“倒贴”。因为爱情不是施恩的谢礼。这里的风气与街里相比,哪里更好?确实“难说”。大淖的风俗和人物的行为当然不全是金子。金子混在砂子里,一切都还是一种混沌状态。巧云被刘号长强行破了身,媳妇们只骂一声“这个该死的!”巧云对自己爱情的执着追求,也不是意识到自己奴隶地位的自觉反抗。那是环境造成的,人物的行为摆不脱环境的制约。
矿砂并不就是金子。金子却在矿砂里。《大淖记事》不是人物带出环境,而是从背景中推出故事。它象剥笋。不,在剥之前,先是连根带泥都掘起来。然后再一层层剥下去,最后才见到那透明纯净的笋心。在这浪淘沙式的选择里,作者找到了对待生活应有的态度。
作者的情感倾注在人物的命运里。他没有为她们流悲天悯人的泪。他知道这反倒会亵渎了她们。向着未来执着的追求,使作品神骨健美。它没有抽象的道德说教,却把你的灵魂吸引了过去。在这充满带有几分野性的生命活力的美面前,你得到了从那些听厌了的道德说教里,从那些哀哀戚戚的悲歌里永远得不到的精神和道德的熏陶。是作者说服了你?是作品中人物的品格说服了你?这都有。因为作者的心贴到了这些可亲可爱的人物身上,我们提不出异议。
这些人物,这种生活形态,在现实中,也许特别稀少,那临近大淖的街里就没有。但正因为稀少,才显得特别可贵。这些特殊的生活形态和地方风俗,是哪个时代或哪些文化传统的产物,谁也没法说清。但它确实有,不仅过去有,现在又何尝没有?不信,你去生活里寻找,只要你肯。即使真找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关键在于作品处理得合理不合理。《大淖记事》在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我们找不出大的毛病。
《大淖记事》给人的教益,主要不在它的题材本身。作者不是诱惑读者去猎取特异的世态风俗,也不只是让人陶醉于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透过题材的表皮,我们获得了一种启示:应该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它触及到一个虽不是永恒,却决不是一个短时期就消逝的问题。《大淖记事》里的故事早成过去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仍在困扰着现代人的心。作者从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里,看到了某种闪亮的东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对不对?许多人会这样发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问题也许得不到统一的结论。但我敢说,《大淖记事》对生活矛盾的回答,不是悲泣,不是绝望,它具有一种向上的自信,一种健康的力。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也许逾越了题材本身的范围,散射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面对现实世界的一切矛盾。
这种向上的自信和健康的力从作品描写的生活里透射出来。但作品在风格上,却不以粗犷见长,秀丽才是它的本色。刚健的灵魂装在秀美的躯壳里。外柔内刚,刚柔相济,是《大淖记事》的独特格调。
通篇是风俗画的连缀。作者对社会风俗的熟悉、了解,写来如探囊取物,不见任何杜撰的痕迹。娓娓叙来,如数家珍。三教九流,人情世态,观察得细致入微,毫发毕现。保安队捕匪过街,锡匠们唱“香火戏”与挑担游行、顶香请愿,媳妇们在大淖里洗澡……,使人应接不暇。作者写风俗,并非全般实录,他有选择。虽不是美化,却是诗化了。作者从民风民俗里,别具只眼地提取出“诗”来。一切都那么情趣浓郁,诗意盎然。
有诗必有情。《大淖记事》调子轻快,但不轻佻。在现代文学中,我们也见过类似的题材,类似的写法。但那些作品大都带有一种感伤。《大淖记事》洗去了这种感伤。感伤并非一定不好。那时的作者,身处那个时代,没法不感伤。黑暗的压力太重,他们看不到足以使人自信的东西。翻阅解放前的杂志,偶而见到作者四十年代的一篇旧作,题为《囚犯》。同样是写士兵押送囚犯的情形。虽然作者也看到囚犯身上“有一种美,一种吸力”,但字里行间却透出对人生命运的迷惘和感伤。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今天看昨天,蕴藏在生活中的内在的力凸现出来了。这是站在今天审视过去生活的好处。也许,作家在审美过程中,真得有这么一点距离?
这种秀丽的格调,取决于作者诗人的眼力,也取决于作者运用语言的功力。读作者的小说,你会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倾倒。句子短峭,很朴实,象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每句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美词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锻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
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叙述朴实,却有声有色。越过文字的表皮,你没有听到生活的内在节奏,感到人物身上生命的活力?
小说不是没有缺点。将大淖的风气与街里那些没有爱情自由的封建婚姻形态相比,优劣自无需评说。但大淖的风气里毕竟羼杂着渣滓。违背生活真实,人为地加以净化,固然不必;要求作者生硬地加以议论,于艺术也属无益。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对结构的要求,是布局的匀称。《大淖记事》从环境中推出故事,这无可厚非。但作品对大淖风俗铺述过多,进入情节较慢,前后篇幅的安排,使人略有失重之感。尽管如此,《大淖记事》仍是一篇优秀之作,从近几个月来作者连续发表的几篇小说看,作者在有意发展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有对前代作家的借鉴与继承,却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创。在不断尝试与探索中,作者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我们这样期望着。
一九八一年四月,于北京大学
(《大淖记事》,《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