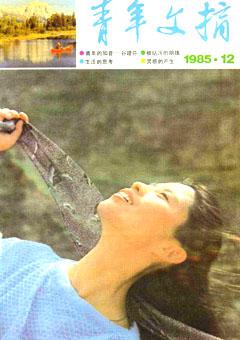青年的知音——谷建芬
周玉明
乐谱上的一个黑点,
作曲家的一滴血汗。
——题记
也许,因为她是作曲家,是由七个音符构成的音乐精灵,她才受到年轻的音乐爱好者们如痴如狂的迷恋。瞧,她一下子就被包围住了,她一下子就得对付那么多个甩来的“?”!
“谷建芬,你原来是女的?女的怎么有这么厉害,六年里竟写了五百多首曲子!”爱唱谷建芬歌曲的大学生,见到矮个子、清秀端庄的谷建芬本人,竟毫不掩饰地叫嚷起来。
“男的有叫芬的吗?”谷建芬也觉得奇怪了。
“贝多芬不是男的吗?”那大学生可真聪明。
有意思,谷建芬自己召开新歌试唱会,自弹自唱自己新创作的歌曲,并发给每个到会者一张民意测验表,请他们写上意见和评语。
惜时如金的大学生被作曲家的真诚吸引了。他们倾巢出动,汇集到礼堂里,围聚在谷建芬周围。
她似乎太累了,眼圈有点儿发黑,那早就失去了红晕的脸也有点儿苍白,可她的眼睛是晶亮的,闪烁着青春和活力。她微微弯身,向大学生们鞠了一躬,用她低沉而有节奏的声音,诚恳地说:“今天,我是来接受开门考试的,真的,你们都是我的老师。”她不会客套,也不善词令,但心胸里奔涌着感情的潮水。她撩开散在额前的头发,露出宽阔的额头,她竭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可鼻尖上已沁出了汗珠。不多说了,还是让作品说话吧。
当谷建芬的双手按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她的歌声随情而生,倾泻而出……作曲家并非天生的歌手,没有珠圆玉润的歌喉,她的嗓音是略带沙声的,但她质朴而又深切地把自己的感觉和感情,变为可感、可视、可听、甚至是伸手可触的东西。是的,她那中音偏低的音色算不上美,却充溢真情,焕发着魅力。她用奇妙的七个音符勾勒着、描绘着大学生所熟悉的一幅幅生活图景……
谁说这个既不在音乐厅、又没有乐队伴奏的试唱,出不了效果呢?大学生们的眼界够高的,也挺会挑剔的,但他们现在还真算得上是注目凝神,洗耳恭听!
是嘛,他们不是说台湾校园歌曲很好听,很有味道,盼着有大陆特色的校园歌曲?不是给作曲家寄去了歌词,寄去了希望吗?现在你们可以如愿以偿了。
阳光透过绿叶的缝隙从窗外轻轻洒落下来,洒满在作曲家那汗珠闪闪的脸颊上。已经唱了十七首歌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自弹自唱,谷建芬的嗓子哑了,十指也有点麻木了,可当主考官的大学生们却纹丝不动,他们还想听下去,考下去,谁也没有察觉作曲家的嗓音已经声嘶力竭了。
应试的谷建芬也想一直唱下去,考下去,可肉做的嗓子终于哑不成声,提出无声的“抗议”了。她只好歉意地站起来,大学生们这才也如梦初醒似地,感到该让作曲家下台喘口气了。
哦,她是太累了。她先后出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大连工学院、大连海运学院和上海同济大学等十三所大专院校的新作品试唱会上。谷建芬带着自己新谱的校园歌曲上门征求意见,年轻的大学生们作出了热情的酬答,有一万余名同学认真填写了自己的感受和评价。
谷建芬无意陶醉在充满太多太多赞美和鼓励的评语里,却郑重其事地从几千张民意测验表中,选出一张珍藏着。那上面的评语是一个数字:“17=1”。谷建芬懂得这是说她的歌曲雷同,变化不多。她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
真的,谷建芬心里一直装着这个“17=1”,这个沉重的等式。当我与她交谈时,她是那么坦诚地感叹说:“这几年,我写了几百首歌,可金子太少,沙子太多,经常雷同,有的格调不高。能算是好歌的不就才《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校园的早晨》、《那就是我》几首嘛!”作曲家一边说一边摇头,她对自己不满意,真心真意的不满意。
一
艺术的责任感,常常会使艺术家内疚不安。1980年5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谷建芬和小女儿在北海公园散步。看到几个青年弹着吉他,嘴里哼唱着音不准、调不对的歌,有的还学着海外歌星的腔调象断了气似的唱歌,手中的吉他也只是做做样子在乱弹……谷建芬与他们擦肩而过时,只觉得心里“格登”一下,好象被什么东西猛砸了一下,火辣辣地疼。是同情,怜悯?还是惭愧,内疚?一种复杂的感情缠绕着她。回到家里,谷建芬坐立不安,那怪声怪调一直追随着她。
“是啊,他们唱得是不好听,可我这个作曲的也太无能了,还算什么‘作曲家?为什么不给他们好歌唱呢?!为什么我们的抒情歌曲竟奇缺到不得不靠‘引进来填补的地步?”谷建芬急不可耐地翻找着歌词。哈,太好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词恰好反映了谷建芬的心境,她的激情和灵感火一样呼呼地燃烧了。青春的火光、青春的热力,化成了青春的旋律:“啊,年青的朋友们,美好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一曲《年青的朋友来相会》,一下子把谷建芬的心和青年人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了,她赢得了青年人的信任和友谊。年青的朋友们一封封倾诉感情的来信飞向中央歌舞团,飞向他们所尊敬的作曲家,“这首歌唱着它带劲,向上,好似美好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
当谷建芬走在大街时,她欣慰地看到那些平时爱乱弹吉他,哼唱胡诌乱编的没有准词儿的街头音乐家,也弹唱起《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还得意地叫着:“这首‘盖了!”
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连同谷建芬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获得了八一年《歌曲》月刊优秀作品奖。谷建芬是唯一的得奖女作曲家,也是唯一的有两首歌曲得奖的作曲家。后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又被联合国文教组织评为亚太地区优秀歌曲。
二
贝多芬早就精辟地说过,音乐能够“从心灵——到心灵”。
可不,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了。一个摇轮椅车的残疾青年,怀里揣着一张他自己写的歌词《希望的曙光》,冒着六、七级西北风在偌大的北京城里,走街串巷,他的后面有一串长长的跟随他匆匆往前移动的影子。他要找作曲家谷建芬,可他只知道谷建芬在北京的一个乐团工作,却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轮椅车从中央民族乐团摇到中央乐团,又从中央乐团摇到中央歌舞团。好心人告诉了他谷建芬的家庭住址,四个多小时的轮椅车的运行,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艰难得犹如一次长征。他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谷建芬的宿舍楼前。
门口一个男孩望着残疾青年冻得僵紫的脸和手,自告奋勇地当通讯员,他爬上四楼,对正在洗衣服的谷建芬报告:“阿姨,楼下有个坐轮椅车的人找您。”
谷建芬顾不上擦掉手中的肥皂泡,急匆匆地下楼迎客。她站在残疾青年面前,象个大姐姐对小弟弟似地热情对他说:“我是谷建芬,外边冷,请到家里坐吧。”她搀扶着这位青年一级一级楼梯地挪上了一个拐,又挪另一个拐,青年的身躯压得那付木拐杖发出阵阵“吱吱”的呻吟,胸部发出拉风箱的喘息声。青年不时地朝着小心翼翼扶着他的谷建芬报以自我嘲讽的一笑。谷建芬意识到,他是以此作为后盾来抵御残疾者与正常人在一起时所感到困窘。
残疾青年在沙发上一坐下,就从怀里掏出一张被捂热了的歌词。谷建芬送上一杯热腾腾的茶水,关切地问:“你们生活得好吗?”
“我们虽然残了,却不想废了!”青年淡淡地一笑,随即便急切地向谷建芬诉说自己的心境。他是一群残废青年中的一个,很喜欢唱谷建芬的歌曲,他们有着共同的阴影——共同的自卑、痛苦和不幸,但又有着共同的阳光——追求美好的、丰富的精神生活,这追求高于一切。他们虽然没有工作,却都在刻苦自学,为了开拓和丰富自己的精神,每人都订有一份刊物,还互相交换着阅读。正是从这些刊物中,从电台播音中,他们知道了谷建芬的名字,熟悉了谷建芬的歌。这个年轻的朋友,带着期待的神色和语气,对谷建芬说:“你近年来写的歌曲,我们几乎都学会唱了,我们多么渴望有一首自己的歌啊。”这是真情的请求,却又无异是前来下战书!
残废青年抬起头来凝视着谷建芬,只见她的眼睛里有一道奇异的热情的亮光在跳动。谷建芬接过歌词,轻轻地读了两遍,认真地说:“我一定写!一定写!”“您同意啦!”青年人的一声欢呼,充满了感激和信赖。
灵巧的手指在琴键上翻滚,倔强的音符,不向命运低头的音符在跳动。那位上门请求作曲家并下了战书的青年,一接到谷建芬新为他们谱的歌曲,第二天又来到自己敬爱的作曲家的家里。他用大伙儿凑钱买来的磁带,录下了作曲家亲自弹唱的《希望的曙光》。他带着无以抑制的感激,带着如获至宝的满足,不辱使命地回去了。他带着录音机一家家放给残疾青年听,他们一个个跟着学唱。生命的绿树,希望的火光,美好的理想,全都在这歌声中映现、闪烁……
歌声似一条友谊的彩带,把作曲家和残疾青年紧紧连在一起。谷建芬和一批残疾青年相约,相会在景山公园,她还和中央歌舞团的几位青年演员一起,为残疾青年举行联欢会。没有双手的青年书法家刘京生,把笔绑在胸前,写下了“青年之挚友,抒青年之真情”的条幅,赠送给谷建芬。四十七岁的谷建芬却象个害羞的孩子似地涨红了脸,她觉得受之有愧,心里在责备自己:我写的歌呀,太少!太少了!张海迪一到北京,就托人带信问谷建芬好。她真挚地说:“我最爱唱谷老师的歌,感谢她为我们残疾人写了好歌。”在我国第一部立体声广播剧《海迪》中,张海迪又在剧中自己演唱了这首希望的歌。歌声呼唤着更多人的心灵,飞入更多人的心灵。在团中央和中国音协向全国青年推荐的十八首歌曲中,谷建芬的《大地的爱》、《校园的早晨》也被列入推荐之列。是啊,音乐的世界是感情心声的世界,而谷建芬的歌恰恰是长于抒情而无意说教,发自肺腑的音符,才能飞进和撞击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三
对于谷建芬来说,生活不可能是一首和谐、美丽的歌,她的艺术生涯布满了乌云。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的打击接踵而来,而她的创作热情却有增无减。乐圣贝多芬说得好:痛苦诞生了欢乐,诞生了乐曲。谷建芬愈是丰富地体味了人生的艰辛,便愈能产生绵绵真情,在旋律中“寄此无穷音”。歌曲往往能真切地展现出作曲家的生活和心境。
“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
我也曾苦苦追求。
但那生活中卷起的汹涌浪涛,
却把我带进滚滚激流。
我走过漫长的道路。
寻找我失去的梦。
如今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旁,
啊,生命的星,
请你不要离我去远方!……”
这首题为《生命之星》的歌,是谷建芬的挚友和合作者,歌词作家王健,在了解了谷建芬的艺术生涯后,特意为谷建芬写的歌词。谷建芬称《生命之星》为自己的歌,也是奉献给中年人的歌。这首歌以优美、深沉、舒缓的旋律,概括了生活的坎坷和曲折,倾诉了人生的艰难和欢乐,鸣响着记忆的足音。
谷建芬从小是由音乐“喂”大的。在日本经商的父亲,经常带她去看日本歌舞伎、民歌手演出。这使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唱一口日本民谣。谷建芬六岁回到故乡大连。她虽然不会说中国话,可长得伶俐、活泼,童花头下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里终日闪着好奇、探寻的目光,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
圣诞节,谷建芬变成了白雪公主,穿上闪光的带亮片的衣服,踩着优美的音乐声,爬上由孩子们搭起来的象金字塔似的圣诞树的最顶峰。她跟琴有着不解之缘。每次排练时,谷建芬一走到老师弹奏的风琴旁,她的双脚就象在地上生了根,挪不动了。眼睛紧紧盯着老师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弹奏着的双手,一只小手偷偷地抚摸着风琴。“快往前走!”老师拍了她一下头,她才恋恋不舍地挪动了双脚。可是当她第二圈转到风琴旁边时,她又停住了,贪婪的眼睛盯着老师的手发愣,老师又拍着她的头:“咦!又是你!”
“爸爸,我要用手弹的琴,就象老师那样的。爸爸,给我买,给我买……”谷建芬一回到家就缠住爸爸,她不是在请求,而是在苦苦哀求,不,简直是“最后通牒”了,足有一股爸爸不买她死不罢休的蛮劲。慈祥的父亲屈服了,他不忍让女儿伤心,给她买了一架处理的教堂用的管式风琴。从此这架琴便天天和谷建芬作伴,她的小手每天在琴键上冬冬乱敲,心里怎么想就怎么敲,琴成了谷建芬最好的对话者,妙语如珠的对话者啊!
大连解放时,日本侨民纷纷回国,把一架架钢琴拉到大街上兜售。谷建芬又被钢琴迷住了,她一走到那钢琴旁,脚又牢牢地被粘住了。她一架架地看,一架架地试弹,竟痴痴地从大街的这一头弹到大街的另一头。再向后转,又回过头来从那头弹到这头,连上学都忘了。父亲怕她思物伤神,便给她买了一台亚马牌1号钢琴。
谷建芬第一次打开琴盖,真象新郎第一次揭开新娘的面盖,高兴得心里冬冬直跳。从此,她一放学就直冲回家,扑到钢琴上,她要赶在哥哥回家前“独占鳌头”。以后父亲把这架钢琴作为谷建芬结婚时的陪嫁运到了北京。啊,这架珍贵的纲琴,唤起谷建芬和她丈夫邢波几多回忆。
小学时,五年级的谷建芬是学校唯一的钢琴伴奏,六年级的邢波是校歌咏队的指挥。他们老是亲密合作,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邢波家境困难,每当吃中饭时,他总是悄悄地一人躲到平台大石头那儿趴着,不愿看别的同学吃饭,谷建芬就偷偷从家里拿来饼干等点心,塞给邢波吃。邢波总象大哥哥似地护着谷建芬,他到哪儿,总希望谷建芬也跟他到哪儿。
谷建芬还在念初中三年级时,已经到大连文工团工作的邢波来找他,急切地问:“你想进文工团吗?”
“那儿有钢琴吗?”
“有,你把钢琴练好可以担任伴奏。”
“光伴奏?能不能独奏,我真想当钢琴家。”谷建芬在大哥哥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弹好了,行!”邢波简直象个大权在握的文工团团长,他哄着她,唯恐小妹妹不去。他多想跟她在一起啊!
两个人一起去大连文工团工作,又一起去东北鲁艺学习。被同学称为小精灵的谷建芬可真有股韧劲。几乎每天清晨五点,她就抢占好钢琴位置,随着起床号一响,她的双手“当”地敲响琴键,一天的紧张生活就在这“当”的一声中开始了。她还真是学习得如饥似渴呢!195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与邢波一起分配到中央歌舞团工作。邢波既当舞蹈演员,又能编舞。那时的谷建芬已不满足于光弹好钢琴了,她已经大彻大悟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职业能象作曲那样,把自己的思绪、幻想、激情和喜怒哀乐都融为一体。作曲就是她的生命。作曲于她,不仅是事业,而且是生与死的必要性。
谁想到,反右时,谷建芬和邢波因为对个别党员干部提了意见,被定为“极右思想”,差点划成右派。加上谷建芬有海外关系,两个人都成了“内控对象”,被发配到苏北的穷山沟劳动改造去了。谷建芬含着眼泪,卖掉了在京的全部家具连同那心爱的钢琴。当那钢琴被搬走时,她感到心被掏空了,一切都毁灭了,准备一辈子死心塌地地当农民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邢波又被打成“5·16”分子,隔离审查了两年多。作为妻子的谷建芬“理所当然”地受到牵连,连当农民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也被隔离,关在一个只有一个小透气孔的羊圈里。冷啊!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彻骨彻髓的冷!
又冷又疼,谷建芬的风湿性关节炎发作了,浑身止不住地颤抖,真象《卖火柴的小女孩》里的那个可怜的小姑娘。
黄金般的青年时代,就在被“内控”的整整二十年中,从生命中猝然离去了。在这期间,谷建芬整理、改编了五十首民歌,上海文艺出版社本要出版,却因不能署谷建芬的名而报废了。心中的泪流织成抑郁如咽的旋律,记录在《我的小路》这首歌中。后来,第一个选唱这首歌的李谷一动情地说:“无论谁唱《我的小路》这首歌,都会被触动心扉,唤起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而涔涔泪下。”
失去的梦终于回来了,带着金色的光环回来了。谷建芬的生命开始了新的乐章。人到中年的她,一股劲儿地要把二十年憋在心底的歌唱出来。回顾起来,她痛苦过、酸楚过,然而心灵的键盘不能仅仅弹奏一个主题一一悲哀。她的泪留给了艰难而孤寂的昨天。她张大着充满活力的眼睛,寻找生活的亮点,不放过每一个今天。诗意,柔和的旋律从心田潺潺流出。生活那么充实,人生的每一步都象是一个单独的音符,孤零零看没什么含意,但组合起来就是旋律、和声、律动和复调……就能产生巨大的回响。时代需要作曲家,她在日新月异的生活中,捕捉更新更美的旋律,来表现她亲爱的祖国,亲爱的父老兄弟。
令人惊异的是,经过漫长痛苦折腾的谷建芬,身上依然保持着孩童般那种纯真、好奇的性格,丝毫没有“成熟”后的衰朽和暮气。谷建芬的歌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感情真诚、朴素。她的作品的风格和色彩,近似绘画或文学中的“白描”,纯系天籁自鸣。她善于用通俗易懂的音乐语言来表白自己的感情,不掺假,不造作,这正是她的歌曲的魅力所在。她的笔伸向各个角落。她的足迹遍及工厂、农村、工读学校……
歌声在飞扬,舆论也随之而起。谷建芬的歌被传唱得多,被评头论足的机会自然也多。众说不一。
好在歌声只要属于人民,人民就会保护歌声。非议,反而使谷建芬赢得了更多的知音。近几年来,她的歌曲被录制盒带与唱片的就有一百多首。无论是试称为严肃唱法、西洋传统发声方法演唱的,还是民族民间唱法的歌唱家罗天婵、楼乾贵、靳小才、刘淑芳、梁美珍、朱逢博、李谷一、王洁实、谢莉斯等都向谷建芬要歌曲唱。欢快明丽的歌、深沉爱恋的歌、如泣如诉的歌,象流不尽的小溪,从谷建芬的钢琴上、心灵上,飞向四面八方、五湖四海……
四
心脏病的警报已拉响了多次,谷建芬腾不出时间去看病,她从不怜惜自己,因为她一直在想着比她自己更为重要的七个音符。再说她是个贤妻良母,总想把家务全包了,让丈夫工作,让孩子多读点书。她珍惜每一分钟,经常一边在锅台旁操劳,一边歌声琅琅。
什么时候心脏开始出故障的?谷建芬自己也闹不清。记得第一次发作,是她在一次巡回演出归来:她看见女儿海娃右手悬吊着,象个“伤员”,她着急了。邢波哄骗他说:“海娃的手不小心被烫了!”烫伤的手怎么要吊那么长时间?谷建芬生疑了。当她知道,女儿的手指在学工劳动中,被机器轨断了,她只觉得头脑轰地一下,心都碎了。
小女儿海娃,是谷建芬失去的梦中的精灵,她要将自己二十年所失去的在女儿身上夺回来。五岁的女儿跟着母亲学钢琴,她任性、不听话,不爱学那大玩意儿,她更爱跟自己的布娃娃谈心。谷建芬望女儿成材心切,从不发大火的她,不知打过多少次海娃,海娃就反过来打钢琴。妈妈一走,她就对着钢琴“拳打脚踢”。女儿哪里懂得母亲的心哪!母亲执着的追求,终于使女儿弹得一手好钢琴,十岁的她前途在望。不料,灾星降临,缠住了海娃,谷建芬让女儿成为一个钢琴家、继承自己未竟的事业的愿望破灭了。
谷建芬确实疲乏不堪,医生建议她静养,邢波也在她耳边多次说:“去海边吧!”
海,好象久违了,又是那样熟悉。
潮水涌来了。海浪的巨手拍打着,象无数热情的听众在鼓掌欢迎她。真的,在谷建芬看来,远处那弯弯曲曲的一条条浪波,真象五线谱;而那飞翔着的海鸥,就象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符。嘿!这是怎么了?真是职业性神经质,想入非非!连她自己都觉得可笑。
谷建芬望着大海在思忖:人的胸怀应该象大海。象大海那样豪迈,象大海那样坚定,象大海那样深沉,象大海那样激情,象大海那样不息地运动……海,给了谷建芬气势和灵感。《那就是我》《啊!生活》《大海,我不会忘记你》,等歌曲,从她的心海里、琴键上滚滚滔滔流泻出来了……
“无论我走到那里,
大海我怎能忘记你,
我将追随你奔腾的波浪,
永远为你歌唱。
……”
她又远离大海了,但她是海的女儿,胸中起伏着海的声音。是的,她这个从海的摇篮里诞生的作曲家,应该感到欣慰和自豪:七个音符之所以有蓬勃的、旺盛的、乃至无限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所反映的这个世界是无限的,就象这永恒的大海……
(大为摘自《萌芽》1985年第8期,原题为《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