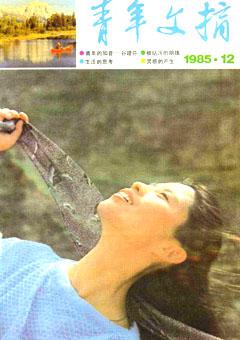鲁迅——巧用动词的魔术师
白 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一位成功的作家,不能不同时是一位语言艺术家,而对动词掌握和使用得如何,常是其语言功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堪称一位高超的“魔术师”,他的不朽的小说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故乡》以有限的篇幅,不仅绘出了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生活图景,而且塑造了好几位呼之欲出、眉目传情的人物形象。所以能如此,除其他因素外,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动词的精彩选用上。例如,怎样写闰土让躲在身后的水生出来,这里显然有许多动词可供使用:拉、拽、领、牵、扯……等等,但先生却出人意料地选用了一个“拖”字,试想,如果用“拉”等动词,只能使读者想象到一方——闰土的动作,却看不到水生的一方的心理和动作。而“拖”呢,不仅“拖”出了一个画面——大人用力焦急地往前用力拽;孩子双脚用力蹬地、躬身蹙额的情态;而且披露了国土的心理:在“老爷”面前的不安和恭谨,对于刻画他的麻木自卑的性格起了一定作用。在《一件小事》中,如此一字千金之笔也不乏其例。当车夫扶起老女人时,问她:“你怎么了?”“我摔坏了”——请注意这个“摔”字,如果老女人象“我”揣度的那样装腔作势借以讹人的话,就不说“我摔坏了”而要说“你把我撞坏了”。老女人用“摔”而未用“撞”,就等于说,是我年老体弱、力不能支摔倒的,与你无干。这样,老女人虽穷且老但却忠诚正直,不刁不赖,形象自然可亲可敬;而车夫呢?虽然责不干己,对方又不咎之,却要主动关照,就更见其善良和高尚,自然“须仰视可见”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动词,竟为两个人物形象着上了亮色,那么先生巧用动词的秘诀在哪里呢?大概至少有两点:其一,着眼于描述的“形象感”,即如“拖”;其二,属意于词汇意义上的多层内涵,如一“摔”字。
同写交酒钱的动作,孔乙己与阿Q大不相同。一个是“排”,一个是“扔”,但却都恰到好处地起到了塑造人物性格的目的。孔乙己是读书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付款分毫不爽,就在柜台上一文一文地“排”出九文大钱,一个“排”字,尽传精神。而发了财的,腰间搭连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的阿Q,却是另一番派头,绝不似孔乙己那么小家子气,而是伸手抓一把,满把“银的和铜的”,便往柜台上一“扔”!好一个“扔”字,它是多么生动地画出了阿Q那踌躇满志、得意忘形的神态。同样的精妙之笔在《阿Q正传》中真是不胜枚举。阿Q扭住了小尼姑的面颊又用力拧了一下之后,除了胜利的陶醉外,还别有一番滋味象蚂蚁一样酥酥地爬上了心头。我们这位本可以做圣贤的阿Q被“女……”所蛊了。然而作者还是不直写心理,却巧妙地选了两个动词,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而又幽默地刻画了阿Q的心理状态:这时的阿Q,不再象平时“混”到深夜,待到酒店要关门才“踱”回土谷祠去,而是飘飘然“飞”了一通,“飘”进了土谷祠。一“飞”一“飘”把个腾云驾雾般的阿Q描述得真是淋漓尽致。
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生活的。高尔基认为叙事文学应有三幅画:人物肖像画、风景画和社会风俗画。这就要求对动词的使用除使其含义丰富外,还应该具有鲜明的形象感。
阿Q进静修庵偷萝卜时,是“爬”上矬墙,“扯”着何首乌藤,“攀”着桑树枝,“跳”进里面的;而逃出来时却是连人带萝卜“滚”到了墙外,人和萝卜同在地上“滚”可真是画家笔下的好素材。倘只说跳到庵里、拔了萝卜跳到墙外就跑,该是怎样的大煞风景。阿Q要与小孤孀吴妈困觉的桃色新闻传出后,未庄的女人都一下子害起羞来,就连五十多岁的邹七嫂见了阿Q也跟着别人乱“钻”,这个“钻”也一定程度地勾勒出了人物动态画和社会生活画,也绝不是“躲”或“藏”之类所可以代替的。总之,由于对动词的巧妙驾驭,确使鲁迅先生的作品增强了表现力。
为什么动词最富表现力?
阿·托尔斯泰说:“在艺术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动词”“因为全部生活都是运动”“月亮下面没有不变的东西”。是的,没有运动便没有世界,自然也就没有艺术;但这只是从文学的外部规律——文学与生活的角度着眼的,似乎还应从文学的内部规律上问一个为什么。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美学注重含蓄,不尚直露,这就决定了文学在表现手法上的形象性、表达方式上的间接性和表达目的上的审美性。同是表达思想,哲学家可以用抽象的推理去阐述静止的观念;作家则必须借助形象去构成一幅活动着的场景,而动词即是使画面的人和事活起来的“连接点”和“关钮”。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动词之所以比其他类词更富表现力,那是因为,第一,它能够反映出生活本身的动的特点;第二,它符合艺术品的动的和形象的美学需要。
(何芳摘自《语文月刊》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