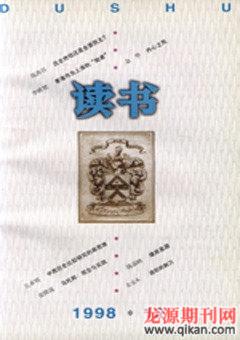《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族裔性与文学
杜 凝
时至九十年代末,族裔性(ethnicity)很难说还是一个新起的话题,但其势头在欧美文化界仍方兴未艾,其对社会政治各方面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还大有潜在能量。而对这个词语的解释和运用却处于极为分化的状态(哪个词语的实际生命不是存在于历史性的多元歧义中?)。表面明确的交锋、对话常常掩盖着前提和假定上的差异,而对差异的敏感又吸引着更多的学者加入讨论。一九九八年一月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的“族裔性与文学”专号可以说是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对这一热门话题的重点反应之一。专号的中心部分是对英语文学作品的解读。从一百○八篇来稿里筛选出的六篇论文,三篇关于“经典(准经典)”,三篇关于“当代(准当代)”,在理论或历史分析的同时,都牵涉精到细致的文本阅读,反映了编者对“文学评论”的选择评价标准。而不同的切人角度与分析方法则标志着编者必须认可因包括族裔、女性主义及性别等当代理论而扩展的丰富的阅读可能性。
梅兹杰尔(Mary Metzger)通过犹太富商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来重读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力图超越近年来以新兴理论对经典解读时热衷于分离个别概念而忽略复杂性的倾向,综合分析剧本中的宗教、族裔、性别等多种文化建构,并将其投射于十七世纪末剧本创作时的英国社会政治背景中。在什么意义上莎翁有同时创造两个犹太角色的需要?为什么杰西卡与夏洛克既有不可分割的复制性又必须高度对立?为什么“好”犹太人最终要由女性来代表?梅兹杰尔认为,无论当时定居英国的犹太人人口比例多么低,这些剧本构成中的重要因素都指向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极不稳定的文化、宗教、社会甚至肤色等标志,及其因不稳定而获得的建构能量,使莎翁得以从一个特殊角度艺术地凸显英国将新教奉为国教时回应正统天主教的方式。
借用不确定肤色来寻求主流社会中自我定位的策略也表现在拉丁美洲移民作家的作品里。与处理犹太裔问题的传统不同,拉美移民作者对肤色的焦虑更集中地表现在作者本人对暗肤色的认同而不是排斥,读者不能不意识到人权运动渐起对社会意识变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拉美裔作者和评论者来说,在不确定的肤色以外,还有尚待确定的语言问题。当双语教学持续成为美国政治热点时,即使是少数族裔作者写少数族裔,其英语写作行为中包含的主流精英姿态本身就指向其政治话语中的悖论。假定有一天拉美移民作家坚持以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在美国写作,他们的作品建构或表现的是美国文学中的族裔性呢,还是西班牙语文学中的族裔性呢?
无论是肤色还是语言,在美国黑人文学中都有着更明确的界定,从而使问题更接近于女权主义的思考方式。本奈特(Paula Bennet)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文学家——女奴菲利斯·惠特蕾(phillis Wheatley)诗歌作品的阅读表现出黑人文学界持续而艰苦的努力;既要坚持优秀黑人英语文学有世界性的普遍性价值,又要坚持他们有着由其社会地位、文化传统、性别身份决定的审美特殊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哪里汇合?用巴巴(Homi Bahba)的话说,就在于保持普遍与统一下的陌生化距离,保持对陌生化的自觉与敏感。这和女权主义要求平等但反对同化的思路有明显一致性。
巴巴的这一阐述就收在这一期专号所附的论坛专栏里。论坛栏的四篇文章均取自现代语言协会一九九五年年会的一个专题讨论。巴巴论点中的两个潜在问题在这里受到挑战,两个挑战都是因犹太人文化或文学而起。首先,陌生化敏感性的适用范围如何界定?或者说,谁更有资格谈论对于被同化的焦虑和抵制?如果族裔/文化陌生性是如巴巴所试图论证的客观心理状况,文本因而永远具有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潜力,则解读只在尽力获得对陌生性的认识和自觉。在这种情况下,族裔/文化陌生性的定义在理论上的危险是滑向原教旨主义一类非历史化的不可知论,实践上则可能停留在以生理特征为区别标志,或无限扩大陌生性群体,或否定特定群体的陌生性。这正是伯亚林(Daniel Boyarin)对斯皮瓦克(G·C·Spivak)的质疑。后者在阅读心理分析与文学文本关系时提出,白种犹太人对有色人种而言具有先天优越性,可以在白色人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上更容易地通过倡言普遍性而消除或掩盖其本身具有的陌生性,并进而突出有色人种“非我族类”,维持以白人文化定义“普遍性”的祭坛。弗洛依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伯亚林反驳说,这是无视白色人种的内部多样性及其长期以来难以消弭的白种族裔间的紧张关系。对他来说,尤其不能接受的就是将犹太人文化社会地位单一地描述为优越的、霸权文化的精神帮凶。对比本期专号中两篇牵涉犹太人问题的文本阅读论文,不难想像,问题很可能在于当批判理论与批判实践密切相关时,理论认识复杂现象与实践要求明确口号立场之间的冲突。
对巴巴观点的另一挑战来自文学领域自身。专号特约编辑吉尔曼(Sander Gilan)在编辑导言里委婉而尖锐地指出,如果文学是语言生产,文学中的族裔问题恐怕只存在于同一语言的文化生产中,例如,英语世界恐怕并没有权力把用日语写作的文学作品称为日裔文学,而日语文学对英语世界的语言陌生性则无可避免无法掩盖。因此,巴巴所依赖的“普遍性”概念本身被置于可疑位置(这些印度裔学者不是先验地被置于英语世界的吗?),其关于“陌生性”敏感与自觉的论述同样面临进一步深化的任务。由语言生产,吉尔曼又将问题引向“经典化”(canonization)的历史,以德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证明,语言文学生产进入区域化“普遍性”概念的过程是近代史上“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追求加速瓦解了地方性、族裔性文学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建构了现代发达的“精英”文化的“普遍性”意义,定义了非“精英”的“地方性”或“特殊性”(在德国是当列那狐寓言成为经典起源时,西意第绪语和十八世纪希伯来语作品被排除于“文学”之外)。中国文学在现代的实践历程很可能同时表现出对内对“非精英”文化的压制和对外追求“普遍性”接纳的焦虑。而目前理论探讨的发展则在特定方面指向非“普遍性”共存共进的可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全球化”威胁时巴巴关于陌生化自觉性的论述对“中国文学”在对内对外方面都仍有重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