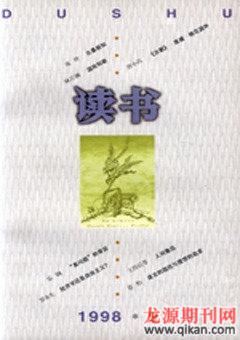“真问题”的背后
乐 钢
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提出了“真问题”,对此我同意卞悟的看法(见《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六期)。我以为《陷阱》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它提醒中国的思想界面对现代化这一过程必须有足够的问题意识。不能假设陷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一旦这样思考,也完全可以反过来以假设为前提,将现代化抽象为意识形态的宏伟叙事,为伪历史主义的不可避免论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不幸的是,假设的谬误已得到证实。《陷阱》不仅仅勾勒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个隐喻同样指涉着现代性这一覆盖全球的历史过程与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真问题。换言之,对《陷阱》的讨论,应该也包括对现代性这一陷阱的讨论。
“自由选择”这一概念,为卞悟先生分析当代中国问题提供了主要理论前提和价值尺度。但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从来就不是一个仅仅与滥用“强制”相对立的政治学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原则规范下的自由选择,同样受制于资本化的权力强制。更重要的是,后面这种强制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对“自由选择”的抽象表述,将社会的不公正合理化了。因此,不应该把“自由选择”剥离出具体的历史过程和权力关系。这种问题化的方法追求的是理论的复杂化。具体讲,对“自由选择”的批判,并不反过来证明“强制”就是合理的。为了步出意识形态的陷阱,关键是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不能在试图从一个陷阱中挣扎出来的同时又跌进另一个陷阱,不能为了达到前一个目的而将后者神化。
卞先生认为,关于姓“社”姓“资”或姓公姓私这一“伪问题”的争论,应该重新定位于对强制还是自由选择这一“真问题”的思考。其理论前提与价值归属是自由市场原则,如“公民自由产权”,实现这种产权的自由选择,即要么“自由地选择‘单干”,要么“自由地(即不是被迫地)把自己的资产加以合并、自由地组织经济联合体”。实际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表述中意识到的问题比卞悟先生想像的要复杂,作为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公民,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有种种差异和利益冲突,多数公民实在谈不上拥有自己的资产,从而更谈不上自由选择了。所以,为了使“自由”这一政治理念对多数社会成员具有现实意义与意识形态召唤力,对“自由选择”的界定必须宽泛而灵活。对多数公民讲,拥有多少资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自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机会作出选择。也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所承诺的,是起跑线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正。
问题的另一面是,决定市场经济起跑线公平与否的关键,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机会均等跟自由选择,而是对资本、市场、资源等有形物的占有与占有程度。结果的不公正首先是由竞争的不平等决定的,因而所谓公平原则在这里是不适用的。用一个通俗的比方,在这条起跑线上待发的,有航天飞机和越野跑车,也有老牛破车和饥肠辘辘仅靠两条腿走路的穷光蛋。不错,总有个别赤手空拳的好汉(如比尔·盖茨等),凭着超人的机智与机遇,一跃而成亿万富翁;也总有一部分人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扔掉自行车换上小轿车,或是骑上自行车,这些人构成了当今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自由市场的信奉者正是利用这一部分人的成功,对那些尚在步行的多数人说:看,这场竞赛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场零的游戏;雪球只会越滚越大,并且通过涓滴效应惠及所有的人。部分人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自由市场原则的意识形态召唤力:过去二十年间,正是美国经济走向后工业化的同时,一方面科技进步极大地提高了效益,另一方面白蓝领职工的绝对劳动时间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按理说,这两者相加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再加上人们又“自由地”选择勤奋的工作,这不是很好吗?但涓滴效应的结果却是,也就是这二十年,特别是里根所代表的正统自由市场派成为主导势力以来,美国的社会不公进一步恶化了:占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之五与底层的百分之二十间,收入差距从七十年代中期的十一比一扩大到了九十年代初的十九比一;大企业主管与职工的收入差距,由三十四比一上扬到一百八十比一。事实上,这一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已不再是发达国家中的所谓相对贫困。仅九十年代的头七年,以单位时间所得计算,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见JeffFaux文,“TheAmericanModelExposed”,theNa-tion,October,27,1997)。这种据说是只在资本主义早期才出现过的绝对贫困现象,恰恰是在美国经济最新的一轮翻番中重现的。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对收入的分配从劳务向资本的严重倾斜,即“资本贡献”对“劳务贡献”(卞先生所引弗里德曼语)的掠夺。
这一现象在最能代表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股票市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根据最近的材料,仅站在顶尖的百分之一的投资者,其获益便超过了底线往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的获益总和。(注意,这个一对九十之比,还不包括没有能力参与股票市场的、占人口百分之四十的低收入阶层。)而占百分之九十的这部分投资者就是构成所谓“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参与股市的基本工具就是他们的雇主和个人退休保险。也就是说,他们投入股市的个人资产,就是他们晚年的生计。这百分之九十的小本投资者占总人口的近百分之五十五,加上毫无获益的那百分之四十人口,结果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还不如百分之零点六的人(见ToddSchwartz文,“TheBullandtheBearandtheWoollyMammoth”,OregonQuarterly,summer1998)。
不少人以为,股票市场毕竟可以帮助企业筹资,从而扩大就业机会,实现工人的“劳务贡献”。但实际上美国企业的筹资比例,百分之九十是经由内部方式进行的,剩余的百分之十,又常常先从信用和债券市场上实现,然后才是股市。而另一方面,公司对自己的股票行情又十分在意。通常的情况是,当一个公司的利润下降,股值下跌时,只要提出结构调整,宣布裁人多少多少,无论其经营状况是否会好转,这一着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出现股值回升。这就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股票市场对企业集资并非想像的那么重要,另一方面企业对其股票的市场表现又很重视,这是为什么呢?只要想想前面提到的那个百分之一就明白了:正是这些人控制着资本的大头,因而也就把持了企业的董事会与经营决策。大多数人的“劳务贡献”只是他们实现自己“资本贡献”的工具罢了(见DougHenwood《WallStreet:HowItWorksandforWhom》)。
最有启示意义的还是,按自由市场的标准话讲,凡在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都叫“公”司(publiclylistedcompany),这包括了美国几乎所有知名的大中企业。只有非上市的企业才称作“私人持有”(privatelyheld)。这一美式“姓公姓私”的界定当然不会引起中国式的争论,因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对每个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公民来讲,在法律上的确是“公有”的,具有认购的“均等机会”。至于大多数人是否有这个购买力,至于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少数人以“公”肥私,出现零点六对九十五的“等”式,对不起,自由市场原则从来没承诺过结果的公正。经济自由主义的召唤力表现在,当它把极度的不公正合法化的同时,它还会进一步逼问那些可能抱怨的小民们:谁让你那么懒,甚至谁让你智商那么低。别忘了,要没有那些能人管理我们的经济,要没有那些富人的“资本贡献”,哪有你的饭碗?正是通过对这种意识形态假设前提的确认,美国多数民众接受了自由市场原则的合理性。他们不患贫,也不患不均;他们站在“机会均等”的起跑线上作着成功的“美”梦。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澄清自由市场的另一个神话。不少人常常以为,里根撤切尔式的当代西方正统自由市场派,主张尽量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规律而不是官僚意志决定经济的实际运作,无论其施政的结果如何,初衷总是不错的。这种看法把自由市场在道德上神圣化了。殊不知,撒切尔时期的非国有化,正是通过强大的国家干预而实现的。关键问题还不是有没有国家干预,而是这种干预是为了谁的利益。撒切尔对国有资产的瓜分,是不可能让每个公民去自由选择的,其大部正是经过市场的“公有化”而流进了少数人的私囊。这场非国有化,与《陷阱》揭示的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英国的自由市场制度远为健全,所以看起来显得井然有序,理性合法罢了。
再看里根吧。按说美国没有欧式“福利社会主义”的包袱,“里根经济学”又那么崇尚自由市场,主客观条件使得政府干预既不应该亦无必要才对。其实不然,仅举一例。美国以前有家汽车公司,资格老得干脆就叫“美国汽车公司”。它造的“吉普”牌越野车后来在中国干脆就叫“吉普车”,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可今天还能有吉普,绝不是因为自由市场运作的结果。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西德的小轿车以其节油价廉等优势对美国汽车工业造成了空前的挑战。到了八十年代初,“美汽”资不抵债。这时里根政府出面,以债务信贷税收等方面的种种优惠政策为条件,要克莱思勒公司兼并“美汽”。兼并后自由市场原则才又重新运作,工人该裁的照裁不误。结果是:“美汽”的原股东们并未因他们自由选择的失败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
无疑,美国的开国传统和早期的人文地理环境,哺育了一种富于理想主义的自由平等精神(尽管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有色人种)。正是这种精神为民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但我们千万不能把政治上的自由精神等同于市场原则控制下的“自由选择”,把平等与“机会均等”混为一谈。事实上,自由精神与资本主义市场间,社会平等和效益优先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特别是随着大资本对民主制度的腐蚀,知识生产的学院化科层化,以及大众消费文化的稀释效用,早期形成的自由平等精神,其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对资本与权力的约束也愈发无力。
美国历史上真正能代表自由精神的人就包括卞文中谈到的那些“公有制”的实验者。但是,卞先生把关键问题搞混了。首先,这些人作出的自由选择,恰恰就是不选择资本操纵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从根本上拒绝站在那道虚幻的“机会均等”的起跑线上,拒绝参加那场不平等的竞争。卞先生的最高价值取向既然包括社会公正和人文关怀,怎么可以无视这些边际性的实验与主流经济秩序在价值选择上的对立呢?第二,卞先生说“至于它们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在道义上的凝聚力是否能持久,那是另外的问题”。另外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避而不谈这些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活生生的事例,特别是它们背后的那些“另外的问题”,却又同时把它们剥离出来以论证自由选择的抽象原则,这样讨论问题有什么意义?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卞先生在这样两个关键问题上却背离了自由市场的精髓:在西方,越是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人,就越不会把这些“公有制”实验与主导经济秩序混为一谈;同时,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突出前者的那些“另外的问题”,以证明后者的合理性。从他们的逻辑出发解释历史上那些实验的失败,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常识”般的结论:即“公有制”违背了人的“天性”。
卞先生把美国历史上那些“公有制”实验者的“自由选择”作为规范现代性的最重要的(也是文中最诱人的)标准。那么,与欧文等同一时期,更多的白人男性自由公民,通过“自由选择”对印地安人的种族屠杀,并“自由选择”了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奴役,这些是否也应归到现代性中?德国人通过“自由选举”把纳粹推上了台,这算不算?放到全球范围内,别的就不说了,就说我们熟知的鸦片战争吧,这种“自由贸易”是不是也该算?如果我们按这种逻辑推下去,凡是在现代性建立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应该算才对。而这恰恰就应该是我们讨论现代性的出发点,即把被意识形态删改抹掉的物质性冲突与权力关系还原,分析它们的时间空间型态,从而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与地理位置作出比较准确的标定。
我们不仿暂时搁置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现代—后现代”这类顺时性的理论叙述方式,从空间的民族国家形态入手,先看看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的资源分配图。
现代化经济范式首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却占有消费着全球百分之八十的资源;仅美国一国,就以不到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费着三分之一的资源。也就是说,要在全世界实现“美国梦”,这个地球的资源只能维持八亿人的消费。用中美互为参照,按人均占有的可耕地和淡水计算,要么就是把中国的现有人口只保留十分之一,要么就相当于把美国人口乘以五,然后统统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东。这一赤裸裸的生存现状是不需什么大道理就能说清楚的。
关于现代性的讨论首先应当从这一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历史成因谈起。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描述几个主要线索。首先要说明的是,价值批判必须建立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具体讲,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之前,欧亚大陆间、欧(洲)阿(拉伯)非(洲)之间跨疆域的贸易就已存在,有的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帝国间族群间为争夺资源的战争也一直存在,对异族异域的掠夺本身并非欧洲殖民主义的专利。事实上,欧洲人在海外的早期殖民经历更具这种“前现代”特征。换言之,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还必须有另外一些条件。讨论现代性的形成条件及其现实意义,最少可包括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1)欧洲殖民主义对海外原料市场进行的有组织的商品开发,经过贸易分工建立起的与之相应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市场配置。与“前现代”对资源的掠夺占有不同,殖民地式市场经济把无偿得来的资源商品化,进入资本的再生产,因而“合理化”了。形象地讲,欧洲殖民主义者先是以海盗的方式抢来了鸡,但得手后却没有像海盗一样简单地杀鸡取蛋,而是要鸡不断地下蛋孵卵。这只鸡不仅是无偿占有的,而且是“无价”的。这里讲的“无价”,一是指几十倍于西欧的自然资源,二是指古典经济学(也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未考虑过计算生态成本,而只计算开发这些自然资源的费用。从世界经济史谈现代性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一无偿资源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成本效益。综合渥伦斯坦和一些环境主义学者的观点,若把无偿占有的自然资源和以后开发消费造成的环境破坏同时计人成本,以当代的可比价计算,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个亏损型体系。
应该指出的是,仅仅从经济学的立足点出发进行成本效益评估,不但永远也算不清(首先价格尺度就离不开具体的时空,而已经被毁灭的大量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未来预期价值今天根本无法计算),同时也在复制着以资本为核心的一整套关于“价值”的话语。要进行成本核算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量化过程,只要想想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上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非再生性资源,仅仅在过去二百年间就差不多用尽或者毁掉了最少一半;而直到三十年前都不计价的“空气”(如臭氧层),今天也变得“稀有”(薄)了。更重要的是,还有绝不能用价格计算的社会成本,最“昂贵”的就是侵略战争,种族屠杀和蓄奴制。现在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改造自然并改造自身的老话倒过来讲的时候了:资本在创造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的同时,也毁灭着人类和地球。
(2)与这种市场经济秩序配套的社会组织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即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法律体系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全球资源的再分配几乎是同时开始同时完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把“地球”变成“世界”的一个成功秘诀,就是通过这一体系将资源的不平等占有永久化,秩序化。这种秩序化的结果,从发展主义的角度看,就是所谓发展的不平衡;在消费上的表现,就是现今世界的资源消费图;以生态成本论,就是自然资源赤字。问题的关键是,民族国家通过不断地复制这种不平等秩序,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本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间进行了极不平等的再分配。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的亏损型发展非但没在西方国家的成本核算中表现出来,结果反而是“高效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水涨船高的情况下,今天富国的穷人看上去过得不比穷国的小康人家差,而且因此为富国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并未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而式微(欧盟等形式的区域性国家集团的“对外”的功能并无本质变化)。在资源的占有与消费、人口控制(移民)、环境保护等方面,西方的民族国家功能实际是强化了。全球性跨国资本的流通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只是从广义的“生产”的角度解释目前的世界格局;以广义的“消费”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除非发达国家偿还旧债(而这又是不可能的),现行秩序只会继续下去,而维系这个秩序的机制就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有揭示意义的是,西方自由市场派这时却不谈什么机会均等了,因为它实在不可能让人相信民族国家间还有什么平等的起跑线;相反,它却要坚持诸如贸易平衡这类所谓结果的“公平”。正是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富国继续享有它们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并将高消费的经济社会环境成本转移到穷国,把穷国变成了它们的夕阳工业区和垃圾堆。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内爆型特征:当这个地球被瓜分完后,资本主义这个亏损形经济体系只能允许它的后来者把现代化的社会和生态成本就地处理,把自己的家园变成角斗场,变成荒山秃岭。这一成本转移过程当然不会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均衡负担,而只会不成比例地依内部权力关系出现反向“涓滴效应”。
(3)由于这个主导世界秩序是伴随着欧洲人的海外扩张而形成的,为这一秩序合法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只能是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但对欧洲中心主义应该历史化,作为话语对待,而不是机械地套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模式。这种意识形态的话语特点,就是它既是虚构的,是在欧洲人“发现”别的文化的同时而构建的,同时又是写实的,即对“野蛮人”的掠夺征服教化等具体行为过程,常常是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从话语实践转变为社会实践。殖民地市场经济建立的一个理念前提,就是欧洲殖民主义者认为“野蛮社会”没有私有财产这一核心观念及由此演生出来的一整套“天赋人权”。就是以这种话语关系对权力和权利关系的界定,殖民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占有才可能是“free”的(即占有方式的“自由”与占有物的“无偿”或“免费”)。将意识形态话语化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这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阐释是一个不断的建构、修订、改写、流通和复制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方人”的参与和贡献是使它在全球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只能指出其中的一条线索。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面对的并非单一的它者:除了那些“野蛮”社会外,还有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文明,同欧洲一样拥有成熟的文字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套“传统”。从莱布尼兹到伏尔泰,不少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中国是一个在很多方面比欧洲还要先进的文明社会。这一“马可·波罗情结”出现价值认同上的逆转,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黑格尔。德里达就曾指出,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建构,就是通过对“太阳”的隐喻转换而完成的:文明之源的东方像自然界的太阳一样,永远遵循着自身的轨迹简单地重复自己;当太阳运行到西方时,它才真正成为有意义的光明之源,内化为人的自由精神,照亮了历史进步的方向。这一本质论的二元对立,奠定了关于东西方、自然与人、古代文明的自生自灭和现代历史的目的性等现代性的经典叙事。
对现代化这一陷阱提出质疑,并不意味着就要回到某种想像中的“传统”中去;一旦被历史逼人这个陷阱,回路就已经堵死了。只要我们的根本生存方式就是在这个陷阱里挣扎,现代性就永远是个“未完成式”。但也正是这种深刻的悲观,迫使我们寻找别的精神资源,以进行一点最终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抵抗。至于这点精神资源来自“传统”还是别的什么(后者当然包括“西方现代性”中的反叛力量),只要它能反抗绝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