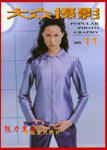众人谈影(等四篇)
值得深思的黑白
陈光俊
我们在谈论黑白的时候应该有所区分,真正经典类的黑白照片与新闻报道类的黑白照片应该是有所区分的,对于新闻报道类的黑白照片来说,拍摄的瞬间应该是第一目的,影调素质等其他要求便排在第二位了;但是我们在看一些非常经典的黑白摄影画册时,诸如亚当斯、韦斯顿以及现代美国的一些声望极高的摄影家,他们选择拍摄的主题可能都非常一般,一间房子、一根草、一朵花……,我们谁都可以随意找到这样的题材,但是我们最终出来的结果却不一样。为什么呢?这就是关系到对摄影的理解问题。过去我们拍的黑白照片主要重视题材,内容也多是赞美生活等等向上的主题,而对后期的制作便有所忽视了。其实黑白照片的后期环节含有很大的艺术成分。我们的摄影教材中也有亚当斯的“区域曝光”之类极具价值的技术文章,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严格地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所以一个好的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一定知道这张照片应该怎么冲洗、制作,这才是最关键的。
过去我们用伊尔福、柯达的涂塑相纸已经感觉非常好了,其实这种相纸纯粹地是为新闻报道而设计的,这种纸的优势是快,可以用机器冲洗,而纸基纸是不能用机器冲洗的。国外一些好的黑白摄影者一定都是用纸基相纸。也许我们已然拥有了很好的材料了,但是我们能否把材料的水平发挥到极至,这才是关键,也是最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现在,我们国内的摄影人士只要条件允许,从照相机的机身、镜头到胶卷、相纸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与国外一样,绝对不会比国外摄影师的器材差。我们试想一下,象亚当斯、韦斯顿、纽曼那个年代的镜头怎么可能与我们现代的镜头相比呢?可是他们所达到的影像效果却是我们至今所达不到的。这是很值得去深思的。
现代黑白照片的主流方向应该是属于经典类的,这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黑白照片已经完全是两个概念了,过去拍摄黑白照片是因为黑白照片冲洗简单且经济,而现代拍摄黑白却是一件冲洗工序复杂且消费昂贵的工作,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高速率、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注重结果,但忽视过程。所以目前黑白照片不可能大规模地得到普及。
在国外,黑白照片也是非常贵族化的,很有钱的摄影师才会进入黑白摄影,而有条件的家庭也多以经典的黑白照片作为装饰,黑白的品位和地位也是彩色不可替代的。在国内,喜欢拍摄黑白的人士仍将受到各类条件的制约,如:是否有经济条件建立标准的暗房,是否具有一整夜做一张片子的韧劲,是否有时间静下心来对摄影的全过程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所以我个人认为,现代黑白的主要消费群体不会太大,因为它太复杂了,也因而更值得我们去深思了。
黑白需要用心去感受
张 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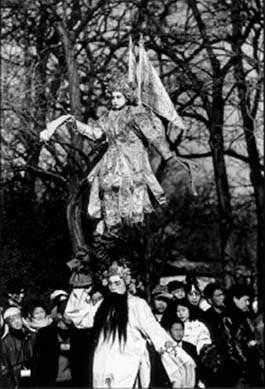
想起自己刚搞摄影时,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拍照片只能从黑白做起。自己也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勤奋踏实地学习,利用一切时间去拍摄,精心细致地去制作每一幅照片。多少个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我的努力也是这样始终如一。逐渐地,自己掌握了一些拍摄技术以及黑白照片的制作技巧。并深深地感受到用黑、白、灰表现五彩缤纷的社会和人生的独特魅力。
现今,彩色图片受到了数字影像的猛烈冲击,黑白照片则更加无奈地在摄影这个纷繁的大环境中黯然生存。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照片的需求越来越多,彩色的真实、黑白的写意、数码的便利……。艳丽的彩色摄影比陈旧的黑白灰更直观,也更简单;数字影像更加简捷,各类效果在数字化面前更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展示。与前两者相比,黑白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已然越来越远了。它的制作太原始、太累人,太难掌握了。
谈到摄影,我认为应该要走自己的路,拍摄出有自己想法的作品。所以我不想去追求彩色摄影,更不想去操作数字影像。可以说在目前的摄影走向面前,我保守,我依然会执着地对待黑白摄影和暗房制作,我认为只有把拍摄和后期加工完全统一起来,才能体现出摄影创作的魅力。
我喜欢默默地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喜欢体味黑白给我带来的乐趣和享受。现如今,在各类影赛、影展和画册中,黑白的比例太小了,在绝大多数的商店中也很难见到黑白胶卷,更别说相纸、药品了。从这一点不难看出黑白的市场需求已是极为惨淡了。摄影爱好者们大都愿意将金钱投入到新型相机、高档镜头,拍摄效果不理想时,便改用120,再不尽人意时,又瞄向了4×5、8×10。很少有人会重视后期制作的,更谈不上在暗房设备方面进行投资了。
在许多上乘的摄影佳作中黑白照片居多,能留存的、有味道的照片仍是黑白的,哪怕是一张留影纪念照,也不难从中感受到黑白的内在韵味。我希望爱好摄影的朋友,有机会还是多拍些黑白照片,有条件的最好多动手做做黑白照片,仔细地品味拍摄和制作的乐趣,用心去感受黑、白、灰独特的美感,或许会从中领悟到摄影的真谛。
贵族化的黑白
闻丹青
这年头,拍黑白照片可不容易,得自己冲自己放,哪象彩色片,拍完之后往冲印店一送就齐了。虽然个别也有一、两家专业店有黑白业务,但价格高,质量也不尽如人意。现在玩黑白要有时间有钱才行,不象二、三十年前,因陋就简凑合一下就可以了。
1970年前后,正是文革中期,最初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过去了,抄家、打人、游街、武斗的少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大串联结束了,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几乎所有业务工作停止了,只有政治运动在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这时,许多还没有受到冲击或遭受过一些冲击暂时平静或冲击了别人也受到别人冲击或不积极参与运动的人们成了逍遥派(逍遥派多么好听的名字,好象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门派。岂不知逍遥派与它的对应词——造反派、保皇派、当权派,在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心中,在已经写就但还未成文的中国历史中,是多么沉重的词语。)。人们获得了大量的时间,织毛衣是女同胞的日常工作,玩矿石收音机、无线电、半导体是孩子们最好的智力消遣,而照相则为许多人所热衷。
有一段时间,王府井的照相馆里,不仅店堂贴着“为人民服务”,也落实在行动上。人民群众有自己印放照片的要求,照相馆就出售配置好供人零散购买的显影液、定影液,盛在带龙头的搪瓷水桶里,一百毫升几分钱。相纸一般都是裁成小张小包装,更令人兴奋的是隔段时间就出售一批按斤两卖的裁切下来的纸头纸边,窄的也有两英寸,宽的四、五英寸,这简直是最新指示之外的最大喜讯,院子里的孩子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
最开始都是印相,两片玻璃一夹,台灯一开就曝光了,接着显影、定影,照片就出来了。后来找几块木板钉巴钉巴自制成印相箱。再后来,开始自己制做放大机,铁制暖瓶外壳当灯室,固定上两块凸镜,下面拧上个镜头,再加上些木工铁工,虽然晃晃悠悠,也不甚美观,但的确可以放出照片。我见过有些心灵手巧的人自制的放大机也颇象模象样。相信时至今日不少人家里还会存有这玩艺,只可惜中国现在没有摄影博物馆来收藏它,若是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得以实施,收将进去也是历史的一个碎片。
照片出来之后需要上光,这可是件既有意思又令人心焦的事,在擦干净的玻璃上涂些滑石粉,再把照片贴上去。照片逐渐干透,逐渐翘起来,最后“咔”的一声掉下来,看着一张张照片“咔咔”落下,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有时由于处理得不好,照片就是稳稳地贴在那里,或是有个局部不肯松开,性急的就上手撕,结果常常把照片的药膜撕下来,搞得好扫兴。
那时放照片都在晚上,把门窗稍加遮挡就可以了,夜是静静的,数着秒表的嘀嗒,暗暗的红光里充满了无数的乐趣。
现在,还是放大照片,放大黑白照片,要想拿出真正的黑白照片,没有高质量的设备,没有好的材料,是几乎不可能的。过去自制的或低档的放大机放出照片四角发虚,制做虚光照片倒是歪打正着,放制一般照片由于主体通常处于中心,四边发虚就凑合了。用高质量的放大机放照片,从中间到四角光线均匀同样清晰,感觉真的不一样。
如果把整个摄影过程细细数来,胶卷是第一关,适合需要、质量上乘的胶卷是一切的基础。对于拍摄过程,撇开对照片的主观处理如构图、用光、立意等不谈,从技术上说拍摄时最重要的问题是曝光正确和把持相机的稳定,再下来就是胶卷的冲洗,以上步骤的总和,决定了一张底片的优劣。好底片是好照片的基础,否则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将底片没有纪录的东西放出来。
当你拿着一张上好的底片走进暗房时,就开始考验暗房了,放大机怎样?放大镜头如何?暂且不谈它的便捷性与舒适性,只要求它对底片的表现能力。我们曾作过一次试验,同一台放大机,同一张底片,使用几百元的镜头时画面中的细节模糊一片,使用几千元的镜头时,同样的细节清晰可辨。
放大纸的选择性就更大了,国产的、进口的,固定号数的和可变反差的,涂塑的、纸基的,还有更重表面类型的,总之为最佳效果可以选择最适合的。
放大过程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足可以著一本书。这里只想就显影问题说两句,它本应该是定时、定温严格而又单纯的一步,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我们常常温度随室温,时间更随意,影像差不多就提前起锅,还差点的多泡会儿,实在不行还有药液加温、局部摩擦等高招。把本应单纯的复杂化,打破严格的时间,增加了可变因素,使整个过程难以量化。
现在,玩黑白摄影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很多人没有好的条件,而有条件的人常苦于没有时间。野菜原本是穷人无奈的选择,时代变了,它登堂入室被称为山珍。黑白摄影似乎也是这样,低水平制做的照片拿不出手,投稿、参赛日益难以取得效果。所以说黑白摄影趋向贵族化。
不轻易招惹黑白
窦海军

吴寅伯 摄《水巷》1982年5月摄于苏州(苏州古城内河道纵横,有东方威尼斯之称),作者立于略高于地面的一座石板桥中央,以初夏的较密树叶遮挡了直射镜头的太阳光,用哈苏相机、50mm广角镜头加二号黄滤色镜、柯达plus X胶卷、F11光圈、1/100秒拍摄。
很长时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彩色照片在评选时比黑白的占便宜。不只是一种说法,事实也如此。不知不觉地,这个说法不但没什么人提了,甚至还有倒过来的苗头。在如今较高级、较艺术的评选中,黑白照片反倒比彩色照片更加招眼,尤其是制作精良的黑白照片,更有着先声夺人的优势。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转换?最表层的原因是彩色照片的普及率比黑白照片高出很多,满眼皆彩照,造成了人们视觉上和心理上一定程度的麻木,于是又把目光转向相对稀少的黑白。求新求异是人的本能之一,他同样表现在审美趣味方面。就此,惯有“创新到死”之称的毕加索还有一句少为人知、不大好理解的话:“我就不相信艺术中有什么创新,艺术只有轮回”。不说这话是不是真理,但也却有一定的道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黑白照片的苗头,恐怕也不乏怀旧、轮回的根据。
就我个人而言,如今也是更喜欢看优质的黑白照片,尤其是前些天在“中国摄影在线”网上看了亚当斯的一些彩色作品,就更觉得黑白照片的魅力是永远不会被取代的,甚至不会因时间之水的冲刷而削弱。
20年的影龄,我自然也是拍黑白起家的。然而越干,越看,越感到拍好、洗好黑白照片的不易。最让人泄气的是,在美术馆看亚当斯的原作展时,我的老师也坦言自己洗不出这样的照片。如今回想,那时我已经结识了不少的摄影前辈和名家,但却没有一人、一本书能够就如何做出纯影派照片给我个详细答案。我敢说,时至今日,中国在黑白摄影语言的把握方面也没能赶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纯影派的水平。虽然我们今天可以搞到世界上最好的相机、放大机和感光材料,但我们的软件——技术和艺术方面还没过关。这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我井底之蛙不见中国黑白摄影之真人。
谈黑白,总拿纯影派说事儿,难道只有它是黑白摄影语言的唯一至高境界?当然不是,多元化才是艺术语言的根本,黑白摄影语言同样如此,纯影派的语言只是黑白摄影语言的重要风格之一。但应该肯定的是,纯影派时期是西方人探索精确控制黑白影像技术的大成时期,其意义不单单是制作出了细腻丰富的黑白照片,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取了驾驭黑白影像的经验和能力,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技术方法的基础。可惜的是,中国的摄影师至今也没能真正补上这一课。
虽然控制黑白影像的方法属于科技范畴,但它最终还是不能脱离艺术的,所以与心境有关。毛毛躁躁的心情,急功近利的活法;琐事缠身、创作欲望淡弱,又怎能扎在暗房里平心静气地参黑白之禅,悟影调之道?尤其自己连个暗房都没有,做片子之前那套准备工作实在是好心情的杀手,等到将底片插进放大机时,精力、体力和好心情都损失了一多半。如果进入不了状态,如果没有好心太的支撑,就还不如做个光想、光说不练的虚把式、嘴把式;就还不如把反转片往图片社一扔来得舒服、痛快。谈到好心态无非有两种,一是超乎一般的痴迷执著,二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平和沉静;唯有浮躁、巧滑、心猿意马是艺术的大敌。我想,当自己还不能洗去虚浮的时候,当自己还不能像静夜独品一杯香茶那样对待艺术时,最好还是别去招惹比彩色要纯净许多,比彩色更需要真功夫的黑白摄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