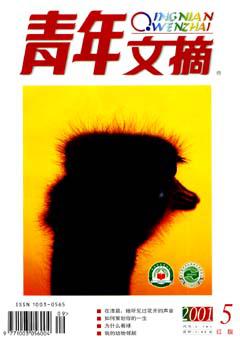在清晨,她听见过花开的声音
何 宇
穿过逼仄、昏暗的楼道,吴春梅慢慢走进了家门,午后的斜阳正倾泻在这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斗室中;轮椅上的父亲已经将摊落一地的鲜花拾掇妥当;母亲和妹妹正要准备出门卖花,他们都急切地抬起头问:“录取通知来了吗?”
“嗯。”只有这样一句轻声回答一个庄重的点头;泪水,却已在刹那间涌上全家人清癯的面庞。
时间是2000年8月11日,高考成绩是513分(上海卷)!卖花姑娘吴春梅终于如愿以偿地跨入全国重点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门槛。上海虹桥路乐山新村的过往行人没有意识到,从这一天起;他们熟悉的那个年轻美丽的卖花姑娘就要从他们视野中消失,从不幸的蛹中羽化成彩蝶;
一
所有的悲伤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那天,爸爸说:“孩子,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一夜之间,噩梦降临到浙江绍兴市的这个四口之家;吴春梅清楚地记得,“那是1989年年底,那天很冷,耳边只听到北风呼呼地吹。”
这天上午,正在念小学四年级的春梅背上书包兴冲冲地去学校。离家时,做供销员的父亲笑眯眯地叮嘱她注意安全。下午放学,春梅意外地发现父亲母亲竟然不在家,邻居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她:“你爸爸出车祸了!还不快去医院?”小春梅眼前一片昏黑,飞也似的赶到医院急救室。只见母亲坐在长凳上悄然抹着两腮的泪水。春梅忘不了那情景:“好像天塌了,妈妈的身影在长长的走廊里显得那么孤独无助。”“爸爸脊椎受伤,刚开始时我们全家都不相信他再也站不起来。妈妈跑遍了绍兴所有的医院;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惜倾家荡产。”不久,在绍兴的一家医院为父亲动了第一次手术,结果不尽如大意,他还是只能瘫在床上,全家人反复商量后决定:“带爸爸到医疗技术先进的上海来做手术,也许还有希望。”
当时,小妹妹春园只有3岁。为了照料好孩子,母亲毅然决定举家搬到上海:“爸爸在哪几看病,我们就在哪儿陪着他。这个家不能散!”一家人的命运在噩梦之后,画了一道陌生的弧线,他们变卖家产、拖幼携残、一路颠簸——今后,在飘零和痛苦之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
爸爸在中山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我们满怀着希望。手术做完后,医院说‘中枢神经已经创伤性断裂;下肢瘫痪。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了!医生说,惟一能做的就是给你爸爸买一辆轮椅,他得用一辈子——“我哭了。现实一点点地逼着我们接受,虽然我不想这样……”
一家人还得活下去,老家已经卖得一点不剩了,也许,在繁华的上海,更容易有个盼头。他们在中山西路租了间小屋,为活着,也为了还看不见的希望。
二
妈妈说,你卖花只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那一年,春梅15岁。
全家人都住的小屋只有1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里外两间,父母住在“外屋”,姐妹俩挤在里边。书桌是木板钉的,白天翻起来挂在墙头;好腾出空地,晚上放下来,悬一盏光秃秃的日光灯夜读。除了床和堆得高高的书籍,空无一物。
小屋的租金是350元,对被病魔折腾得一贫如洗的春梅一家,这是每个月压在心土的大石头。要在大上海生活下去,油米柴盐,哪一样省心啊!
爸爸说,我们怎么也得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他东挪西凑买了辆残疾人车,拉客挣钱。大夏天,他在滚汤的车上一坐就是10小时,生了大块大块的褥疮。妈妈心疼得哭了。那以后,妈妈去做钟点工,每天做4户人家,一小时挣8元钱,起早摸黑还是挣不出全家的生活费。一天晚上,春梅听到妈妈轻声说:“听说卖花能多挣两个钱,可单靠我们看来是不行了,得让孩子搭把手。”
“不行,他们必须读书、上大学,不能毁了她们的前途。”
春梅再也忍不住,拉着妹妹冲到外屋:“爸爸,我们可以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我们会比以前读得更好!”
妈妈又流泪了,不过,这泪水和以前不同,除了辛酸,还有欣慰——眼前懂事、要强的女儿,不就是他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希望吗?
从那以后,每个傍晚,母亲和春梅骑着自行车去陕西南路批发来两大捆鲜花,一来一去大约花一个半小时。回家之后,爸爸和妹妹帮着她们修整花枝、包装、扎花篮,匆匆扒几口饭,接着再干,一直忙到万家灯火璀璨。第二天清晨,春梅和妈妈合力把花摊推到乐山新村路口,用有点羞涩的声音吆喝着:“卖花啊,又便宜又新鲜的花啊!”
三
春梅姐妹上课的时候,妈妈一个人守着花摊,为了和那些装潢华丽的大花店竞争,她们的花卖得很便宜。一直要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打烊收摊。天气好的时候,她们一天能卖掉七百多元鲜花,可以挣三十多元。双休日和节庆日是她们的好日子,一小半的收入得靠这有限的几天,我也是春梅最忙的时候。她忘不了那些老客户,有一次,常来买花的老阿姨请她们母女到家里扎个花篮,说是装点房间,又摆出好茶好糖果招待她们。春梅去厨房洗手的时候,听见了老阿姨和邻居的谈话:“这卖花姑娘不容易啊,听说是考上了市重点中学呢,还是第三名,我们买他们家的花,也是帮助了一个好孩子。”春梅听着,眼眶湿润了。
高一暑假,春梅头一回独自卖花。她下午骑车批发来一大捆单色康乃馨,价钱倒不贵。但湿漉漉娇嫩的花;带回家可真不容易,好在爸爸替她在车架后边安了块木板,说是把花全搁上去;用绳子扎起来就行了。可是春梅总扎不好,在闷热的大棚里,从清晨4点一直折腾到6点,才算弄妥,人已经汗流浃背;像刚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推着自行车上街卖花,没有妈妈助阵,害羞得不得了。自行车推来推去,“卖花”两个字就是喊不出口。有想买花的人看到一个文静、清亮的女学生推着花徘徊,迟疑地问这花是不是卖的,春梅这才红着脸点了点头……
后来就不这样,经过风吹雨淋的磨炼,春梅长大了,不是变得世故,而是镇定了,能干了,独当一面
四
在赫赫有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春梅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美丽开朗的优秀生。而在街头呢?在那些与她匆匆邂逅的行人的眼里,她只是个卖花女,纤弱卑微。每天,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必须学会扮演好两种角色。
妈妈总在提醒春梅:“你是个百分之百的学生,卖花只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当学生。”在街头,卖花卖到腿软喉干的时候,春梅就想像眼前是交大古色古香的朱漆大门——“进了大学,除了学习我什么都要努力忘却,忘却所有的艰难困苦。”大学梦,是她在迥然不同的两个角色间平衡的支点。
在学校,春梅知道她与其他无忧无虑的同学不在生活的同一起跑线上:“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在我有信念、也许越有信念未来就会越好。我不在乎别人怎样看我,事实上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家境贫寒鄙视我。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守望好自己的麦田。”
她的理由,是一个年轻生命的精神家园,灌溉它的,是春梅读过的上百本文学名著,是艰辛与美好并存的现实,是梦想——在这片麦田里,她一天天“明白做人的道理,遇到困难能有解决的办法”。当林林总总的困难像高墙一样堵在她面前时,她就凭借内心的力量去推倒它们。
有一次,她放学后去批发鲜花,途中天雨路滑,她连人带车翻倒在地。望着一她狼藉的鲜花,她哭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学生倒在街头哭泣成什么样子?那一刻她没有多想,她放声为折断的花草哭泣,为目睹的生命的脆弱哭泣——许多次她推车奔走在大大小小的菜市场,吆喝卖花,刚开始她没有执照,免不了要遭到驱逐、斥责。众目睽睽之下,卖花姑娘低头缄默,只有在人散之后她才悄悄抹泪,然后装出开心的模样回家。
终于,她等到了一纸录取通知书——生活弧线变成了彩虹,她的生活完全不同了。出人意外的是,她最想改变的不是她的清贫,她说自己喜欢“纯学术的东西”,希望能“安静地从事我的工作”。她一直为贫穷所困,却没有兴趣追逐金钱。
现在,春梅住进了交大远在闵行的校园。她不可能去市区卖花了。我问春梅,以后有钱了会不会开家大花店?她的回答耐人寻味:“我大概不会以此为职业的。我想。做一个养花人也许会更喜欢鲜花。”我一直记得她那句诗意的话,当我问她当了那么多年卖花女有什么收获时,她轻声说、她听见过花开的声音……在清晨。
(王红娟摘自《现代家庭》2001年第3期上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