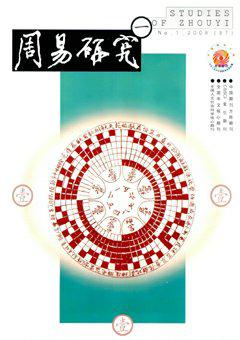论罗汝芳的易学思想
梁隽华
摘要:罗汝芳三十四岁时得传《易》学,悟得易理贯通四书五经,认为《易》乾坤的“生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仁,也是心;“太极”不在“易”之外,而本身就是乾坤,是有和无的统一,实有道体又圆融无碍,它成为性命的根源,而其自身又是超越善恶的“至善”。从乾坤本体的生生之理又引申出即本体即工夫,“不动心”及“自然”的工夫论。
关键词:罗汝芳;易学;天命之性;生生之理;仁;本体;工夫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1-0019-06
On LUO Ru-fangs thought on the Yi
LIANG Juan-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LUO Ru-fang was imparted Yi-ology at age of 34,and then he comprehende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Yi threads through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holding that the principle of “creative creativity” in the Yi is the human nature endowed by heaven as well as the benevolence and heart/mind;Taiji (lit. the Grand Ultimate) is not outside of the “Yi” (change) but the Qian and Kun and the unity of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In addition,he insists that,as the source of human nature and destiny,the substantial Dao is penetrating and all-inclusive,and it is inherently the utmost goodness transcendent to good and evil. From the principle of “creative creativity” of Qian and Kun,LUO attained the unity of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practice and the integrity of “calm mind” and “the natural principle.”
Key words:LUO Ru-fang;Yi-ology;nature endowed by heaven;creative creatity;benevolence;noumenon;practice
罗汝芳(1515-1588年),字惟德,号近溪,当时与王阳明的亲炙弟子王畿(龙溪)并称“二溪”,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为泰州学派第四代传人。牟宗三先生称其“更为清新俊逸,通透圆融”,为阳明后“王学之调适而上遂者”、“真正属于王学者”(第221页)[1]。
一、《易》学渊源
据载,近溪三岁始觉母子亲情,五岁从母习《孝经》,十五岁志于道学,十八岁读王阳明《传习录》得解身心重病,二十六岁得颜均(山农)以“当下日用”的“体仁”点拨,“如大梦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学有真传,遂师事之”(《近溪子附集》卷一)[2]。
在关于近溪的生平叙述中,记载了他学《易》有得的经过:
戊申(注: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罗汝芳34岁。)学易于楚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旧以举业师先生,先生知其《易》有传,迎致之执弟子礼,胡喜,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间谓:“若知伏羲当日平空白地着一画耶?”先生略为解说,胡默不应,徐曰:“障缘愈添本真愈昧。”如是三月然后见许。(《近溪子附集》卷一)[3]
对此事,近溪自己作了如此叙述:
自幼蒙父母怜爱过甚,而自心于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怜爱,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读《论》《孟》孝悌之言则必感动或长要涕泪,以先只把当作寻常人情,……后来诸家之书做得着类吃苦,又在省中逢着大会与闻同志师友发挥,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径。……从此回头将《论语》再来细读,真觉字字句句重于至宝,又看《孟子》又看《大学》又看《中庸》,更无一字一句不相照映。
其时,孔孟一段精神似觉浑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横穿直贯,处处自相凑合,但有《易经》一书却贯穿不来。
幸楚中一友来从某改举业,他谈《易经》与诸家甚是不同,后因科举辞别,及在京得第,悔当面错过,皇皇无策,乃告病归侍老亲,因谴人请至山中细细叩问,始言渠得异传,不敢轻授。某复以师事之,闭户三月,亦几亡生,方蒙见许。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时孝悌之良,究极本原而已。从此一切经书皆必归会孔孟,孔孟之言皆必归会孝悌,以之而学,学果不厌,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万物一体而万世一心也。(《近溪子集·乐》)[4]
从上看到,近溪早年对“仁爱”“孝悌”有至深的切身体会,故在读《论》《孟》之时至深之情与至切之理贯通,继而,又能悟得《论》、《孟》、《大学》、《中庸》之相映贯通,但未能与《易》“贯穿”,此时当在师事颜山农之后。近溪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中举,时二十九岁。次年当以举人参加会试,但自认为“吾学未信,不可以仕”。因此不就廷试,归而寻师问友。此时所谓“未信”,恐怕与其未能贯通《易》有关。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年),近溪三十一岁,于家乡从姑山建从姑山房接引来学。胡宗正从近溪学,当在此之后。近溪先为胡生师,当时知其谈《易》与别人不同,似未深究。后胡生别,再得知其《易》学有传,于是反以其为师。师生易位,是为一美谈。胡生所传者何,不得而知,而其点拨之语,禅意颇浓重,近溪后有论及所悟。近溪闭门三月始得少许,值得注意的是,近溪称其尔后所悟乃是于孝悌“究其本原”,“一切经书归于孔孟”,在此应是《易》归于孔孟,因为之前已经悟得四书相通、孔孟精神直贯四书。到此,才真正谓“学既通”。
宋明理学从北宋周敦颐、张载起,致力于打通《易》、《庸》、《论语》、《孟子》,使仁与天、心与性、天道与性命通而为一(注: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牟先生认为,孔子未言仁与天合一,孟子未言心性与天合一,《中庸》、《易传》有天命之实体(或乾道)与个体之性关联之意,但未能明确说天命、乾道内在于个体而为其性,宋明儒则明确表示天道性命通而为一。),《易》在理学中,成为构建仁体、道体的形上根据,如周敦颐以“诚体”释“乾道”,把“诚”的道德本体与“乾元”的宇宙论本原合而为一,诚体即乾元,而“乾”本身又有“创造性”,是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源,因此乾道流行变化就自然把天命之性直贯到万事万物中,个体之性就是天道之落实。理学家在学理、论证方法上得于《易》者良多。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时也潜心读《易》,并称其读易处为“玩易窝”,“龙场悟道”与其对《易》的钻研不无关系。与近溪同时略早的龙溪,对《易》亦有相当见解,并与学人有就《易》理进行争辩之史实。可见,在“四书学”盛行乃至泛滥的宋明,《易》依然是学者的必修课,对《易》领悟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正因为如此,近溪在领悟到四书与《易》的贯通之后才能说真正领悟到仁体为万物一体,万世一心。这才是达到了理学的制高点。可以说,离开《易》,便无法认识到近溪的思想整体,反之,离开孔孟的思想源头,也无法理解近溪的易学思想。
二、《易》理贯穿四书五经
自汉起,《易》成为儒家“群经之首”,“大道之源”,首先因为其“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在理学中,《易》有如此重要地位乃是因为其义理贯通于四书五经。
近溪说:孔孟“皆是以仁为宗,吾夫子此个宗旨既原得诸《易》,而易则原本诸天,天何言哉,极究其体,则止是时行而不息,博观其用便是物生而不其穷。夫惟其有得于天之时行而妙乎不息也”(《近溪罗先生一贯编·论语上》)[5]。“孔子一生话头独重两个字面,一个是仁字,一个是礼字,两个字长相为一套却乃各有重处。仁是归重在《易》,礼则归重在《春秋》。”(《会语续录》卷下)[4]孔子(同样也是所有儒者)的宗旨是“仁”,“仁”得自“易”,归于“易”。本来在孔子思想中天与人尚有一段距离,“仁”基于人的亲情,人格性的主宰天已经远去,客观化的天成为“命”作为外在力量对人形成压迫,孔子把“知命”作为君子的必要条件,至少表明二者原来是疏远的,但在其“天何言哉”、“逝者如斯乎”的感叹中又透露出对不言之天成就着万物的生生不息、川流不止的尊重和向往。近溪认为孔子的“仁”与“天”并不存在距离,是内在相通的,天的生生不息就是“易”,是“易”之“乾坤”。他以“易”理消除了孔子思想中天人的紧张。同样,他也认为孟子的“浩然之气”也是从“易”之“乾坤”“翻出”来的,其“至大至刚”不过是对乾坤的另一种描述。
对于《易》与《学》、《庸》的关系,近溪认为,“盖统天彻地尽人尽物总是一个大道,此个大道就叫中庸”,“此个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经》中来”,“‘中庸其至的‘至字原是从《易经》上来”(《近溪罗先生一贯编·中庸》)[5]。这个大道就是“道体”,所谓“平平常常遍满乎寰穹,接连乎今古”“无昼无夜”的天命之性,“其条理就事务铺张出去”就是“率性之道”。近溪认为,《易》的“生生”之理,正成为《中庸》这两句的根据,因为“天命”就是《诗经·颂·维天之命》所说的“维天之命,於穆不已”。 天命不已表现为生生不息,而《易》之理就在“生生”:
孔门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统之以“生生”一言。(《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易》)[5]
孔门《学》《庸》全从《周易》“生生”一语化将出来。盖天命不己,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孙拟至曾玄。故父母兄弟子孙是替天命生生不已显现个肤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父母弟兄长慈子孙通透个骨髓。直竖起来,便成上下今古;横亘将去,便作家国天下。(《近溪语要》下)[4]
以生生释天命,使冷冰冰的天命成为一股暖流,流遍万物,流遍古今,人人一体,人与万物一体。天命之落实又为性,此性在人中为天生的仁爱之心。这样,人道的伦常获得了形上的根源,透过对天命、仁体的体悟,“横”“直”打开,便可由内圣而外王,家国天下得以齐、治、平。这样,《大学》之理也就收摄到《易》的“生生”之理中。
“时”的观念在孔子那里体现着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灵活地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论。孔子讲“君子而时中”,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孟子·万章下》)。对此,近溪说:“盖天道人心总是一个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时,心以生生而习乎其时,故生生之易。易也者,变通以趋时者也。”(《近溪罗先生一贯编·论语上》)[5]“孔子时中只是个易。孔子之易,只是个乾坤。孟子翻出,便叫做浩然之气……”(《近溪罗先生一贯编·孟子上》)[5]并认为《乾》体现了“时”,也贯穿于五经:
乾行之健即时也,自强不息即习诸己而训诸人也。……奉天则以周旋而时止时行时动时静也。推之即《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中节之节,亦即《大学》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礼》《乐》之损益,《春秋》之褒贬,《诗》《书》性情政事,更无出于时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经之源乎?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经者难且甚矣!(《近溪子集·射》)[4]
三、以“生生”释仁体
仁体在近溪看来也就是就是心体:“仁,心体也,克复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体。”(《近溪罗先生一贯编·论语下》)[5]因此“宇宙间其一心矣乎!”天地古今皆由此生。以心体统仁体,统天道,并进一步说此心“无间”又“无外”。近溪对“仁”的阐明深入于两极:一极是实存的、感性的、人本能的亲情“赤子之心”,故以孝悌说“仁”,“以亲亲为大”;于另一极则上溯至乾坤来构建其形上的根据(其曰“吾兹有取《易》之乾坤矣”)。乾坤在此不是作为元气本体,而是作为德性的本体。“仁”在近溪这里是“吾心生生之仁”。他以“生生”释“仁”:“仁是天地生生的大德,而吾人从父母一体而分,亦只是一团生意,而曰形色天性也。”(《近溪罗先生一贯编·论语上》)[5]其为德是生生之德,而这生生之德则来自《易》之《乾》《坤》:
《易》生生者也。夫乾之与坤,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
乾坤合德而莫非吾心生生之仁,贯彻乎人己之间至一而匪二,浑合而弗殊者也。(《近溪罗先生一贯编·论语下》)[5]
《易传》称乾为“乾元”坤为“坤元”,乾德是“刚健中正”,坤德是“厚德载物”,《系辞上》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坤合德,是为生生不息之源。在近溪,以易释仁转而实际上以“生生”释仁,“仁”既是本体性的又是功能性的,既是“知”(“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又是“能”(“坤以简能”),产生一切又主宰着一切,乾坤的创生的功能成为仁的功能,仁体借助《易》成为“既存有又活动”的生命本体,把道德本体化,上通天命、天道,下贯人心、人性,“乾坤混沌贯通一团而曰天命之性”(《近溪子集·射》)[4]。另一方面,他又以仁对“易”进行互诠,把本体道德化:“乾知大始始即元也,元则的确是善矣。”(《会语续录》卷下)[4]生生之仁落到个体成为他心中的“生生大德”,化为本能的爱人仁人的良知良能,天道即是人道,天命即是人心、人性。这样,在宋儒那里打通的天道、性命,通过“易”理的统摄而更为圆融透彻。因此,近溪说,把握仁体须借助“易”,学“易”须通“乾坤”二卦:
《易》所以求仁也。盖非易无以见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谓易,……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浑融透彻,只是一团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近溪罗先生一贯编·论语下》)[5]
大抵学易先须乾坤二卦识得明尽。盖乾以始坤,坤以终乾,乾之始处未尝无坤,坤之终时未必非乾,二者原合体而成者也。(《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易》)[5]
四、从“太极”“乾坤”论本体工夫
近溪从“乾”“坤”上溯论及“太极”,他否定“太极—阴阳—四象—八卦—万物”的宇宙论把“太极”看作宇宙万物之源的观念,抛弃了对太极的宇宙生成论的解释,他说:“易有太极,是夫子赞易之辞,非易之外又有个太极悬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无极而太极,又以赞太极之辞,亦非太极之外又有个无极悬在空中也。”(《近溪子集·礼》)[4]“太极”一语只是对“易”的“赞辞”,源自伏羲观天察地,取诸身诸物,最终悟得天地人物“浑作个圆团团光灿灿的东西,描不成,写不就,信手秃点一点,元也无名、也无字,后来却只得叫他做乾画,叫他做太极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近溪子集·射》)[4]如果说宇宙论用顺的方法把“太极”放到万有之源(元)的位置,那么近溪则是相反,用逆证的方法,从实存的天地人中“会得”“太极”,因此这“太极”不在万物之先、之上、之外,而就在万物之中。所以他又说:
易何以便谓之太极也耶?曰:窃意此是吾夫子极深之见极妙之语也。盖自伏羲周文三圣立画显象之后,世之学者观看便谓太虚中实,实有乾坤并陈,又实有八卦分列,其支离琐碎宁不重为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极之所生化,盖卦象虽多,均成个混沌东西也,若人于此参透,则六十四卦原无卦,三百八十四爻原无爻。……伏羲自无画而化有画,自一画而化千画,夫子将千画而化一画,又将有画而化无画也。(《近溪子集·礼》)[4]
在他看来,时人对“易”偏于言“实”,实有乾坤,实有八卦,这样就走向支离,使太极、道体的有无、动静、显微不能相通。所谓伏羲一画,乃近溪当年学易于胡生所受点化处,近溪于此悟得此一画是“有”而又“无”,说其“有”是有此画,有“太极”有“乾坤”,此“有”意为实;说其“无”是此画本“无名无字”,“描不成写不就”,无法放入到现有的知识系统中去(“无名”),也不能以求知的方法达到,它是贯通天地人的一个“混沌”(无名之名)。他以这种“遮诠”的方式表达了“太极”对万物既内在又超越的关系。近溪认为,知得“太极”“乾坤”,就可明有无、动静、显微相通,无碍无滞,以此可观道体是“实实地有这个道体,安得谓无,乃间亦言无者,则是叹羡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圆融了无滞着焉耳,非谓可以有无而分剖之也。”(《近溪罗先生一贯编·中庸》)[5]道体之“神明不测”“显微无间”也由此而知:
盖吾人为学云是学圣,圣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测者也,故明可测则不神,明不神则难通,谓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个,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虽乾坤亦是此个知字。(《近溪罗先生一贯编·孟子下》)[5]
从本体的虚灵神妙、显微无间,近溪进而论证心学的基本命题“心外无性”、“心外无命”:
惟以乾知太始而独得乎天地人之所以为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虚而未见乎气,至神而微妙其灵彻天彻地,贯古贯今,要皆一知以显发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显发也,而心之外无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无命矣。……命,天命也,生化无方,而性天性也,终焉神明不测,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易》)[5]
近溪认为,乾坤之理既是“至有”又是“至无”,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与《中庸》“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之理相合,这样一个本体,就是阳明所言“无善无恶心之本”,是“至善”:
性之为性乃乾坤神理,无善无不善,无不善亦无善,所谓上天之载,声臭俱泯而为善之至也。
夫惟不见不闻而寂然不动,是以能为天下至无;夫惟体物不遗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为天下至有。为天下至无,则岂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为天下至有,则岂惟善其所能为,即不善亦何所不能为也?(《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易》)[5]
近溪从对太极-乾坤本体把握引申到工夫论,提出“易言修辞立诚是学者工夫第一”(《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易》)[5],把工夫看作是通过把握“易”(易理)而得到“修辞立诚”。在此他论及如下几层:
(1)即本体即工夫
近溪说:
今果会得此心浑然是一太极,充天塞地更无一毫声嗅,彻表彻里亦无一毫景象,则欲得之心泯而外无所入,欲见之心息而内无所出,如此则其体自然纯粹以精,其功自然洁净而微,其人亦自然诚神而几以优入圣域,莫可测识也已。(《近溪子集·礼》)[4]
能悟到心与太极浑然一体,则心体就是道体,打通了天人、物我、内外,同时也就完成了全部的工夫,即本体即工夫。本体是“浑然一团”的,故工夫决不能有支离,只能是对本体的整个的体悟。若要分工夫为“渐”“顿”,则近溪的工夫论只能是“顿”教。
(2)“不动心”
近溪认为孟子所说的不动心(“不动的工夫”)是从“孔子之易”,从“乾坤”“翻出”的,因为“人生而直,乾动而直。人生而直,则生生不已,便无害其为直矣;乾动而直,则乾乾不息,亦无害其为直矣,岂又不从心体不动描出一个分毫不动的工夫,增也增不得,减也减不得。不增便不助,不减便不忘,浑是一团妙理又浑是一团生机,而叫做集义所生。孟子之所以为心,孟子之心所以为不动,是如此入头,是如此着落,是如此以愿学孔子,则将说是不动的未尝不动,将说是动而未尝或动。”(《近溪罗先生一贯编·孟子上》)[5]在心学一系,孟子所言“不动心”,“勿忘勿助”一直是主要的工夫,其理论根据是良知先天、内在于人心,不假外求,故工夫在于不受外物所动,在于“养心”。前人以独断论的方式肯定心之“知能”之为“良”,近溪在此则从本体直贯而下,讲“直养无害”是因为乾动而直,其直在生生不息,而人同样“生而直”,其直在于生命自身不断复制、传承的“生生不已”,乾之生生之理与人之生生相贯通、相包含,在理而言是“一团”,在生而言也是“一团”,因此,心的作为便必然是不作为,任何作为都只能是对“生生”的干扰,“不助不忘”,保持“不动心”就是最恰当的工夫。
(3)“自然是工夫之最先处”
近溪说,易理中“易首乾坤而乾则又统乎坤也”,对此理,“易辞原明白顺畅”,但世间的解释者反未能顺之而理会,使德不能顺,不识得性体,“而工夫不识性体,性体若昧自然,总是无头学问。细细推来,则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处,而工夫却是自然之以后处”;“故某尝云为学必须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学问有成者万万无是理矣。”(《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易》)[5]
由乾坤引申到工夫的“自然”,其根据在于乾坤合德就是生生之仁、天命之性,也就是心体,故只须顺着乾坤之理的“自然”延伸、扩展,即可识得“性体”、“心体”本来自然,工夫也应自然:“盖说做工夫是指道体之精详处,说做道体是指工夫之贯彻处,道体既人人具足,则岂有全无工夫之人?道体既时时不离,则岂有全无工夫之时?”(《近溪子集·书》)[4]若有意于工夫或者某种工夫,则是落于向外、落于意念、落于有所执。但意念本身并非心体,故近溪对“持敬”“静养”的工夫论进行批评,他多次以“童子捧茶一般”来说明其理想的工夫是“心也无个中,也无个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会语续录》卷下)[4],是“将圣贤学问只当家常茶饭,实实受用”。以自然为工夫,也就是达到“无工夫”,才能真正会得道体。
五、余论
牟宗三先生认为,“宋明儒以六百之长期,费如许之言词,其所宗者只不过是《论》、《孟》、《中庸》、《易传》与《大学》而已。”(第31页)[6]“宋明儒之将《论》、《孟》、《中庸》、《易传》通而一之,其主要目的在豁醒先秦儒家之‘成德之教,是要说明吾人之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第32页)[6]而依对上五书的所依托不同,牟先生把宋明理学分为三大系:其一,“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以《论》、《孟》为主。”是为胡五峰、刘蕺山系;其二,“以《论》、《孟》摄《易》、《庸》而以《论》、《孟》为主者。”是为象山、阳明系;其三,“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是为伊川、朱子系。(第42页)[6]罗汝芳为泰州学派传人,当归于阳明一系无异。其门人杨起元概括其一生“十有五而定志于洵水,二十有六而正学于山农,三十有四而悟易于胡生,四十有六而证道于泰山丈人,七十而问心于武夷先生。”(《近溪子附集》卷二)[7]另一说“罗汝芳师事颜均,谈理学;师事胡清虚(宗正),谈烧炼,采取飞升;师僧玄觉,谈因果,单传直指。”(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8]可见近溪所受又非完全陆王。黄宗羲言:“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8]近溪子为谦谦君子,主张“喜怒哀乐总是一团和气,天地无不感通,民物无不归顺,相安相养而太和”(《近溪罗先生一贯编·中庸》)[5],并非黄氏所描写的“狂者”。就学理而论,近溪学问宗旨为“赤子之心”、“不虑不学”,明显属孟子学而上接陆、王,但因其于《易》特有所悟(注:“善治易者叹曰:‘甚哉,先生之深于言易也!”(《近溪子集·数》)),以《易》统《学》、《庸》,又直贯《论》、《孟》,以易理打通性体、心体,使天命、仁体、心体融通于“乾坤”之中,以此对王学作调适,又近于牟氏所论胡五峰、刘蕺山系之路向。或许,这是阳明之学传至泰州之后“渐失其传”的另一表现。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周汝登.圣学宗传[A].罗汝芳.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近溪子附集[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0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3]刘元卿.诸儒学案传[A].罗汝芳.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近溪子附集[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0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4]罗汝芳. 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130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5]熊傧,钱启忠.近溪罗先生一贯编[M].四库全书存目:子部第86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杨起元.明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明德夫子罗近溪先生墓志铭[A].罗汝芳.耿中丞杨太史批点近溪罗子全集二十四卷·近溪子附集[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0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8]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李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