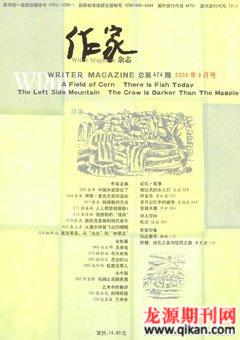人人都爱钱德勒?
郭春林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为这篇文字起头,脑子里总是会涌出这些天从电视和各种各样的媒体中看到的东西。我知道“百无一用是书生”,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候,更是禁不住对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生出怀疑,连浑身上下的无力感都无力遣散,即便在读了大江健三郎的《面对巨大灾害,文学何为?》之后,无力感依然如故。我相信,和我有同样感觉的人绝不在少数,也并非只限于文学专业的人才有。可日子总还要过下去,事情是否真如灾难时刻所感受到的那样,一时尚无法确定,因为灾难其实并没有结束,留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文学也许总有出场的时候,总有派上用处的地方。况且,我不能食言,答应了的事情就得做,虽然是在5月12日之前。
既然是关于侦探小说的话题,也就很自然地想起被誉为侦探小说始祖的爱伦·坡。1844年,爱伦·坡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认为人类的努力对人类本身不会有明显效果。与6000年前相比,现在人类只是更活跃——但没有更幸福——没有更聪明。”面对地震带来的灾难,这样的感觉就更其强烈。但爱伦·坡所说显然不是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不幸的是爱伦·坡恰恰生活在一个普遍认为通过人类的努力一定可以获得更大幸福的美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相信进步的发展主义深入人心的世界中。爱伦·坡去世几年后,法国的波德莱尔在与别人论战的文字中,捍卫他心中的英雄,以他华丽而又雄辩的语言,分析并向世人描述了一个优雅、深刻却命途多乖舛的爱伦·坡形象,并进一步引申、发挥了爱伦·坡上述的见解:“进步把快乐变得多么美妙,就把痛苦变得多么完善。”而且,他甚至将爱伦·坡的死因部分地归咎在这个神话般的新大陆,“在那里,时间和金钱的价值是如此之大!物质的活动被夸大到举国为之风靡的程度,在思想中为非人间的东西只留下很小的地盘。……爱伦·坡在那里是个孤独得出奇的人。”当然,还有“舆论的专制”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暴政,笨蛋的暴政”。
波德莱尔说爱伦·坡“天赋过人,无所不能”,他开创了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文学类型的先河。据《爱伦·坡精品集》的译者曹明伦称,在坡生活的时代,还没有“侦探小说”(detectivestories)这个语词,“坡自己将这类作品称为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其“初衷只是想证明自己具有分析推理的天赋,而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小说类别”。可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世间实在太多这样的事情。既为鼻祖,后世自然受其影响很多,且很大。据说,福尔摩斯这个职业侦探就脱胎于爱伦·坡笔下的业余侦探迪潘,而其塑造者柯南道尔就说过这样一番话:“一名侦探小说家只能沿这条不宽的主道而行,所以他时时都会发现前方有坡的脚印。如果他偶尔能设法偏离主道,独辟蹊径,那他就可以感到心满意足了。”(转引自曹明伦译《爱伦·坡精品集·译者前言》)坡用三四篇小说在向世人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天才的诗才之外的才能后,又重新返回了他热爱的诗歌之园,再也没有回来。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这几篇侦探小说实际上是坡横溢的才华随意滴落下来的几颗珍珠,而后来逐渐“生长”为一种文类的侦探小说已经是另一种东西了。无论是就创作者而言,还是就阅读的体会来说,其中所受到的现代性的引导和影响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雷蒙德-钱德勒或许就是这一引导和影响的产物。
某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名为《午夜文库》的丛书,收在该文库中的钱德勒卷的勒口上有这样的文字:“遴选160年侦探小说史上最纯粹、最经典、最具智慧的作品”,旨在“让阅读成为娱乐;让阅读成为冒险;让阅读成为智能训练”。已经出版的有劳伦斯·布洛克,迈克尔·康奈利、雷蒙德·钱德勒和马伊·舍瓦尔与佩尔·瓦勒,前三人均是美国人,第四个是瑞典人,即将出版的两人也都是美国的,杰夫里·迪弗和艾勒里-奎因。我没有对侦探小说史做过什么研究,就目前的这个阵容而言,美国作者占了绝大多数,或许也能说明点什么。就因为侦探小说的鼻祖是他们的先祖,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美国成为侦探小说的生产和阅读(消费)大国?其实英国、日本似乎也都很发达,为什么没有选是一方面,但我要问的是譬如中国,干脆地说,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却都不怎么样?侦探小说之进入中国也已经百多年了,中国侦探小说之委顿不前难道与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相关?
还是让我们回到钱德勒。阿城在钱德勒卷的总序《关于钱德勒》中说:“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意思是说,钱德勒作为作者的生平等等,也像一个侦探故事一样,不该预先介绍给读者,但偏偏这篇《关于钱德勒》却又放在了卷首,言下颇为有悖那个“道德约定”而不安。可是阿城偏有这样的本领,笔锋一转,说:“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也就是说,“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阿城当然没有忘记对至今仍不知道钱德勒其人其书的读者揶揄一下:“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不知者不为罪。知道错了就改也还有救。何况阿城在文字中为我这样的读者还开列了一串大名鼎鼎的钱德勒的“粉丝”,加缪、奥登、奥尼尔,还有村上春树。如此说来,这个“不知”也就真的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了。于是,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抓紧读,赶紧读,唯恐贻笑大方。
可是,读了三部(《重播》《再见,吾爱》和《漫长的告别》)后,再也提不起精神来拿起那第四本。除了《漫长的告别》,其他两种实在乏善可陈。是我的眼光太差,文学修养太低,还是自己太理智,要不就是太弱智了?总之,我实在找不出阿城说的那个动力,“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甚至被村上春树定义为“准经典小说”,且获得过爱伦·坡奖的《漫长的告别》,我也不想再读第二遍,即使阿城特别强调,爱伦·坡奖是“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奖项。
有意思的是,钱德勒的死因倒有几分像爱伦·坡,都是与酗酒有关。波德莱尔是这样解释诗人(爱伦·坡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位诗人,或首先是一位诗人)的酗酒的:“酗酒既可成为刺激,也可成为休息。……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爱伦·坡的酗酒是一种帮助回忆的手段,是一种工作的方法。这是一种有效而致命的方法,但适合于他的富于情感的天性。”我不知道钱德勒因什么而酗酒,我也不知道阿城先生知不知道,或许可以运用推理的方法来揣度。
因为,只要不是天生的酒鬼,总是有某种原因将他引上酗酒的路,而对一个作家或诗人而言,探寻这一点无疑是理解他的重要路径。
检讨一下自己一定会有收获,就如同中国的古话所说:开卷有益。为什么那么多名家、大家喜欢的钱德勒,我却不能保持兴趣,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完这几本?
就侦探小说而言,正如阿城所说,要点在天机不可泄露。所谓天机,也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尾或结局。但仔细地说,所谓结尾或结局,还是有所区别。既云侦探,自然是刑事案件,多为凶杀等恶性案件,因此,最大的天机就是凶手是谁,也就是案件破解的最终答案。可天机绝不是仅此而已,它实际上还包含了事件的发生、发展,特别是侦探破解的过程,否则我们就只须查找到有关部分。这就像伪球迷只关心比赛的最后比分,最多了解一下进球的球员是谁,而没有耐心看完一场90分钟的比赛一样,可真正激动人心的,揪住你,使你始终坐在电视机前,合不得离开的是那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侦探小说来说就是它的情节。所以,侦探小说要想赢得读者,必须依赖充满变数的情节,用我们习见的词语说,就是“离奇曲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说实话,要做到这一点委实不那么容易,而钱德勒确乎是做到了的。然而,仅有这一点显然还不够。离奇曲折云云是一个抽象的描述,落实在每一部作品中就得是各不相同的情节、人物、心理、事件、性格等等,而最关键的恐怕还在不模式化上面。模式化的结果是可以将不同的作品拆解开,然后依一定的规则重新组装,而就阅读言,一个必然的感受便是似曾相识。钱德勒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也像希区柯克的电影给我们的感觉相似,虽然钱德勒曾经批评希区柯克的电影不像真的,遗憾的是,他的小说同样不像真的。
先就故事及其结构来说。就这三部小说而言,起首似乎也都有点奇崛,是要吸引人继续读下去的招式,其实也是整个事件(案件)的开始。随着案情的向前发展,人物越来越多,事件也似乎越来越复杂、多绪。而且,钱德勒多半会引出另一个看似并无多少关联的案件。于是,两个案件仿佛两根绳子,交织着、缠拧着向前延伸,然后又合为一股,继续向前。经过马洛不懈的努力,最终真相大白。《漫长的告别》是最明显,也是最充分地体现这一特点的作品。小说的开头叙述马洛似乎有点见义勇为意味地帮助了酒鬼伦诺克斯,很快两人凭感觉成为好朋友,可不久伦诺克斯就死了,马洛被牵连入狱,并挨了警察的揍。警察当然要揍他,因为他是私家侦探,是与他们抢活儿干的人。更要紧的是马洛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私家侦探,而警察局却成了合法的黑帮(这其实也是好莱坞电影的老套路)。马洛在伦诺克斯之死的调查中遇到了少有的麻烦和障碍。要生存的他正准备放弃,另一桩生意送上门来。可看起来它似乎与伦诺克斯案没有丝毫的联系,乃是一个出版商请他看守一个畅销书作家的任务。钱德勒当然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将两个毫不相干的事件搅在一起。随着情节的向前推进,其间的明明暗暗的关联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也就是戏剧性的增多,最终自然是水落石出。其中的复杂性,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人物之间关系的错杂无疑是其成功的关键之处,也是钱德勒这一部作品最出色的表现。而另外两部则因错杂关系的减少,不仅显得逊色,甚至使人读到半中间就可以隐隐约约地猜出凶手来。毫无疑问,出色的侦探小说是不能这样的。
倘就人物来看,阿城和很多读过钱德勒小说的人都说,钱德勒以系列小说的形式,成功地创造了马洛这样一个“硬汉”式的侦探。诚然,马洛是一个硬汉,可文学作品中的硬汉多矣,如果马洛只是以侦探这一身份演绎海明威或者好莱坞电影中的西部牛仔等硬汉形象,那么文学形象所谓的独特性也就根本无从说起。在目力犀利、眼光敏锐等职业素质(特点)之外,马洛还有正义感、英勇、不为利益所动(也许不包括女人,其实这也是好莱坞的套路,因为“真正的英雄”都该有缺点,原则性的缺点显然不能有,脾气暴躁等小节之外,最无伤大雅的也就是对美女的兴趣了,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真实性就更值得怀疑了)以及幽默等性格特征,不幸的是这些性格特征实在是在很多很多文艺作品中的形象身上都能够找到。
既然人人都爱读钱德勒,依照柯南道尔的说法,他的小说中就该有一些不同于爱伦-坡的地方。不同自然有,显然钱德勒的节奏更快,小说的叙述就好似好莱坞快节奏的电影,一环套一环地快速向前推进,叙事的主要方式乃是简洁的叙述和人物对话,间以马洛的心理。可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些地方少了爱伦·坡优雅的节奏和细致的描述,以及似乎有些繁复却极其缜密的推理。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钱德勒的侦探小说才受到了现代人的欢迎。因为我们既要时间,也要刺激,我们已经来不及考虑优雅,也没有精力和心力去理会那些细致和缜密。有意味的是钱德勒模式化的侦探小说还提供了一个美国想象的图景。可这样的美国想象恰恰与一百多年前波德莱尔对于美国的批判形成了一个遥远的呼应。
我固执地以为,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当然,所谓有益于世道人心并非指教化,倘真的能做到该文库所说的“娱乐”、“冒险”和“智慧训练”,也就已经达到了对世道人心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回顾一下近代中国引进侦探小说时的情形或许不无裨益。
作为文类的价值是其一方面,因为侦探小说普遍被认为是中国所无,而西洋特别发达的一种小说形式,所以,在“咸与维新”的时代里,译介之风大盛。最早“翻译”侦探小说的当然还是那个林琴南。1899年,林琴南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华生包探案》,并且将这两个浑然不搭界的小说类型合刊出版。小说史家陈平原因此说:“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西洋的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可以鉴赏,但不必模仿,中国有的是此类佳作(谁说《红楼梦》不是言情小说的佳品,《金瓶梅》不是社会小说的杰作?),唯有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为我所无,需要积极引进。‘新小说理论家花了很大力气介绍这三种文学类型,不只是划定表现范围,更注意到了各自独特的表现技巧,如强调政治小说的‘以政论人小说、侦探小说的‘一起之突兀,以及科学小说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个不太被一般读者所忽视的是,当时译介西洋文艺作品,无论是哪种类型,都要特别强调其政治意义和启蒙价值。1904年,周桂生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牟言》(按:“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即福尔摩斯探案)中就说:“吾国视泰西,风俗既殊,嗜好亦别。故小说家之趋向,迥不相侔。尤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
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人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用能迭破奇案,诡秘神妙,不可思议,偶有记载,传诵一时,侦探小说即缘之而起。”刊于1905年《新小说》杂志的《小说丛话》有署名“定一”的一篇文字,其中说:“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且侦探之资格,亦颇难造成。有作侦探之学问,有作侦探之性质,有作侦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故泰西人靡不重视之。”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语是后来成了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实践者的刘半农(署名半侬)先生所写,他说:“彼柯南道尔抱启发民智之宏愿,欲使侦探界上大放光明。”而“侦探事业”“其变也,如风云之莫测;其大也,足比四宇之辽夏;其细也,足穿秋毫而过”,可是,这样的学问又不能“强编之为教科书”。怎么办?刘半农说:“势有不能,而此种书籍,又为社会与世界之所必需,决不可以‘不能二字了之,则唯有改变其法,化死为活。以至精微至玄妙之学理,托诸小说家言,俾心有所得,即笔而出之,于是乎美具难并,启发民智之宏愿乃得大伸。此是柯南道尔最初宗旨之所在,不得不首先提出,以为读者告也。”
自然,并非所有“新小说”的译介者都只在教育、启蒙的立场上来理解侦探小说。林琴南在翻译了《华生包探案》后又曾续译过另外一篇,取名《神枢鬼藏录》,后来觉得“命名不切”,遂更名为《奇案开场》。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序》中,林琴南就说:“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始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寥寥仅三万余字,借之破睡亦佳。”这当然说的是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属于技术层面,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最后那几个字:借之破睡亦佳。显然所指乃小说的娱乐价值。一定程度上说,来自西洋的侦探小说最初被赋予的启蒙价值逐渐被娱乐价值所取代,侦探小说和其他言情、科幻类小说逐渐成为边缘化的文类,最终彻底沦为通俗文艺,这其中所包含的意味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
回到钱德勒。钱德勒以“梦工场”的所在地好莱坞为其系列侦探小说的主要发生地,或许在满足读者好奇心之外也寄托了他对好莱坞和美国的批判态度,即使只是蜻蜒点水,即使只是一种类型化的呈现。他在作品中所展示的美国社会和现实,以及私家侦探的身份同样补偿了读者对体制的不满,甚至愤懑之情。然而,像马洛这样的“浪漫派”(马洛自云)显然是将希望寄托在良知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之上,也因此使钱德勒的创作最终堕入模式化的陷阱,而其作品也就只是林纾所谓的“破睡”佳品而已。
所以,我说,如果这样的阅读唯一的功能只是让我们遗忘,包括遗忘灾难,那么,它的价值实在有限得很。
2008年6月2日凌晨于同济新邨
责任编校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