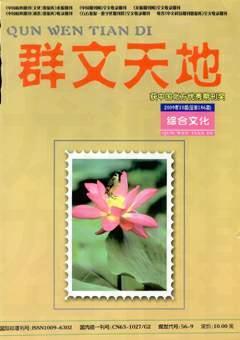青海眉户六十年
石 永
眉户戏,青海地方剧种之一。广泛流行在西宁地区及海东诸县的民间,牧区州县的汉族聚居地区也有流布。约在清代咸、同年间陕西曲子西延,传入青海。先在西宁地区流行,后来逐步普及到西宁周边诸县。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受当地语音、民间音乐、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逐步发生变异,具有了青海地方特色而成为青海眉户。它不但在唱腔曲牌上与陕西眉户具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演出的剧目内容上也有所不同。青海眉户中的许多唱腔曲牌除了少数几支外,其余的在陕西眉户中找不到相应的曲牌,就是弦乐曲牌在两者之间也少有共同之处。在总体的曲牌构成上青海眉户有其自己的体系,两者相去甚远。独有的眉户音乐,表现出浓浓的地方风味,为青海民间广大群众所喜爱。
眉户戏从传统剧目上看,它擅演三小角色(小生、小旦、小丑)被称之为三小戏,而秦腔则称之为大戏。
初具型态先天不足
眉户戏从传入青海的早期到逐步形成为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剧种,以至发展到今天的繁荣局面,大约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它在传入我省的初期,完全照搬陕西眉户的原样,其剧目内容和语言都是陕西眉户。《张连卖布》、《花亭相会》、《李彦贵卖水》、《王妈问病》等都按传播者的排练并演出,或从别处观摩学得都不改陕西味。人们认为只要按陕西口音演唱,才是戏,才够味。
演员化妆因陋就简,非常简单。穿一件褂子,戴一顶小礼帽或小帽儿,手持折扇,就是小生;穿上女人们的花裤子和花袄儿,头上包一块羊肚儿手巾,就是非常漂亮的小旦。须知那时羊肚儿手巾在农村是非常稀罕的奢侈品。戴一顶破草帽,腰勒一条腰带,鼻梁上画一豆腐块,小丑是也。至于脚上穿什么呢,大体上附合人物的身份即可。
乐队更加简单,小鼓、小钗、小锣。此小三件即为乐队武场;三弦、板胡、竹笛即为乐队文场。板胡往往是自己动手制作的纸壳板胡,扬琴很少有。有能工巧匠偶而为之简易的两排码的小扬琴出现在某个眉户戏班,那便是非常阔气的乐队了。
眉户戏没有严格的程式表演。演员的简单叫板之后,没有板头击乐,也没有前奏过板。因之乐队伴奏更多的是随腔奏出主旋律;击乐则用快慢不同的连续击敲送演员上下场和走圆场而已。
至于演出场地就更是因地制宜了,有舞台则更好,如无舞台场院平台、庭院阶前、堂屋檐下皆可作为演出场地。当年农村人少,几十人、更多时只有十多人,甚至一条长条板凳能坐五六人就是全部观众了,所谓的板凳戏者,即指此也。那时民间文化生活极度贫乏,逢年过节有爱好者敲锣鸣鼓,弹唱演出,人们倾巢出动观看,就那样简单的小小眉户戏,唱得人们津津有味,让群众大饱眼福,乐此不疲。
阳光雨露催其成长
历史的脚步跨入了1949年的秋天,青海迎来了解放。星转斗移,百废待兴。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眉户戏迎来了发展的新高潮。民间戏曲工作者心情舒畅,工作积极,各地业余剧团恢复活动或创建了新的眉户剧团、文艺宣传队、演出队如雨后春笋。在老一辈眉户戏演员的带动下,年轻一代的业余演员成批涌现,有的剧团还有青年女同志参加。那时各地都有一批有名气的眉户演员,如大通县黄家寨的杜占福(旦角)、清平乡台台村的童维生(丑角),湟中县西堡乡佐署村的甄治邦(小生)、堡子村的甘得荣等。还有乐都、平安等县的剧团都有自己的演员队伍。随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进一步推行和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基层业余剧团不但传统折子戏演出甚为红火,而且一些宣传政策和配合中心工作的新编小戏陆续演出,如湟中汉东乡下扎扎剧团演出的《小保管上任》、大通毛家寨剧团演出的《算细帐》,还有一些剧团移植来的新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这些新编小戏的陆续上演,既丰富了眉户戏的剧目体系,又给眉户戏的发展方向带来了曙光,使青海眉户戏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眉户戏的基础设施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各地都建起了露天舞台,也配备了新的乐器,新式的板胡代替了纸壳板胡,又有了新的二胡、三弦等乐器。又购置了铜器,伴奏也逐步丰富。新编现代戏的出现,彻底解决了演员的服装问题,既降低了剧团演出的成本,又新颖时兴,贴近群众生活。有不少剧团的节目在省、县、乡的汇演中频频获奖。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眉户戏呈现出迅速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文革动乱,青海眉户戏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遭受了厄运,演员被批判,剧目被指为四旧而扫除了。
改革开放硕果累累
青海眉户戏的发展繁荣和提高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文艺界迅速恢复了正常的活动。青海眉户戏焕发了艺术的青春,步入了创新发展和进一步提高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
首先,各地民间业余剧团迅速恢复演出,老、中、青三代人团结进取,努力工作。很快在乐队、演员、剧目、唱腔、场地等多个环节上有了较大的改善,一批新的眉户现代戏应运而生。从1979年10月建国30周年文艺献礼演出上看,眉户戏大展风采,获得好评并获得奖项。乐都代表队演出的《一篮子鸡蛋》、湟中代表队演出的《一担水》,以小型、清新、轻便的姿态令人刮目相看,它在大演现代戏的路子上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之后,连续几年省、地、县等各级文化事业单位对眉户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创新和提高工作。以举办讲习班的方式,在培养演员及编导人才,丰富及规范唱腔,提高乐队的演奏艺术水平、强化程式、眉户戏的音乐设计手法等诸多环节上进行创新尝试和培训,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青海眉户戏原先没有固定的板头击乐,也没有前奏过板,只有简单的等板,唱腔也不多,又不规范,也没有过场行弦音乐。就是说它的演唱和伴奏没有进入固定的程式圈子,随意性很大,这大大影响了眉户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因之,讲习班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解决眉户戏的程式化和规范化的问题。它的音乐表现的层次应该是叫板,板头击乐、前奏过板和规范的唱腔以及结尾。这一系列的环节是一根链条上串起来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层层迭进的。讲习班辅导干部借鉴秦腔的板头,结合眉户戏的音乐特点,对上述各环节,在实验演出的剧目中进行了精心设计,并反复演练,效果很好。经过几年的多次实验演出,那些简练的、有艺术特点的好记易背的板头击乐和前奏过板以及过场行弦都为各剧团乐队和演员所接受,并普遍应用。
创新工作的重点是唱腔设计。对于各主要角色的主要唱段尤其要精心设计。按人物的性格特点、心态和情绪,结合唱词的内容,选择适合的唱腔曲牌,用戏曲艺术的手法对唱腔曲牌进行艺术处理。对主题乐句或进行变化,或只选用核心部分;对曲牌可以掐头去尾,也可以中间穿插过场音乐,更可以延伸或强调旋律主题,适当加用击乐和行弦,待过场走完再结束唱腔采用结束句。如果原封不动地唱完某个曲牌,再伴原尾部过门,那就不是戏曲的手法,而是曲艺模式了。如在《打碗计》里孙奶的悲怆唱段选用大悲动人的《菊悲》,曲牌原本是上下句连唱,中间没有过门,为了强化无限悲愤的心情,唱完上句“北风吹,刺骨寒,雪花扑面”之后加奏长段过门,音域拓宽,高音衬托,调式主音拖长尾音,唱腔进入高潮。第二句“儿不孝,媳不贤活受熬煎”唱完后再次升华情绪,渲染悲愤,用回旋下行的旋律作为尾部过门。不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深受感染,饮泣泪下。
《小两口赶路》是生活小戏,情绪欢快。女主角阿香用小舞步出场。为了表达此种情绪,开场锣鼓加开场音乐送演员上场,结束句紧接着演唱《花音剪靛》“春风吹,百花开,小俩口赶路进城来,买了一台电视机”之后穿插设计过场击乐和行弦,演员心花怒放像雀跃,像蝴蝶翻飞,在欢快的过场音乐中以快步舞蹈动作把喜悦之情彻底表达出来,行弦完毕亮相,再接唱剩余唱词“……一家大小乐开怀。”这样的处理既让演员充分抒发情怀,又让观众尽情领略角色的欢快情绪,既不同于越弦,又强化了戏曲艺术效果。
眉户戏的音乐是曲牌联缀体,它不像秦腔那样的板腔体,没有花音苦音之分,这大大限制了剧中人物多变情绪的表达和艺术感染力度的进一步发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并强化眉户音乐的艺术感染力,我们对一些常用曲牌设计了相对应的花音和苦音的曲牌。如《花音剪靛花》、《慢连相》、《花音扭丝》、《花音催字》、《花音琵琶》、《花音东调》、《花音五更》等八支比较欢快的新编曲牌,这些曲牌与相对应的原有曲牌情绪迥异,对比强烈,表现力强。在讲习班多次设计采用,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实践证明这些新编曲牌的出现既丰富了眉户音乐,又提高了其音乐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基层剧团和演员的欢迎,并广泛采用。
眉户戏除演传统小戏之外,尤善于表演现实题材的新编剧目。在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举办的眉户讲习会上实验演出的皆为眉户现代戏。有隔壁两家结冤而又变成亲家的《冤家亲》,有不孝儿子媳妇恶待亲娘而又被新来的孙媳妇教育得到彻底转变的《打碗计》,有儿女支持老人再婚的《果园会》,还有夫妻二人在买回电视机的路上互相逗趣的《小两口赶路》等,一批批新编现代戏不但丰富了眉户戏的剧目内容,而且在眉户戏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们有各自的主题音乐形象和艺术风格,互不相同。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在音乐设计上又根据眉户唱腔音乐的基本特点,采用戏曲音乐的手法进行设计和改写的唱腔,演员易唱、易记,学起来容易,所以在实践上又是可行的。
一般地认为眉户音乐缺少阳刚之气,不便表演大戏中大净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我们大胆地进行了设计尝试。对传统折子戏《三对面》中包公的唱段用《岗调》和《紧赋》等曲牌表现包公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性格,演出后大获成功,成为眉户戏创新的精典作品,否定了眉户不能演大净的误解。
巩固成果遍地开花
综上所述,所有这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使青海眉户戏整体艺术表演水平迅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些各个环节上的具体做法为基层眉户剧团所接受并广泛采用。如今不少农村眉户剧团的演职员经过省、县文化部门的培训之后,其表演技艺水平迅速上升,他们可以按省、县讲习班学到的戏曲知识设计唱腔,用新的手法排戏,并用较为整齐的乐队伴奏,使基层眉户戏的整体面貌更上层楼,大为改观。如乐都县汉庄眉户剧团演出的《打碗计》、《抢公公》,大通县毛家寨眉户戏剧团演出的《冤家亲》、《农家趣事》,湟中县民间戏剧曲艺协会直属队演出的《果园会》等等,有的按讲习班的原型设计演出,有的自己设计音乐唱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如今,青海眉户戏经过创新、培训、提高等一系列的举措,它的总体面貌和艺术上的成熟与六十年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剧种了。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在当今“非遗”保护的社会大文化背景下一定会更加兴旺繁荣。愿眉户艺术之树常青。
(作者简介:石永,青海省文化馆退休干部,江河源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