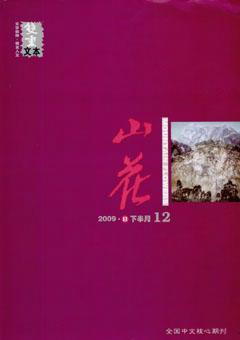老井
马 军
漆黑如墨的夜晚,万簌俱寂的子时,一个瘦小的僧人“嗖”地蹿出庙墙,羽毛一般悄悄飘到一口井旁,在井台上立定马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对着井内奋力击打,每打一下,井里的水就要蹿出老高。这个多年来常常出现在我梦中的场景不是武侠小说或影视屏幕上的特写镜头,而是生长在我家乡的那块黄黄的土地以及那口平常的老井。
它位于后街当中,青砖砌就的井台,已被岁月的鞋底磨去了一小半,井口有一米宽,往下略呈扩大之势,井壁的砖缝间生满绿色的苔藓。井水幽幽的,静静的,有一股恍如黑洞一般的力量让人又畏又敬,就像我的那位乡邻大哥。
大哥就住在这口井的旁边。他经常在早晚间特有激情地摇着辘轳,来灌溉他当院里的小菜园。“吱呀!吱呀!”不紧不慢,一匝匝地摇着,一罐罐的井水便唱着笑着倾入他一个又一个的菜畦里。我特别爱听这种声音,觉得它就像一曲非常古老的歌谣,永远是那么舒缓、宁静,让人听了想睡上一觉。他家的院子,好像一个花山,绿的菜,黄的、红的、白的花,还有一条条鲜嫩滴汁的黄瓜,香气四溢的甜瓜,带着玫瑰红小花的豆角、丝瓜爬满他家的院子。我特别羡慕大哥的身板,我常常在心里边将其比拟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还羡慕大哥的匠心独运,那双巧手怎么就那么摆弄摆弄就把孙猴子的花果山请到了家中呢?我更羡慕大哥的运气,这口井仿佛就是专为伺候大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大哥不光菜园侍弄得好,故事也说得好。他的嘴巴只要一张开,就像河流打开了闸门,澎湃汹涌,曲折跌宕,缠绵悱恻,滔滔不绝。让我或兴奋,或惊讶,或神往,或恐惧,一条闪亮的丝线紧紧地牵着我的心,在故事的海洋里遨游。
他说起这口老井的掌故来,就如同亲历一般。
清朝末年,村内大庙中住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高僧,功夫十分了得。每天刷牙时要到房柁上去刷,那里有一个大钉子,往上轻轻一纵身,就将下颏挂在钉子上,天天如此。他更有一种秘不传人的功夫,叫做“百步神拳”。就是出击时,根本不用靠近人,一百步之内百发百中,敌手非死即伤。这个功夫就是在这口井处练成的。他看我惊异的样子,更是来了兴致。练这种功夫比较神秘,需要在每晚子时,独自一人悄悄来到井旁,对着井内用力冲拳一百下,练至七七四十九天,这当中,不能有任何一点声音打扰。在一次与访友比试武技时,双方约定,在一百步之距,各打对方三拳。他接受了三拳之后,安然无恙。待他将拳击出,势如狂风霹雳,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随之疯狂地扑向对方,访友仿佛瞬间看到了死亡的魔影,他可不想乖乖地变成肉饼,情急和恐惧之下,也就顾不得什么君子约定了,一个旱地拔葱,蹿起来一丈多高,躲过了致命的一击,可他背后的巨石影壁,却一下子被击得粉碎。我听了,嘴惊得半天没有合拢,我怎么也想不到,就这口普普通通的老井竟然会有这么深厚的积淀。
他还告诉我,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是影响过历史的古战场。唐朝初年名将罗成在此与敌手大战,多日不分胜负,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战马将地上的尘土都踏到天上去了。远远看去,人马全在黄沙的大雾中拼杀,这场战斗,时人皆谓“罗成大战黄沙雾”。我们的村子“黄沙务”因此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后来,罗成受困于唐朝李家兄弟的内斗,得不到支援,终于寡不敌众,丢盔卸甲,向北败退,这就是邻村“卸甲庄”的由来。罗成为避开敌人的追杀,只有带着余下的亲兵往西北处躲藏,遂有“躲各庄”之名。但敌兵不想放虎归山留下后患,遂穷追不舍。为彻底摆脱追兵,罗成本想骑马涉过村后的小河,向北退走,不想河水不深,但下边的淤泥却很致命,结果,人马俱陷其中,被随后赶到的敌兵乱箭射死在河中。这条河从此叫做“淤泥河”、也叫“箭杆河”。后来,由于河流改道,那块地方已变成了宅基,上面盖起了民房。而我家后面的小河,却仍然还是老河道。一次,河水干涸,一个乡邻去挖坑泥,竟挖出一把生了锈的宝剑,大家颇为惊奇,多人传看,有的竟说,这把剑有可能就是罗成丢下的。
我还知道了,这里曾经有这样一个人,性情古怪,跟谁也没有交往,但是却有奇技在身。倘若谁家的小孩有个头疼脑热,他上去摸摸脑袋,就没事了。或者,谁家的小孩被狗追咬受到了惊吓,晚上不睡,哭闹没完,他就领着到老井的边沿,不知默叨几句什么,孩子即刻就安静下来了。或者给点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吃下去后,孩子就好了。在他的手里,什么都可能是药,越是医院看不好的病,他就越有办法,他的办法也和他的人一样,古怪得很,有的甚至让你接受不了,张口骂他,然而他的修养好得很,任你怎么骂,也绝不生气,将你晾在一边,干自己的事去了。而当你饿极了,或是痛得没有办法了,只得眼一合,牙一咬,发着狠吃下去后,却发现,原来那么难缠的病魔已被一手抓走。之后,便是患者提上礼品,红着脸,去他家里一再地赔礼说好话。而他仍是不理不睬的样子,由于他从来不在乎收多少钱,因此,多少年后,人们仍然不时地念叨他。
“咱们这地儿所以出奇人,就是这井好。喝一口,倍儿甜。用它浇菜,菜好吃;馇粥,粥乎;沏茶,茶香。”
尽管这样的话他已说过不知有多少遍了,但我听起来没有丝毫的厌倦感。因为我知道,大哥是在用自己的心来说,用自己的生命来说,我怎能不用心来读它呢?
在我的感觉里,老井就像一个谜,随着季节的变化,呈现不同的魅力。
秋天中,天地恍然成了一幅画。白云好似仙女的裙裾,穿行在水墨里,翻卷在波澜不惊的幽深里,清爽的风儿悄悄地与它低语,说了什么只有它自己知道。即将南归的鸟儿一头扎进它的怀中,落在滑腻凉沁的井壁上,啄下难舍难分的情愫,井依旧静默着,无声地包容了它的心声。井台上,挑水的很少有等着排队的,或是早晨老早就挑回去了,或是晚上天擦黑了,挑上一挑,即使彼此见了面也简短地打个招呼,然后是让人浸透肌肤的幽静。水桶无论怎样地颤动,但心是静的、甜的、美的。
待雪花将菊花送走后,井台就逐渐结下寒冷的果实。曾经诗意蒸腾的地方俨然变成北冰洋上的一个窟窿,根本看不见它青青的原貌,而是白白的,亮亮的,光光的,远远望去,宛如天宫上无意间坠落了一个玉环。排队等候的挑水者,一个个戴着厚厚的棉手套,不断地哈着气,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两句咸的淡的。而此时在井台上担水的人则紧张万分,一是脚底下太滑,穿鞋时就要考虑了,断不敢穿塑料底的鞋;另外,要当心,井口小了,人需要使劲往前伸出手臂,左右摇晃,选择最佳时机,稍一松手,让水桶倾斜扣下,水落满水桶,这时,再用力将水桶拉上来。待一桶水提上来后,往往都气喘吁吁的了。然后赶紧将水桶提走,给别人腾地方。
井台上永远是高手们表演的天地,看吧!稳稳地往那一站,左手握紧扁担一边的钩子,用那边的钩子钩住水桶的横梁,左右一晃,身子往下微微一坠,一桶水就满了,然后,三把两把就把水桶拉出了井台,那熟练的身手和健壮的身躯,给人一种特殊的美感。多少年以来,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绝美的造型,非常生动又富有质感,若有天才的艺术家能够适时将其捕捉,凝固成永恒,绝对是一件不朽的艺术杰作。倘若再是一个铁娘子,凹凸有致的轮廓,矫健敏捷的身姿,不让须眉的身手,艺术效果无疑更佳。我常常以一副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敬佩他们的英武强大和有力。我暗想,等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们那么厉害有多好,天若有个把儿,地若有个环,我也会毫不费力地舞动起来呢!
我知道自己的本事,往那儿一站就心发虚,腿发软,水桶好像也故意和我斗气似地怎么也不听话。而刺骨的北风已将我的手冻得生疼,我的心咚咚地紧张个不停,怎么办呢?总不能空着桶回家吧!我有些急了,使劲一晃,然后,一松手,这下不要紧,水桶彻底脱钩,咚咚咚沉入井底。我心里一惊,汗顿时下来了。我不敢往井里看,赶紧退回到井台下边,对着井台发愣。也真怪了,水桶掉井里了,这时也来人了。我的神态和空握着的井绳,已让人猜测到是我的水桶掉井里了。我至今不能忘记,他们没有只顾自己挑水回家,而是放下自己的水桶,四处去找“毛抓”,这是一种专门用来捞桶的工具。这个活计需要特别耐心,一起一落,一遍遍地找、试,有时甚至要趴在井口上。那天,几个人配合,鼓捣了有二十分钟,每个人都弄出了一身汗,终于将我的桶捞起,又为我提满另一桶水,让我体面地挑回家中。多年来,每逢想起这一幕,一股暖流便从我的心头升起。它不仅让我感动,还让我升华,让我正直,让我善良,让我发扬光大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老井多像一个千年蜂巢,使一个又一个的身影,一年年,一代代,乐此不疲地酿造着生活的蜂蜜,其沁人的甘甜和芳香,使这里的每一颗心自自然然地黏合在一起。
七月流火,从地里拔麦子回来的农民,一个个浑身紫红,汗湿衣衫,气喘吁吁,他们到家后,首先要做的不是躺下歇歇,或是吃点东西,或是洗洗身上的土渣,而是抄起扁担,挑上水桶就来到井台,刚才还是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的困顿之军,一到井台上,马上就变得换了个人一样,精神抖擞,力大无穷了。许是井水和清凉之气,爽了他们的精神,也许是关于清爽的想象,激发了他们身上残存的一点潜力。
只见一桶桶清澈透亮的“井拔”凉水随着流星一样的脚步和身影流到了各家的盆里,碗里,一张张口里。无论男女,在这清凉的水桶面前,都恢复了精神和活力,不时喊一声:“痛快,真是痛快!”有的在桶里泡上啤酒,从自家小院里摘下黄瓜、茄子,然后咔嚓吃上一口,爽死了。不一会儿,女人们就要将快刀切出的面条下锅,这时就会唤:“大妞,快烧火!”“二丫,剥蒜!”“铁蛋,去小卖部买醋!”有时也会夹杂着一两声斥骂,那是嫌孩子贪玩儿,或手慢,误了饭时。这样的时间不长,风风火火的主妇们就会将面条捞出,这是如外边天气一样火热的面条。但他们不怕,因为早有一大盆冰凉的水在那里候着,只一淘,面条就凉了,这还不够,要再淘或者三淘。这时的面条可就冷了硬了,咬起来卜楞卜楞的,有些冰牙根了,这才最好,才到时候,这才解渴呀!小饭桌上,既火热,又清爽,“叭”地一声,用口咬下瓶子盖,一股特有的苦香味似从地底下钻出来,爽得让人欲醉,这是正牌的“燕京啤酒”。男人有时问一句:“他妈,你也来一杯吧!”“不用,你自己喝吧!别喝多了就得了。下午,再加把劲儿,那块地就收拾净了。”女人自己挑了一碗面条,和孩子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春天的井台是诗意的,人们仿佛是来聚会的,散心的。他们一个个悠闲地挑着扁担,有的干脆都不用手扶,就那么肩上一担就来了。我观察过,最多时,这儿有十六副扁担。挑水时,大家有掬有让,因为家里并不是火急火燎地等水用。看吧!人往井台上一站,先是直一下腰,这是要放松地舒展一下,因为脚下不再危机四伏,而且井口往上升腾着一种湿润之气,享受一般地伏下身去,稍稍一晃,水桶就满了,轻盈地挑在肩上还要扭着肚子说几句闲篇儿。这时偶或有谁家的老母鸡刚下了个蛋,“咯咯嗒,咯咯嗒,咯咯嗒”地来几嗓子,好不美妙和谐,有时,还会有一两只狗前后追闹,更增添了一点乐趣,若是它们兴致再高些,大一点的狗爬上娇小一点的狗身上,表演一下充满生命意味的节目,又会使这挑水的人们发出一片笑声。大家都乐意在这盘桓一下,还因为这儿是一个生长新闻的地方,张家如何吵架,丈夫最后被关在门外,哀求了半夜;李家媳妇如何会过日子,纺线纺到深夜了;王家和赵家婆娘因为一句闲话,在街上滚起来了;大队干部又往谁家跑得勤了。还有种子如何了,化肥又涨价了等等,所有的信息和传闻,如一只又一只的鸟儿从这儿飞起,不一会儿便家喻户晓了。
我此时常常格外兴奋,这除了可以甩掉厚而臃肿的棉衣,能够孙猴子一样轻灵地欢乐,还有一年一度的淘井,现场那十分火暴的气氛,让我期待、激动和迷恋。
这事儿由住在井边的大哥出面操持,家家老少都很高兴,如同要上演一场精彩社火。
“一、二、三,嗨!”“一、二、三,嗨!”拉绳的号子此起彼伏,使现场的人们心都要悬起来了。随着喊声的起落,众人齐齐地由近及远地拉拽,桶在井口支起的坚实的滑车上也上上下下地进出。最为抢眼的活儿是井下作业,这是最苦最累也不乏危险的活计,选的一律是精壮的小伙子,穿上一身皮衣皮裤,握一把小铁锹。我曾专门和下过井的大明聊过,他绘声绘色地对我说,从井底往上望就觉得天是那么小那么小的一块儿,井壁就像成心要从上边合拢它,绝对不敢往上看。最让人难熬的则是阴森无比,寒气就像无数长了眼睛的针,专门往人的骨缝里扎。他的话让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也让我对他格外崇敬起来。当我面对一桶澄澈清幽的井水时,不知怎的,总有一种敬畏感,让我不禁想起深深的井底和淘井的人,就对脚下的土地充满了感激。
后来,我搬进城里,再也不用挑水了,水龙头一拧,哗哗干净的自来水就散珠碎玉般地喷涌而出。水桶用不着了,井绳用不着了,需两个人才能搂过来的大水缸没用了,扁担也送了人。我不免有些怅然,曾经与井有关的那么多刻骨铭心的东西只能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据说,那口老井,原来还有大哥打打罐,浇浇园子。后来,大哥走了,便没人再去光顾,曾经热烈的聚谈转移到了张家或李家的麻将桌上,一个十分善良且有口皆碑的八旬老者,就因为一张牌爆发争执而丧命。井台上拉满了鸡屎,不知谁家的小猪掉到井里淹死,人们也懒得再捞它,而为了防止小孩不慎掉入井中,干脆石板一盖,上面盖上厚厚的土。
曾经哺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父老乡亲的老井就这样默默地走了。它带走了沧桑,也带走了诗的梦幻和迷人的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