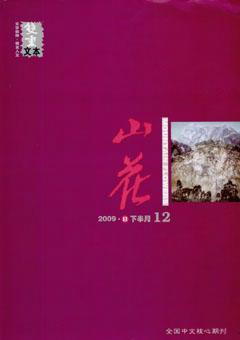《儿子与情人》中的生态批评
陈 婕
D.H.劳伦斯的早期重要作品《儿子与情人》通过一个“恋母情结”的故事展现了男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带有极强的自传色彩。作者把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灾难和不幸,以及父母的错误婚姻带来的心灵创伤,有机地融进这部小说中,使得小说的意义不只局限于对个人进行精神分析,而是体现作者对自然环境生态和人性生态的忧虑与反思。
劳伦斯生活的19世纪末期,工业化和机器文明成为主宰一切的社会力量,各种社会罪恶应运而生,下层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美丽富饶的土地沦为浓烟滚滚的矿山和工厂,机器的轰鸣淹没了自然的天籁之音,现代工业使人异化,工业文明衍生出一代机械和缺乏生气的“阉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华美的箴言被一幅幅撕裂的社会图景所粉碎。道德沦丧,信仰削弱,物欲横流。工业生产、金钱原则吞噬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山林,吞噬着荒凉、孤独的人心。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作家,劳伦斯既看到了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又看到了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看到了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被金钱意识物化了的人格。他大声疾呼恢复现代文明的正常进程,保持自然的平衡以及生命本质的回归。完全可以说,在当时大多数人向着工业文明顶礼膜拜,庆幸它所带来的丰富物质利益而无视对自然生态和人性生态的破坏之时,劳伦斯却先知先觉地明锐地洞察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性的异化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尤其是男女性关系的扭曲和摧残。劳伦斯的作品体现出他对生态问题的深切关注,《儿子与情人》是他关注自然生态和人性生态的代表作。
一、自然生态
年少时的劳伦斯在乡村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那清澈的溪水、纯净的天空、清新的泥土和农民质朴的情感给他以全新的感受。劳伦斯记忆中的乡村是美丽的,令他热爱与向往。他坚定地认为,人类从自然中来,是自然的儿女。所以,人类永远离不开自然界,人类生活和自然界更是息息相关,只有通过与自然的交融,人类才能从自然界获取生命力而重新恢复活力。劳伦斯对大自然的这种近乎疯狂的感情,大量地流露在《儿子与情人》中。作者对自然景色,尤其是对花鸟的描写特别集中,而且经常出现。这是因为作者把自然景色的描写看成叙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法,所以不厌其详,不惮其烦。书中有不少自然描写的片段与人物内心活动相互交织,情景交融。有的描写如恬静的田园诗,有的如素朴的风景画,读来回味无穷。他借助自然景物,或烘托人物性格,或暗示情节发展,或反射人物的内心世界。正是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劳伦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寄寓到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中,无所顾忌地抒发着自己的全部情感。
劳伦斯极其关注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破坏。《儿子和情人》的开篇就描述了19世纪中叶英格兰中部诺丁汉、德比郡一带煤、铁矿区与水乡纵横的画面:“从席尔贝和纳塔尔往下一带的河谷接连开发新矿,不久这一带就有了六个矿井。铁路从纳塔尔出来,顺树林环绕地势很高的砂岩地下行……六个矿就像几枚黑钉子分布在乡间,由一条弯弯曲曲的细链——铁路线连接起来。”
矿工居民区也颇具特色:“洼地区包括六排矿工住宅,每三排为一行,恰如一张六点的骨牌那样,每排有十二幢房子。这两行住宅坐落在贝斯伍德那相当陡峭的山坡脚下。前窗,至少是阁楼窗口,正对着通往席尔贝的那座缓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栩栩如生但又遭到破坏的乡野景象,是人类因贪婪逐步走向灭亡的真实写照。
通过生动的描写,劳伦斯在作品中预见了工业化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工业的繁荣, 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骄傲与胜利;另一方面却使自身慢慢陷入了种种不可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土地、生物、矿产、森林、能源等资源日趋衰竭,大气、水质、土壤等人类生产与生活环境遭受严重污染而日益恶化,都市过度膨胀, 生活环境质量低劣,在物质财富总量增加的同时, 社会贫困日益加剧, 大量人口生活于贫穷与饥饿之中。联系今天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严峻事实,劳伦斯对工业文明造成的自然生态破坏的先知先觉让读者深深折服。
二、人性生态
这篇小说不仅仅关注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更加关注其对人性生态的摧残与破坏。劳伦斯是清醒的,他透彻地洞穿了人性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揭示出工业经济这一生态链节断裂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特别是婚姻和爱情关系的破坏。
工业文明的兴起,不仅异化了大自然,把人也异化了。矿工们为了微薄的报酬而不得不成年累月地在黑暗、潮湿的坑道里干着非人的苦工。他们就像是生活在地下的一群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的动物,为了生活苦苦挣扎。尽管瓦尔特·莫雷尔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他的薪水却一再下降。在漆黑井下工作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莫雷尔当时干活的矿坑是个苦地方,他总是干到副手歇手时才收工。工作的艰辛、环境的恶劣让他变得易怒、暴戾、缺少人情味,甚至对儿子保罗的降临人世也显得无动于衷。莫雷尔只是当时英国千千万万个矿工中的一个,他每天早晨唱着忧伤的歌爬进矿坑,晚上又喝得烂醉回到家中发酒疯。他无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享受阳光的爱抚和家庭的天伦之乐。甚至在妻子生了儿子,也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份喜悦。他的这种本性所需要的权利被工业文明所剥夺。他拥有的只是黑暗,他失去了光明的自我意识;他拥有的只是那乏味的机械的下井、出井生活,是一种活着的死亡。
一个男人被毁了。看起来好像是由于家庭的不和,或者说是由于他和妻子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缺乏共识。但我们究其源头才能找到这样一个男人悲剧的内在原因。劳伦斯认为,在大工业化进行之前,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人性得到自由发展,劳动也是一种美。但现代工业在提高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极大地破坏了大自然的美。此时,劳动已不是自发的活动,而是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异己的活动,它压迫人的精神和肉体,夺走了自由和支配自己的权利。莫雷尔作为一名矿工,他的生活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白天他拼死拼活地在地下挖煤,这时他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生命、只有动作的生物而已。只有到了晚上,下班以后,回到家里,或到酒馆他才恢复了男人的气息。然而,家庭的重担再一次将他推到崩溃的边缘,他的人性渐渐被这种异己的劳动所异化,而这种异化的人性又导致家庭的异化,所以说,是工业文明践踏了家庭。劳伦斯通过莫雷尔的家庭冲突企图说明异化世界中的一个恶性循环:“机器毁了男人,男人毁了女人,女人又毁了儿子们,而儿子们被母亲所软化,重又毁了自己的女人。”[1]劳伦斯犀利的目光看到了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戕害。
《儿子与情人》中不和谐的夫妇关系、畸形的母子关系使威廉和保罗兄弟俩都摆脱不了自己的心理病症,不能建立自己的爱情生活。这里,母子之间、青年男女之间不和谐的性关系正是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社会悲剧。劳伦斯笔下的男男女女无论是否拥有爱情,都始终生活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阴影中。换言之,由于工业化和机械文明破坏了自然,扼杀了人性,所以人们被抛进了丑恶而狭小、贫困而屈辱的生活环境之中。早在《诺丁汉与矿乡》一文中,劳伦斯就已说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兴盛时期,有钱阶级和推动工业发展的人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是:他们将工人投入丑恶、投入卑贱和丑恶凌乱的环境,投入丑恶的理想、丑恶的希望、丑恶的爱情、丑恶的衣服、丑恶的家具、丑恶的房屋、丑恶的劳资关系。”[2]从工业社会对人性生态破坏的这个主题来讲,小说《儿子与情人》正是作家上述思想观念的艺术体现。英国文学批评家阿拉斯泰尔·内文不愧为劳伦斯的后世知音,他曾经以极其精练的语言,概括了劳伦斯小说博大的思想内蕴:“劳伦斯认为,英国的工业生活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留下了烙印及一般难以洗刷的污斑,削弱了他们的人性,缩小了他们的视野。被机械所奴役,为工业化、生产率与消费这种神灵所驱使——这样的生活是荒芜徒劳的人生。”[2]
工人在资本家的盲目竞争及变本加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丧失了自己的个性特征,成了机器的奴隶,遭受统一化的苦难,在生理和精神上严重退化。劳伦斯在后来所写的自传片段中,曾为他父亲之后的那一代矿工被驯化而深感悲哀,“与带着强劲而美丽的孤寂、半荒弃的旷野景色相呼应的,与远远地踏着泥水走来的矿工和赛狗相呼应的”那样一种“潜在的野性和未经驯化的精神”,在新的一代矿工身上消失了。他们变得“节制、谨慎而一本正经……我们这代男人们被弄得循规蹈矩、温良恭让。”[1]
不仅如此,人的异化和对金钱财富的极度追求亦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异化扭曲。在物化了的工业社会,人际关系堕落成了冰冷的“机械关系”或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成了精神上的“阉人”。人们希望占有更多的金钱和财富的这种强烈的占有欲荼毒了人的心灵,使他们还渴望从精神上或肉体上占有他人。在劳伦斯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扭曲了的“占有关系”,诸如丈夫“占有”妻子,妻子“占有”丈夫,父母“占有”子女,雇主“占有”雇工等。正如多萝西·范·格恩特在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中也揭示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及心理现象:“人们往往不能尊重并正确对待他人完整的最终的个性存在,总有一种畸形的愿望去占有别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先要占有丈夫,然后要占有儿子;米丽亚姆要在精神上占有保罗;克莱拉要在肉体上占有保罗。劳伦斯认识到这种对他人个性的侵犯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病态。从两性关系的这种侵犯还可以延伸到社会、经济或政治等领域,比如:把人变成无名的财产,军事单位,或思想意识的机械物体。”[3]因此,劳伦斯毕生所憧憬和追求的便是“摧残我们和宇宙之间虚假的、无机的联系,特别是基于金钱的联系,恢复活的有机的联系,与宇宙、太阳和大地,与人类、民族和家庭的联系。”
劳伦斯的作品具有持久的魅力,其魅力在于他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把心理分析同生态批评相结合,并以独特的眼光洞见未来。他的作品,一直着力描写人的自然本性如何受到机械文明的摧残,资本主义工业化及金钱原则如何对人与人之间和谐自然的关系进行破坏,从而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色——生态批判和心理探索相结合。在当今呼吁保护生态平衡的生态文论视阈下,《儿子与情人》深刻独到的生态批判主题无疑是有预见性的,这也是劳伦斯作品永葆青春魅力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弗兰克·克默德.劳伦斯[M].胡缨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6. 9,23.
[2]阿拉斯泰尔·内文. D.H.劳伦斯:小说[M].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 40,41.
[3]刘之宪. 劳伦斯研究[M]. 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124.
作者简介:
陈婕(1976— ),女,湖北宜昌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外语教学与文学,翻译理论;工作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