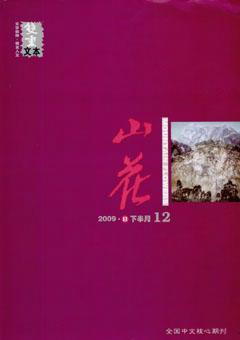否定之中的继承
伊迪丝·华顿(EdithWharton,1862—1937)被誉为“世纪之交的风俗小说家”,因其作品对美国纽约上层阶级腐朽和丑陋本质的揭露而著称于世。这位出身纽约豪门的女作家深谙其中的规则和“社会符号”。这个小团体在华顿的笔下被冠名为“老纽约”社会。在对“老纽约”旧传统由全盘批判到既反抗又肯定的过程中,华顿完成了自己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变迁。在资产阶级旧贵族日趋衰落,而财富大大增长的资产阶级新势力逐渐崛起的历史时期,华顿对新、旧两种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审视和透析,而在她后期的作品《纯真年代》(TheAgeofInnocence,1920)中则表现出对旧传统某种程度上的继承以及对新秩序的肯定。
华顿的小说尤其关注上流社会中的女性命运,并且把女性的问题置于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道德角度下加以观察。曾经深受社会习俗戕害的华顿在笔下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反抗“社会符号”的女性形象,比如《豪门春秋》(TheHouseofMirth,1905)中的丽莉·巴特,《乡土风俗》(TheCustomoftheCountry,1913)中的安丁·斯布拉格和《纯真年代》中的艾伦·奥兰斯卡。这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华顿小说创作的前、中、后期。“每部作品都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暴露,是作者的‘心声或‘情态的表露。”通过对这三位女性主人公的分析,我们可以管窥出华顿自身社会道德观念的发展和演变。
一、丽莉·巴特:软弱的反抗者
华顿从小生活在“老纽约”社会的旧贵族群体当中,受到封闭式传统教育的束缚,并对纽约上流社会的虚伪和丑恶洞察分明。这个由私利围筑起来的小圈子令年轻的华顿感到厌恶。由资产阶级旧贵族为主要构成的“老纽约”社会体系,严格恪守陈旧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顽固抵制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正如卡兹恩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毫无生气、极端保守的阶层……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无益于智慧和文化的发展,就连仅有的娱乐也不过流于形式。”这些旧贵族们倚仗祖辈遗留下来的大量财富和房产,整日花天酒地,沉迷于奢侈空虚的生活之中。他们极度害怕变革,“害怕丑闻甚于疾病”,而“置体面于勇气之上”。
“老纽约”对于旧传统的卫道还可以从其对女性的待遇中体现出来。陈旧的社会习俗压抑人性,为女性心智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上流社会的女孩被禁止自由学习艺术,也不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华顿本人也几乎成为这种不平等传统的牺牲品。“她(华顿)的母亲不允许她广泛涉猎书籍,打压她对文学的热情”,因为“阅读和写作被认为是男性专有的知识领域和权利”。上流社会的妇女不仅受到畸形教育模式的危害,还要顺应整个社交圈对于外在美貌近乎狂热的膜拜情绪,投入金钱和一切精力装扮得美丽优雅,犹如商品般等待未来丈夫的选购。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符号”的控制下,女性不过是缺乏独立人格的花瓶和玩偶。
在《豪门春秋》这部早期的文学尝试中,华顿试图揭露并抨击纽约上流社会所崇尚的习俗和遵循的行为标准对于女性情感和智力发展的局限。借丽莉·巴特这个人物,华顿探讨了个人道德和社会习俗之间的对立。丽莉·巴特赖以生存的“老纽约”是一个以金钱为一切社会行为主宰的社会。人们以金钱和财富作为衡量的标准,只要在银行里放上大笔存款的人就都能在社交场合中如鱼得水。丽莉无疑也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家道没落的丽莉本有机会依靠和新富罗西德联姻改变自己穷困的处境,然而,她的道德良心却一次次阻碍她采取果断行动。这表明她高尚的趣味和对旧传统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的反叛。然而,这种反叛却是不彻底且软弱无力的。丽莉既不愿意拿婚姻作为商品出售,又不甘心脱离上层社会成为她心中“道德清白”的人,原因在于她无力改变自幼就形成的人生观。上流社会拜物主义的价值观扎根于她的意识之中,使她贪慕虚荣,迷恋时髦服装,不能自拔。即使在她被上流社会逐出之后,她还想道:“我恨透它了!但一想到和这种生活一刀两断,又觉得活不下去。”丽莉保持着一定的真诚与清白,但是力量微小,既不足以对抗强大的习惯势力,也没有决心同社会环境决裂,“显而易见,她早已变成造就她的那个文明社会的牺牲品。她那宝石手镯恰似把她和命运锁在一起的手铐。”华顿在自传《回顾》中明确地表达了《豪门春秋》的主题:“一个轻佻的社会只有通过它的害人之处才能表现出戏剧意味。这种悲剧含义就在于它使人堕落,使理想泯灭”,“我的女主人公丽莉·巴特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二、安丁·斯布拉格:否定的胜利者
20世纪初,美国上层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夺权步伐加快”。“来自中西部的一股商业巨流正吞没着纽约,甚至整个美国”。在新势力的冲击下,“老纽约”社会封闭的体系变得岌岌可危,旧的价值观逐渐失去其影响力。正如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64)所说,“在社会权利机构之中的变化产生了在认识形式之中的变化”。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问世的《乡土风俗》反映了华顿在道德观上的一次重要转变。社会的变迁使她对新旧势力的态度发生巨变。她曾经批判过“老纽约”社会的习俗与观念,力图通过写作来摆脱其束缚,重构女性身份,然而,对于社会急剧的变化和商业社会浮躁功利的价值观,华顿持保守态度,同情的天平开始倾向她所成长的“老纽约”社会。在塑造安丁·斯布拉格这位资产阶级新贵的过程中,华顿明确地表达了否定的观点。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安丁·斯布拉格以一个入侵者和胜利者的形象出现。与懦弱善良的丽莉截然不同的是,安丁实际而精明,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丝毫不顾及道德规范。她的一切行动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在她眼中,父亲是供她挥霍的支票簿,丈夫是她攀升更高阶层的阶梯,孩子则是破坏她身材的潜在威胁。作为西部暴发户的女儿,她利用自己的聪明和美貌,与旧世家联姻达到进入“老纽约”社会的目的。然而她并未就此罢休。她不顾道德的约束,玩弄高超的手段,辗转于几个男人之间,以求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安丁被塑造成一个精力高度充沛、野心勃勃的怪物。“她没有自我,除了渴望占有更多的金钱和拥有更舒适的生活之外,她的脑袋空空如也……直到小说结尾处,安丁还在想着如何通过再次结婚达到圆满和快乐的状态”。
安丁的所作所为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功利主义,为达到成功的目的不择手段。暴发户出身的她颇具侵略性,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主导势力。他们觊觎“老纽约”社会的特权,希望取而代之。华顿塑造安丁这样一位女主人公正是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对资产阶级新贵的崛起,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造成的巨大冲击,华顿感到不安,开始怀念旧秩序的规范与安全,因而这部小说中充满着“自省的精神与坚守旧传统的道德观”,华顿就此完成了她对旧传统的第一次继承。这一精神在她后期的作品《纯真年代》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三、艾伦·奥兰斯卡:反抗的继承者
20世纪初叶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多事之秋。一战爆发后,旅居法国的华顿亲眼目睹了战争中被摧残得满目疮痍的巴黎,从而唤起了对战前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怀念之情。她说:“在我年轻时,我觉得我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都像一堆空瓶子,从没有新酒装进去,现在我觉得这些瓶子自有它们的用途”。《纯真年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该作反映了华顿对逝去的传统和“老纽约”社会的眷恋。虽然文中仍不乏对“老纽约”社会禁锢女性发展的揭露,但华顿更侧重于对传统的再思考,对其强调道德义务和顾全大局等优良传统的颂扬,其中揭露和讽喻的笔调也比以往的作品缓和得多。华顿强调秩序的创作理念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纯真年代》中,华顿为强调传统文化的优良方面,塑造了一位完美的女性形象——艾伦·奥兰斯卡。她出生于美国上流社会的贵族家庭,在巴黎长大,而法国巴黎正是华顿本人十分推崇的自由艺术之地。艾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长为一位对艺术和音乐有敏锐洞察力和欣赏能力的贵妇。艾伦的知识涵养丰富,其理智和分析能力丝毫不亚于男性。更重要的是,她有着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男性而生存,这一点与华顿小说中的传统女性完全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艾伦绝对是一位反抗传统的典型女性,已经完全超越了丽莉等等这样懦弱无能的角色。作者通过对艾伦的塑造透视了女性的压抑与反叛。在故事的开始,她发现丈夫屡屡不忠之后愤然出走,回到纽约并准备离婚。女性追求自由和独立,这在当时的“老纽约”社会是无法容忍的行为。艾伦还进一步与表妹的未婚夫阿切尔坠入爱河,种种举措都扰乱了“老纽约”人所奉行的社会符号。然而,这位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新女性还兼具传统女性的美德——牺牲精神。在得知表妹怀孕的消息后,艾伦决意成全他俩,毅然担负起对他人的责任。她既敢于追求个人幸福,也勇于作出自我牺牲。艾伦的行为既保持了个体的尊严,也体现了她对“老纽约”上流社会道德准则的尊敬和作家对逝去传统的追忆。
小说的后记部分进一步加强了作品对传统道德的颂扬。已经成为鳏夫的阿切尔出于对自己婚姻的尊重而放弃了与艾伦重续前缘的机会。华顿进一步肯定了“老纽约”社会旧传统的力量,“说到底,旧的生活方式也有它好的一面”。如果将华顿本人的经历和艾伦的故事加以对比,不难看出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回到欧洲的艾伦坚持自己独身生活,拒绝社会给予女性规定的角色,在异国的土地上开创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三位女性人物的刻画体现了华顿创作心路历程的演变。《豪门春秋》中懦弱善良、摇摆不定的丽莉是华顿表达思想的萌芽,开启了华顿小说中女性觉醒微弱的第一声。作为新富代表的安丁尽管是“老纽约”世界中的征服者和胜利者,但与丽莉等“老纽约”社会的贵妇相比较,她缺乏内在的修养和强烈的道德意识,是华顿用否定性笔调书写的人物。《纯真年代》写于一个旧的生活模式和思想观念崩溃的时代,华顿在小说中返回她曾经摈弃的过去,并且试图与过去取得某种和解。在经历了时代变迁,尤其是一战的血腥蹂躏之后,华顿开始重新审视过去,重新肯定传统和秩序的力量,期盼着一个既坚守旧的伦理道德又不乏自由精神的稳定未来。她的作品是“20世纪复杂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的一部分”。华顿对于她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的褒贬既令人信服,又令人回味。
参考文献:
[1]关于“社会符号”的提法参见《金莉:〈伊迪丝·华顿其人和作品介绍〉》(序),意指社交活动中被默认的准则和习俗,载Edith Wharton, The Age of Innocence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 vi.
[2]朱振武.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9页.
[3]Kazin, Alfred, On Native Grounds [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6, p. 55.
[4]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Z].赵兴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92、303页.
[5]Waid, Candace, Edith WhartonsLetters from the Underworld [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 7- 11.
[6]伊迪丝·华顿.豪门春秋[Z].张澍智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94页.
[7]杨金才.〈欢乐之家〉与伊迪丝·华顿的自然主义倾向[A].载汪义群.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二辑)[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8]Wharton, Edith, A Backward Glance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8, p. 146.
[9]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第88页.
[10]加里·古廷.二十世纪法国哲学[M].辛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11]Fullbrook, Kate, Free Women: Ethics and Aesthetics in 20th Century Womens Fiction [M].New York: Harvester Wheat sheaf, 1990, p. 26-27.
[12]Singley, Carol J., Edith Wharton: Matters of Mind and Spiri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0.
[13]俄康纳.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M].张爱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6页.
[14]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Z].第303页.
[15]潘建.美国作家伊迪丝·华顿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1),第164页.
作者简介
廖嵘君(1985— ),女,上海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