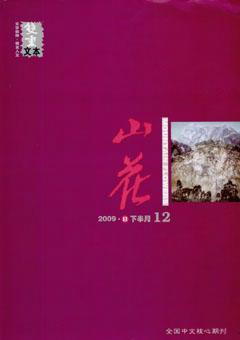生与死的诗性沉思
马建高
作家作为生命个体,对于生命与死亡这一人生主题反应尤为强烈。著名理论家丹纳认为,“作家从出生至死,心中都刻着苦难和死亡的印象”,感悟到:“尘世是谪戍,社会是牢狱,人生是苦海,我们要努力修持以求超脱。”[1]这就需要他构造一个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对抗,摆脱对死亡的苦痛的印象,置身于一个生命自由、死亡消隐的完美精神境界。某些作家具有自然天成的悲剧意识和死亡意识,他们对死亡的表现具有浓厚的艺术兴趣,对于死亡赋予诗意的反思,呈现形而上的哲学意蕴,这源于他们对现象界的审美选择。
一
正如弗洛伊德所分析的那样,在人的无意识的心理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动向。一种是生的动向,另一种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心理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性功能。[2]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许多作家的心理结构中,这两种动向有时会强烈地对峙和交织。其中有一部分作家往往死亡动向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迷恋。中国伟大的作家屈原、庄周、阮籍、嵇康之类,外国伟大的作家凡·高、海明威、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川端康成之类,他们对生命的意义大彻大悟,也就对死亡生成了审美意义的接受。
1.死亡即美。“死亡是生命的最高虚无,虚无又是精神的最高的悬浮状态,是接近宗教和诗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美和灵魂的升华。”[3]在某些作家的思维逻辑里,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诗意的存在方式。莎士比亚、海涅、歌德、雪莱等西方诗人,都歌咏过死亡所包含的强烈而神秘的美。中国的古典诗人,如屈原、宋玉、陶潜、阮籍等,更凭借对感性自然的隐喻与象征,含蓄而幽雅地表现死亡所蕴藏的玄妙奇特的美感。日本现代作家川端康成“对于死,仿佛比对生更了解”,体悟到“生即是死,死中有生”。“在日文里,‘悲哀与美是相通的词。”[4]死亡在川端康成的审美逻辑里即是最高悲哀的美。他还标举所谓云游虚幻梦境的新感觉主义的审美观,虚幻代表美的至高存在,也是心灵纯粹的瞬间印象,它趋向空灵的哀愁。这种哀愁象征爱的无常和多种可能,只有死才是精神与美的共同终极。川端康成的艺术思维空间,美与死同属一个潜在联系的有机结构。而他的作品,死亡均被浸染了玄幽神秘、哀艳如梦的美。文学巨匠曹雪芹也将死亡理解为美的极致,是生命状态复归到美的故园。他借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传达了自己诗意的体悟:“……始知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素女约于桂岩,宓妃迎于兰渚。征嵩岳之妃,启骊山之姥。龟呈洛浦之灵,兽作咸池之舞。潜赤水兮龙吟,集珠林兮凤翥。……”含冤致死的晴雯幻化为芙蓉仙子,在如梦如烟的神话世界里抵达绝对美的峰巅。
2.死亡即自由。有些作家认为,死亡是精神通向彼岸世界的风帆,唯有它会才引导心灵走入绝对自由的宫殿。庄子借骷髅寓言描述了生命的累和苦,而死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负担的解脱,即意味着获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自由。“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无疑这是对死亡即自由的一种诗化的理解。西方哲学家对自由的阐释不尽一致,但有部分哲学家有前思维的共通之处,他们在潜意识状态或在诗意的思维状态,把自由与死亡作为逻辑的并列。如加缪、萨特、海德格尔等人,他们均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将死亡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方式之一。而作为更注重直觉和体验的作家,他们更趋向将死亡与自由联系起来,认为死亡是最直接最高阶段的自由,它象征肉体与精神的最大限度的解放,也是知识圆满、情感圆满的境界。如歌德写浮士德之死,就把死亡赋予了最高自由、最高知识和真理、最高快乐的美学意义。作为作家的加缪和萨特,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都将死亡规定为自由的本真状态,抒写了死亡的诗意特征。死亡是他们领悟自由的最终也是最高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免会令人悲哀同情,但更赢得欣赏者的审美崇拜。
3.死亡即超越。诺瓦利斯认为:哲学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精神的家园[5]。有些作家认为死亡也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返回精神的家园。死亡是对生命起点的回溯,是对生命之家园的归返,更是对精神家园的归返。这种归返即被理解为超越,这种超越在作家的心灵界是指向这几个层面的:
首先,死亡超越了时空。死超越了时空限定走向绝对的永恒和存在,这似乎接近了神话和宗教,但却是许多作家的心理逻辑。其次,超越是指向知识的圆满和智慧的妙悟、真理的降临这一意义的。在许多作家看来,唯有在死亡之际,精神才获得完善的知识,才接近悟境,如歌德以浮士德的死亡体验,折射出自己的这一心理感受。再次,死亡超越是指向爱与美的完满境界。生命潜藏着无限的欲望,而爱欲是最大、最强烈、最持久的原欲,它与善是存在矛盾的。而死亡在众多作家看来,它消解了所有的欲望,或者说它达到了所有的欲望,其中当然包括爱的欲望。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作家为了爱欲去发狂,去竭尽生命所能去写作,或去自杀,或者在他构想的艺术境界里写为了爱欲而自杀的人物。最后,在某些作家的心理深层,往往认为只有死亡才能进入神圣的宗教领域,只有它使自我存在与上帝连为一体,自我也达到精神的永恒和不朽,才悟出生命的终极意义和获得最高的快乐。因此,就作家心理本能而言,他们许多人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对死亡存在着迷恋情结,至少是用诗意的眼光来对待它,将之赋予美学的意义。
二
卓越的作家多是人生苦海里没有功利目的、丧失情感家园的孤舟,他们往往面临财富、爱情、权力的多重匮乏,伴随终生的是生存的艰辛和孤独。弗洛伊德强调“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作家创造心理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从童年、青年、中年至老年这几个时间段的不幸的生命历程,才赋予作家深沉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使他们更敏锐地体验生命与死亡,领悟其深刻内涵,并演化到文学的情境之中。
1.家庭经历。许多作家童年时期家庭的不幸,尤其是亲人的亡故,会在他们稚嫩的“白板”一般的心灵刻下强烈的情感印记。川端康成即是典型一例。他于1899年生于大阪,两年后,父亲患肺病去世。一年后,其母又撒手仙逝。双亲病故给川端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刺激,死亡阴影从此袭罩在心头。年幼的川端体弱多病,也渐渐养成离群索居的孤独性情。7岁那年秋季,祖母又不幸离世,带给他更强烈的死亡意识的感悟。川端从此与既聋又瞎的祖父相依相伴,生活在凄凉愁苦、孤独无助的境遇。三年后他仅见过两次面的寄居在舅父家的姐姐又撒手人寰,10岁那年,唯一的亲人——祖父也终弃他而去。川端的童年与少年是在目睹家庭亲人的不断亡故的过程中度过的,这使他滋生了“有种早逝的恐惧”和“少年的悲哀”。川端在悲哀之中相信佛教经典的轮回说,用童稚的心歌唱生命的梦幻,死亡成为他的抒情诗。正是由于童年的创伤性经验,由于童年与少年目睹众多亲人的亡故,川端康成的心理深层沉积了张力巨大的死亡意识,而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偏爱表现死亡意境的美和他自己最终选择自杀来结束人生,无疑与这种死亡意识密切相关。川端康成的例证使我们领略到:体验过家庭的疾病与死亡的作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题。
2.社会经历。如果说家庭经历给艺术创造主体最初的生与死的体验和意识,那么,社会经历则进一步丰富和加深这种体验和意识,为他的艺术创造提供更深厚的矿藏和更广泛的契机。如果我们稍稍比较这两种经历所带给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感受,就会发现某种差异性。如果说前者经历一般赋予作家有关死亡的感性经验,偏重于直观的印象和情感的近距离投入,较少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没有沉重的理性逻辑的分析,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索,那么后者的经历则往往提供作家有关死亡的理性知觉,偏重于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冷静的适度距离的旁观,有关社会历史的种种观念便与死亡现象产生密切的联系,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也往往置身其中。这两种经历对艺术创作而言,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前者有助于作家表现死亡意境的经验的感性直观,有助于幻觉与想象的拓展和情感的宣泄;后者有助于作家对死亡意境展开社会历史观念的理性思考,并赋予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这两方面经历的综合更易使创作既具艺术的审美特性,又具艺术的理性知觉。
在上述简略的比较分析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描述社会经历对作家死亡意识的形成及其选择死亡意境的审美表现所起的作用。建安时期的“七子”、蔡琰等众多诗人,经历社会的战乱和黑暗,饱览悲惨的死亡景象,其诗作慷慨悲凉,充溢着死亡意识。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6]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所作《七哀诗》,即是诗人由长安避乱荆州时写途中真实景象。诗人亲目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悲惨景象,形之于诗篇,对由帝王意志引发的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悲剧予以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控诉!距王粲之后不久的阮籍,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与黑暗内幕看得十分清楚,历史只不过是杀人和被杀的交叉演绎,死亡意识浸润他的心头。“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7]他将寓藏内心的痛苦用诗歌形式宣泄出来,将他由社会历史所赋予的死亡意识形诸艺术,表达对生命的关注和对死亡的无可奈何的谦卑和接受。
卓越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从1851年起,他到高加索沙皇军队当下级军官,曾亲身参加了1854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目睹众多生命的伤残和毁灭,他的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即是这段生活经历的艺术记录。他的军旅生活为《战争与和平》这部史诗般的巨著提供了生动宝贵的素材,也为作家对死亡意境的精彩刻画奠定了基础。像“安德烈之死”这样鬼斧神工的艺术画面也唯有亲临战场的刀光剑影、烽火硝烟的作家才能传达出来。再如以“迷惘的一代”著称于世的海明威,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前线负了重伤,亲身目睹了无数生命的流血和死亡,对战争有极深刻的领悟。他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谴责毁灭生命的战争,呼吁世界应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海明威在他丰富的社会经历中形成了所谓的男性势能,它代表作家内心与死亡意识抗争的力量。“海明威的生平事迹,正可为男性的势能——体力、狩猎同性力——勾画出一幅明显的图画,他本人的死亡意识很强烈,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性无能时,死亡对他更构成了强烈的威胁,最后他便以戏剧性的动作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肯定自己的势能。”[8]无论是所谓男性势能还是死亡意识,这均是作家丰富的人生经历所带来的精神存在,尽管有些是属于潜意识的本能部分,但更多是社会现实所赋予的。它们均对海氏艺术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助于死亡意境的审美表现。
三
死亡不是呈现出具体的现实性存在,而是转换为审美情感体验可能把握的艺术化的对象,成为精神自我观照和沉思的境域,而属于这一境域的作家心灵则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形式和情感逻辑去阐释死亡和抒写死亡,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艺术结果就获得了。这个结果,就是作家所构想的死亡意境,这个死亡意境也相应地凸现作家所持有的独特的美学趣味。
如果说心理的本能迷恋和个体的生命经历属于作家得以感受死亡、滋生死亡意识并获得表现死亡意境的心理契机,那么对于死亡的审美情感体验和艺术传达则是构成死亡意境的独特的美学趣味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文学创造主体的审美情感体验和艺术传达方式是多姿多彩的,审美选择充满个体的趣味和风格,很难以几个简单的逻辑归纳达到涵盖和包容,为了理论描述的方便, 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视点,总结某些文学创造主体有关死亡意境表现的美学趣味。
1.神游山水。这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心灵表现死亡意境的美学趣味之一。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物我两忘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也影响到古典作家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表现。中国古典诗文表现死亡意境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趣味就是偏爱写神游山水,对山水景物的审美观照,流露出生命暂时性和自然永恒性的忧愁情绪,或以对山水的心神向往之乐冲淡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将死亡意识隐藏或消解于自然美景之中。此种美学趣味,一方面透出古典心灵对于死亡的智慧性解脱,另一方面也反映古典艺术对于死亡的情感回避和审美静观。诗人似乎用槛外人的目光淡泊超脱地静观死亡,他置身于幽美奇丽的山水之中,与死神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尽管死亡的阴影间或袭上意识,带来忧思和烦恼,但死亡的愁云被大自然的风花雪月、鸟语花香所驱赶,心灵终究在山水美景中找到超越时间的永恒休憩的家园。这类美学趣味的代表作有,屈原《九歌》,汉无名氏《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陶潜《饮酒》,等等。
2.沉醉酒药仙。中国古典诗人往往凭借“酒、药、仙”这三样东西来逃避死亡畏惧,或凭借这三样元素去构想诗文,营造一个忘却生死、精神麻醉而得以幻觉性自由的天地,由此摒弃死亡之思,并获得审美快感。这种美学趣味尤其体现在魏晋时期的诗人及其作品方面。有关酒与沉醉的诗文既是对黑暗现实的暂忘,也是对死亡意识的暂忘,借写酒及沉醉来表达对死亡的审美情感体验,并呈现独特的美学趣味。阮籍《咏怀》、刘伶《酒德颂》、嵇康《酒会诗》、陶潜《饮酒》等诗作,以抒写酒的沉醉来映衬淡隐的死亡意识,以享乐主义和精神麻醉手段展现死亡意境所描画的独特的美学趣味。服药是饮酒的补充和递进,同为魏晋文士的雅好。服药起于道家哲学的卓越阐发者——何晏,他改进了“五石散”。以石钟乳、石硫黄、白石黄、紫石英、赤石脂为成分配制成所谓能“身轻行动如飞”(王羲之语)、“可长生不老”(葛洪《抱朴子·金石篇》)的“药”。暂且不论这药的功效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具有麻醉神经和致幻的功能。正是对于这一功能的需求,魏晋名士在生活行为和艺术创作上都与“药”结下不解之缘。在生活行为上,用服“五石散”来放旷畅神,蔑视专制阶层的“礼法”和“名教”,放任自然,发言玄远,行为遗世而独立。在艺术创作上,以药刺激神经,激发想象力或幻觉,进入到与天地共生,万物齐一,生死两忘,荣辱皆无的意境,药成为超越生死乃至人生万象的审美工具,也成为审美情感体验的手段和艺术内容。当然,这种与药密切关联的艺术文本就成为品位独特的艺术审美对象。突出的诗人仍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古典诗歌另一沉醉对象是“成仙”,这同样也是抵消死亡意识的途径之一,也为表现死亡意境开拓了另一片空间。“成仙”既可能出于一种半迷信、半宗教的神话思维心理,更可能源于一种假想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感寄托的缘故。诗人借诗歌所幻想的羽化登仙的审美情感体验来遮蔽死亡意识,或者与死亡进行非现实性的沟通,嵇康《圣贤高士传》与《游仙诗》,郭璞《游仙诗》等均是这类美学趣味的杰作。
3.寄寓性爱。此为中西古今的作家逃避死亡之畏的共同喜好的精神对象。有所差异的是,中国古典作家及其作品偏重于对女性的纯粹的审美迷恋,关注精神的超越性和内在和谐,往往升华为女性崇拜或女神崇拜;西方无论古典或近现代的作家及其作品,偏重于对女性的感官沉醉,倾慕灵与肉相统一的性爱欢乐,使审美掺杂了欲望和享乐,女性往往被降低为性爱的工具或玩偶。当然,有些情况下,也有对女性的崇拜,不过这种崇拜不排斥性爱的成分。中国古典诗人往往有较明显的恋美情结,可以说屈原开了一个浪漫的先河。这种恋美情结一是指向大自然的山水草木之类的美之存在;二是指向外秀内慧的“美人”,而这种“美人”一般是女性形象。对于美人的沉醉是暂忘死亡之忧的绝佳途径,女性的美引导精神步入纯粹的审美情感体验,诗意的情怀自然孕育,一种本能化的艺术创造冲动得以张扬。屈原《离骚》,香草美人生发了诗人生命永恒的情思。陶潜《闲情赋》,绝美佳丽令诗人忘却时空,忽略生死,沉湎在爱情的审美幻觉。美升格为诗人的神灵一般的崇拜,女性不再是简单的性爱对象,而是超现实的幻觉化的审美对象,是一种排斥了性爱感的纯粹的爱与美的化身。她象征一个没有死亡、没有恐惧与忧愁的完满世界,诗人通过对女性美的沉醉抒写对死亡的拒绝,以形成一个特定的艺术风格。西方作家倾慕女性之美,注重形与神、灵与肉的和谐统一,对她们寄寓性爱观念,在具体的文学表现中以此与死亡概念抗衡,创造独特的审美意境。如但丁《神曲》描绘的贝阿特丽彩,歌德《浮士德》描绘的海伦与甘泪卿,劳伦斯小说中的厄秀拉等女性,她们不同程度作为性爱的象征品,成为作家超越生死之限的精神工具,构成独特的审美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