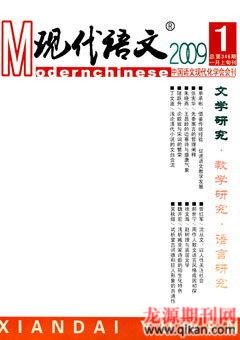浅析臧克家诗歌的“陌生化”特色
魏开宏
摘要:臧克家的诗歌语言新奇生动,形式独特多样,展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音、形、色的和谐。同时,他的诗歌也充分体现了俄苏形式主义倡导的“陌生化”特色,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而广泛影响。
关键词:臧克家诗歌陌生化
一、导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臧克家以其健康清新的笔调、朴实沉稳的风格描绘了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新诗多元化的竞争中,他始终保持忠于生活、忠于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熔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和现代诗歌美学于一炉,描写他热爱的农民、农村、大自然,博得了“农民诗人”、“乡土诗人”的称号,并于2000年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人奖_终身成就奖”。如此崇高的荣誉在中国诗歌界史无前例。
纵观臧克家的诗歌,在我们赞誉他的诗反映现实之真实、生活之丰富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为诗人作品语言的凝练生动、形式的独特多样、构思的精巧新颖所折服。他的诗歌体现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听觉与视觉的完美结合,更具有音、形、色的和谐之美。本文试结合俄苏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分析臧克家诗歌中的“陌生化”效果,进一步探讨其诗歌独特的形式艺术魅力。
二、“陌生化”概念
“陌生化”概念是西方文论史上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苏形式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著名的诗学命题。“陌生化”意为在诗歌语言中使用变形、扭曲、悖论式的词语使读者与已熟知的事物或形象的距离拉开,变得陌生,从而延长读者的审美过程,引起读者的注意。俄苏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知,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作家在创作作品过程中不可能原样照搬,因此,要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陌生化”就是必不可少的方法。“陌生化”的实质就是要“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
形式主义理论家在谈“陌生化”问题时,主要强调语言的陌生化,他们还探讨了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区别。日常用语是熟悉的、被“感觉自动化”了的语言,它以交流为目的,而诗歌语言是有意为摆脱感觉自动化状态而“人为地”创作的语言,是“受阻碍的,扭曲的语言”。在这种语言系统中,语言的实际交流功能退居二线,而其他构词因素(声音、节奏、韵律、形态)获得独立价值。
三、臧克家诗歌语言的“陌生化”
臧克家以其丰富的想象,敏锐的才思突出运用“陌生化”手法,在平淡的诗句中凸显语言的新颖,开拓了别致的意境,取得新奇的效果。
(一)日常用语的诗意表达
在臧克家的诗歌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大量日常用语、口语在诗句中出现,尤其是在描写农村,.反映风土人情的诗句中。这和诗人扎根于农村,生活在农民中间,熟悉这片他热爱的土地是分不开的。“我就是在这样的乡村里,从农民的饥饿大队中,从大自然的景色中,成为一个泥土的人”,“我不爱/刺眼的霓虹灯/我爱乡村里/柳梢上挂着的月明”(《铜铁的灵魂》)。在这些平白如话、清新洗炼的诗句中,除了诗人所蕴含的真情外,语言本身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分析其原因,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语言,诗人却把它富有诗意地表达,组合,从而产生新奇效果。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词语之间搭配的不和谐:“铺一层大地,/盖一身太阳,/头枕一条疏淡的树荫”,(《歇午工》),“送行的队伍/锁住了大街/掌声把一串串眼泪/拍落下来”(《送战士》)。(2)诗句的颠倒:“认不清亲疏远近/饿花了的眼睛”(《饥馑》),“一根棘条上咬烂了狗牙”(《冰花》)。(3)悖论语的运用:“在马粪香里/一席光地/我睡的又稳又甜”(《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臧克家提倡诗的力度,悖论语言使这首诗产生了很强的张力,无疑是一首极有力度的好诗。”在诗人的笔下,这些日常语言被强化、颠倒,是“对普通语言所实施的有暴力的组织”,由于“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反应变得陈腐、滞钝了,或者——如形式主义者所说——被‘自动化了。”这些诗歌语言不符合人们日常交流的语言习惯,使读者一下子不习惯这种表达,从而被拉开距离,心理上引起注意,甚至重新回味一下,这大大延长了感知的时间。藏克家诗集中那些传世的名篇佳作、鲜活生动的诗句很值得人再三斟酌玩味,这一方面与诗人浓厚的生活底蕴和严谨的创作态度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诗人创作出的语言的“陌生化”效果。
(二)修辞手法的新奇运用
在臧克家的诗集中,艺术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烙印》、《泥土的歌》。诗人创造性地运用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称等多种修辞手法使得平常的事物在他笔下有了新意,抽象的概念被形象化地展现出来。这里有“日头坠到鸟巢里/黄昏还没熔尽归鸦的翅膀”的傍晚,有“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的黎明,也有“自从宇宙带来了缺陷/人们为了一种想念发狂/精神上化出了一个影像/那就是你——美丽的希望”。
诗人用恰当的比喻,抓住事物的本质,一语切中,又不入俗套。如写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一万条太阳的金幅,撑起一把大伞”(《依旧是春天》);写夏日的干旱“大地是旱海,/风尘是长帆,/村庄是死的港口,/生命的船只搁浅在里边”(《旱海》)。诗人也用其它手法来描写事物,活灵活现、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如写炉火“炉火卷起条条红舌/舐得屋内温柔四溢/壶水喁喁向人说话/口里喷出缕缕热气”《一年》(拟人);写饥民“眼前有石头/也抓过来充饥”《饥馑》(夸张);写祖孙三代人:“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排比),写犁地“一双老黄牛/齐步向前/一只手把犁/跟在后边”(对称)。充分运用这些修辞手法,展现诗意的美、形式的美、艺术的美。
(三)意念形象化,意象、叙述视角的突转
臧克家诗歌的意念丰富且形象化,王佐良在《英诗的境界》中指出: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诗歌的一个特点是将抽象的名词人格化——“雄心、豪华、荣誉、知识、贫寒”等。意念形象化是臧克家常用的手法,他在1942年至1943年间写的生活小品辑“希望、爱情、友谊、热情、欢乐、思想、世故、生活”等中将抽象的意念比拟成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形象。如他写“希望是开在人心头的一朵花,/只许站在远处看,/不让你用手去触它。”(《希望》);“爱情是火/它以高度的热/吸引着玩火者”(《爱情》),这就使得原本抽象的概念变成非常熟悉的事物,也丰富了读者的想象力和审美空间。
还有一个现象是诗人所描绘的意象,叙述视角在途中突然转换,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不符,甚至矛盾,从而造成了读者的“期待受挫”。“这种想象的惯性又时常难以为继,受阻遇挫,诱使读者进入一个超越自己期待视野的新奇的艺术空间之中,在这样的阅读活动中,读者可能会因期待指向的暂时受挫而不适,但很快又会为豁然开朗的艺术境界而振奋,会因扩充和丰富了期待视野而感到欣慰满足。”
首先是意象的转换。《村夜》中写到:“太阳刚落/大人用恐怖的故事/把孩子关进了被窝……/再捻小了灯/强撑住千斤的眼皮/把心和耳朵连起/机警地听狗的动静”。在常人的想象中,应该听的是门外的动静,诗人却把意象转到“狗”身上,从而转移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也提高了诗的艺术魅力。同样,意象突转还表现在《穷》里:“屋子里/找不到隔窗的粮,/锅/空着胃,/乱窜的老鼠/饿的发慌。”诗人写人穷,不直接表达,却笔锋一转,描述锅的一无所有和老鼠的饿昏了头,这完全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不相适应,在感性上是违背的,但理性上又是合理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诗人观察的精妙和眼光的独到,创造出如此丰富的意境。
其次是叙述视角的突转。在臧克家的诗篇中,有不少作品在叙述的过程中,突然插入一句不同视角下的叙述话语,从另一层面来表达。最典型的是《老哥哥》这首诗:“老哥哥,翻起破衣裳干么,/快把它堆到炕角里去好了。”/“小孩子,不要闹,时候已经不早了!”/(你不见日头快给西山撞下去了?)“老哥哥,昨天晚上你不是应许/今天说个更好的故事吗?”/“小孩子,这时你还叫我说什么呢?”/(这时你叫他从哪说起?),臧克家运用了“戏剧化”手法,在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和一辈子作短工的“老哥哥”之间展开对话的同时,突然插入一个冷静的幕后人——第三人称(括号里的话语)的声音,他的话语不仅对表现诗歌主题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也展现出诗歌形式上的特别、与众不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