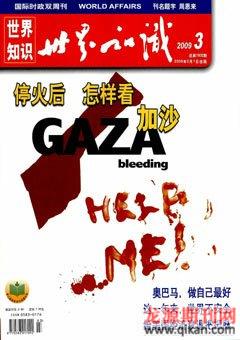埃伯斯塔特报告:战后美国安全体制的基石
牛 可
总有一些历史文本,因其透露出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可用以标识历史进程。关于冷战的启始,自然也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本,比如斯大林1946年2月在莫斯科选区的讲话、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和“X文章”、1947年宣示“杜鲁门主义”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还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等等。但是,有一个文件的历史内涵和意义绝不亚于上述各个篇章,却较少为人所知。这就是奠定了战后美国外交国防体制的埃伯斯塔特报告(Eberstadt Report)。
常言说,美国是商人和平民的国家,根深蒂固地信奉洛克式小政府,乃至于有美国式“反国家主义”之说。再则,美国自立国起即一向对大规模常备军和军人权力深怀戒惧,奉“文官控制军队”为基本政治准则。20世纪以前,美国大概可以说是西方大国中最不尚武、也最少武人政治的一个了。政府和军队都是“必要的恶”,不得不有,但总是要把它们的规模和权力影响压到最低限度才好。与此相关,美国人自开国总统华盛顿以来就以孤立主义自处,觉得在商业之外,最好不要卷到海外的纷争中去。这样,政府小,与外交和军事外交相关的部门的规模更小。所以,虽然经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海外扩张热潮,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直到1930年代中期,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梅的说法,美国联邦政府的设计仍然大体上面向内部事务,掌管对外事务的机构规模小,地位边缘。当时,三个主要的对外事务部门——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居然都挤在一座办公楼里,与财政部一个部的办公面积差不多大小。的确,在当时的美国联邦政府里,财政部、农业部、劳工部和商业部才是最显赫和权力最大的部门。那时的首都华盛顿,当然也远没有今天这般的武威轩昂的帝国中枢气象。
不久前去世的学者查尔斯•梯利,长期研究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其最著名的观点之一就是西欧各国的国家体制受到战争和战备的深刻影响,成所谓“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塑造国家”之说。这个说法,拿来看待20世纪以前的美国历史,颇不切合;但如果用以状述二战后美国的政府体制嬗变和总体政治发展趋势,则很可以说得其大体。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和形制在20世纪中叶以来急剧变化,其动力固然有来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建设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的因素,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重新塑造美国国家体制的作用,其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经过冷战初年的政府体制改组,美国创生了一个“国家安全国家”——一个将对外事务和军事事务置于突出地位,奉行“国际主义”或者“全球主义”的国家战略和政策,能够统筹整合外交和军事、政治和经济,能够动员内部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用以建设和支撑庞大的武备,具有帝国形制的国家。在这样一个重新塑造现代美国国家的进程中,埃伯斯塔特报告至少是一个关键的环节,甚至可以说是起点。
美国是在珍珠港的硝烟中仓促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中美国政府在军事指挥体制、政府组织体制和决策程序方面都暴露出不少问题,特别是军种之间、军事部门和外交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而且缺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资源动员的组织机制。为此,在战争期间政府和军队都进行了不少临时性制度安排或者改组,比如“国务院、陆军和海军协调委员会”。战争临近结束时,美国政府内一些深谋国是的人就开始总结战时经验,并考虑在战争结束后对军队和政府的组织体制施行全面改组,以建立永久性的战争准备体制,确立适应“总体战”时代的外交国防的决策机制。二战中得来的教训,加上关于未来战争必定是以全面动员体制为支撑的“总体战”的判断,使得美国政府和国会就军队和政府体制改组的必要性形成广泛共识。这是埃伯斯塔特报告出台的大背景。一个小的背景是,当时“军种间战争”趋于白热化,海、陆军(当时美国尚无独立的空军建制)之间为了在战后军事体制和资源分配格局中占居更有利的地位,而争相提出各自的军事体制改组方案。为了对抗陆军方面提出的对美国武装力量实行一体化的改组计划,作风自信而强悍的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在1945年6月任命他早年的公司合伙人、老友和私人顾问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召集一个研究小组,就军事和政府体制的改组进行专项研究。
埃伯斯塔特在战争期间曾担任陆海军装备委员会主席和战争生产委员会副主席,对军队和国家体制已有成熟思想和诸多设想。他的组织哲学的核心在于“协调”一词,即认为当前体制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统筹协调,在军种之间,在战略、政策的规划和执行之间,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之间,在军事和经济之间,存在着妨害决策和执行的效率的鸿沟。二战以前,美国当然也有“安全”的概念(除了security之外,safety也常用),但“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词尚不通行。二战中,在对现代战争的总体战特性有了切身体验和更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美国政府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以“国家安全”一词为标号的政策观念(乃至于意识形态)。这种政策观念旨在超越和消除外交与国防、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传统区隔,以其内在的总体性、综合性以及背后强烈的危机感为特征。而埃伯斯塔特的工作小组和外围顾问人士的共识和出发点正是当时新近形成的这种国家安全观念。在进行了三个月的研究、讨论、咨询、分头撰写和统稿之后,9月25日,埃伯斯塔特向福莱斯特尔提交了最终报告全文。埃伯斯塔特在政府、商界和学界人脉深厚,可资其调动的智力资源甚为可观。这是一份着眼大局、通盘考虑,旨在对美国政府组织体制(而不限于军事体制)做出重大改组的蓝图,海军方面维护自身地位、阻止陆军改组方案的初衷在其中只占了极小的部分。
报告包括具体的政策建议以及讨论原则和历史问题的背景研究两大部分。其所申述和论证的要旨是,必须从广泛的和综合的观点看待军事组织问题,美国必须建立一个与其在总体战时代的国家目标相符的有效的组织架构,以及一个永久性战争准备和动员机制。报告认为必须扩大国家安全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并在这些机构之间建立协调统筹的制度化机制。在这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是新设一些永久性的机构,包括作为国家安全体制基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军事装备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等;设立空军,同时将武装力量组织为三个内阁级别的部即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并在相互之间实现更大程度的制度性协调。另一方面,报告还主张建立新的对国内经济、科技和意识形态资源予以全面动员的制度机制和长远规划,并通过制度化的顾问体系来保持和强化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调动和吸收各领域专家参与国家安全事务的运筹和操作。
这是一份强有力的报告。1945年12月,该报告由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公开发布,而福莱斯特尔和埃伯斯塔特为此进行了频密的游说和“教育”活动,在政府、国会和社会各界取得广泛支持。杜鲁门总统当时对埃伯斯塔特和福莱斯特尔的主张并不中意,而更倾向于陆军的方案。但是形势比人强,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实际上是以埃伯斯塔特报告为蓝本加以制订的。埃伯斯塔特报告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等都被此项立法加以确认。两者之间惟一重要的差异是《国家安全法》在军事组织的一体化上更进一步,设立了一个文职的防务首长,统领由三个军种部组成的一个松散的“国家军事组织”。1949年修改《国家安全法》,改“国家军事组织”为“国防部”。
埃伯斯塔特报告和1947年《国家安全法》奠定的美国国家安全的组织体制,几十年冷战期间历经局部修改而大体延续,以至今日。规模和经费支出都极其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五角大楼作为形象代表的那个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世界瞩目的运作帝国武力、筹划秘密行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还有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权力过大,对经济自由和民主制度构成威胁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或者“国家安全权势集团”,所有这些,对美国来说都是二战以后出现的新东西,或者夸张些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埃伯斯塔特报告的产物。
Report to Hon. James Forrestal, Secretary of the Navy on Unification of th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and Postwar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October 22, 1945,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Nav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45,此即通称的《埃伯斯塔特报告》
Jeffery M. Dorwart, Eberstadt and Forrestal: A National Security Partnership, 1909-1949,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