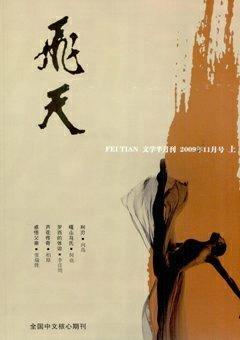诗歌的表达方式上的“温柔敦厚”观简论
路泉刚 蔡少阳
以“诗教”论诗是儒家诗论的重要传统,“温柔敦厚”说是孔门诗教的标准之一。“温柔敦厚”最早当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礼记》是汉人的作品,其所引孔子之语,未必一定是孔子的原话,但是“温柔敦厚”受孔子影响,是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概括和提炼则是可以肯定的。
熟参先人之论述,可知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其二是表达形式方面。于思想内容方面,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思无邪”可谓其最得当的概括。对此历来论述颇多,本文不做讨论。于表达方式而言之,笔者以为可以细析为二,即诗歌形式与语言。
闻一多先生曾说,诗歌有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作为建筑美的诗歌形式是诗歌不可或缺的,亦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被奉为“诗教”的“温柔敦厚”在诗歌形式方面亦展开了什么样的形式合乎诗教的争论,并且这一争论也是唐宋诗之争的内容之一。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顶峰,其诗风浑雅,贵蕴藉空灵。宋诗于唐代这一高峰上寻求开拓,另辟蹊径,其诗精能,贵深析透辟,形成在格律、押韵、用事等方面都显别于唐诗的新诗风。苏、黄是宋诗的最重要之代表,苏、黄之于宋诗,犹如李、杜之于唐诗。当苏、黄之世,宋诗业已成熟,苏、黄诗风极为流行,然其流弊也开始显现,批评之声也开始出现,张戒是其中之一。张戒《岁寒堂诗话》论诗以言志为本,以“温柔敦厚”之诗教为宗,反对苏、黄这种过分注重形式技巧,尚雕琢之诗风,他说:“用事、押韵,何足道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3]又:“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3]这一批评非常尖锐,深中时弊,表现出他反对这种只重形式美的倾向,要求恪守“温柔敦厚”之诗教。
对这种尚雕琢、重技巧的诗风,林弼在《跋丰城航溪朱光浮诗集后》中批评说:“诗本人情,情真则语真,故虽不假雕琢而自得温柔敦厚之意。”[4]林弼认为诗本于人之自然性情,要不饰雕琢才是合乎温柔敦厚的。古诗原本无论工拙,至律诗始有工拙之别,乃有古诗尚拙,律诗尚工的观念,计工拙则难免刻画,刻画便有可能不合乎所谓温柔敦厚之诗教了。
郝敬批评律诗说:“盖诗至近体,不免雕琢,更加凑砌,虽堆金积玉,兴味已尽,而葛藤蔓延,甚觉无谓。故余于长律,不甚解颐。”[5]郝氏不喜长律,因其雕琢,而喜“清婉流丽”之绝句,以其合于温柔敦厚,在他看来雕琢的律诗是不合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沈德潜在《说实啐语》中也说:“至有唐而声律日工,■兴渐失,徒视为朝风月、弄花草、游历燕■之具,而‘诗教远矣。”[6]也是认为讲求声律之工的律诗是有乖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
可见,古代的批评家以“温柔敦厚”来批评诗歌时,诗歌的外在形式也是其角度之一。律诗格律精严,因此律诗也成为了主要的批评对象。在格律、押韵、用事等这些形式技巧上,唐诗虽然也受到不合于温柔敦厚的批评,但是相对于“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宋诗而言,在形式的温柔敦厚这一点上,它得到了更多的肯定。清代方南堂的《辍锻录》中说:“诗莫盛于唐,而格律亦莫严于老杜,汉魏六朝而下,得风人之温柔敦厚和平之旨,舍唐其谁与归?”[7]这里方南唐便在形式技巧是否合乎温柔敦厚这一点上给予了唐诗很高的肯定。
郭绍虞说:“孔门诗教,可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兴观群怨说,一个是温柔敦厚说。”[8]作为“兴观群怨”说之一的“诗可以怨”,乍一看似与“温柔敦厚”不和谐,实则不然。“温柔敦厚”在表达方式上面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语言,语言选择上的“温柔敦厚”即是对“诗可以怨”的一种限制。《毛诗序》论诗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仪”,此七字可谓温柔敦厚的同义语。又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可见,“诗可以怨”是要以“温柔敦厚”为条件的。
山谷认为诗可以抒发诗人怨愤之情,然一定要注意语言的表达,要温柔敦厚。“不怨之怨”可谓是温柔敦厚的注脚。黄山谷虽肯定“愤世疾邪”的怨刺作用,但是反对谩骂,要求合乎温柔敦厚。
他认为诗是“人之性情”的体现,是自然而然的,但要使之“发乎情,止乎礼仪”,若“以快一朝之忿”而获罪,则是“失诗之旨”,不合乎温柔敦厚之诗教。
“诗可以怨”,可以刺,但是刺与讥是泾渭分明的,诗可刺而不可讥。史绳祖曰:“《诗》三百篇,只有刺而无讥。如刺者,与讥字义不同。《诗》注云:‘风刺谓譬喻不斥言也。岂讥刺之谓欤。”[9]严格区分“怨诗”与“刺诗”很好地说明了语言上的温柔敦厚之规范,对此,杨时说:“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讽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10]《风》是刺诗的典范,“主文而谲谏”,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才是讽谏之本旨,作诗之目的。若不懂得“温柔敦厚”之诗教,使“闻者怒之”,则有可能因文字而获罪。
在王鏊看来,刘禹锡与苏轼等因文字获罪,是不解温柔敦厚之诗教,非徒以小人之言。东坡文好骂,陆世仪《思辨录辑要》批评说:“东坡于文学何如?曰:东坡文,全是纵横,其诗则全是戏谑,无温柔敦厚之意,非圣门文学也。”[11]陆氏之论虽有失偏颇,然亦可见东坡诗之一斑。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慎重选择语言只为关键,尤其是讽谏诗,使其“发乎情,止乎礼仪”,一方面可使自己免于以文字获罪,另一方面可以显现含蓄蕴藉的审美特征,更为人所欣赏。
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黄庭坚一方面被张戒等批评悖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另一方面他又是“温柔敦厚”之诗教的推崇者,这是否矛盾呢?其实不然,从上面所引之论述可见,黄庭坚与张戒等人在论述“温柔敦厚”时其角度和所指是不同的。张戒等人是从诗歌的形式方面,即押韵、用事、格律等形式技巧,而黄庭坚是从诗文的言语方面,即如何选择和组织语言,以使文字和情感的表达不过于激烈。因此,黄庭坚被批评不“温柔敦厚”与他自己推崇“温柔敦厚”是毫不冲突的。
任何批评者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从自己的角度来展开批评的。张戒等人从诗歌形式的角度来展开论述,认为宋诗不合乎“温柔敦厚”的诗教,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宋诗的真实性,但是却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倾向。本文没有去辩驳他们观点的全面性、客观性等,只欲将从诗歌形式上来论述“温柔敦厚”的这一观念展现出来。也许只是片面的,但是确实是存在的。
【参考文献】
[1]礼记·经解[A].十三经注疏[Z].中华书局影印.1980.1609.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3.53.
[3]陈应鸾.岁寒堂诗话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0.16,36.
[4]林弼.林登州集:卷二十三[Z].四库全书本.
[5]仇兆鳌.杜诗详注[Z].北京:中华书局,1979.2329.
[6]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上[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6.
[7]方南唐.绰锻录序[A].清诗话续编[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35.
[8]郭绍虞.兴观群怨说剖析[A].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篇[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90.
[9]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一[Z].四库全书本.
[10]胡仔.龟山语录[A].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引[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22.
[11]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九【[Z].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路泉刚、蔡少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