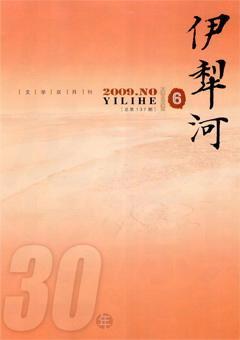花语
王 往
天刚亮,有雾,鸡鸣声在雾里碰碰撞撞。雾不大,薄薄的,轻轻的,东一块西一块挂在小树上,披在猪圈、牛栏上。雾里有麦壳和艾叶的焦味,淡淡的。好多人家门口都堆着加了艾叶的麦壳,那是夜里薰蚊子用的,有的还在冒着烟,直直地升上去。雾里还有微微的臊微微的酸,那是牲畜的粪便和树叶、青草混合着发酵的绿肥味。
天河醒了。他闻到了一股血腥味。推开西厢房,床上的知青小汪还在睡,地铺上的知青小仇也在睡,两个人身上都叮着一两只蚊子,肚子吸得圆溜溜的,他们也不知道。天河笑着说,嘿嘿嘿,叫你们睡,蚊子要把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血吸干了。
天河睡在堂屋,他把门板下了当床,很凉快。堂屋里已经透出亮来了,看得出门前的丝瓜架子了。天河站在门槛边,伸了个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身上来了精神。这时,天河又闻着了一股腥味,比刚才更大了。他扭头看了看东厢房,门关着。东厢房住着知青小潘,一个上海姑娘。小潘是有蚊帐的,怎么也有蚊子飞进去了?天河想肯定是美帝国主义放进去的蚊子,才那么厉害。
天河这样想着,就跨出门槛,站到丝瓜架前,握着拳头,举起来,喊了一声,“打倒美帝国主义”。喊完了,一摸肚子,瘪瘪的,就去菜园里找吃的。那条短裤,汗渍斑斑的,斜吊在胯骨上,他也不往上提。菜园很小,只有几张桌子大,蔬菜倒不少,有韭菜,有茄子,有西红柿,有黄瓜。瓜果都很小,天河找来找去,找着了一个拇指大的黄瓜,摘下来,“格崩格崩”嚼着。天河总是要找东西吃,能吃的都不放过,倒在牛屎塘里做肥料的豆饼子,拌在牛饲料里的棉花籽,他都吃。没得吃了,天河呆呆地站了一阵,然后,像想起什么大事一样,跑向小河边。
小河边有芦苇,有芋头,有河瓢瓢,有野蔷薇,有野草莓,有黄花菜,还有很多正在开花的小树和小草。晨雾里,那些花湿漉漉的,很干净。它们有的开在枝上,有的开在茎上。天河去掐那些花,喇叭花是黄的,尖鼓花是白的,木槿花是红的,苕子花是紫的。天河掐了一大把,用一根狗尾巴草缠好。他要把这些花放到小潘的窗台上。他每天早上都要给小潘掐一把花。
小潘和小汪、小仇住天河家两年多了。三个上海知青是那年春天来到赵庄大队的,那时候,赵庄的角角落落里都开着花。他们来到赵庄,最高兴的就是天河了。天河戴着柳条编的帽子,一头绿叶,像一个鸟窝。他跟着他们,不敢太靠近,隔着几步远。这几个人皮肤自,头发亮,衣裳干净又整齐,说着他不懂的话,让他好奇。他们当中的一个姑娘,小潘,走路很好看,腿长长的,袜子上,正对着脚股拐那儿有一朵小小的花。她的胳膊也长,一会儿指着树上的花,一会儿指着田里的花,笑着对那两个人说话。后来,小潘也折了几根柳条,编了一个柳条帽,然后,一转身,拿着柳条帽,对着天河晃了晃。天河嘿嘿地笑了一声,跑开了。三个知青都笑了,笑得很好玩儿。天河这下不怕他们了,又跟在了他们后头,靠得很近。知青们到了大队部,大队长就和几个干部商量着安排住处。天河站在门外,头伸向门框里,两眼直愣愣的。干部们商量了几家,都没有合适的。那时家家房子都小,孩子又多。天河说,住我家去呀,我妈煮饭给他们吃。天河这么一说,先有反应的是黄会计。黄会计说,大队长,你还别说,就数天河家最适合呢。大队长笑起来,让这痴子提醒了呢,对,去和赵婶说说,住她家吧。大队干部到了天河家时,天河已经跑在前头到家了,催着赵婶快快煮饭。
天河家有三间房子,草顶瓦檐,挨着主屋还搭了一大间锅屋。天河父亲去逝了,一姐一妹也出嫁了,这样住房就比人家宽敞多了。大队干部和赵婶说了,赵婶说好的好的,不嫌我家脏不嫌我家乱就来吧,我收拾一下就是了。这当儿,黄会计把天河叫到一边,说,天河,不要动不动就脱裤子,要是不老实,就把你绑起来去游街,听到没?天河说,我不脱,不脱。大队长也对天河说,记着啦,再脱裤子就把你绑起来。
天河是个花痴。22岁那年,他看上了相邻大队的姑娘眉娥,眉娥也喜欢,但是眉娥家里不同意,嫌他漂。漂,就是不本分、轻浮的意思。其实,天河不漂,就是爱打扮,爱热闹。他喜欢穿白衬衫,还把下摆扎在裤子里。他不爱穿布鞋和解放鞋,老是穿一双蓝球鞋,鞋带子系成蝴蝶扣。他身上总是藏一面小镜子,说照就照,脸上的汗疙瘩却越照越多。另外,他还爱跟着宣传队到处跑,看电影时喜欢给小丫头买葵花籽。眉娥后来嫁给本大队民兵营长的弟弟了,天河就急成了痴子。刚开始的时候,样子很怕人,有时走着就把裤子脱下来,担在肩上,跟着姑娘、小媳妇追。后来被人绑起来,打过几回,好了一些,但有时发了病,还是改不了。天河痴了以后,还有两个毛病,一是爱喊口号,二是爱给自己封官,一会儿说自己是民兵营长,一会儿又说自己是革委会主任了。
小潘他们三个知青住进他家后,天河就再没脱过裤子了。赶牛车的光棍赵大俞一看见天河就出坏点子,赵大俞说,天河,小潘在那儿呢,你去她跟前把裤子脱下来。天河摇着头,我不脱,我要是脱了,她会跑了的。赵大俞就从牛车上拿出东西,一个玉米棒子或者一个南瓜,对天河说,你去脱嘛,脱了就跑,脱了我就把这个给你。天河两手抓住裤带,往上提了提,我不脱,脱了她会跑的。
天河对知青的一切都好奇。小汪有个相册,他天天缠着要看,指着小汪的妹妹,说,这是眉娥,在上海工作;又指着小汪的女同学,叫小汪把她们介绍给他做媳妇。小仇有个笔记本,天河一得到手,就要在上面写写画画,说是给毛主席写信,请毛主席老人家让他去天安门站岗。小潘住在东厢房,她不让天河进她的房间,走一步锁一步。就是天河帮她掐了野花,她也是接过去就走进房间,不让天河跟进去。小潘只让翘嘴唇家的儿子谷小培进她房间。谷小培从不给小潘掐野花,她还是让他进去,教他作业,还教他唱歌。天河说,小潘,让我进你房间看看嘛,小潘说不行,不要进我房间啊。她不让天河进她房间,天河还是给她掐野花。晚上小潘放工回来,总会带一把野花回来,天河也早就准备了一把野花,小潘一进家门,天河就给她。小潘把那些野花插进缺了口的陶盆里,插进刷干净的酱油瓶里。每天早上,天河还要掐一把花,放在小潘的窗台上。小潘起来时,天河就会问她,小潘,这些花好不好看?小潘说好看。天河就很得意,说,是我掐的。队里的社员逗天河,天河,你怎么老是给小潘掐花?天河说,她喜欢花,她天天掐花回家。那她喜欢不喜欢你呀?天河嘿嘿笑起来,用花挡着脸,不回答。社员又问,那你喜欢她吗?天河不笑了,点着头,把花摇来摇去,说,喜欢,天天喜欢。你想不想她做你媳妇?社员又问。想,天天想。过了一段时间,再有社员问他为什么要给小潘掐花,天河就说她是我媳妇。有一回,人家又这样逗天河时,刚好被小潘听见了,小潘就竖起扁担,要打他的样子。小潘说,天河,你说谁是你媳妇?再瞎说,看我不打你!天河赶紧捂着头,说,我不说了,我不
说了,我媳妇是眉娥。周围人都笑起来,小潘也忍不住笑了。不过,小潘的笑只是在嘴角上一闪,很快就冷了脸,扫了那些人一眼,扛起扁担就走。那一回,天河掐了两大把花,比平时多了许多,小潘刚到家门口,他就把花递到小潘面前。小潘没有马上接,说,以后再不准瞎说了,再说我就打你,不要你的花了。天河说,我不瞎说了,我就掐花给你。小潘这才接过了花。天河笑着跑着去找赵婶,见了赵婶就说,妈,妈,小潘还要我的花呢!
有早起的人家开始打水做饭了,水盆碰着缸口,“丁零丁零”,在雾里响着。还有人在磨镰刀,“咝哗,咝哗”,也在雾里响着。天河闻着雾里也有血腥味了。他把花放在小潘的窗台上,就闻到了从窗子里发出的血腥味,很浓很浓。小潘的房间里哪来那么多蚊子呢?会不会把她和血都吸了?天河就去了锅屋,叫赵婶起来。天河说,妈哎,我闻到血味了,你闻见没有?赵婶光着上身,胸前挂着又黑又瘦的乳房,她叹了一口气,儿啊,你的病什么时候好啊……天河着急了,妈,你出来,你闻闻。赵婶出了锅屋,嗅了一下子鼻子,说,是有血味,儿啊,你在哪闻到的?天河说,妈哎,到处有哩,雾里也有,小潘的房间里也有。
赵婶扶着墙,走到东厢房窗下,嗅了嗅,就慌了,她叫天河去她床头把钥匙拿来。
天河拿来钥匙,赵婶已经在拍东厢房的门了,小潘,小潘,开门,开门。里头没有动静。赵婶打开门,房里有了一丝光亮。小潘斜躺在床上,手上尽是血,黑的血。赵婶把门开大了些,看到了地上的血也快到门边了。
赵婶往后一退,倒在天河身上。赵婶说,不得了啦……快去叫人啦……
知青小潘死了,自杀的,用蓝边碗的碎片割开了手腕。听说了这事情,最怕的是翘嘴唇。翘嘴唇叫甘凤芝,两片嘴唇又厚又黑,上唇翘得高,快挡住鼻孔眼了。小潘死了,翘嘴唇慌了一阵,赶忙押着儿子谷小培去了天河家。
昨天夜里八九点钟的样子,翘嘴唇揣了一条布袋,去了庄后的槐树林,槐树林尽头是玉米地,她想偷几个玉米。哪想进了槐树林,就听见知青小潘的说话声。不过没听清说些什么,翘嘴唇好奇,就弯着腰贴着树干,慢慢摸到那有声音的地方。到了跟前,声音没了,就见小潘和她的儿子搂在一起,小潘的手在儿子背上抚弄着。翘嘴唇大喊大叫起来。小潘和儿子就分开了,跑了。翘嘴唇追到天河家。翘嘴唇踢门,门不开,拍窗子,窗子不开。翘嘴唇就又拍腿又跺脚地骂开了。翘嘴唇骂人很厉害,什么脏话都骂得出口。一个大队的人都被吵醒了,整个上半夜,村庄里都是脚步声说话声。那个晚上,天河的话比平时少多了,他问那些围住翘嘴唇的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人理他。天河就爬到树上,倚着树杈唱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我是一个兵》。唱了一会儿,又对着树下的人叫:“还不回去睡觉,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回去睡觉哦,明天上工哩。”天河的话引来一阵阵的笑声。
天河家门前早就围了几层人。天色更亮了些,但雾还没散。门前的丝瓜花,一朵连一朵地开着。雾里晃着急急赶来的人影。天河站在他家墙角,见一个人就说,小潘死了,小潘死了,我和我妈发现的哩。
翘嘴唇一手拿着柳条,一手推着儿子。儿子高高的,比翘嘴唇足足高出一头,但是脸上还是嫩嫩的,才冒出软软的胡须。翘嘴唇推一下,儿子走一步,儿子停一下,翘嘴唇就推一下,再补上一柳条。人群往两边让出一条缝。翘嘴唇押着儿子到了天河家门口,猛地对着儿子抽了一柳条,“叭”一声响。翘嘴唇对儿子说,跪下!儿子就跪下了。
堂屋里,大队的干部们都来了。知青小汪和小仇掩着脸在哭。翘嘴唇擦了一下红肿的眼泡,你们都在啊,在就好!
翘嘴唇把柳条扬起来,对儿子说,小培,谷小培,你这个祸根,你给我说说,当着干部的面说清楚了,昨天晚上,小潘是不是叫你去槐树林里了?
谷小培低着头,不出声,肩膀在抖。
翘嘴唇“啪”的一柳条抽在儿子背上,你说啊,是不是,她勾引你,叫你到槐树林里了?
谷小培往前一倾,又挺直了身子,低声说,是的。
翘嘴唇看了一眼干部,又问儿子,她是不是在你身上摸了?说呀,当着干部面说清楚!
谷小培鼻子里发出哭声,是的。
翘嘴唇走到门槛边,一脚踩在门槛上,对干部说,大队长,黄会计,刘队长,马记工员,你们都听见了,是她小潘勾引我儿子的。我儿子才16岁啊,她多大了,她29了啊,她祸害我家儿子。我儿子这么小的人,懂什么……翘嘴唇说到这儿,一下子坐到地上,哭起来,一边拍着腿一边说,她勾引我儿子,我就骂她几句,她就寻短见了……我儿子名声啦全让她毁了。
大队长走出屋子,踢了翘嘴唇一脚,不要哭了,起来。翘嘴唇立刻就收了哭声,嘴里嘟嚷着,大队长啊,你要给我家小培证明啊。
大队长姓谷,和翘嘴唇是本家,按辈份,谷小培是他侄子。他点上香烟,轻轻摇着火柴棒,躲开周围人的目光,看着菜园边的一排柳树。树行间的雾还没散,树梢上湿湿的,冷不丁响起一声蝉鸣,很尖,又很短促。大队长把目光收回来,伸脚踢了一下谷小培的屁股,真是她勾引你的?
谷小培还是低着头,说,是的。
几回了?他又问。
一回,就昨晚一回。
怎么勾引你的?
给我吃大白兔糖,给我吃马头饼干,给我讲成语故事。
噢——,大队长拖着长长的声音,点着头。
这时候,天河钻到谷小培跟前,说。人家对你这么好,就摸你一下,你妈就骂人家呀,要是摸我,我妈就不会骂。
大队长朝天河一挥手,说,一边去。天河就往后退了一下。
大队长朝几个干部招招手,黄会计,刘队长,你们三个人和我上公社去一下,马上报告到革委会。大队长又看着蹲在地上的小汪和小仇说,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害入不浅啊,一下子就把人害死了。
翘嘴唇叫儿子起来,推着儿子往人群中钻。翘嘴唇说,儿子,大队长给你洗了清白了,你是上当受骗的。
太阳升起来了,薄雾很快就被收走了。村庄一下子明朗起来。树间的蜘蛛网在微风里晃动着。到处是鸟叫声。梧桐树上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社员都是向阳花》,喜气洋洋的曲子。有几个起早去拾粪的人,远远地看到村路上的人比平时多了很多,就把握在手里的粪铲插到了粪兜里,快步往回赶。
天河从五队跑到四队,从四队跑到三队,见人就说,小潘死了,是我发现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红袖章戴着,手里还拿着一个语录本。人家不理他,谁不知道这个事呢,他就扬起语录本说,你们知道么,是美帝国主义派人暗杀的。天河去二队时,碰上了光棍赵大俞。赵大俞正在门前刷牛毛上的泥块。天河不想理他,赵大俞却把他叫住了。赵大俞说,天河么,来坐坐嘛。天河说,我不坐,我有事呢。赵大俞自己先坐到牛车帮上,拍拍牛车帮说,天河。来坐坐,我不叫你做坏事,来嘛。天河看赵大俞脸上不像以前那样怪笑,不像要叫他做坏事的样子,就不怕了,就想把小
潘死了事说给他。天河还没说,赵大俞先开口了,天河,小潘死了。天河说,是美帝国主义派人暗杀的。赵大俞说,天河,你伤心么?天河说,等到公社让我当上民兵营长了,我就把美帝国主义抓起来。赵大俞起身,又去刷牛毛,刚刷了一下,就停下了,伸出一只手,扶在牛角上,对着牛说,小潘死了。
快到中午时,大队干部从公社回来了。天河也赶快跑到大队部去了。
很快,大喇叭里就想起了大队长的声音。大队长点了几个人的名字,都是木匠,让他们赶紧到大队部去一趟。大队长是叫他们给小潘打棺材的。
几个木匠赶到大队部,我望你,你望我,都不点头答应。
天河把头伸进门框里。直愣愣地看着他们。
木匠二保说话了,大队长,叫我们给伤风败俗的人打棺材,这心里有疙瘩呀。
其他木匠跟着点头。木匠五银就接过二保的话,大队长,为这么个人犯不着浪费人工、木料……
大队长就把脸转向黄会计,要不,连席子带被子好歹卷走算了?公社是让尽快处理掉的。
黄会计说,这个……
天河说话了,天河说,大队长哎,就给小潘打一口棺材呗,我家有树哩。
大队长看他一眼,挥挥手,天河,去旁边玩去。
天河说,你们不给小潘打棺材,我去找袁爷去,叫袁爷来打。
袁爷是老木匠,七十多岁了,家离大队部不远。天河跑到了袁爷家时,袁爷正坐在榆树下听广播,白胡子、白对襟褂,白拐杖。天河喘着粗气说,袁爷,没人给小潘打棺材哩,你去给他打,我家有树。袁爷愣了一下,问天河,谁说不给打的?天河说,大队说不打的,木匠也不肯。袁爷拄着拐杖站起来,说,我去大队部看看。
天已经很热了,头顶的太阳白花花。袁爷的白胡子、白对襟褂,白拐杖让阳光给照模糊了。袁爷的拐杖快速地点着地,天河还在一旁催,袁爷,快些走快些走!
袁爷到了大队部,将拐杖重重地在地上捣了一下。那几个木匠就低了头。其中有两个是袁爷的徒弟,头就更低了。
袁爷说,那个知青的事我听说了,一个人死了,要是随便卷了,没一口棺材,做木匠的还有脸吗?
大队长和黄会计也把脸别到一边。
袁爷说,人要积德,我就不信连天河都想到的事你们想不到。小潘是死在外乡的,谁能保证自己一定死在家里?
袁爷这话有骂人的味道了。两个徒弟先抬起头。一个说,袁爷,我们去打棺材,你消消气。一个说,袁爷,这事包在我们身上了。
大队长给了袁爷一支烟,说,袁爷,你放心了,这事我们会处理好的。
袁爷说,那就好,都回去拿家物(方言:工具)吧。说罢,转身走进白花花的阳光里。
大队长对黄会计说,那你就去负责这件事吧,早点把棺材打好,争取明天就下葬了。
天河跳了起来,拍着手说,打棺材打棺材,小潘有棺材了。
天河又在黄会计前头到了家。
黄会计到了天河家时,赵婶正在河边洗布头,她把屋里的血擦了。
黄会计让天河把她叫来。
天河就大声喊,妈,妈——
赵婶上了码头,两手在围裙上抹着。
黄会计叫了一声婶子,就抬头看菜园边的柳树,边看边顺着树往前走。
赵婶走到黄会计跟前。黄会计说,赵婶,想用你一棵树。
赵婶说,用树?
黄会计说,大队要给小潘打一口棺材。
赵婶说,行呢行呢,我没意见。
黄会计摸着眼前的大树,赵婶,这棵树就算20个工分吧。
赵婶说,用不着,黄会计,这树算我们娘俩送小潘的,小潘没少给我东西,给过香胰子,给过布,给过白糖……
天河说,是的是的。还给过我妈一面小镜子呢。
赵婶也伸手摸那树,手一放上去,眼泪就下来了。赵婶问黄会计,小潘家里人都不来?
黄会计说,不来,听公社的人说,她父母在江西呢,右派,一个哥又在北大荒。
黄会计说了这话,眼睛也湿了,叹了口气,吸溜着鼻子。
中饭一过,几个木匠就背着家物来了。斧子,锯子,刨子,凿子,锤子,一路闪闪亮亮的。木匠来了,天河又跑向袁爷家。袁爷睡在榆树下的凉床上,让天河吵醒了。天河说,袁爷,袁爷,木匠去打棺材了,给小潘打棺材了。袁爷笑笑,骂他,天问哟,你这痴子,这么大太阳你跑来做什么……天河嘿嘿地笑,我不热,不热,袁爷,我回家看他们打棺材了。袁爷没再理他,翻了个身,接着睡。
天河到家时,木匠们已经忙开了,有的在调锯弓,有的在磨斧子。天河就跑到树间,搂着用来打棺材的大树,说,你们看。多大!松开后,又去搂另一棵,说,这棵也大这棵也大!
黄会计指着那棵大树对木匠们说,你们先把树放倒,我去供销社买棺材钉子,晚上再给你们准备几盏马灯,大队长说了,争取明天上午下葬。
晚上九点,棺材打好了。几个木匠把马灯捻到最大火头,抬起棺盖试试,严丝合缝。二保拍着棺盖说,可惜了,要不是鲜木头现打的就好了,这东西一缩水就裂了。五银说,没办法,只好将就了。天河也摸着棺材,从这头到那头。一个木匠说,天河。我们马上就走了,棺材放你这里,小潘又在屋里,你怕不怕?天河说,不怕。
雾,早就升起来了,还是薄薄的。轻轻的。一地的刨花、木屑,发出淡淡的香味。马灯撤走了,周围显出比往日晚上更深的黑暗。赵婶点了两盏油灯。叫上小汪和小仇,去了东厢房。天河也跟着去了。赵婶在小潘枕边和脚头各放了一盏油灯。在当地风俗里,这两盏灯叫长寿灯,也就是上天堂的引路灯。赵婶说,有了这灯,魂灵才不会迷路,下辈子才能过上好日子。小汪和小仇扶着赵婶,呆呆地看着小小的火焰,看着躺着的小潘。天河看着陶盆里和瓶子里的花说,妈哎,我掐给小潘的花都枯了,我去给她换上好的花。
小汪、小仇坐在棺材边,天河也坐在棺材边,三个人围着一篮子野花,一枝一枝地理着,用狗尾巴草缠成一把把的花束。赵婶对小汪、小仇说,孩子,应该用白花的。小汪说,阿姨,这我们懂,可这是天河采来的呀。小仇学着当地方言说,大婶,小潘就喜爱各种各样的花。赵婶说,你们城里来的孩子有文化,说话有道理,也好也好。天河拿起一枝白花说,妈,这不是自的么?有白的哩。
他们劝赵婶睡了。小汪对天河说,天河,等到我们回上海了,也要带你去玩,好不好?
天河说,那我去了,你们带我去看花吗?
小仇说,要带的,带你去公园,那里有很多花的。
天河说,小潘也说要带我去的。
小汪问他,真的?
天河说,真的,有一回,我去掐花,她也在那里掐花,我看见她全着一枝花,淌眼泪,我就问她,小潘,你哭了,你哭什么。小潘也不告诉我。
她哭什么?小汪问。
她不说,就是哭。天河说。我就问,那上海有花吗。她说有。我就晓得了,上海也有花。我说,我也想去上海看花。她说,好的,以后我回城了,带你去看。
小汪说,以后,我们会带你去上海的。
天河说,我不去,小潘不去了,我才不去呢。
天又亮了。雾里还是以往的声响,还
是以往的气味。黄会计早早派人去挖坑了。坑挖在村庄南边的含沙河北坡上,朝阳,顺水,河堤上的一条大路通向公社,是个不错的地方。黄会计叫来赶牛车的赵大俞,负责拉棺材。黄会计对赵大俞说,本来想叫几个人抬棺的,一叫呢,又要闹着加工分,那几个挖坑的人已经加了一些工分,要是再加上几个拾棺的工分,就太多了,怕有人说闲话,叫你一个人就只算一份工,你吃点苦吧。赵大俞说,黄会计你不要说了,我不要工分,一个工分也不要。黄会计拍拍他的肩膀,大俞,我头回见你高姿态哟。
棺盖抬下来了,小汪、小仇、赵大俞、天河就去东厢房抬小潘。拾到棺材旁的时候,赵婶摸了摸小潘的脸,说,闺女,走好啊。小潘入了棺,黄会计说盖上吧,天河说等等哟,等一等。天河拎来一篮子野花,一束一束摆在小潘身边。然后,又把小潘养花的泥盆也搬去,放到脚头,又把养花的瓶子也拿来,放到枕边,都插上了花。
黄会计说,封棺吧。
几个人就抬上了棺盖,轻轻盖上了。木匠二保拿起锤子,把方肚尖顶的棺材钉往下砸去。丁——当,丁——当,一声声,在雾里起伏着。
这时候,天河忽然哭了,我媳妇呢,我媳妇不见了,啊啊啊……
没有人觉得天河的话不妥,都跟着天河掉下了泪水。
这一阵子忙碌下来,雾已退去,阳光从树梢透了出来,村庄一片明净。
赵大俞一抖牛绳,牛车的木轮“格吱吱”滚动了。小汪、小仇、赵婶、天河跟在牛车后。经过翘嘴唇家门前时,就见门关着,门口一只鸡也不见。赵大俞说,这家才像死了人。
牛车出了村庄,上了大路,赵大俞就哼起了小曲:
姐在南园摘石榴
哪一个讨债鬼隔墙砸砖头
不偏不巧砸在奴家头
咿呀喂,不偏不巧砸在奴家头……
这小曲叫《摘石榴》,流传在江准一带,歌词是带着调情味的,调子却是哀怨的。赵大俞的声音很小,词儿很含糊,只有那调子一波一折地走出来:
要吃石榴你拿了两个去
要想谈心你随我上高楼
何必隔墙砸我一砖头哟
呀儿哟呀儿哟
依得依得呀儿哟
何必隔墙砸我一砖头哟……
赵大俞一遍遍唱,小汪、小仇哭出了声。赵婶一个一个拍他们的肩,孩子不哭,不哭,人死了也是享福呢。其实,赵婶也在哭,泪水汪在她又深又黑的皱纹里。天河走到赵大俞身边,叫赵大俞把牛绳给他。赵大俞迟疑一下,点点头,让他接过去了。坑挖在村庄南边的含沙河北坡上,朝阳,顺水。
一到含沙河边,天河就去掐野花了。等小潘的坟圆了起来,天河也抱来了一大捧花。小潘的坟头就五颜六色了。
过了几天,有人看见天河在小潘坟前哭,逗他,天河,哭谁呢?
天河说,小潘。
人家又逗他,小潘是你媳妇呀?
天河说。不是的,她不肯。
那你哭什么?
我看见她就想哭。
天河经常去小潘坟上哭,每次去,都放上新掐的花。反正是痴子,人们当作笑话,看看算了。
那一年春天,含沙河边驶来一辆黑色的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位老人,他眼前的坟墓上簇拥着野花,每一枝都很鲜艳。老人用一块很大的的白绸,取走了墓中的骨骸。老人请村民将墓坑填平后,又安排司机去了县城。司机从县城返回后,老人的手里就多了一大束花。老人捧着花,慢慢地向村子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