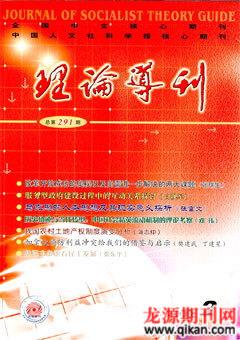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品性的逻辑特征
付粉鸽 杨玛丽
[摘要]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之所以如此,既与其独特的有机宇宙观密不可分,也与其阴阳和实生物思想直接相关,而由此形成的有机辩证精神更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宇宙在中华文化中不是机械的物理结构,而是生机勃勃、意趣盎然的生命场所。阴阳和合互相作用产生了宇宙万物,基于此种认识,中华文化形成了有机的辩证思想。这种辩证思想是有对精神、时中取向和发展创新品质的统一,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中华文化。
[关键词]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宇宙;阴阳;辩证;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2-0080-03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如一条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大河,在历史的流变中,始终保持着巨大生机和活力而从未中断,表现出极强的整合性、稳定性和创新精神。可谓生生不息、绵延不绝。那么,中华文化何以如此呢?
一、生生不息的本体追溯——有机的宇宙观
在中国古代先民的视野里,生命弥漫于宇宙中,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的生命场所。《诗经·大雅》有“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老鹰在天空自由飞翔,鱼儿在水中欢快地跳跃,《诗经》借鸟飞鱼跃说明宇宙间万物并生、生意盎然的气象。孔子则从经验性观察出发,赞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地宇宙是没有意志、默默无言的,自然的法则就是春夏秋冬四时的更替和万物的竞生并长,化生万物是宇宙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周易》中得到明确表达,《周易·系辞下》称“天地之大德日生”,指出天地的至上品德就是生养万物,天地间阴阳消长、刚柔相济,造就了一个万物竞长、生机盎然的宇宙,因此说“生”是宇宙自然运动变化的基本法则和品性,正所谓天地有其生生之德。这种生生之德使整个宇宙处于不断流动变化、创新不已的过程中。
古人的好生、生生思想被宋明理学家继承和发挥。理学家们一方面肯定宇宙就是一个生命场,处处皆有生意;另一方面将宇宙的化生与古代的伦理范畴相结合,从伦理的角度阐发这种生生之德,认为宇宙的生生之德就是善、仁,万物的孕育和竞生正是宇宙之善和仁的体现。“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二程集》)二程认为生化万物、创生不已是天地宇宙的根本品性。人如果能够顺承天地的这种品性,便是善。对于“善”的此种理解恰是中国文化有机宇宙论特点的体现。“善”不仅仅具有伦理道德意义,也是契合宇宙生成论的价值范畴。它不单是对道德规范的遵从和践行,同时也是对宇宙化生精神的承继和发扬。因此,生长、化生成为“善”的内在意蕴,这种化育万物的“善”就是仁,“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万物生机盎然是最奇妙的景象,这正是元为四善之首的原因,就是“仁”了。《周易·乾》“元、亨、利、贞”的卦辞被理学家视为四种品德,此四德俱善,而“元”居首位,因此元之善为长。程颢指出“元”作为四德之首,恰恰在于“元”代表着万物初生,体现了宇宙生生不已的气象。“仁”之本意在于生物,所以观天地间的生物便可体会“仁”了。程颢认识“仁”的此种特殊理路,代表了当时理学家们的共同方法,即从自然现象出发体察宇宙的法则与价值。周敦颐窗前草不除,说与自家意思一样;张载观驴鸣;程颢喜鸡雏初生意思可爱;程颐说观游鱼欣然自得,体验生意。理学家们视宇宙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场所,认为天地的伟大正在于到处都有生意,而这生意就是仁,他们将道德伦理学说与宇宙生成论统一,对于今天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今人深思。
生命的孕育和化生是天地德性的体现,天地的这种生养大德无穷无尽、没有止息,理学家朱熹的概括是一语中的:“天地别无所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朱子语类》卷五十三)因此,“宇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从来不是一个死寂的机械的物理结构,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生命场所。基于此,中国人的宇宙观从来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不是片面的而是整体的,此种有机宇宙观与西方人的机械宇宙观截然不同。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的:“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
二、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和实生物
那么,宇宙何以能化生不止、生生不息呢?古人认为宇宙是对立性因素的统一,其中阴阳之间的对立和互相作用是其化生的动力所在。阴阳,最早指山水的背向,后来常用于指代两种不同的性质。古人认为宇宙及其间的每一物,都包含阴阳两种属性,阴阳互相作用构成了宇宙及万物,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都认为阴阳相互作用化生宇宙万物,阴阳的相互作用就是宇宙之道。这个“道”就是宇宙化生之道,“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原善》)清代学者戴震将阴阳化生与宇宙生生不息的内在关联性明确地揭示出来,指出阴阳变化实质就是天地的化生之道,是天地宇宙不断产生和化育万物的过程。
基于此,古人在认识宇宙、探讨生命时,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阴阳,在阴阳的此消彼长中成就了生命。阴阳化生成就了宇宙生命,而阴阳往往多指两种不同性质的气,即阴气和阳气,“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人作为宇宙万类之一,也是阴阳之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气聚合便是生了,气消散了便是死亡。阴阳之气的聚合消散使生命持存消亡,在阴阳之气的离离合合中万物此消彼长,生生不息。
化生是在阴气与阳气的交感作用中实现的,阴阳之气交通成和万物生成,因此,“和”是万物生成的重要环节,也是生生不息的最佳表征。正是对生生不息的关注,“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和”思想可谓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就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和”指会合、包容,即不同的事物会合交融而使之均衡。会合不同事物于一处,然后才有新事物的产生,即“和实生物”。“同”指“以同裨同”,就是同一事物相加。如果将同一事物相加,则所得仍旧是原来之物,所以“同则不继”。“不继”即不能继续、不能生生不息。可见,远在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原因正在于其阴阳相“和”的品性。《国语》这种“和实生物”思想被后来思
想家继承和发扬。孔子将其概括为“和而不同”,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观。“和而不同”使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和吐故纳新能力,拥有自我更新能力,已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机制,在现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中仍起着积极的作用。
三、生生不息的方法论探寻——辩证精神
古人在认识宇宙天地化生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以阴阳为主要体现的矛盾性在事物发展的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有机辩证思想。这种辩证思想是有对、时中和创新发展思想的统一,在三者统一的基础上中华文化形成了一套辩证逻辑系统。从辩证逻辑出发,中华文化从不以孤立、静止、片面的态度去认识宇宙和万物,而总能从矛盾出发,在承认对立中追求和谐。正是这种对立和谐的有机辩证精神,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变易品质和变通精神,使中华民族从来不偏执,也不保守,而是立足整体,以开放的态度追求不断的发展。而这种有机的对立和谐精神在现代社会仍有其重要价值,为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有对精神
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已有了朴素的辩证思想,认为万物是对立性因素的统一,在对立因素的互相作用中万物生成和存在。由此,形成了有对思想。《左传》有“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这里“物生有两”的“两”即有对,《左传》认为每一物之所以存在正由于包含矛盾,矛盾、“两”是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源泉。道家的始祖老子更将有对贯彻于其思想的始终,从抽象的本体之“道”到现象界的具体存在,处处充满矛盾,事事皆有对立,恰是在矛盾对立中成就了万物。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第2章)有无互相生成,难易互相成就,长短互相形成,高低互相包含,音乐、声音互相合成,前后互相追随,从自然界到人事社会,任何一种存在无不如此,因此,矛盾及其对立是世界的永恒法则。
对立无处不在,而对立又以统一为前提和目标。由此,古人形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春秋繁露·基义》)汉代大儒董仲舒指出,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都是相对而存在,相配合而产生。因此,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必须有辩证的普遍联系观点,既能看到正,也能看到反,避免只抓一个方面或一点。宋代理学家张载将矛盾的这种对立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概括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没有矛盾之间的互相依存和相互作用,就没有事物。反过来,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如果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也就不会有对立面的互相作用,所以,事物与其矛盾的双方彼此不可分割,互相依赖。由此,张载又回到了古人的“和”思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有形象之物必是有对立面的,有对立面必然有相反性;有相反性就有矛盾(即斗争),矛盾变化发展逐渐会走向和解。“和”是万物运动发展的最终结果。
(二)时中思想
“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是一个单纯刻画机械变化的物理单位,更多是在体认自然变化前提下,表征人事活动与自然变化协调统一的社会性范畴。“因时制宜”是古人活动的基本准则。
《诗经·小雅》有“物其有矣,维其时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一方面指出合于时宜对事物存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人的活动必需灵活而机动,随机而成、待机而动,君子应该具备灵活应变能力。当然这种灵活的通变精神,也是每个人需要具备的。人只有顺应了情势变化,才能跟上事物的变化、时代的发展。“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尚书,说命》),考虑好了,再行动,行动一定得随时而变。《周易》继承了这种待时而变思想,并将其提升至宇宙论高度,以变易认识宇宙及其存在,正所谓“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周易·系辞下》)。《周易》以变为宇宙的普遍特性,因此,作为承天而生的人,就应该顺承变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周易,彖传》)能够通晓变化被《周易》视为人的最大德性,“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周易·系辞下》),穷尽神妙,知晓变化是最高的品德。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进一步将其抽象为宇宙的法则和大道,指出“道因时而万殊也”(《周易外传》卷五)。“道”作为宇宙和人事的法则是不断变化的,由此,形成了王夫之的进化历史观。与进化历史观相统一,王夫之主张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历史进步的时代潮流是不能违背的。在一定意义上,违时即背道,是与“道”的日新富有、趋时更新本性相违背的。正确的态度应是“因时制宜”、“与时行而不息”,不断地研究时代变化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思想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可称得上是“与时俱进”思想的古代表述,值得现代人学习和坚持。
中华文化虽然重视因时而变、权衡灵活,但却不是没有原则的肆意妄为,其变化是有原则、有要求的,这个原则和要求就是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管是因时而变,还是权衡随机都以适度为原则,以中正为目标的,即“随宜应变,在中而已”(《河南程氏易传·震卦》)。在古人看来,这种适度和中正恰恰就是天地的秩序和人类存续的法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因此,尚中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早在《尚书》就有“允执厥中”,指出要守住精细纯善的道心就必须坚持中道,不偏不倚、公正得当的行事。这就是后来儒家所说的“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即“中庸”。儒家认为,“中庸”不仅是君王执政的原则,也是普通民众处事的原则。甚至,不偏不倚的中道精神被儒家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孔子曾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叹息现实中具有中庸品德的人已经很少了,人们好像已经遗忘了中庸。后来的《中庸》甚至以此来区分君子与小人,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趋时而中,处处多方考虑,既不过分也不会不及,往往是恰到好处;而小人不知时中,只盯住一点不放,往往走了极端,违背了中正、适度原则,逾越了礼仪规范的要求。所以,要成君子须有“时中”的品质。在现实社会,不仅君子要能时中,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此品质。因为时中是对极端的克服,它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按辩证法来说,就是适度。时中即适度,是全面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告诉人们干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分寸。正由于具有了趋时而中的灵活变通精神,中华文化从不偏执和凝滞,也没有肆意和张狂,而一直在不断变化和更新,从而跨越了历史的局限,生生不息,在现代社会仍焕发着魅力。
(三)求新发展的精神
辩证的精神是一种发展的精神。在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中,新质的东西不断孕育、壮大,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创新,是辩证精神的逻辑必然。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注重创新,强调生生不已就在于不断创新,变中求新是中华传统文化熠熠生辉的亮点。这种变中求新的精神,被古人称为革故鼎新精神。
在中华文化中,从无形的精神和制度到民间百姓的日用生活,处处都在求新;对那些止步不前、沉迷守旧的行为,中华文化历来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因此,从上古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到《周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再到王夫之的“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内篇》),创新不已的思想已经渗透于各代文化中,成为超越于各代文化殊异性之上的一种共有品质。这种品质培养和塑造了一个拥有不断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民族,成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面对新的历史时代,中华文化特有的创新精神将又一次被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