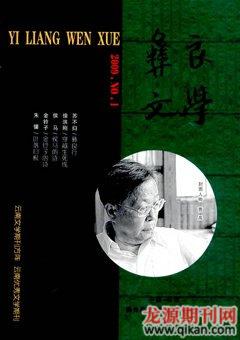低端访问:新长征路上的独唱
提问者:乌 蒙(北京)
回答者:陈衍强(云南)
访谈方式:时空连线
时 间:2007.07.16—17
问:你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诗人贾薇认为这与你最终成为诗人具有一定关系,你认为呢?
答:我在《卑微者》中写道:“其实我刚生下来/就开始廉价/但我不诅咒命运/把我降落在贫苦农家/我也不后悔只读过初中/对我有用的并非知识”。我认为只要骨子里就是一个诗人,不管出生在哪里都会成为一个诗人。
问:你是怎么写起诗来的?写下第一首诗的当时,你的心情有些什么微妙的反应?
答:一不小心就走火入魔了。我写下的第一首还不应该叫诗,而是一种打油或顺口溜的东西,正如“太阳出来红微微/好比豆瓣夹戈魁/东边一天出一个/落在西边一大堆”,虽然好听,但没有“太阳出来绯红/照在石头上梆硬”这样干脆和痛快。
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你游荡了大半个中国,有没有什么奇遇发生在你身上呢?这一段游荡之旅对你日后的写作有些什么启发?
答:有很多对我的误传。其实,我没有游荡大半个中国,只不过在1987年曾经西出阳关,就是从彝良坐班车到四川宜宾,又从宜宾坐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坐3天3夜的火车到乌鲁木齐,最后从乌鲁木齐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121团,现在想来真的幼稚和好笑。1987年的第一场雪,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往事;1987年的第一场雪,只剩下我写的《新疆》:“为了放牧爱情/我从成都火车站直抵天山下的冬天/只看见迷途的羊群上升的灯火/和在石河子的背上打滑的汽车/……这是1987年的疼痛/这是一首半途而废的诗”我觉得那是一次情感和时光的浪费,至今残留在心中的似乎只有:梦里不知身是客,醒来躺在大西北;不到边关,就不知天高地宽,就看不到800度近视的月亮……
问:你读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吗?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家的诗人还是一个在路上的诗人?
答:凯鲁亚克?这名字好怪哟!听都没有听说过,总之在我的老家叫不出这样的名字,所以不晓得什么《在路上》。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我是人在家中,诗在路上。
问:十多年前,你写过一首叫《小芳》的诗,一开篇你就这样写道:“整个中国都是农村/就算我在城里居住/也是被农民的骨头支撑的……”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已日渐稀少,请问你对这一中国现实如何看待?
答:《小芳》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抒情,发在《女友》上的。至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已日渐稀少和对这一中国现实的看法,我完全可以用我发在《大家》杂志的《农村现状》来概括:“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掉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掰包谷/夜晚守着三间瓦房/和两声狗叫”
问:你有阅读小说的习惯吗?哪些小说家被你青睐?你的不少诗篇读起来颇有小说味,是否得益于小说?
答: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那时看的多半是《高玉宝》《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之类。前几年喜欢读刘震云的小说,最欣赏他的《故乡相处流传》。我写诗没受小说的影响,但我的有些诗的确是小说的提纲,如果有耐心完全可拉长成为好看的小说。
问:你在写作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是起自语言还是形象?
答:好像莽汉诗人说过:写诗要用天才的鬼想像和不要脸的夸张。我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散打诗歌。如果要总结我的诗歌,其实就是两个字:“散打!”我拒绝诗歌理论,正如贾薇在评我的诗时说的“诗人比诗评家更懂诗”。什么是文化?我觉得四川李伯清的方言评书就是文化;啥子叫艺术?李伯清的那张嘴巴说出的就是艺术。
问: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称他是为一小群人写作的,那些人大都是他的朋友,请问你的诗是写给谁看的呢?
答:我希望我的诗能写给所有的人看,但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的诗歌很民间,所以可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君儿在评我的诗时一开始就为我惋惜:“我敢说,如果陈衍强把他的才华都用在‘刀刃上,20多年的诗歌创作,他应该早已是不争自成的‘真大师。”贾薇也说我“虽然多年来一直不被更多的人提及,但却一直拥有着最忠实的读者”。尽管我的诗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那些被“热捧”的诗歌除了“圈子”和“帮凶”又有多少读者会鼓掌呢?
问:你写过好几首以毛泽东为题材的诗,请问在诗歌以外,你对毛泽东作何评价?
答:毛泽东——一位爱幻想的诗人,一位用“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民间写作”的大师!其实,他更像一位在暗夜里高举光明的父亲。
问:我曾经听外省人说起,昭通出两种人,一种是土匪,一种是诗人。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答:昭通出土匪应该是解放前吧?那不是昭通的特产,座山雕就不是昭通的。昭通不仅出“云南王”龙云,还出国学大师姜亮夫,也出鲁迅文学奖得主,我的家乡彝良也出过些人物,如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的那位将军罗炳辉,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彝良的小草坝还是世界天麻的原产地,而且彝良不仅出英雄还出美女,在这种地方适合写诗,出诗人并不奇怪。
问:作为一个大山里的诗人,山对你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多久不爬山,脚底板就会发痒的体会?
答:山对我意味着什么?请看我写的《大山坡》:“大山坡是八十度的斜坡/只要刮大风下暴雨/不管根有多深的大树/都会四脚朝天/如果不是那些插进坡里的房屋/谁会相信大山坡上可以劳动/大山坡的人/为了播下的种子站住脚/每年都要挖出很多坎子/大哥在坎子上割草/不小心碰松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就会滚到坡底/砸烂小妹洗衣的瓦盆/他们恨透了大山坡/又无法离开/大山坡是他们的命根/一年的希望都长在上面/谁也不知道有多大的收成/大山坡的人/没有谁比他们更懂/爬坡腿软下坎崴脚/连发脾气也找不着一个坝子/真恨不得一脚把大山坡/踢到它的背面”只有在乌蒙山中,我才能写出如下的诗句:“群山拥挤着/压迫着我的呼吸和歌声/鱼的化石浮在空中/我的爱情没有边缘/只有天空才是我放牧的原野/我的幻想是流浪的风暴/在高原的尽头也找不到家园”
问:什么样的女人招你喜欢?在女人中间,你的表现如何?
答:当然是喜欢我的女人招我喜欢。至于在女人中间的表现,我脸皮薄。
问:如果故乡可以自主选择,你会选择什么地方作为你的故乡?
答:如果真有如果,我会选择离县城近一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回家看父母方便。
问:一些从不读诗的人,读了你的诗,觉得好玩,请问生活中的陈衍强是否也像他的诗那样好玩呢?
答:应该差不多吧,尽管我内心很郁闷。
问:你是否认为诗歌与人应该保持一致?能分析一下吗?
答:没必要保持一致,但诗人多半比其他什么人真诚是肯定的。正如我交朋友也是把诗和人区分开,因为有的人的确写过几首真诗,但人很阴很装逼很不好玩,而有的人虽然写的东西不能容忍叫诗,但为人厚道。
问:如果出门远行,时间无限宽裕,经济上也没有任何压力,请问你愿意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为什么?
答:当然是乘飞机,我是急性子啊。
问:你读后辈诗人的作品吗?他们中的哪些人令你产生“吾道不孤”的欣慰之感?
答:读!我最看好的是余毒,欣赏他的毒言毒语。此外还读猩猩他表弟、三个A、朵儿、嗄代才让、莫小邪、春树等的诗。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以前常读同时代人李亚伟、廖亦武、柯平、邵春光、宋渠宋炜、万夏、潇潇等的诗。
问:你有信仰吗?依你看来,从事艺术创造的人是否需要信仰?
答:不需要!
问:在你的生命中,爱情占有怎样的位置?说一说你的爱情吧。
答:爱情可能在别处。
问:你对目下的国学热怎么看?据说你不太喜欢读老外的作品。
答:这与我吃不来肯德基、汉堡包是一样的道理,我喜欢吃烧烤摊上的炸洋芋、臭豆腐。我虽然不会用一串老外的名字装门面,但我的书架上不仅有我读过的《金斯伯格诗选》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有我没有读完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梭罗的《瓦尔登湖》等。
问:美国诗人威廉斯说,酒精使世界缩小成微妙的一点。似乎诗人们都比较嗜酒,你呢?有无一边喝酒一边出口成诵的经历?
答:我只爱抽烟不好酒。我烟瘾越来越大,一天抽3包啊。我不喜欢喝高度酒,每喝必醉,难受啊!我不像有的人:“酒精虽有毒,不喝不舒服;酒是一包药,喝死当睡着。”
问:在古代诗人中,谁的心性与你最接近?
答:李白、李渔、白居易。
问:你在美食方面的造诣如何?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写作有些什么影响?
答: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吃粗茶淡饭长大的,没有李渔的雅兴和口福。我不是饮食影响写作,而是因为写作常把饭菜忘在饭桌上。
问:工作之余,你最喜欢玩儿什么?级别如何?
答:前几年喜欢打不带赌博的双抠、斗地主,现在因为工作清闲所以喜欢上网。
问:你的家人知道你写诗吗?你有无把你的诗念给他们听过?他们理解你吗?
答:我的家人当然知道我在写诗,但我没念给他们听,因为他们对诗不感兴趣。我儿子认为我写的不是诗,因为我的诗与他在小学课本上看到的的诗不一样,我的诗字数不整齐而且不押韵啊。
问:当代中国诗人中,你认为哪些是在严肃地尝试做一些诗的工作?
答:中岛、徐江、黄礼孩、赵思运、李霞、小鱼儿、任意好……
问:什么时候你的想象在起作用,什么时候它受到压制,逆境能感觉出来吗?
答:心情好的时候写出来的诗要晴朗一些,心情糟的时候写出来的诗要阴暗一些。我多半是愤怒出诗。
问:作为一名始终奋战在写作第一线的诗人,你对从经济领域归来的“还乡团诗人们”用钱砸诗的行为有何评价?
答:我先摘录海男2005年给我的信中的一段话:“多年来我一直关心着你的写作。彝良对于我来说并不遥远,因为,陈衍强一直坚持在那座滇东北小县城写作,你应该是少数坚持下来写作的人。”至于你说的用钱砸诗,我与他们不一样,所以我无话可说。你可能不知道,我用一个人的工资养一家三口,还要报答在乡下种地的年迈的父母,活得很不容易。
问:你信任诗朗诵吗?你如何看待诗和朗诵的关系?你的朗诵水平怎样?
答:我的每首诗歌开头基本没有“啊”字,不太抒情,只适合用云南靠近四川的方言说出,如用普通话朗诵就仿佛让梅兰芳演李達或刘德华演蒋介石,有可能变成“恶搞”,因为我的很多诗只有视觉上的快感。再就是我讲不好普通话,如果硬要我朗诵,我的诗只能朗诵给四川方言语境的人听。
问:写诗二十来年,“为什么要写诗”对你是否依然是个问题?如果拿写诗和人类的其它活动相比较,你认为写诗与什么最近似?
答:诗是我表达我想法的最好方式。我的经历,我的痛苦,我的隐秘,只有诗歌才能帮我说出。写诗和人类其它活动没有可比较的,尤其不能与演唱和体育相比,永远达不到万人喝彩的效果。写诗永远是孤独的,是一种不声不响的表演,是一笔倒贴黄瓜二条的买卖。
问:在物质上,你的梦想是什么?在面临需要大把花钱的消费时刻,你是否有李白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
答:谁不想当富翁?谁会与钱过不去?但不可能个个都能够乱搞乱发财。
问:想过有一天不写诗吗?如果不写诗,你认为干什么最适合你?
答:我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只要还有想象力,就会把诗歌坚持到底!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如果不写诗该去干什么,总之,我是一个不想干大事也干不了大事的散打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