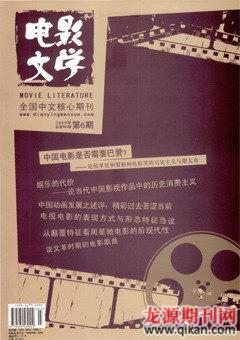以“杂化”僭越“边界”
苏东晓
[摘要]《喜马拉雅王子》以多重杂化的方式试图僭越东西方边界的表述策略为中国电影如何在后殖民语境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探索。从文学叙事的层面上看,它叠加了西方经典叙事结构与东方文化主题;从影像叙事的层面上看,它叠加了西方经典叙事结构和东方影像;从民族认同的层面上看,它叠加了西方“东方主义”的凝视与东方的反凝视。
[关键词]杂化;后殖民语境;表述;中国电影;《喜马拉雅王子》
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在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国际影展上获得了奖项,更有一些甚至进入了西方电影市场并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针对这些情况,电影界和文化评论界都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和总结经验教训,试图闯出一条中国电影的自强之路。电影界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更重视自身创作的电影是否能获得国际大奖,是否能打入国际市场获得可观票房;而文化评论界从理论的高度出发,更关注从“中国电影走向国际”这一命题抽象出来的民族身份的认同,东西方对话等关乎民族自立、自尊和自强的问题。
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之下,早期获得国际认可的中国电影,以张艺谋为代表,被看做是以东方奇观,尤其是落后隐秘的东方陋俗来满足西方的猎奇欲和偷窥欲,从而获得认可,这是在西方“东方主义”的逻辑下滋生出的一种自贬式的“自我东方主义”,因此,张艺谋早期的探索并未得到完全的认可,并不被看做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示范之路。但是,如若没有东方主义的审视眼光,过于单纯的民族性直接走向国际并不是最佳的路径,因为,两个过于陌生的文化是很难交集并产生对话和交流的。交流存在,在逻辑上就必然区分出自我与他者,文化交流是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间的流变,流变的实现,必然要求双方对彼此都有兴趣。在东方主义的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兴趣点猎奇与窥视欲必先于理解与尊崇。于是,在实现第一步跨越时,暂时的低姿态或迎合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绝不是长久之计。
有评论者认为,张艺谋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努力走出过往的以单纯的民族性获得西方“东方主义”目光的关注这一模式,但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舍弃民族内涵追求所谓的“世界性”。在其影片中,张艺谋无意探究中华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内在性”,只是把中国文化的外部特征影像当成一种代码,以表征某种带着普泛性的概念、意念,如其一度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英雄》,秦王、侠客、武功都只不过是表述其“和平”概念的影像工具。这使其与好莱坞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中国元素影片并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区分。在这里中国性的元素仅仅是供“他性”消费的对象,并没有赢得更多主导地位和自我表述的尊严。
那么,后殖民语境下弱势者如何巧妙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呢?有研究者在研究后殖民史诗时指出了后殖民史诗创作中的双重化叙事策略。所谓的“双重化”,指本土经验的表述与西方经典之间的转换关系。研究者指出,如沃尔科特这样的后殖民作家,他们大都受过西方教育,运用西方强势语言创作,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借用或挪用西方经典中的形象、结构、体式等为自己作品的结构框架和叙事要素,但他们所写的却是发生在本土的事件或本土经验。于是,这种本土经验由于借助了西方经典已被公认的话语权力,就被扩展或上升到某种普世的高度,使之具备了某种跨文化的传播能力,从而使得长期被压抑的声音为世界(主要是第一世界)所听见,而这种叙事(或许应被称为反叙事)反过来又形成了对经典文本的一种改写和颠覆。正如南非作家J·M·库切所说“对于一种权力神话的回应不一定是反抗,因为如果这种神话预言了反抗,那么反抗只能加强这种神话,神话科学告诉我们,一种巧妙的反抗是颠覆和改写这种神话”,而如沃尔科特的方式就是一种巧妙的反抗,用拉什迪的话来说就是“逆写帝国”,即在不断地颠覆和改写神话的同时,创造自己所属的民族或族群的神话。后殖民史诗这种双重化叙事的策略可以移用到中国电影的表述中,实际上,中国电影工作者有意无意地也在实践着这样的表述策略,而胡雪桦导演的《喜马拉雅王子》就是实践这种表述策略的典型例子。
《喜马拉雅王子》的模式实际上与上述后殖民史诗的叙事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双重化”叙事,一种本土经验与西方经典的结合,从互文中获得转换、跨越的自由,而因其是一个影像的文本,它又比文学的文本更多了另一种力量,有了新的变奏,因此,笔者更愿意将其称为一种以多重的杂化试图僭越东西方边界的叙事模式。
《喜马拉雅王子》叙述在波斯求学的西藏甲波王子拉姆洛丹惊闻父亲去世的噩耗,回国奔丧,却发现叔叔克劳盎已登上了王位,并娶了以前的王后、自己的母亲,如同《哈姆雷特》一样,老国王鬼魂显灵,告之其死亡之谜,并要求他为父报仇,拉姆洛丹也同哈姆雷特一般,陷入犹豫的延宕中,并请来戏班演戏,以图刺探真相,之后又误杀情人奥萨鲁央之父波拉尼赛,最终在与奥萨鲁央之兄雷桑尔决斗中完结悲剧。《喜马拉雅王子》的情节与《哈姆雷特》如出一辙。除此之外,《喜马拉雅王子》的人物名字及台词与《哈姆雷特》更是非常地相似,几乎就是《哈姆雷特》的翻版。人物名字方面,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名字都与原剧谐音,很容易让熟悉《哈姆雷特》的观众对应上原剧中的人物,如:哈姆雷特——拉姆洛丹,奥菲利娅——奥萨鲁央,克劳狄斯——克劳盎,波洛涅斯——波拉尼塞。而在台词方面,虽然不是机械地照搬原剧,但很多地方仍保留了原台词中的核心隐喻,同样很容易让熟悉《哈姆雷特》的观众对应上原剧的片段,如哈姆雷特(拉摩洛丹)装疯中的一段对话:
《哈姆雷特》:
波洛涅斯:你认识我吗,殿下?
哈姆雷特:认识认识,你是一个卖鱼的贩子。
波洛涅斯:我不是,殿下。
哈姆雷特:那么我但愿你是一个和鱼贩子一样的老实人。
波洛涅斯:老实,殿下!
哈姆雷特:嗯,先生;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
《喜马拉雅王子》:
波拉尼赛:您认识我吗,殿下?
拉姆洛丹:认识认识,你是一个奴隶。
波拉尼赛:殿下,我不是……
拉姆洛丹:那么,我但愿你像奴隶一样是个哑巴。
波拉尼赛:我也不是哑巴,殿下!
拉姆洛丹: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哑巴。
《喜马拉雅王子》无论从故事框架、人物还是台词等方面都沿袭了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并且在影片开场的电影字幕上也清清楚楚地打出“根据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改编”的字样,在电影的宣传上也借改编自莎翁名剧(《哈姆雷特》为自己壮声势。借助这样一个经典文本,《喜马拉雅王子》的表述就获得了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能力,使其所叙述的故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深受西方影响的东方都不存在理解上的难度。在此基础上,胡雪桦把《喜马拉雅王子》故事的场景搬到了古代西藏,让哈姆雷
特穿上了西藏王子的锦袍,西藏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雪域高原旖旎的风光和民族、宗教、风俗人情散发着无尽的魅力,喜马拉雅王子——拉姆洛丹的复仇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神秘之地展开,借助着东方的影像和声乐以及东方智慧与哲理,哈姆雷特的复仇实现了一场华丽的东方转换,换言之,《喜马拉雅王子》借助东方的文化主题、东方的影像和声乐改写了西方的经典文本,并在这种改写中颠覆了西方中心的话语权,创造出东方民族自我的神话。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东方文化主题对西方经典的改写与颠覆。
《喜马拉雅王子》虽然借用或挪用了西方经典《哈姆雷特》中的形象、结构等为自己作品的结构框架和叙事要素,但在处理两剧共同的“复仇”主题上,《喜马拉雅王子》用本土经验改写了《哈姆雷特》中的西方经验,建构了“复仇”表象背后的“爱与宽容”深层动因。这种改写主要表现在几个人物形象的变奏上。
其一,不同于克劳狄斯,克劳盎不再是篡位夺权的阴谋家,而是为了保护爱而陷入杀戮的悲情人。胡雪桦表示:“原著对于叔父和王后的勾勒是相当不合情理的,作为王后怎么会那么快投入杀死自己丈夫的凶手怀中?我一直觉得这是相当牵强的,至少莎士比亚对这两个人物的处理是含糊的。在《喜马拉雅王子》中,叔父不是个单纯的反派角色,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爱的人们。这样的理解也是我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于是,克劳盎的杀兄夺位娶嫂就有了一个深受同情的理由:原来,王后和克劳盎曾是两情相许的痴情恋人,只因王兄横刀夺爱,棒打鸳鸯,有情人未能成眷属,隐忍17年之后,王兄还要恶毒地惩罚这对藕断丝连的有情人。克劳盎选择了杀戮,是为了保护爱。在最后,克劳盎的死也不是畏罪自杀,而是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以爱的名义犯下的罪孽赎罪。其二,不同于哈姆雷特,拉姆洛丹在复仇过程的延宕中表现出来的不再是冷漠与厌世的情绪,不再是在人文主义者的悲天悯人与父仇不可不报的传统伦理相互抵触中步步被动地走向悲剧结局,而是在爱与宽容的博大感召下逐渐成长成熟,最终完成了精神上的升华,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救赎。最后,不同于《哈姆雷特》,《喜马拉雅王子》中出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狼婆,每当仇恨的火苗燃起,纯洁的甲波天空出现阴霾时,狼婆辽远深邃的声音就响起,她是洞明一切的先知,是光明的引路人,是爱的化身,她在拉姆洛丹心中浇灌爱的种子,引导她宽恕心中所恨,当先王的鬼魂谴责狼婆:“拉姆洛丹是我的儿子,你在教他什么咒语?”狼婆回答说:“爱,博大的爱。”狼婆的出现,将《喜马拉雅王子》“爱与宽容”的主题突显得更为明确。
《喜马拉雅王子》主题的变奏是多种东方哲理浸润的结果。有评论者认为,《喜马拉雅王子》浸润着藏族“苯教”文化与汉族儒道文化的精气。儒家文化主张“人性本善”,主张“仁爱”,道家崇尚“道法自然”“返璞归真”,苯教关注生命的延续,因此,《喜马拉雅王子》中才不会在王后与克劳盎的恋情是否合法,拉姆洛丹是否是真正的王子,拉姆洛丹的非婚生子是否能合法地成为新的甲波王等问题上陷入伦理道德层面的纠缠,才能将一场兄弟阎于墙的权力之争演绎成一场令人动容的爱情之争,将一场尔虞我诈的宫廷悲剧解构成一场关于人在爱与宽容灌浴下的成人礼。此外,影片的结尾,在壮美的金色阳光下,狼婆高举襁褓中的婴孩,拉姆洛丹含泪宣布新一代甲波王的诞生,这不由得不让人想起了中国古典悲剧中大团圆的其结尾。
《喜马拉雅王子》以西方经典叙事结构为自己作品的结构,同时又通过巧妙的改写,颠覆了西方经典的主题,用东方文化的内核浸润了西方叙事结构的外壳,这种杂化的叙事方式使得西方话语不再只是东方族群表述自我的压抑者。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东方影像与声乐对西方经典的改写与颠覆。
《喜马拉雅王子》在内在的叙事结构上借用或挪用了西方经典《哈姆雷特》,但在外在的影像和声乐的呈现上却是地道的西藏故事。《喜马拉雅王子》的故事发生在西藏,在故事的进程中,大量的西藏自然风光出现在屏幕上,广袤的高原、湛蓝的天空、绵延的雪山、明净的池水、血红的斜阳、时没时现的狼群,一幅幅壮美的图画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美感;故事中的人物穿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衣饰、说着地道的藏语、按照藏民族的风俗喝酒、格斗、祭祀,酒仪中的那种豪情、格斗中的那种狂野、祭祀中的那种震撼人心,伴随着低沉的号角、有节奏的鼓点以及富有西藏风情的宗教音乐和舞曲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些景观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它们可以称得上是“东方奇观”,有着满足西方他者的东方想象的一切因素,用西藏的“纯净”、“神秘”和“野性”满足西方对原始自然的一种回归情怀。另一方面,我们毋宁可认为这些“东方奇观”同样也具有“反凝视”的功能。这主要归因于电影影像的衍生性。歌德说:“观念在形象里总是永无止境地发挥作用而又不可捉摸,纵然用一切语言表达它,它仍然是不可表现的。”爱森斯坦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奥斯图热夫的‘吐词并不比歌舞女主角的紧身裤的颜色更重要,敲打定音鼓同罗密欧的独白作用相同,炉边蟋蟀声也并不亚于观众坐席下面的爆炸声。”而吉尔·德勒兹则说:“这电影的新时代,这画面的新功能,是一种感觉教育学,这种感觉教育学代替了支离破碎的‘世界百科全书。”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评价一部电影时,不能只着眼于它其中的角色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还要看电影屏幕上展现的全部影像,聆听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声音,这些因素并不比台词情节次要,它们同样具有无限的意义衍生空间。而影像的衍生性源生于电影的仪式化,电影不同于文学文本,也不同于日常影像,它具有将影像“仪式化”的功能,影像一旦被“仪式化”以后,它就具有自己的独立生命,它不仅属于某一部影片的某一个情节,而且从故事的链条中挣脱出来,从而衍生成为一种隐喻,具有多样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通过电影的仪式化,《喜马拉雅王子》中的东方奇观也衍生成为一种隐喻,不应只被看做是在西方“东方主义”的逻辑下滋生出的一种自贬式的“自我东方主义”的表述,还应被看到其建构积极的自我民族想象的一面。因为西方的“东方主义”中诚然有猎奇欲和窥视欲,也还有通过他者反思自身的诉求,迎着西方审视的目光,强化民族优秀面的自我想象无疑也能反击他者不怀善意的“凝视”,雪域高原的纯净、神秘、野性不正是异化的现代西方所或缺而渴望回归的本真吗?那么拥有如此本真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凭此而骄傲呢?这就是所谓的“东方奇观”自身所具有的“反凝视”性。因此,在西方“东方主义”的眼光注视下,以东方奇观为载体也可以成为增加东方族群自我表述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正如上述,《喜马拉雅王子》本身也已完成了东方文化主题的嬗变,那么也就是说,《喜马拉雅王子》中的东方奇观就不仅仅是因影像本身的衍生成为隐喻而获得颠覆性的,而是在其叙事本身就已获得了颠覆性的意义。于是,《喜马拉雅王子》中的东方影像和声乐也就不再是所谓的自贬式的“自我东方主义”,而是借助“反凝视”不仅实现了对原西方经典叙事的改写和颠覆,并且因此增强了这种改写和颠覆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统合以上两个层面,我们可以说,《喜马拉雅王子》有几重叠加的文本。从文学叙事的层面上看,它叠加了西方经典叙事结构与东方文化主题;从影像叙事的层面上看,它叠加了西方经典叙事结构和东方影像;从民族认同的层面上看,它叠加了西方“东方主义”的凝视与东方的反凝视。这多种文本的叠加,使其意义得以拓展衍生,各自文本间的旧有疆域因此被跨越。这就是《喜马拉雅王子》以多重杂化的方式试图僭越东西方边界的表述策略。
综上所述,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所谓强势者向弱势者倾轧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面对这种必然的趋势,弱势一方的态度却可以有多种,两种极端的态度分别是:全面屈服,惟强势者是从或者强烈抵制,闭关自守。事实证明,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面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弱势一方不是要在迎合或抵制中构建自己的民族想象,而是要学会如何在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存在的现实中,既能确立自身的民族身份,又能够与强势一方达成某种对话,使得文化流向的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间交流、沟通和融合,真正达成民族的自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电影进入国际市场面对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后殖民语境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而海归导演胡雪桦的藏语电影《喜马拉雅王子》以“杂化”僭越“边界”的表述策略为此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