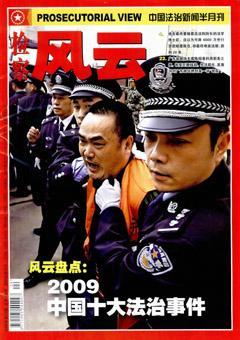元代制瓷大师吴益子及其后代
巴土嘎.刘


在元代制瓷历史上,有一位不但本人,连子孙数代都留下盛名的制瓷大师,他就是江西省浮梁县瑶里村的吴益子。他生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殁于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享寿86岁。
吴益子,本名叫吴灵四。按照吴氏历来的孝、义、忠、勇的祖训和吴氏宗谱排法,本人名之前,须排有个父名,称“某子谁谁”。大师父亲名叫吴进益(一作吴益),故他对外称自己是“吴益子”,很少写自己的谱名“吴灵四”。
吴益子大师的远古祖籍,在太湖北侧梅里,即今江苏无锡。后祖上迁居到安徽新安休宁县。元至元末元贞初(1294—1295年),休宁吴门七十四世公的四世孙吴涛子汉、吴涛子海、吴睿子湖、吴益子灵四叔伯兄弟四人,迁往江西浮梁县。第二年(1296年),吴益子到江西金溪县拜师,学习烧造陶瓷。学徒七年期满,把家安在浮梁景德镇石板桥(今十八桥)后,仍返回金溪,与师父合伙经营作瓷营生。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初十病殁,葬于浮梁县辛正都瑶里的缑岭尖山中,子孙从此落户到瑶里。
他是有记载的元代著名制瓷大师的首位嫡传弟子。师父仅年长他8岁。因他在前朝南京做过学生,在瓷业师徒中,诗词文采算是上乘,颇得师父和师父的四师兄弟的青睐。他的制瓷经历,不但可以作证他师父的部分生涯历史,也可印证元代制瓷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变化。他留在元瓷上的铭文词句和他的精瓷作品,对复原元代景德镇及景德镇以外某地窑场的制瓷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器底铭文的研究价值
先辈留下的元代瓷器中,有四件一套硕大的白釉龙纹釉里红盖罐,说是从吴益子后人手中购得。其中一件,器底有25个字的铭文:“江南金溪九峰东轩,弟子吴益子谨记,至正八年五月良辰吉置”。
可以想见,吴益子大师在半个多世纪的制瓷生涯中,亲手烧制的瓷器,一定不在少数。也许是他为人不事张扬,致使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留有他自己姓名的款识铭文瓷器,十分罕见。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目前能看到的,除了师伯亡故时,奉师父之命,他作过哀悼的祭文外,便是在师父大限到时,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仍不忘师恩,亲手烧制了追思师父恩德的硕大釉里红盖罐。
虽然仅是这两次留铭,却直接和间接地反映出元代初期和中后期制瓷发展的某些情况,解答了几百年来令人们不解和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
早在父辈开始考查吴益子身世的80多年前,在那时,景德镇年过八旬的老瓷工中,还在重复着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说一位首创大匣钵、发明烧造各种釉色大器的元代著名瓷器大师,有师兄弟四人,后来加入了一位带着侄儿在瓷器上写字作画的及第进士,共师兄弟五人。
后来,经过我们考查证实,这位专在元瓷上写字题笺的人,系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陈文龙榜的徽州休宁籍进士黄雷履。他的侄儿黄秋江(又称黄清夫、黄一清)跟随他,为元朝新开的官控窑场作画题字。顺帝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74岁的黄秋江去世后,又有吴益子的好友、清江人刘永元跟随吴益子学习作瓷,在瓷胎上作画。与刘永一起出入窑场画房的,还有他的结社好友,游戏人生的杨谦、杨士弘、彭镛等人。
元大德四年(1300年),吴益子的师父的大师兄熊德方病故,师父和师叔王厚伯合送了两对蒲公英云龙纹大瓷瓶,用以镇墓。而尚在学徒期的吴益子,因诗词文采,便代表师父、师叔和他本人,撰写悼文。把悼文落写在胎坯上的,便是这位前朝进士黄雷履。
1300年在金溪窑场烧制的这对青花缠枝莲蒲公英飞凤云龙纹象耳瓶,左右两个瓶颈上都有铭文。
右瓶颈上的铭文,是:
“孺人之德,均且壹兮,佳哉金牛;葱且郁兮,惟德故寿,天可必兮;子子孙孙,安且吉兮。前京学生吴益子啜书。前进士黄雷履题笺。”
左瓶颈上的铭文是:
“江南金溪九峰东轩,奉圣翁弟王厚伯,喜舍香炉花瓶一对,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大德四年二月良辰谨记。故孺人翁兄熊德方打供。”
1300年在金溪窑场烧制的另一对同样纹饰图案的釉里红釉、青花字象耳瓶,两个瓶颈上,也有基本相同的铭文。
我们是2005年春上在田助忠的书中看到这两对象耳瓶和铭文的照片。起初,从照片上看,我们认为这是有相当功力者制作的高仿品。因为国人的想象力和仿冒能力太强,只要实物一公开,仿冒随即问世,两者几乎是孪生兄弟。但是,在我们比对了大德年间金溪窑场制瓷情况、吴益子当时的身份、制瓷大师及其师兄弟在大德年间的变化等后,我们很快否定了最初“不看真”的看法。原因是:
在我们没有公开我们两代人对元代金溪窑场的调查情况,也丝毫没有披露元代几十位制瓷大师经历的情况下,没有人知道金溪县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元代烧造大器的窑场;也没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承认元大德年间金溪窑场烧造的元青花大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很少有人知道大师中有叫吴益子的,那时仍在学徒;没有人知道南宋咸淳年进士黄雷履为什么会跑到外省的窑场去;更没有人知道制瓷大师熊德方病殁于大德三年(1299年)冬;也不会有人能编造“佳哉金牛”等重要字句,却不懂其真实含义等等。
当然,本文发表后,会有多少“同样”铭文的瓷器出现,就不知道了。这也是几十年来我们不敢把几百万字的调查结果和盘托出,只能一点一点地披露的原因,尤其是近些年来,没有法律约束而且令国人并不反感的各种“山寨版”潮流出现和蔓延,更是让人望而却步。
金溪地方,我们先后去过很多次。这次,为了落实这两对大德年间烧造的象耳瓶出处,我们再次到金溪住了一个月。通过已成了好朋友的过去的向导,帮助细致暗访。最后得知,这两对元瓷瓶,出自金溪与贵溪交界的,原四十九都辖内的金牛山南麓半山一座古墓。原来,吴益子在悼文中所说的“佳哉金牛,葱且郁兮”,不但说明了师伯熊德方的葬地,还描述了阴宅墓地当时周围的风水环境。同时出于墓中的,还另有类似的瓷瓶数对,香炉九件,瓷罐数个。这是我们费尽了周折,挖墓的当事人才肯和我们见面,交谈中,得到了宝贵的印证,解答了我们心中的疑问。
金溪窑场,是元朝新开的官用瓷总烧造地辖下的一个分烧地,有烧造点十几处。我们另有文章专门详述。包括金溪窑场在内的总烧造地各处,都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5年)起烧的。元政府设立浮梁磁局,为了保护官家用瓷的新开烧造地,对景德镇各窑的烧造,有严苛的规定。就是说,当景德镇各窑还在严格执行元朝中期人蒋祈在《陶记》中的“景德镇窑……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罚”的政令时,而地处两省四县的新开烧造地,使用南宋朝传下来的“二元配方”,已经烧制出大量炉火纯青的青花瓷大器和近臻完美的青花釉里红大器。这种情况,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官匠总师傅于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去世,和浮梁磁局大使赵延宗于当年八月辞官隐居后,景德镇各窑那种只准许生产黄、黑、白(包括影青、白、卵白)三色釉的规定,才渐渐被松绑。
这里需要商榷的是,当代一位著名的景德镇瓷器研究大师,也许是为了捍卫家乡景德镇在元瓷制造中的地位的缘故,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把元代中期景德镇人蒋祈的《陶记》说成写于南宋1214—1234年之间,并在当地作为定论,向世间公布,做法欠严谨,易造成历史的扭曲,使元瓷研究在模糊中再添混乱。我们另有文章专门分析。
在这里先提一点。我们前面发表的文章提到过:元代景德镇,尤其是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之前,根据浮梁磁局规定,景德镇仅是官控用瓷的集散地和转运站,不能烧制官用瓷,瓷釉也不允许超出黄、黑、青白(影青、白、卵白)的釉色;凡官控窑场运来景德镇的瓷器,先入分类仓库;瓷器出库转运前,要在水单上标明产地,正如景德镇兰浦、郑廷桂在《景德镇陶录》中所讲的,只可标明是“镇器”,之后必须加上“江西窑器”和“某某窑器”字样才可出库。
他处窑场转来景德镇的官控用瓷,分类入官贵用的“官用仓”(俗称“蒙人仓”)和售卖用的“汉人仓”两种仓库。而具体某个仓库的名称,则是以官定管库人的名(不用姓)作为库名,这就是元人蒋祈在《陶记》中所说的“土居之吏,牢植不拔,殆有汉人仓、库氏之风,五也”。
应该知道,在汉族人建立的北、南宋两朝,不可能在瓷造业出现有自污自蔑、还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汉人(仓)”或“蒙人(仓)”称呼,在南宋也不会有官家用瓷的官控仓库以管库人的名字命名的。
从吴益子作悼文的这两对象耳瓶上,可以看出,早在大师尚在学徒的大德年间,元青花大器和釉里红大器的烧成,无论是在釉色上,还是纹饰上,都近臻完美。终元一朝,几乎未变。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元代青花釉里红的配方和窑烧技术是严格保密的,就像元代烧成大龙缸一样,只在极少数师徒间传授。徒弟能接受这项技术,必须是总师傅信得过、能代表师父意志和身后意愿的出师后的小师傅。可惜的是,两省四县的官控窑场停烧后,虽然有部分瓷师转到了景德镇各窑场,但青花釉里红的烧制技术,没能在景德镇传承下来。就是说,有元一代,景德镇各窑场没有成功地烧造过元代青花釉里红精品大器。
史料显示,为人忠厚的吴益子大师,从学徒开始到收徒传授技术,始终坚守在他所管理的那处窑场。其他窑场的瓷师们,尊称他所在汝水河畔、三十一都白云峰下那处窑场为“吴陶坡”。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他的师父去世时,已经儿孙满堂、年近八旬的吴益子大师,不忘师恩,亲手制坯、施釉,烧造了硕大的釉里红盖罐,并写上“弟子吴益子”置;还在六都的崇峰山顶,建造了怀念师父的“祖师庙”,又立牌告示,改崇峰为“百岁峰”。人到七十手颤抖,吴大师八旬还为师父造瓷。昔日师徒恩情之久远,令人感叹唏嘘不已。
吴益子后代制瓷大师“壹隐道人吴十九”
为了落实吴益子制瓷大师的后代传人的记载,我们拜访了他的第二十六代孙、吴代族长吴文盛老人。老人家不但讲述了元末朱元璋避难县城红塔,浮梁人相救,得天下后又怒杀浮梁人,反差极大的历史故事,也聆听了老人讲述先祖感人的历史功绩。看完族谱中记载,更燃起我们对吴氏浮梁迁祖公吴益子的敬意,对他孙儿吴承允“孝义忠勇”行为的敬佩。
其族谱中,有《允三公急义从公颂》一段,载:“我祖允三公,性纯笃,任事出肝胆。元时,本里解琉璃瓦之役。签伯氏名时,无嗣,堂上有隐忧。公默体亲志,毅然请代兄行。间关跋涉,无息肩,遂于金陵不禄。夫我祖之先意承颜者,孝也;保护同气者,义也;劝劳王事者,忠也;尽瘁不惧者,勇也。备此美德,佑启后人”。这里讲的是,朱元璋称“吴王”时,在金陵造宫殿,准备登基之用,派令瑶里十三姓烧造琉璃瓦,并及时解送金陵。按照规定,由吴益子长孙吴承时解送,但吴承时无嗣,父母忧虑。其弟吴承允自愿代兄前行。后因时限逾期,吴承允和同行瑶里人,全部被杀。
吴文盛老人告诉我们,自吴氏浮梁一世祖公吴益子起,吴氏代代以制陶烧瓷为业,子承父志,经久未歇。其中最有名的,是吴益子的六代孙吴为。
吴为,字邦为,生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在浮梁吴氏同辈中,排行十九,家中称他“吴十九”。制瓷出名后,单称“吴十九”。吴为自幼随父兄学习技艺,不但继承了祖上五代人的技术,还有所创新。尤其在烧制薄胎瓷技术上,超越了前辈。还常在瓷器上留下清美的诗句,字里行间带有祖公吴益子诗句的韵味。
吴为制瓷精道,用古人的话说,美轮美奂。他烧制的“流霞盏”,色如晚霞余晖,光彩照人;他的“卵幕杯”,胎薄无比,莹白剔透,轻如纱缦;他的“紫金壶”,色淡青,无水纹,胜过官、哥之器。为了有别于其他窑瓷,他在瓷底上常留款“壶隐道人”。时人遂称他的瓷窑为“壶公窑”。有明一代,古籍中所言景德镇瓷,“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其声如磬”,其实是以他的瓷器为标榜。
明万历朝太仆少卿李君实,在《紫桃轩杂缀三》中,赞美吴为的“流霞盏”:“为觅丹砂斗市尘,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云汛兰亭九曲泉”。
御史大夫樊玉衡(樊以齐)谪戍雷州,经景德镇,拜访吴为,惊叹吴为制瓷之精湛、诗赋之优雅,赠诗道:“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吴十九,更有小诗清动人,匡卢山下重回首。”
一直到了清代,人们仍对吴为的瓷器赞不绝口:“龙泉兄弟知名久,甄土新载总后尘,独有流霞在江上,壶中高隐得诗人。”
目前世上流传吴为的瓷品,只有北京故宫珍藏的“娇黄凸雕九龙方盂”。口沿上有铭文,“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万历吴为制”。“兮体诗”,仍有祖上吴益子的诗韵味道。
吴为吴十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病逝,享寿71岁。吴为之后,浮梁瑶里吴家虽然仍有几代后人烧陶制瓷,却没有能与他们的一世祖吴益子灵四、七世祖吴为吴十九相比的。
另外,吴益子的另一位六代孙、吴为的十兄吴帮振吴十的墓穴,于1973年在江西都昌被发现。圆形的青花墓志瓷版上,记有“吴公讳邦振,行吴十,号近泉,先生浮梁之景德镇人也……生于正德戊寅年(正德十三年,1518年)……敬择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初八寅时,与公金砖寄焉”。以生年或殁年的生肖对应相同生肖属相的日或时殡葬入土,这是元明时期徽州、饶州地区阴宅风水要求。此处是以生年对葬时。另“金砖”,非金银之念,据《康熙起居注》记载,明清时期,称五色琉璃瓦为金砖。■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