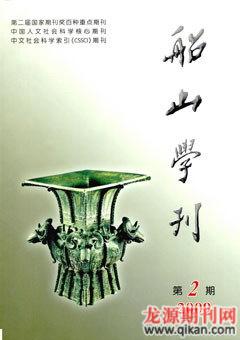以诚论性
赵载光
摘要:博大精深的船山学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以宋学为宗,继承周敦颐、张栽和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以诚论性、性气合一、道器合一。从而纠正了程朱理学以理论性,性气分立的性理之学。并且在理欲关系、人性善恶等一系列人性哲学、道德哲学问题上对程朱理学进行纠偏,形成与理学和心学都不相同的思想路线。
关键词:性命之学;以诚论性;气性合一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105-05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学术是“以复古求解放”,清初实学批判明代的心学,最初是回归到宋学。说到宋学、人们往往是讲程朱理学,但实际上,清初实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在批判王阳明心学的同时也在批判程朱理学。王夫之回归的宋学是以周敦颐、张载为代表的性道之学。
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认为:宋学是“以性为宗”,明学是“以心为宗”,这确实抓住了宋学的基本思想。宋学内部不同的思想流派。是围绕论性的不同方向而形成的。周敦颐主张性即是道,以诚论性,成为性道之学的奠基者。同时期的张载与之互相呼应,对性气合一,诚明论性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后南宋的胡宏、明代的刘宗周沿着这条思想路线,对性与道、性与气、性与心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发明。这是性道之学,也就是以诚论性的一个派系。
从程颐到朱熹的理学。主张性即是理,性气分立,形成性理之学一派。南宋以后成为统治中国的官方哲学。北宋的程颢提出以心识仁体,南宋的陆九渊主张性即是心,形成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在明代经过王阳明的大发展,形成可以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一派。
船山学术以周敦颐、张载为旗帜,批判陆、王心学,也批判程朱理学。坚持张载以气为本,性气合一的宇宙本体论,宏扬周、张以诚论性的伦理哲学。他的思想与同时代的颜元主张“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存性篇》)。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都可以说是回归性气合一的宋学正宗。
一、以性为宗的性道之学
船山学术博大精深,但他的思想主线是清晰的。这个主线就是以儒学为宗,批判佛道;以宋学为宗,批判明代心学,同时也批评汉、唐的注疏儒学。他说:“自秦以后。所谓儒学者。止于记诵词章。所谓治道者,不过权谋术数,而身心之学,反附释老。”(《读四书大全说》卷四)。他认为汉唐儒学论治道只是法家的权谋术数,没有发展有关人性天道的哲学,所以让佛道二教思想大引其道。直到周、程、张、朱才发展出这种“为万事万物之本”的学术。“朱子又云推其极只是性,则原程子言外之旨原有性学二字,以别于俗儒俗吏之学。”(同上)
船山正式提出“性学”的名称,以指称宋代的道学。他所说的性学,包括周敦颐、张载的以道言性,也包括程颐,朱熹的以理言性。对于陆王心学的以心言性,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性道之学和性理之学两个派系中,他又高扬周敦颐、张载“性气合一”、以诚论性的性道之学、对程朱理学的性气分立、理气分立进行了批判与纠正。
什么是性?船山认为:性是人的本质。“人之体唯性,人之用唯才。”(《尚书引义-洪范三》)。性与道相对应,在天为道,在人为性。道是理与气之统一在天(自然)。性是理与气之统一在人。从天授予人生命能力的角度叫做命,人接受天的授予而逐步形成的人之为人的特质叫做性。人的形气是自然赋予的,人的精神是建立在形气基础上的。其它万物也有性,但与人性的等级不同,所以人与万物不能混同。
什么是道,道就是路,是万事万物所由发展的必然性或规则。从必然性的角度,规则或规律是不可见的。是虚,所以船山又称道为总体的理,在这里船山与程朱理学的观念是相同的。但是另一方面,船山认为天是实,是万事万物所由生之自然。虚与实。道与天。实际上是统一的。没有离开自然实在而虚悬的道与理。理与气、性与形也是统一的,故“道可载物,物以载道。”(《尚书引义·康诰》)。强调道与物的统一,是船山努力纠正程朱理学道器分立,理气分立的重要理论任务。与周敦颐、张载及湖湘学派的胡宏相比,船山更强调性与道的实在义。把性放在实实在在的物质之气中,没有神秘性。可以进行分析。
什么是理?周敦颐论性论道没有运用理的概念。二程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把理作为论性论道的基本范畴。张载把“天理”与“天德”相对应;“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王船山继承张载的观念,同时也吸取程朱的理的内涵。一方面是理与道同大,理与性同在,这里程朱理学的观念。另一方面他反对程朱的理气分立。他认为理与气是一个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因此船山论性就不是朱子的性等于理,而是性中有理。性中除了理之外,还有性之德、德是气之良能。在天,是自然的运动;在人,是生命的功能。这是周、张、王船山论性的特色:性是有时空实在的生命创化运动。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规律——理。所以他们把性定义为“诚”,所谓诚就是实有、不虚。
性为实有,是生命的创化运动,就把人的文化精神与感性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象程朱理学一样把人欲排除在天理(性)之外。船山说:“善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性。理与欲由自然而非由人为,故告子谓食色为性亦不可谓非性,而特不知天命之良能。”船山论人性与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差别是:船山继承胡宏的观念,主张天理人欲是统一的,都是人性的组成部份。这是对流行了几百年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口号的批判。
程朱理学的理与欲之所以对立,它导源于本体论的理与气的分立。理是纯然之善,气则有善与恶的各种变态,人欲是气的本能。所谓气质之性。它是天命之性(天理)受到气的污染而形成的。实际上是把感性生命的各种本能欲望看作是恶。王船山从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立场,批判了程朱理学理气分立的本体论,也批判以性归理,以欲归气的论理哲学。他说:“以生归气而以性归理,因以谓初生有命,即生而命息;初生受性。既生而但受气而不复受性;其亦胶固而不达天人之际。”把性与气分成两截,以性归理而以欲归气,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的人性论。即“初生受性”,“初生受命”。船山认为这是一种“不达天人之际”的观念。
与程朱理学的理是善,气有恶的观念相反,船山认为气本身是善的,因为理就包含在气之中。他说:“性里面自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与天之元、亨、利、贞同体,不与恶作对。”故说善不如说诚,“惟其诚是以善、惟其善。斯以有其诚。”所谓元、亨、利、贞,他指的是气的运行状态。“和气为元,通气为亨,化气为利,成气为贞,在天之气无不善。”他批判那种贵性贱气即把性与气对立起来的观念:“贵性贱气之说,似将阴阳作理,变合作气看,即此便不知气。变合因是气必然之用。其能谓阴阳非气乎?……阴阳显是气,变合却亦是理。纯然一气无有不善,则理亦一矣,且不得
谓之善,但可谓之诚。”气与理是不可分割的。气是纯然不善。但不是与恶相对的那种善,那是道德之善,是以人类文化作为评价标准的。这种纯然之善的恰当的称呼是“诚”。所谓“诚”,就是实在实有,不乱不妄。以诚论性,也就是强调性的实有与不妄。
王船山以气论性、以诚论性。其思想源头一是周敦颐的“以诚立性”,一是张载的“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船山认为张载说的这个“虚”就是理,所以实际上是“合理与气有性之名。”他批判程朱“天即理”的说法,更反对陆王“心即理”的说法。他宏扬张载性气合一的思想说:“然则欲知心性、天道之实者。舍横渠其谁与归。”他认为:“就其气化之流行于天壤,各有其当者日道,就气化之成于人身,实有其当然者则日性,性与道本于天者合。”他的性、道之本合于一。这个一就是自然的气化流行。性气合一。克服了道即是理的抽象性,也克服了性即是理的先验性。
气化流行的实有实在和必然规律可以用一个“诚”字表达,它也是周敦颐、张载到胡宏以诚论性的本义,船山进一步宏扬了这种思想。他说:“周子下个诚几二字,甚为深切著明。气之诚。则是阴阳,则是仁义。气之几,则是变合。是情才。若论气本然之体,则未有几时,固有诚也。”诚是性体,由几到德。是由诚体展开具体人性的过程。在周子,几善、几恶主要是讨论“几者动之微”的心理活动。船山则把几解释为“气之几”,阐述宇宙阴阳的物质运动。同时也说明人性的变化是实在的气之变合。在船山,他说的人性既包括人的文化精神(道或理),也包括人的感性生命的本能,人的感性存在既不能轻视。更不能把它当作恶。
船山论性继承了胡宏“理欲合性”的观念。胡宏提出“天理人欲同体并用,同行异情”,遭到朱熹的批判。船山对朱熹的批判进行批驳。捍卫了胡宏的观念。他说:“是理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虽居静而为感通之则,然因乎变合而章且用。惟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离欲而别有理,其唯释氏为然。……五峰日: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韪哉,能合颜盂之学而一原者,其斯言也夫。”(《读四书大全说》卷八)。他指出天理人欲对立的观念会走向佛教的禁欲主义,而孔孟儒学并没有理、欲对立的内容。
在心与性的关系上。船山继承了胡宏“性体心用”,“以心成性”的观念,而反对朱熹心有体
用的说法。他说:“性为天所命之体,心为天所授之用,……性与生俱而心由性发。”“性与生俱”是说人性是与生命同在的,所以是体,而心(主体精神)是生命的功用。心反过来可以体认和统摄性。“夫此心之原,固统乎性而为性之所凝,乃此心取正之则;而此心既立,则一触即知。效用无穷。百为千虑而不迷其所持。”性与心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主复的,性主导心,心恢复性。“治心无可常据。而所以主此心者。性也。特性之在未发也。其体甚微。而或无以培护,则因吾心之存亡为消长。”心随物动,应该以性来主导制约。性隐微难见,又要以心之培育达到养性之功。
船山认为:性通于天道之诚,造化之机。他既包含人的文化性(性之理)。又是人的生命能力(性之德)。船山在阐述宋学的性道精微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成人成性的理论,主要有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和“继善成性”的成人论。近人钱穆说:“晚明儒王夫之,可说是湖湘学派之后劲。他极推崇张载之《正蒙》,也极力发挥成性的说法。阐述精微,与胡宏《知言》大义可以相通。”正确地指出船山继承胡宏成性理论的思想传承。实际上,胡宏与张载在性气合一的宇宙本体论、以诚论性的人性论两个基本立场上都是相通的。所以他们才共同成为船山思想的源头。
船山发展胡宏“以心著性”、“尽心成性”的观念,提出“命日受而性日生”,认为人性是一个“日生日成”的动态发展过程。他说:“二气之适。五行之实,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取精用物,一受于天产地产之精英,无以异也。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人的出生与成长都离不开自然的物质和能量的转换。从自然授与人的角度古人称之为“天命”。这个天都并不是人出生时一次命于人的,那是宿命论的迷信。而是人每日都在进行的实在的过程。人每天都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能量与信息、转化为自己生命的发展,精神的成长。人的本质(性),也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成长的过程。在船山。天命没有任何神秘性,人性是自然生命与文化精神的结合。是“日新而富有”的实在过程。
在“日生日成”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船山展开他“继善成性”的伦理哲学。其基本思路是:天道之诚形成文化道德之善,人继天道之善就能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所谓天道,船山指宇宙阴阳之气健运不息的规律或必然性,其特点叫做“诚”,也叫做纯然之善。但不同于一般道德善恶之善。后者实际上是人类文化确定的道德标准。所以船山认为:道不等于善。但道能生善。“道大善小”。所谓“道生善”,就是认为人类道德规则与自然维系生命存在与发展的规律是相通的,这是建立在中国文化有机宇宙论基础上的生态伦理观。人继承天道之善、就能完善其人格,实现其人性,因为人性与天道本来就是相通的。“溯言善,而天人合一之理得。”
“继善成性”,克服了程朱天理就是善的先验性善论的理论困境:即把人性抽象化而与感性生命对立,只能用外在的道德限制人的个性。而“继善”有一个主体继和不继的能动作用问题。既强调了道德之善的客观性,又强调了人进德成善的主观努力的必要性,同时说明了道德生命是人的生命自然存在的一致性。成性、成善不是外加于人的规则,而是人的生命的一种本质的要求。
二、以诚论性,以中论性
周敦颐的性道之学,把“诚”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来阐述性与道的本质特征。张载、胡宏刘宗周和王船山都在继承和发展这种思想。船山说:“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尽天地只是个诚,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
他发展了周子“乾元立诚”的本体论概念,把诚训为“实有”,以表现气化流行的实在性与必然性:“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他解释张载“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说:“诚者,神之实体,气之实用,在天为道,命于人为性。知其合之谓明,体其合之谓诚”。所谓“神”,指气化流行的阴阳不测,实际上也就是道,天道与人性相通的实在性与规律性就是诚。“至诚体太虚至和之实理。与姻缊未分之道通一不二,是得天之所以为天也。”絪缊是气。气中缊含实理,这种实理就是诚,是自然(天)之所以为自然的根据。
从人的角度说,诚是人实在的生命精神与能力。“至诚者。实有之至也。目诚能明,耳诚能聪,思诚能睿。”这种能力也称之为神:“自其变化不测之谓神,自其化之各成而有其条理,以定志趣而效功能者谓之性。”性与神是实在与功用的关系。人性之诚源于天道之诚,发展这种诚,
就能完善人性,实现自我。也就能认识和统御世界。“已无不诚,则循物无违而与天同化。以人治人,以物治物,各顺其受命之正。”达到诚。也就达到了“与天同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人的内在精神如何认识世界?他引用周敦颐诚、神。几的概念来加以说明:“人之有受由内外合也。……合内外者,化之神也。诚之几也。以此为知,则闻之见之而知之审:不闻不见而理不亡。”诚是实体,在人就是性体;神是阴阳不测的造化之机,在人就是精神活动;几是动之微,是由本体到作用,由性到心的过渡环节。“合内外”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之所以能合内外而认知世界,就是因为有诚这个性体动健不息的生命运动。
在自然中,诚与几的关系表现为存在与运动的关系。“天积阳于上而雷动于下,积者诚也,动者几也。……无妄则诚矣,诫则物之终始,赅而存焉。”诚的反面是虚是妄。船山之所以要大力提倡诚。也就是强调世界的实在性。佛教否认世界的真实性,主张“性空”论。船山以诚论性,以实论性,也就是对佛教性空论的否定。实有的诚不是静止的,他的运动不息来自内在的化机,这就是神与几。
为什么要以诚论性而不是以善恶论性?因为人性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范畴。善恶都只是反映人性的一个方面。如果以善恶论性。往往会变成各执一端,互相矛盾。船山认为:从人性与天道相通的实在实有与必然规律的角度,只可以叫做诚。从天道维系生命的生生不息的创化功能,也可以称之为善,但它是无为之善,与一般说的道德之善的意义不同。“若论性,但唤做性足矣。性里面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与天之元亨利贞同体。不与恶作对,故说善不如说诚。唯其诚是以善,唯其善所以有其诚。(自注:天善之故人能诚之)所有者,诚也,有所有者,善也。”诚体有元亨利贞之德,可以生成善,但诚与善是两个层次,不宜混淆。
船山要否定先验的性善论,同时要维护儒家性善论的基本立场。人性之诚与道德之善是什么关系?诚是道,道生善,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有大与小的差别。所谓诚道,指整个宇宙气化流行的规律性与必然性,它是人与万物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本原。道德之善的根本原则,也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从中国传统的有机宇宙论的视角。儒学认为道德的最终根据来自于天。因为有天道之诚,才会有文化道德之善。因为有诚与善,人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性之善。《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一个诚字把真和善两个概念贯通起来。从宇宙万物的真实无妄,引伸到伦理道德的诚实不伪。
船山用诚的范畴把理与气、性与形统一起来。他批判程、朱视理为善、气为私为恶的观念,他称之为“贵性贱气”论。他说:“阴阳显是气。变合却亦是理。纯然一气。无有不善。则理亦一矣。且不得谓之善,但可谓之诚。”气之体是阴阳本体。是诚;气之用是阴阳变合,是几。表现在人性,诚即是性,而几的变合就是情与才。性体无所谓善,也可以说是纯然之善。情与才则表现出人道德的善或恶。所谓善恶,在于情才的行为合不合于正理。所以人要不断地“继善成性”。“继善成性”是道德完善的途径。也是人自我实现的道路。
“诚”见于人性的具体表现是“中”。中道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周敦颐、张载都是以“中正仁义”展开具体人性的讨论。胡宏说:“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从诚到中再到仁,也就是从天道到人性再到人心。三者有层次的差别,但本源是一个。船山认为这个本源就是气化流行之体。他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在天而天以为象。在地而地以为形,在人而人以为性。性在气中,而裁成变化存焉,此不可逾之中道也。”“通天人日诚,合体用日中,皆赞辞也。喻之而后可与知道。可与赞德。”
船山并不是把诚和中作为另外的实体范畴,实体只有一个,就是阴阳之气的物质世界的变合运动及其规律。诚和中都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对这一实体的定义。诚表示其实在实有,中表示其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中道,具体到人性,则表示人性的本然状态。他在注解张载“学者中道以立,则有仁以弘之”时说:“《中庸》自其存中而后发之和言之。则中其体,和其用也。……仁者,中道之所显也。”中的内容是仁义礼智的道德文化,从表现形式看是不带感情色彩的“未发”。
船山把中分析为“中和”与“时中”两个概念,“中和”指性之体。“时中”指性之用,《中庸》讲“君子而时中”,船山认为体用统一而归本于诚。“未发之中。诚也,实有之而不妄也。时中之中,形也。诚则形,实有者随所著以为体也。实在所谓中者一尔。诚则形,而形以形其诚。…‘未发之中”。指人无思无虑的精神或心理于诚,同时也涵有仁爱之善。“时中”指人的行为合中道,它表现于有形。船山认为前者是体,后者是用。
以“中”论性。具体到知性、养性,就是“执中”、“用中”。船山说:“古之知性者其惟自见其衷乎!仁义礼智以为实也。大中至正。以为则也。暗然而日章,以内美也;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以充美也。”衷地就是中。也就是性。“显性之有而目言之,《易》谓之缊、《书》谓之衷,《诗》谓之则,孟子谓之塞;求其实,则《中庸》所谓诚也。”它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它的形式是大中至正,它的特点是贯通内外的和谐之美。这是对《中庸》以诚论道,以中论性思想的发挥。与周敦颐,张载是的是同一个路向、即《庸》、《易》结合的方向。
船山说:“阅尽天下人。阅尽天下学术,终无有得当于《中庸》。而其效亦可睹,所以云‘中庸其至矣乎!”与程朱理学极力推崇《大学》的内圣外王之道有不同,周敦颐、张载极力发挥《中庸》以诚论性的人文思想。程朱以“理”论性,把人性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先验预设。周张以“诚”论性,把人性看作来自于自然的实有生命精神。其本原是宇宙自然的生生不息的造化运动。船山发挥这种思想说:“周子日‘诚无为,无为者诚也。诚者无不善也,故孟子以为性善也。诚者无为也,无为而足以成,成于几也。几善恶,故孔子以谓可移。”“诚无为”表明人性源于天道自然的特点,“几善恶”表明在现实中的变化过程。几者动之微,船山认为几应该分为在天之几与在人之几两种:“有在人之几,有在天之几”,“成之者性,天之几也。初生之道,生后之积,俱有之矣。取精用物而性成焉,人之几也,初生所无,少壮日增也。”所谓“天之几”指“生之道”即自然赋予人的基本东西,如今天所说的遗传基因。所谓“人之几”,指后天的“取精用物”。即后天物质与知识文化的获得。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人性的生成发展过程。
船山坚决反对“悬一性于初生之顷”的神秘主义的天命论或抽象静止的人性论。他用诚来说明人性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用几来表示从无善恶到有善恶的具体变化。他仍然是保持儒家性善论的立场,但作为本体的诚只是中道,可以说是纯然之善,也可以说是无善无恶的无为状态。性善论是人类文化朝着乐观主义方向的精神运动,它促使人类向着希望和理想前进。其缺点是没有具体考虑面对社会诸恶的法律制度解决方法。
王船山以诚论性的第三个方面是主张“性气合一”,气为物之本。性气合一是对朱熹以理为气之本观念的否定,也是对周敦颐以诚论性。张载性气合一思想的继承。“性气合一”突出了气在宇宙万物中的实在性的物质存在。成为船山哲学的重要特色,因篇幅所限另拟专文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