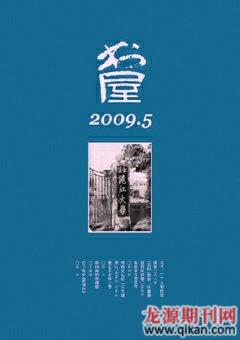“五四”感言:任重道远的反封建
雷池月
自从赵家楼胡同燃起那把大火,九十年来,大约总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学生在作文课时写过“感言”一类文章。由于人数众多,从立意、结构到遣词造句,自然不免重复雷同。记得六十年前念小学时听老师举出的例子:一开始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五四节又到了”,结尾处则无非“一定要继承五四精神,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努力奋斗”之类——陈词滥调,此之谓也。一时,讲台下的诸生,似乎都面有赧色。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求“陈言之务去”实在太难,不要说是学生娃娃,不同时代的大人先生们的有感而发,又何尝不多是些废话和假话。
当然,还有名家学者围绕“五四”精神发表的许多宏论,鞭辟入里者固有,随意挥洒者亦不在少数,更有的立意高远,与时俱进,使人读后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叹。于是,有些疑问,有些想法,横亘胸中,欲一发而不得其时。“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五四节又到了”,便萌动了作文的念头,虽然明知有“陈言”之嫌,也在所不计了。而且,我一直认为,“与时俱进”固然好,而“陈言”也未必一定要“务去”,特别是那些前贤付出极大的努力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一类的“陈言”,尤其不可轻言“务去”。
究竟什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划时代意义
“五四”的划时代意义,大概已经是无须论证的共识。因为多年以来,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就是以“五四”为分野。为什么要如此断代呢?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新文化运动那一个“新”字,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一直就是互为因果地捆绑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主要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前也是有过的,明朝时的一些零星的、很有才气的文艺界人士似乎做得很出色,但终究不成气候,大抵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端。他们输在手中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各种近、现代思潮被大量引进,从马克思到巴库宁,从杜威到罗素,五花八门,纷呈异彩,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濒临绝境的老大帝国,文化上更是失去了任何抵御能力,不几年功夫,传统的封建文化就呈土崩瓦解之势,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从教育体制到教材内容的彻底转换。封建传统文化的溃败,证明了来自欧美的思想武器确实先进。可以说,从此,以反封建为大皈依的新文化已经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因而,这个在历史上具有文化启蒙意义的“五四”时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跨进的开始。
陈独秀把所有从西方引进的“新武器”概括为两样;民主和科学(需要说明一句,所谓“从西方引进”一说不确,大多数“武器”是日本转销的“二手货”,认真盘点一下现代汉语中有多少名词是直接从日本照搬,真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他的道理是不错的,然而,很大程度上,那只是一种呼唤,要说“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对民主与科学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未免失之过于乐观。近年来,学界好像不大提“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比较一致的是只就民主和科学两条说事,或者直接说民主和科学就是“五四”的两大主题。是谁设计了这样的主题呢?或者说,在当时或事后,这两大主题究竟得到了何种程度的凸显呢?依不佞的鄙见,事实上,不要说当时找不出存在这种指导性主题的根据,就连事后作总结也很难看出这两大主题的影响。
先说德先生,当时国人中的精英对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或者多少有所了解,而对于民主和专制两种政体却所知甚少。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党认真地、系统地宣传过民主主义的思想、制度及其运作方法。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可是他在宣讲自己的民权主义时,告诉大众的,是如何开会,怎样提议,怎样附议,如何表决之类常识,并未深入到民主的精髓和要义。他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应该是了解较多的人,不愿多讲,显然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土壤不宜于即时移植民主这株鲜花。所以他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努力的主要目标并不在此。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在实现宪政的道路上做出了“三个时期”的安排,而且,对第一(军政时期)和第二(训政时期)时间的长短从未作出具体的规划(从理论上说,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才算是结束了漫长的训政时期)。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早期带有浓厚的会党气息,辛亥以后,宋教仁曾为实现它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进化付出不少努力,宋教仁一死,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又退回到按手印宣誓效忠领袖的水平。目睹了军阀的混战,一筹莫展的孙先生,最后选择的是按苏俄方式组建全能型政党。
至于赛先生,当年主要是指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而非现在所指的自然科学(中国的第一代现代自然科学家其时大多还在海外学习)。这方面的引进应该说是颇有成效的,于是一度主义满天飞,以致胡适要呼吁大家“少谈些主义”——这当然不可能,引进的主义各有师承,不分个高下,很难解决谁是老大的问题。好在大家在打倒孔老二这点上有共识,或者说,有共同的进退利害的关系,一起动手,于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终于走向崩盘。最先是教育体制的重构和白话文的推行,接下来的是种种礼法观念的瓦解。维护旧传统的人,只能发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和“藩篱尽拆,人心不古”的悲叹。
由于“五四”群众运动以反帝为契机,而新文化运动则以反封建为己任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两者不仅在时间上有所重合,而且确实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所以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说是反帝反封建犹可,指为民主与科学则有拔高之嫌。
或曰,反帝反封建不能仅指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表现又如何呢?此话不错。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文化启蒙走在政治和经济前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何况,当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有迹可循。比如说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街头政治就是当时第一次引进的。封建政治的鼎革大多离不开密室里歃血为盟的阴谋,而街头政治则把诉求和对诉求的反应(镇压或许诺)袒露在阳光之下,这也是反封建斗争取得的进步,虽然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街头政治的过分发育往往会导致极权主义的萌发和膨胀。然而,那是后话,而且也并非什么铁定的规律,比如法国,两百年来街头政治一直十分活跃,但极权主义却从未占据主流。
在经济方面和反封建相呼应的现象,是现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外贸入超从二亿多两减少到一千六百多万两,1912到1919的八年间,民族资本的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的总和。银行、交易所、纺织及面粉等金融业和轻工业发展很快,1921年,中国甚至从面粉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所有这些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突破封建制度的表征。这个局面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是因为一战结束后,列强又腾出手回到中国来瓜分和争抢利益,尤其是日本直接发动野蛮的侵略,加上国内政治的混乱等等原因,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进展,说明中国社会当时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跨越,是一个不争的趋势。
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历史任务。有些学者说,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由于特殊的国情(封建文化的顽固和民众的愚昧)而具有偏激的色彩,因而导致了此后几十年激进主义的政治实践,从而阻碍了反封建目标的最终实现。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新文化运动的偏激和激进主义的滥觞,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特别是把两者归纳为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尤其不当。事实上,激进政治更多地恐怕应该从封建专制主义方面去寻找源流。因为斗争的尖锐,武器的批判取代了批判的武器,这种情形当然也符合逻辑,但难道那就一定要无限期地训政和专政吗?
反封建,在文化这个领域内,“五四”时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把“近代”引入了“现代”。
怎么能说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呢?
但是,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却仍然只能看做是局部性的、阶段性的,三千余年的流毒,绝非朝夕之间便能肃清,嗣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激进观念所导致的悲剧便是明证,真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有识之士大概都觉得反封建这一课,还需要大力补火。这几年,有人发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结束,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以后,中国人便已经不再生活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刚看到这个结论,当时很是有几分惊愕:封建制度已经灭亡了两千多年,那还用得着反吗?不纯粹是白忙乎吗?情况真是如此吗?细读之后,觉得这些文章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出自于科学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它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大约可以综合成这么几条:
第一,什么叫封建制,柳宗元在《封建论》里已经做了解释,即他所说的: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步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而朝觐会用,离而守臣扞城。
为证明言之有据,有人甚至还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封”和“建”两个字的原始含义,总之,封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和郡县制相对应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自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第二,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和中国的封建制不是一码事,两个概念根本不能通用。日本人在引进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时,将feudalism译成封建制度(主义),是从汉学中信手拈来的,不足为据,或者简直就是一种误导。一百年来,我们一直沿用,两者混淆,其实是上了日本人的当。
第三,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欧洲,离开了欧洲,别的地方(如所谓“古代东方”)就不能对号入座,是列宁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才把它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整理成理论,还是在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从此才成了“真经”。
说实话,上述观点也曾让我目眩神迷,以致好一段时间不敢使用“封建主义”一词,怕被人指为无知,跟不上时代。后来想想,觉得还是有些疑惑,便想到利用写感言的机会,说道说道——也按上面的秩序逐一提出问题吧。
一,柳宗元说的封建制度,当然不是一个学术上的现代(或近代)范畴。但是,在中国,一直到十七世纪之前,它却是作为和郡县制并列(相对应)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在理论上一直进行着对抗,在实践上也是相互替代或者并行一时的。两者孰优孰劣的辩论,两千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过,由于没有结论,除了唐、宋两朝以外,其他时代,基本上可以说是封建与郡县并行(元、清两朝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当别论)。
秦祚仅二世,不少人认为实行中央集权是重要原因。刘邦虽然不情愿,却不得不顺应潮流,大封诸侯王国。异姓封王是出于一种统战权术,日子不长就全都收拾干净了,而同姓诸王几十年后却带来了大麻烦,“七国之乱”就差一点把汉景帝掀下宝座。教训太深刻,此后,汉朝尽管形式上还存在藩国,但不仅不能再统管地方的军、政、财权,相反还要处在州郡官员的严密监督之下。封建制似乎是一蹶不振了。
谁知到司马炎建立晋朝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封建制。他的兄弟子侄大多是军人出身,不少人在各自的封国里养精蓄锐,野心勃勃,不几年就开始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并不是八家一齐动手反中央,而是一个接一个地互相消灭,到最后一个实力派完蛋了,西晋也就垮了。随后的南北朝时期,因为大家都是割据性政权,统一大业未成,封建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到日程上来。这三四百年间,封建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处于消沉状态。
隋朝时间短,本来可以忽略不计。但正因为其短,到了李世民手里,封建制又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宰相萧瑀原本是隋朝的国舅,对隋的二世而亡有切肤之痛,他认为隋朝没有搞分封是大错,于是最先向李世民提出实行封建制,他说:
臣观前代国祚所以久长者,莫若封建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四百余,魏晋废之,不能久远。
大概因为自己的尴尬背景,他不提隋朝,而只拿秦朝说事,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逻辑,还扭曲事实说“魏晋废止,不能永久”。李世民本来是有点倾向于他的观点,但是魏征、徐勣、马周等大臣一致反对,最后折中了一下——封王而不建国。
宋在各方面都是基本承袭唐制,此事也不例外,再加上宋朝在国家文官体制的建设上有了极大的进步(参考拙著《帝国的仕途》2008,中国工人出版社),因此唐、宋两代,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完善和加强。到了元朝,蒙古人因为对政治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虽然也分封了好些子弟功臣为国王(有的有疆土,如察合台等;有的没有疆土,如木华黎等),但由于政治机器的简陋,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在汉族地区,没有封建诸侯国,而是开始实行行省制度。所谓行省,就是中央政府(中书省)的派出机构。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推行封建制的态度很明确。洪武三年,一下子就封了九个儿子和一个侄孙为王,建藩于各大中心城市。《明鉴纲目》里是这样记载的:
帝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其制:禄亲王岁万石,置相傅、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籍隶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大臣伏而拜谒……
看来,朱元璋是很倾心于封建制的,但他又是一个最不舍得放权的人(连丞相都嫌多余而被撤销),所以他的封建和周、汉又有所不同:“封藩而不裂土,袭爵而不临民”——虽有军队却没有领土主权,控制地盘却不能直接管理。对于朱元璋的这类重大政治决定,从来没有人唱反调。直到洪武八年,皇帝下诏求直言,山西平遥训导(大概相当县委宣传部长)叶伯巨可能因为官小,不了解朱重八其人的德行,跳出来说什么——
今秦、晋……诸国无不连城数十,异时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愿……节其都邑,减其兵卫,限疆理……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
朱元璋的反应是“大怒”说:“小子间吾骨肉!”马上下令逮捕,叶伯巨不久就在牢里送了命。后来朱棣所谓“靖难”成功,完全符合叶氏的推理。靠封建制上台的朱棣主观上当然不会再想搞封建制了,但自己当初打的是维护父皇政治遗产的旗号,一时也实在不好出尔反尔。果然自己的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后来又想走父亲的老路——从侄儿朱瞻基手里夺取帝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百年后,都还出现了宁王朱宸濠起兵谋逆的事。
满洲人入关,没有搞封建制(清初的“三藩”纯属一种权宜之计,作不得数)。因为是满族人的天下,汉儒大臣们也没有谁敢在这方面多嘴。王船山议论过这个问题,可他当时在野,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以上对“中国式封建制”的简要回顾,是想说明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所谓“中国式的封建制”,一直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在起伏沉浮。说自秦代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式封建制便成了一个“消亡了的历史范畴”,这话不能成立。
二,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东来以后,日本人把feudalism一词译成封建主义(制度),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当然可以说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如果没有错呢?那就是自己的笑话一桩。检验其实是很简单的,即两者究竟表述的是否同一事物。持“秦后无封建”论的先生们认为封建制和feudalism完全是两码事,秦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是feudalism(还另外给起了个名,叫“皇权专制主义社会”云云),不过这里有个小小的悖论——既然秦以后必须改名,那不就等于承认周朝的八百年是封建社会吗?这个封建社会和feudalism是不是一回事呢?从形式上看,周武王和查理曼大帝实行的分封没有根本的差别——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处: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日本人到底是错了还是没有错?以上是个逻辑怪圈,越想你会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