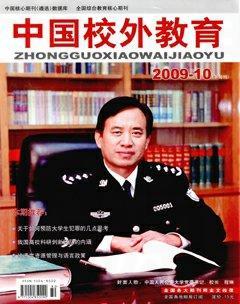施蛰存与冯至的历史小说创作比较谈
杨 莉
[摘要] 历史是历史小说的创作题材,因此历史小说不能完全离开历史随意地创作。然而,同是历史小说却可以有不同的样式,这关键要看小说家从什么角度切入历史。施蛰存与冯至的历史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深入认识历史小说的范例。
[关键词] 历史小说 不同样式 范例
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小说的创作,施蛰存的《将军底头》和冯至的《伍子胥》是很值得一提的。初读起来,你似乎会有一种读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感觉。然而仔细体味就会发现,二者完全不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核心在于解构历史、颠覆历史以至于重建历史。它推崇的是克罗齐的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一切对历史的阐释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所以,作家完全可以用任意的方式去解释历史。历史本体失去了意义,客观与规律不再被作家看中,而相对主义和偶然性成了无限夸大的真相。的确,历史是已发生过的事情,就连历史家在纪录它的时候都难免有自己的主观倾向,对于小说家则更不必说了,其主观创造的自由度更大。然而,不少新历史主义小说似乎发展到了极端,任意调制歪曲历史,创作的动机或为了哗众取宠或为了媚俗,历史成了调侃式的戏语。相比之下,施蛰存与冯至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显然更具有大胆创新而又不失本体意义的价值,他们留下了历史小说的不同样式,因此,在历史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下面我想就这两位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进行个案分析并比较它们的异同,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更接近于历史小说的本来面貌,也因此对什么是历史小说有更深入的认识。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包括《鸠摩罗什》、《将军的头》、《石秀》、《阿褴公主》四个短篇。每篇都有冲突并都是在心理冲突中推演情节,因此读起来情节变化远不如心理感受来得强烈。作者在自序里讲到:“《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的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作者的本意如此,但作品一经产生便有了大于作者本意的意蕴。
《鸠摩罗什》展现的不仅仅是道和爱的冲突,更多的是人和佛的冲突。鸠摩罗什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介事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三大翻译家之一。然而,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与理想中修炼成的佛该有多大的差别!人只有灭绝了七情六欲,真正做到“四大皆空”,才有可能参透佛家的经典历炼成佛。我们先不评论这种宗教的科学与否,只从常理上说,在这个成佛的过程中,人的思想该经历多少复杂的斗争!一方面是自己执着追求的功德圆满,一方面是难以割舍魂牵梦萦的情和爱,做一个绝情灭欲的大智高僧实在太难!情欲一直是这般如丝如缕蔓延、吞噬着鸠摩罗什,妻子死后获得的解脱与自信在长安一点点消失殆尽,一任自己的情欲无限的泛滥,最后只好以魔法的草草收场来证实自己的功德并以警戒他人。
《将军的头》是讲一个赫赫有名的唐代将军花惊定的悲剧故事。花将军是那样“勇猛英锐”,可是在灵魂深处却有着激烈的斗争:是完成大唐将军的使命杀退祖国的乡人,还是反叛大唐回归到中国的怀抱?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将军没法解决,然而一结未解又来一结:从不言爱的将军爱上了被他下令砍掉脑袋的骑兵曾经猥亵的那个美丽绝纶的女子!将军因此无心恋战以至于竟掉了脑袋,执着于爱的无头的将军骑着马终于来到少女的身边,然而,得到的却是一番嘲讽与讥笑,所有支撑生命的意志顷刻化为乌有,将军死了,不会有种族与国家的归属问题,更不会有名誉与爱情得失的忧虑!我们无法公正地指责将军的行为,因为我们控制不住要被将军那种内心的纠葛和执着感动。
《石秀》是一篇更心理的小说。曾经《水浒传》里仗义执侠的英雄石秀是不是心理有过无法让世人知道的隐秘?施蛰存从这里开始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石秀。潘巧云的妖娆妩媚简直成了年轻气盛的石秀难以逾越的诱惑,一边是拜把的兄弟,一边是美艳的女人,石秀用理智和义气压抑着占有潘巧云的欲望,而潘巧云与海和尚的偷情激化了石秀心理本就难以平息的欲望,这欲望没有发泄的出口,积郁久长便萌生了杀机,最终促使石秀怂恿杨雄肢解了潘巧云,并在这血淋淋的“美丽”中满足着。
《阿褴公主》是这四篇里情节稍微复杂的一篇。大理总管段功帮助梁王退败敌军并因此获得了梁王娇美的女儿阿褴公主,故国的妻子和祖国遥遥地等待着他。终于回来了,段功却发现祖国和妻子都不如阿褴公主重要,他又走了,等待他的是死亡的陷阱。英雄段功死在情敌驴儿丞相的阴谋里。阿褴公主失去了丈夫,在众宫女的监视下想的只有复仇,不想被狡猾的驴儿识破反被其所害。在一场政治阴谋中一段悲伤的爱情结束了,留给我们无尽的慨叹。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独特在他从人物的心理挖掘入手,从一个人的心理斗争的角度直入到历史的人,把历史的人首先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和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他们是历史中活生生的复杂的高僧、将军和英雄。历史中的鸠摩罗什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之途上一定也受到不少煎熬!还有在种族和国家、欲望和爱情之间苦苦徘徊的花将军,道义与情欲纠葛中的石秀,种族与爱情、现实与理想无法调和的段功和阿褴……施蛰存正是极度重视了这些历史生命个体的心理本真面目,在塑造这些形象时,突出表现的是历史的这些人而不是简单的这些人的历史。施蛰存在小说中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主要经历,只是由于切入与关注的点不同,使施蛰存获得了不同与以往历史小说新的特质。
总体来说,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确实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尤其在历史人物塑造方面。但是,我们在这条新的路上又不难发现一些不足,当一个作家着力于一个方面叙述历史和刻画历史人物的时候,必然会在突出这一个特殊性的同时忽视了普遍性,这也是经常难以避免的。施蛰存在强调突显历史人物心理冲突时,给我们又带来这样的感觉,这些历史人物难道整日除了没完没了的心理斗争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吗?对于这一点,王瑶先生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描写心理十分曲折,笔锋很细腻,故事结构也颇纤巧,”但是“着重于性心理的曲折的分析,却失掉了人物的完整性和作品的社会意义”。
冯至的历史小说读起来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感受。他的历史小说透着深邃的思想和哲理的火花,阅读时你会情不自禁地进入一种思考状态,时时会感到身上有种无名的重负并直压向心底。这与施蛰存历史小说从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进入历史人物内心感同身受的问题,它带着我们经历漫长的思想跋涉,并在不停地追问中得到一种灵魂的升华。所以,冯至的历史小说是哲理与历史的精妙结合,是沉思者直面现实与人生的拷问。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他的经典之作《伍子胥》。冯至经历十六年的酝酿才成就了这篇杰作,这里蕴藏着太多深刻而丰富的意味。在《伍子胥》后记里,冯至说:“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份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陨落……若是用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象,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我这里写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
子胥从城父到吴市的不平常经历按照一般的写法自然离不开故事情节的千回百转,然而冯至的独特就在于《伍子胥》写得既让你为子胥一路的曲折遭逢揪心,又不让你沉浸于其中。它的情节是以一种诗意的叙述呈现出来,在你体味这段诗意的不平凡经历时,融入太多的情感和思虑,于是这艰难的思想跋涉又淡化了情节,让我们更多的关注投射在子胥这个人身上。又是一部重视人的生命本体的历史小说,然而这显然不同于施蛰存的小说。同样关注人的生命本体,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带读者直接进入历史人物内心尤其是性欲心理,体验更多的是一种内心欲望被压抑的心理历程。而冯至的历史小说带读者进入的是另一个精神世界,如果人的心理世界可以分层次的话,施蛰存历史小说揭示的是底层直接与肉体相连的心理世界,而冯至历史小说展示的却是高层的与精神追求相连的心理世界。它引领我们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生与死、责任与自由、选择与放弃……在这样的思想跋涉中勇敢地直面现实,并对生命和人生进行某种深层的终极关怀。可能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在两位历史小说家的引领下同样进入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但感觉却是这样不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让我们更关注的是个体在相互冲突的矛盾中被压抑的内心,而冯至的历史小说却给我们某种人类的共通感,它超越了历史时空获得了一种不寻常的打动人心的魅力!
施蛰存和冯至的历史小说又都是基本上遵循着不改变原有历史人物的主要经历的原则,但又都不仅仅拘泥于真实的史料,都融入了作家的想象。而这些想象并不是凭空的臆测而是符合人物发展的逻辑,所以读起来没有感到对历史有什么不忠。这显然是与新历史小说解构、重建历史的最大不同。虽然忠实于历史,但是具体怎样去写历史人物,施蛰存和冯至也是有较大的区别。施蛰存重视的是历史人物被压抑的心理尤其是性心理真实,所以小说像一部被作者强化了的历史人物心灵史。施蛰存“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历史小说集《将军的头》,在他看来“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由于作者使我们更关注于历史人物个体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很难有一种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找自身的自觉意识,至多是以人之常情去揣摩历史人物并给予某种符合情理的认同。而冯至重视的是古今人身上共存的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在《伍子胥》中,他投入了许多现代人的关照。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脱去了太多曾经是浪漫的幻想,在后记中,冯至说:“当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所以冯至也明确地说伍子胥的故事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历史故事,它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一个古代逃亡的故事就成了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容易在子胥身上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产生了共鸣。
总的来说,从创新的角度看,两位作家都给历史小说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我们在阅读欣赏中也深刻体会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只是作家创作的题材,它的主要史实不应该改变,同时,历史小说的创作可以尝试多样的方法,究竟如何展示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小说家是可以大做文章的。我想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认识应是一种尺度吧:“历史小说,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小说……现代的人生,是过去的人生的连续……过去的历史可取的是为了它是人类生活的记录……历史小说,既然取材于历史,小说家当创作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束缚的。然而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也没有太拘守史实的必要。”
参考文献:
[1]克罗齐.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
[2]莱辛.张黎译.汉堡剧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60.
[3]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上海:上海书店,1988.
[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298.
[5]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开明书店,1937.57.
[6]叔明.评《将军的头》.现代,1932,9.
[7]田畋.伍子胥.大公报,1946-10-15.
[8]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月刊,19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