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甄静慧
在正确的方向上集中资源打造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多少时间?1991年方正式提枪上马的香港科技大学给了我们一个被国际视为奇迹的速度——10年。
2001年,香港科大校董会找到时在美国休斯顿大学任职,在国际重要奖项上屡获殊荣的朱经武教授,游说他出任这所年轻大学的校长。
“充裕、有弹性的经费;一套公平、开放的寻找优秀教师及升迁奖励制度;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政府的不干预态度——这三个重要的条件使香港科技大学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谈起这所与自己有8年深厚缘分的大学,朱经武的话语里充满自豪感,但也不无遗憾。
虽然从美国带来了不少经验,这些年也渴望力推香港教育制度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的,是高度民主化给改革带来的重重限制。
“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不同的优势和局限。”今年10月,朱经武将结束在科大的任期返回美国。即将离任之际,对香港、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他寄予了不一样的希冀,“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香港比内地走快了一步,已拥有3家国际研究型大学。然而,欲再进一步进行大学结构的合理设定,香港受立法会限制太大,很难成功。而从目前的种种问题看来,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难度固然比当年的香港要大,但因为内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如果找准了方向,进一步进行深度改革的可能性反而比香港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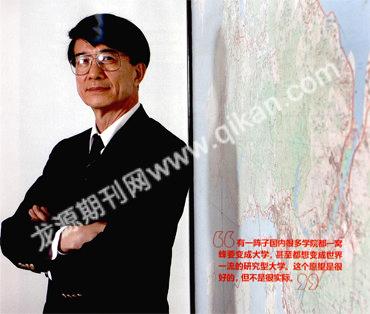
校长就是拉拉队长
《南风窗》:近来内地针对学术自由问题的讨论很多。你觉得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行政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怎样才是比较健康的?
朱经武我觉得学校应该是相当自主的。关于学术自由,不但政府不应该干预,连学校里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反过来行政上的职责是学校行政部门负责的,教授和老师们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最终对外负责的人是校长。
所以。香港的校长也是挺有权的,不过权与责往往要挂钩。据我了解内地的大学现在并没有董事会这个角色,但是在香港,假如我做不好校长这个角色,学校董事会是可以把我裁掉的。
《南风窗》:校长也是由董事会聘任的?
朱经武:由董事会聘任,但也要得到政府的同意。
香港回归以前,校长在香港的地位是很高的,港督下面就是校长。回归以后,政务司司长是二把手,往下依次是财政司、教育局局长,然后到校长。现在校长的地位依然是比较高的。
《南风窗》:你觉得在香港,大学校长具体需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朱经武:我觉得校长其实是拉拉队的队长,要想尽办法使大家都非常积极和乐观地向前走。当然,除了当好拉拉队队长,你还要把这个学术环境建造得很好,包括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但真正做事主要靠老师,校长做不了太多事情。
在大学里当校长不像在公司当管理,看哪个人不高兴就可以把他直接炒掉。在学校,其他教授的学术地位可能比校长更高,你要使他信服,过去的学术地位就一定要很高,并得到同行的尊敬。另外,假如校长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话,在进行其他方面工作时也会更方便,大家会给面子——尤其中国人的社会很讲面子。
教育经费是政府的责任
《南风窗》:内地关于教育经费的争论很多,香港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情况是怎样的呢?
朱经武:香港的大学经费基本上都直接由香港政府给。
香港也有很多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美国州政府只需要给公立学校30%-40%的经费,而香港政府需要给到80%(不算学费)。香港的老师和校长为什么不积极去找别的钱。
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美国除了州政府外,还有联邦政府。虽然州政府基本上只会供给大学进行基本设施和基本教育的经费,但联邦政府给学校的钱是非常多的,而且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可以申请它的经费。
除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也会给学校钱。几年前,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到这里来,说起州政府给他们学校的钱不到30%,相比之下香港政府负担很大。但我再详细地问他。原来他们还有来自美国国立卫生院、能源部、国防部和国际自然基金会的钱,这些全是政府部门,其实仍然是政府的钱。另外州政府还划拨给他们一大笔额外的研究经费。
《南风窗》:以往我们有个错误的认识。国外大学的研究经费很多来自于社会资源,比如财团的赞助。
朱经武:社会资源当然有,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大。
我刚才讲到UCLA的校长来跟我讲那30%的事,我说你们有医学院对不对?他说对,我们医学院很大,医学院的钱绝大部分是美国国立卫生院来的。然后我再问他,你的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州政府给多少钱呢,他说100%,因为这些院系没法申请卫生院和国防部的钱。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美国大学在教育这一块,完全是政府给钱的。只有研究方面的经费需要发展其他资源。好学校可以争取到很多研究经费,不好的学校就很少。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好项目才能拿到钱,使学校之间形成竞争。
《南风窗》:对办学经费内地有很多争议的声音,很多人批评内地大学负债办学的问题,讨论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应该多去发掘社会资源,增加经费的来源。
朱经武负债办学这个现象,是个畸形。
我不太清楚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也许10年前吧,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很快,所以一些办教育的人就大规模贷钱,造成了现在的现象。其实学校是不应该有负债的,因为它不可能赚钱,所以不能贷款,不赚钱的情况下让他们怎么还贷?
当然,你可以说学校还能收学费什么的,但在教育成本上,学校花费了100块钱,最多就只能收100块钱学费,超过100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这样依然不能盈利。
负债办学的问题既然已经发生,我觉得解决方法应该是政府拿钱出来把这些债务全部取消。
至于经费来源的拓宽,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后对学校的私人捐助肯定会渐渐增加。就像香港,霍英东先生曾经一次就给我们捐了8亿,李兆基先生也给了,我们7亿多。但是,社会捐助不是持续性的,他给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给,而学校经常性的经费是每年都需要的。我们学校去年花掉的经费是20多亿。
所以,靠人家捐钱过日子是非常难的。教育始终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对将来的长远投资。
《南风窗》:除了经费问题,内地的大学还存在严重的学术腐败,已经有多起事件被曝光。
朱经武:我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和香港,也有学术腐败现象,但是非常少。内地个别大学有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还是封闭。只要学校完全开放的话,再做这种事的成功率就非常小。
不要一窝蜂做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么说其实不论香港还是美国,大学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政府,
只是来源于不同的政府部门。而不同学校获得经费的差异其实只是在于研究那一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结构其实是促进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
朱经武对,美国是这样子。你要研究、创新,就要竞争才行。
在香港,差异没有美国那么大。香港最好的3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科大只在研究制度上占一点便宜。所以现在香港和内地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应该划分不同类型的大学,不要一窝蜂地向一个方向发展。有时我开玩笑说,如果所有大学都培养出我这样的人,都去做物理,做超导,那这个国家连饭也没得吃了。
《南风窗》:你说的类型分开是指从专业上去划分吗?
朱经武:不是,是从目的去划分。你看加州的大学是分成三类型的。第一类是研究型大学;第二类是4年大学,叫加州州立大学,是以教育为主的,偶尔也做点研究;第三类叫社区大学,这一类大学占的比重非常大。因为一个社会需要很多受不同教育的人来维持。
据我了解,有一阵子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是很好的,但不是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这是做不了的。
做研究型大学第一要有钱,办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中国这么大,如果所有大学都要当第一流的,这个经费不得了。
作为研究型大学,要到全世界去竞争,寻找优秀的老师,工资、资源等付出肯定要大很多。教授要做研究,学校要给他房子、实验室,更重要的是给他时间,不能让他每天教8小时书。
而4年大学的老师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少一些,一个老师可以教3门课,意味着它成本低些。到了社区大学的话,老师根本一点研究都不做了,只教一些很基础的课,课教得多,加上他不是世界的大学者,薪水也不一样,办学成本自然就更低。

第二,研究型大学需要有大量人才,内地有人才优势,而这方面香港则比较缺乏。
所以我觉得内地首先需要设置不同的分工,香港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虽然香港的大学经费非常充足,但香港现在一共有8家公立大学,如果全部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现在香港基本上只有3家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科大当然是研究型大学,但我们也不是综合性大学,主要有理工学院、商学院,虽然也有社会科学学院,但规模比较小。另外两家就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他们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其实不就有了一个区别吗?
朱经武:是,大家都知道,但不能讲。
香港是个相当民主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英教育不能完全走得通。除非是政府强硬地要求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会不太愿意。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内地做起来可能比香港容易一些,因为内地政府比较有权力。
香港政府基本上不会像美国那样,按项目给学校钱,而是看一所学校有多少学生,就给多少钱。但是政府有一个调剂方法,就是研究生数量,给一所学校多批一些研究生,钱就上去了。希望经过这样的调剂慢慢把层次分出来。
但还有个问题,我们的教授跟一些非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相比,薪水差别并不大。幸而很多老师最看重的不是薪水,而是研究环境。
《南风窗》:所以现在香港的大学设置受到了民主化的限制?
朱经武:是的。学校这样的角色分工,之所以加州能做,是因为60年代那个州长跟校长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容易做出来。现在加州模式即使在西方也很难重复了,德州一直想模仿加州分三种类型的学校,但因为州议会的限制,所以很困难。
同样,在香港再建第二所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科大能迅速发展,是因为港英政府还在,没有什么投票啊、立法权啊这些事情,政府说了就算数,说要建校就做起来了,现在很多事情要经过立法会。
《南风窗》:那么针对香港的情况,我们看到教育体制中存在一个矛盾,就是政府到底要不要放权。
朱经武:我是这么看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但强有力的政府并不表示一定会违背民主。我觉得内地政府既需要慢慢放松,也需要很多支持。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当年台湾政府很有实权的,所以工业教育发展非常快。有点像新加坡。现在台湾也打开了民主化之门,很多事情就变得困难了。
台湾有160多家大学,生源根本不够,训练出来的学生又都想当世界一流学者,眼高手低,不会做实事,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内地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所以内地讨论怎么样能恢复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学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南风窗》:那你觉得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和这么多的人口,有多少家大学是适合的?
朱经武:我觉得需要多些。我们现在只有18%的学生能进大学,是纯精英制的教育,但是精英下面就没有了,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块缺了很大一条沟,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是不利的。
高考改革没有完美途径
《南风窗》:关于大学对人才的选拔,内地的高考制度也是一个改革的重点,现在我们基本是一考定终身,有些教授想用一些灵活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学生,但不能够。
朱经武不仅是中国,欧洲也是这样的。
因为社会需要公平,假如我跟一个学生聊聊天,就决定了他能不能进一所好学校,往往会流于主观,有失公平。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你问我考试制度是不是坏的,我想它的确是,应该这么说,是第二坏的。
现在我们学校在香港招生也是通过考试。到内地找学生时,也看他的高考成绩,但只是作一个参考,此外还要面试。但那是因为在内地的招生数量少,才可以这么做。
在考试之外。我们还找了一条路子,凡是真正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免掉他们不必要的考试。比如说很多年前,有一位同学对信息科技发明非常有兴趣,在世界发明奖拿了第一名。但他的成绩其实不是那么好,我们学校就破格收了他。
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不满,说我成绩比他好,却进不了这个学校,这不公平。但我们觉得,如果能够为香港造就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的话,远远胜过培养10个在各方面都平衡、普通的人才。
训练教育通才固然不容易,培养教育专才更难,因为你要在早期发现他。
《南风窗》:关于高考还有个问题是,这些年内地高考制度经常在改,最早考全科,后来文理分科,后来又不分,光是关于文理分科的问题,争论就一直比较大。
朱经武:关于如何选学生,我觉得永远找不到一个完全理想的方法。当年台湾也经历过文理分科的反复阶段:一下分科,一下又取消。
我们发现取消文理分科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有个同学,明明理科成绩非常好,但文科成绩却不理想。取消分科后,学校根据总分录取学生,所以他被分到政治大学去读文科了。后来只好又重考。
所以就算文理不分科,也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出现偏差。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学生需要比较广的知识面,训练专才的时候不可能什么都兼顾到。
总的来说,我觉得最好还是慢点分,但是这个做起来很困难,如果不分科的话,大家都去考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都向钱看,不看兴趣了。
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完全是教育问题。
《南风窗》:那对于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你有什么期待?
朱经武:我希望政府认真想一下,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富更强。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假如目的很清楚,方法是可以商讨的。
在大原则上定了以后,其他应该松绑、宽松。每个地方、每个学校走的路子可能都不一样。让他们自己找路子走,远比规定他们怎么走要更有效。
所以,首先是大原则大方向一定要定下来,然后一些次要的细节,要尽量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