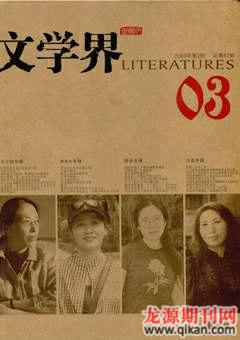我叫她小路
于瑞桓
一把花伞、一条藕荷色裙子,站在烈日下的济南大学46号宿舍楼前,眼神中露着不知该向南向北还是向东向西的迷茫和张慌,这就是小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这个十几年前的影像,并不一定像我所描述的那么清晰,而是在以后的相处中,她超乎常人的敏感和略带惊恐的举止一遍遍地加深了这个最初印象,以至在脑海深处浇筑了这个不变的塑像。
路也在九个月的时候,忙于工作的父母就把她送到了姥姥姥爷身边抚养。三岁那年,姥姥去世,留在她记忆里的第一个人生画面就是姥姥的葬礼,当然是模糊不清的黑白的记忆。等会走路了,她歪歪扭扭地走在济南南部山乡,一看到悬崖或陡坡,就指着那崖或坡的下面,口齿不清地提醒自己要注意安全:“这里找不着妈了”,再走到另一个看上去有点陡峭的地方,还是战战兢兢地指着说“这里找不着妈了”——她的意思是说,如果小孩子从这个危险地方掉下去,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了——她不说妈妈找不着自己了,而反过来说成是自己找不着妈妈了。那时姥爷常在外喝酒,忘了回家,她一个人坐在锁着的大门外面,心生恐惧:“姥爷会不会再也不要我了?”惊恐和期盼成为路也童年情感的母元素。而以后她误入的婚姻、情感误区,和父亲的突然离世,又无不都是在一次次地加剧着她的恐惧。一米五几的弱小身躯和不谙世俗的超脱,本该与“顶梁柱”无缘,而现实的生活却非给她分派个如此高大的形象让她承担:照顾病重的姥爷至到把他安详地送离人世;与伤害父亲的肇事司机对簿法庭;忍着悲伤安慰受不了打击的母亲,这些在常人也难承担的生活之重,一次次毫不怜惜地向她袭来,她挺着,表面看像似钢筋铁骨砸不断压不弯;其实,真实的她却是个早折过多少次的芦苇,只是在无人注意时又一次次把伤口缝上了。生活中她除了几个可以说说话的闺中密友,从来也没有过一个真正可为她遮风挡雨的人走进她的生活。“我跟随着你/ 我不看你 /也知道你的辽阔”,“你是我的白日梦——我脚踏实地地过着虚拟的日子”,想象中的丰富和现实的贫瘠,给她现实的生活织出的是一片虚无斑斓。在生活中,本该是“弱者”的她,被反串成强者;在事业上已成了“强者”的她,反而让人还觉得她是个“弱者”,如果有人夸她文学上的才华,她一定会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接下来更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还会严肃地说“我算什么。”
“其人如文”被路也从生活中复制到诗里了,率真、脱俗、善良,从来没有“转念一想”的狡黠,这是路也给我的第二重深刻印象。大概也是十几年前的一个夏日中午,我到楼下锅炉房打水,看到她又站在烈日的阴影处,我说:“大热天,站这干么?”她说在看易易。易易是我的儿子,那是好像也就三四岁。她以为我出门了,易易回不了家,怕他不安全就一直这么看着他。她自己虽然没有孩子,可对孩子的爱心却毫厘不差,她甚至郑重其事地向文学院提出过要选个连电都没有的贫困山区去支教的要求。汶川地震,单位捐款时要求签名,她捐了款,却拒绝签名,她讨厌借别人的死亡来给自己留名声,在这个时代,随波逐流很容易,孤立悬崖就难了。当看到在汶川地震中有许多老师以血肉之躯顶起钢筋水泥,以他们的生命换回了孩子的生命报道时,她说:“换了我也会一样做,要是学生都死了而我还活着,良心总有一天会逼着我自杀。”这种不符合高格调要求的语言是路也日常生活中一贯的语言风格,不会粉饰自己,率真而为,生活永远都像1、2、3那么简单,没有⒈5,没有过渡。真正懂了她的人会和她成为一生的好朋友;不懂她的人又常会在不经意时被她的别具一格的言论搞得一头雾水。“有个性”,常有人给小路下这类“语义不详”的定义, 其实,她最异于常人的是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但也正是她的不入俗不入流,才使她的人格和作品都如明月清风。
幼年时期害怕失去亲人的恐惧演变成她对生命超常的热爱:爱朋友、爱家人、爱她自己,她家房门朝里的那一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出门前注意:1,拔掉除冰箱外的所有电源插座;2;检查煤气总阀,要关闭;3,窗子关严;4;带上钥匙,把大门锁好。”这是贴在房门后的座右铭,这里有对生命的爱惜,有对危险的极度恐惧,也有形只影单的孤独。“我是你云鬓轻挽的娘子,你是我那断了仕途的官人”。而现实中的路也,虽然空有一袭长发,却没有一个人敢把那仕途断了去为她把长发挽起。她总是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绿袄花裙仍可与她相得益彰,连学生都说她“讲课的声音暖暖的,有着少女的淡淡的甜味”。我想,就是我们都到了80岁,我肯定还是叫她小路。
小路像只永远都把角竖着的梅花鹿,不管在静止的状态还是在运动的状态,都保持着一份紧张和警觉。而也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敏感,才让她喷洒出那么多优美的诗句,把我们从被琐碎平庸的生活和磨钝的感觉中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