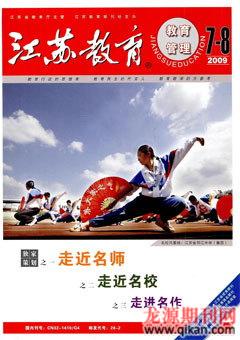启功:历史烟云里的文化追忆
周维强
最早知道“启功”这个大名,是从《红楼梦》这部书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还在念中学,曾经囫囵吞枣地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程乙本《红楼梦》,见书内标明启功注释。这么一部大书(“文革”曾传毛泽东说《红楼梦》要读多少多少遍),名物典章、风俗人情这么多,以一人之力作注(鲁迅先生的著作就不是靠一个人给注解的),“启功”这人真了不得!
及至念大学,才知“启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点校过《清史稿》,与也是毕业于北师大的王重民等著名学者一起编校过《敦煌变文集》。他又是满清皇族后裔,名牌大学“博学宏词”的学者,还有“家学”渊源,当然也就能以一人之力给《红楼梦》作注了。后来又陆陆续续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史》、《学林漫录》(后两种均由老牌的中华书局主办)等杂志上,读到启功先生的谈学(学术)衡艺(书艺)的论文、札记,以及回忆齐白石老先生等的散文,其行文清雅简洁,句句不落空,很耐读。我很喜欢,所以就常常会去找启功的著述来看,譬如那时刚由中华书局印出来的《启功丛稿》(是一卷本,不是前几年出的三卷本)。俞平伯先生允推启功先生的识见和功底,还说过“注《红楼梦》非启元白(引者按:启功,字元白)不可”的话(见邓绍基《读启功先生的学术著作》,载《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北师大中文系编,中华书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叶恭绰老先生在闲谈中对启功等人作的考语(参见黄苗子《夕阳红隔万重山——启功杂说》,载《画坛师友录》,黄苗子著,三联书店,2000年6月)。
听系里的先生说,启功对故宫内的藏品,对故宫,对清史,如数家珍。这些该是属于“传闻”吧。今读《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口述,赵仁珪等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确知这是事实。启先生说:
……从1971年7月一直干到1977年,任务是校点“二十四史”。我的具体任务是校点《清史稿》……和我一起负责点校《清史稿》的还有刘大年、罗尔纲、孙毓棠、王钟翰等先生,其中刘大年先有事撤出,后罗尔纲、孙毓棠也因病离去,只有王钟翰和我坚持到最后。在我们接手之前,马宗霍等人已经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但遗留了很多的问题。据他们说整理此书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满清入关前,即满清建立初期——努尔哈赤时代,很多典章制度都不系统明确,很多记载也比较简略凌乱,整理起来很困难;二是清史中的很多称谓,如人名、地名、官职名,和历朝历代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人名,本来就挺复杂,再加上后来乾隆一乱改,很多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拿不准、点不断了。
但启先生熟稔满清典章制度、清人称谓等等,所以他在这部口述历史里接下来很自信地说道:
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所以工作量虽然很大,一部《清史稿》有48大本之多,但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发现并改正了大量的错误,如《清史稿》中居然把宋朝人的、日本人的著作,甚至对数表都放了进去。经过点校,《清史稿》和其他各朝正史都有了准确、通行的本子。
《王钟翰学述》(王钟翰著,姚念慈等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有关点校《清史稿》的记述,可以作部分的旁证。王钟翰还说道:启功和王钟翰曾向当时的中华书局领导提及要做《清史稿》的《校勘记》,“回答是从未向上级提及《清史稿》要做《校勘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以不出《校勘记》为妥。那时,刚刚打倒‘四人帮,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王钟翰学述》)。
启先生学问中很多部分得自亲历亲验亲见亲闻,而不全来自书本,这恐怕是其他治清史者不太可能有的。启先生在这部口述历史里说道:
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
所以启先生说:
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
司马迁写《史记》,有的材料就是得自民间而非书本(著名的如《项羽本纪》、《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篇章都有例可证)。也是这个缘故,我也很喜欢读一些记录“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譬如启先生这部口述历史书里记录的有关乾隆皇帝为什么对太后非常“孝敬”,乾隆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亲王之间的关系,慈禧和光绪为何会同日而死的“内幕”等等,启先生娓娓道来其中的故实,一一点破其中的关节。这里面就有许多材料可以补充我们从书上得来的知识,增广我们的见闻。这都记在《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里,用不着一一转述其详了。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部书里记录的过去学校里的气氛,师生的关系,其间大有深意。“入学前后”一节里有很多发生在北京汇文学校里的有趣的校园故事,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我和张振先是同桌,一到课间休息,甚至自习课老师不在时,我们俩就常常“比武”,看谁能把谁摁到长条凳上,只要摁倒对方,就用手当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我宫了你!”算作取得一场胜利。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吃饭时,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这种童真和童趣是非常丰富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开明的老师,常能容忍孩子们的这种天性,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
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有趣: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宋衡玉(音),平时常穿日本式的服装。我们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愿意听。有一回在饭厅吃饭时,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着那个人不依不饶,那个人就往饭厅外跑,他嘴里骂着“儿子(读作zeU)!儿子!”地往外追,正好和路过的校长撞个满怀,校长拧着他的嘴巴说:“你又没娶媳妇儿。哪来的儿子?”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觉得校长实际上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游戏中了。
讲完了学生们淘气的故事后,启先生又说:
……我不是提倡淘气,但兴趣是不可抹杀的,在这样的学校,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事发生,大家生活、学习起来饶有兴致。
在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有几则师生的故事,也许也是有深意在的。譬如国文系主任尹石公(炎武)与学生的故事。尹石公“平常爱当面挖苦学生”。有一回,两个学生张学贤、杨万章作文没做好,尹石公就当面讥讽他们道:“你居然叫‘张学贤,依我看你是‘学而不贤者也:你还叫杨万章,我看纯粹是‘章而不万也。”尹石公的挖苦都有出典,“学而”是《论语》中的一章,“万章”是《孟子》中的一章。但接下来,事情弄大了:
不料第二天他(引者按:指尹石公)再去上课,这二
位(引者按:指张学贤、杨万章)给他跪下了,说:“我们的名字是父母所起的,如果您觉得哪个字不好,可以给我改;我们学业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批评,但您不能拿我们的名字来挖苦我们,这也有辱我们的父母。”尹先生一看二位较上真儿了,也觉得大事不好,连忙道歉,问有什么要求没有。这二位也真执著,说:“我们也没什么要求,只求您以后别来上课了。”尹先生一看玩笑开得太大,没法收拾了,便很识趣地写了辞职报告,打点行装,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另谋职业了……
这个故事,可能会对治民国高等教育史有用:对一般的教师,也许也会有点用处,启先生接着说:
现在想起来,这虽是一时的笑谈,但陈校长(引者按:指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教导:“对学生要多夸奖,多鼓励,切勿讽刺挖苦他们”是多么的重要!
这部书还记录了老先生们——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陈宝琛、齐白石、张大千、陈垣、杨树达、余嘉锡、陆志韦、马衡、沈兼士、唐兰等等,以及溥心畲、溥雪斋——的许多逸事,叫我们想见那个时代的老先生们,以及满清皇族艺术家们的风貌,还有书画鉴定里的种种掌故,真是很有趣味。
启先生的书画造诣、古文献学和文物书画鉴定的学问,大名鼎鼎,“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词!”启先生在书中说他的“书画鉴定”:
……自解放前就担任故宫专门委员的,到今天只剩下我一人了,经我眼鉴定的文物大概要以数万计,甚至是十万计,从这点来说,我这一辈可谓前无古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就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知足了。
我读到这里,所起的就不是“知足”或“不知足”的感叹,而是想起古语“观千剑而后识器”。在高科技尚未广泛用于书画文物的鉴定之前,没有对实物的博观,哪里谈得上“鉴定”!以前考古学界有人说,早年就学于北师大史学系的北大考古系的祖师爷苏秉琦老先生好闭着眼睛摸陶片,于是北大的同学也学苏先生闭着眼睛摸陶片。虽则苏先生说这话“三分是夸张,七分是误解”,但他也还是从长期的考古实践中认可这个“摸”对陶器的考古的重要性(参见《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6月)。引申到书画的鉴定,应与启先生的体会是相通的吧。所以我认为现在以收藏文物书画为个人投资者,多半属于不得要领而把钱去打水漂的。还有谁能像启先生他们那样看过那么多的古代书画啊!见不多识不广,谈什么鉴定?无鉴定又哪来收藏?古玩字画鉴定不易,就是当代名人书画,被造假亦有几达乱真的。据闻京城潘家园,有名的古玩市场,各地画商来这儿批发当代名人字画赝品,“捆载而去”(见《雀巢语屑》,唐吟方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自己若无鉴定的法眼,要以收藏古玩书画作投资,难保不会像俗语所说“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现在再来说说《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的记录。有的事,相同的一件,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记录。譬如点校《清史稿》,前引的启先生的口述是:“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但在《王钟翰学述》里,则有另外的记录,王钟翰说,有一回启功对他说:
五礼的吉、嘉、军、宾、凶中,我也许知道其中一小部分,哪能什么都知道呢?
启功还“感慨说”:
我们虽然从事清史研究有年,在某些方面也许多少有些一知半解,但就整个清朝一代300年全面来说,叫我们来干这项工作,是很不合适的,而我们实在也干不好。
记录这些话后,王钟翰又说:“启兄所云,实是通人之论,我也深有同感。”
按王钟翰的记忆,启功负责《清史稿》的“志”的点校,则启功后来在《启功口述历史》中所言(“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应是实话实说。如果王钟翰记忆无误、记录准确,那么,启先生前后对同一事的不同态度(前者“谦卑”,后者“自信”)的变化,细加考究,也许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可以表明,在不同的年代里,启先生这样的曾被划作“右派”、“文革”中又被当成“准牛鬼蛇神”的老知识分子。其精神风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还有一些事。启先生本人即有不同的记录。举一个例子。在辅仁大学时,有一次,启功作诗写溥心畲故居恭王府的海棠,有句云“胜游西府冠郊堙”(海棠常称西府海棠,“西府”是海棠的品种之一)。启功拿给陈垣校长看,另一位“同门”(柴德赓)也在。这位“同门”说“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呀?”《启功口述历史》里接下来说:
陈校长仍不说话,又用手朝他(引者按:指启功的那位同门柴德赓)一指,柴德赓马上意识到又出错了,脸都红了。
但是启功在写于1980年6月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1982年6月)一文里,却是这样写的:
……老师(引者按:指陈垣先生)笑着用手一指,然后说:“西府海棠啊!”这位“同门”说:“我想远了。”
这两处的记述就有比较大的差别,不知该以哪一处的记述为准。
从《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的编辑来看,也许还可以加一个附录,譬如启先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上的《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一文,就可以作为附录,可跟正文对照阅读。《启功口述历史》“院系调整”一节里,说上个世纪50年代,北师大中文系有位教授“专赳李长之先生”:
……有一位教授,虽不是党员,但比党员还党员,成了当时的“理论大师”。他现淘换一些马列主义的词汇标签到处唬人……他的学问是很有功底的,也深通义理之学……他专赳李长之先生……
这段历史对过来人,当然很清楚,对其他人就未必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对这位教授则有指向更明确的表述:
当时中文系师生许多划为右派,只有刘盼遂先生读书多,记忆强,虽没划右派,但口才较拙,上课后在接着的评议会上,总是“反面教员”。谭丕谟同志最受尊敬,王汝弼先生常引马列主义,学生也无话可说,他在批判别人时常给他们加上一些字、词,被批的人照例无权开口
再譬如,《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里说,“文革”结束后,“原来的系主任还有时根据苏联专家留下的理论,说只要把书教好,不需要什么‘科研。他带的硕士研究生不许做论文,而学校制度已然规定要通过论文。学生只得拿着论文请旁的老师为他看”。而在《启功口述历史》“院系调整”一节里,对这位“原来的系主任”则有指向更明确的表述:“师大初建时(引者按:指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时的北师大)任副系主任(引者按:当时仅一位系主任,一位副系主任)后来又担任过主任的那位教授。”
举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把启先生以前写的有些文章,作为这部书的附录,恐怕也是有必要的。
最后给这部书的整理工作,提一个小小的意见。这部书,从头至尾,直到整理者赵仁珪教授写的《后记》,均无启先生口述时的时间和地点的明确的记录,只在《后记》里笼统提到一句“启先生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这对于口述史学来讲,也许是不太够的吧。
佳作链接:
1,《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本书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著作。著者说:“文中多有跑野马处,或者还跑得不很够,亦未可知。但野马也须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这却极不容易耳。”此言得之。
2,《黄药眠口述自传》,黄药眠口述,蔡澈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此书详细记录了药眠先生坎坷、传奇的一生,尤其是他鲜为人知的追求和参加革命的经历。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文化老人,文艺学家,美学家,诗人,教育家,半世动荡的回忆,未及全部写毕,即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