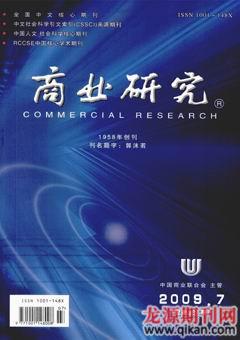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时机选择
俞雅乖
摘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适用情况不同,适宜的制度变迁方式能实现较高的变迁效率和较好的变迁效果。制度变迁进程中须进行方式的转换,因而分析制度变迁的转换时机和条件是问题的关键。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主要包括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和退出两种情况。
关键词:制度变迁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Transformation Time Selection of Institution Evolution Mode
YU Ya-guai
(School of Economic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Ow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ying instances of inductive institution evolution and compulsory institution evolution, feasible institution evolution mode can carry out upper evolution efficiency and preferable evolution effect,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 evolution mode is necessary during institution evolution process,so the analysis of time and condition of institution evolution is the key part.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 evolution mode includes entry and exit of compulsory institution evolution.
Key words:institution evolution mode ; inductive institution evolution ;compulsory institution evolution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其中制度变迁方式是影响和确定转型效果和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的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以探寻出合理的制度变迁方式,充分发挥制度变迁的效果。同时,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不同特点,不同的制度其变迁方式也各有不同,同一制度在变迁进程中不同阶段适用变迁方式也不同。这里主要解决具体制度的变迁进程中不同阶段适用的制度变迁方式。由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效果不同,其变迁的时机选择和确定比较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为了追求制度变迁收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提高制度变迁效率,必须选择合适的制度变迁方式,这个问题就转变制度变迁方式选择问题和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时机选择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问题。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自发进行的,无法选择和控制,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时机选择主要是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和退出时机,具体指强制性制度变迁取代诱致性制度变迁(进入时机)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取代强制性制度变迁(退出)这两种情形。
有的学者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角度来对制度变迁方式进行划分[1],其实是从另一角度对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转换进行分析,突破了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思路。有的研究突破了制度变迁方式的线性角度,运用熵理论从非线性角度对制度变迁方式进行了分析,再次证明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不是对立的,而且是互补的。[2]有的学者分别以农业制度变迁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为例分析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时机和退出时机。[3][4]有的研究从替代地方政府部分功能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形成角度分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替代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5]有的学者分析了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不利影响,包括上市公司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扭曲、证券市场的制度规则混乱和市场结构缺失和功能扭曲、以及竞争、约束和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论证了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方式应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6]有的研究通过分析税收收入增长的制度变迁方式,以说明税收制度变迁在我国税收增长中的重要作用。[7]不同学者的论著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一点是肯定的,一般学者都认同制度变迁方式分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且在分析两种制度变迁方式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互补和替代关系。
二、制度变迁方式之间的转换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拉坦(1994)分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概念是从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技术进步和知识增进对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入手进行了解释,“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项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8](P328)。拉坦侧重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来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认为制度变迁的需求动因主要包括:“……新的收入流是对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变迁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P335)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在于“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也就是制度变迁的需求主要在于追求潜在收益;制度变迁的供给动力主要在于降低现行成本;由此出现了制度变迁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管是追求潜在收益,还是降低现行成本,最终目的都在于“潜在的外部利润”(戴维斯,诺斯,1994,P282)①[9]。
因此,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强调了内生变量的影响,强调了首先利用经济体内部导致非均衡的力量自发的进展,然后沿着非均衡的发展路径再给予一个类似于强制变迁的外部推动力,就能保证改革沿着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相一致的道路加速前进。这样,诱致性变迁不但充分发挥了个人选择和民间力量对改革的原始推动力作用,而且借助于强大的垄断的政府资源的后续拉动力,源及自民间的原始变革需求和初始的改革措施就能够迅速扩展。
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给出了明晰定义的是林毅夫(1989,P384)[10],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这个概念包括了以下要素:(1)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实施主体是个人或一群(个)人。这里的个人或一群(个)人包括了个人、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企业或政府;其中个人、企业是初级行动主体,或第一行动集团,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杨瑞龙,1993);政府(或其代表的国家)是次级行为主体,或称第二行动集团,也是一个决策单位,其作用是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得收入进行一些制度安排(杨瑞龙,1993),推动制度变迁。(2)实施动力是获利机会。即获得“潜在利润”(林毅夫,1989,P392)或“外部利润”(戴维斯、诺斯,1994,P282),或者说是“潜在的外部利润”。用林毅夫的话就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3)实施特征是自发性和渐进性,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4)实施方式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创新的含义包括了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变更现行制度安排或是创造新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