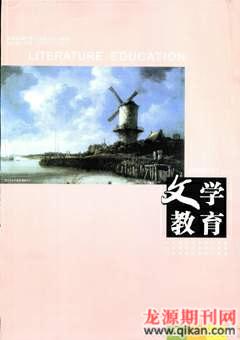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
鲁枢元,男,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生态文艺学研究室负责人,国家人事部命名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诸学科领域有开拓性研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1985)、《文艺心理阐释》(1989)、《超越语言》(1990)、《隐匿的城堡》(1995)、《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猞猁言说》(2001)等。主编的著作有《文学心理学教程》(1988)、《文学心理学著译丛书》(1988)、《文艺心理学大词典》(2001)、《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2002)等。随笔《生命诗篇》,曾入选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
在心理学史上,记忆是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课题。
古希腊神话中说,主宰整个宇宙和人生的万神之王宙斯和记忆女神谟涅靡辛涅结合之后生了九个女儿,即分管悲剧、颂歌、喜剧、史剧、舞蹈……的文艺女神缪斯姐妹。这意味着,文艺女神的父亲是宇宙人生,而文艺女神的母亲,则是记忆。这虽说是神话,倒也生动明白地表达了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于文学艺术活动与人类记忆的关系的看法。
以往的心理学教科书在分析人的识记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方式时,仅仅提到“理解识记”和“机械识记”。前者,即如对于定义、定理、公式、规律的识记,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之上的对事物内部联系的掌握;后者,是建立在意志力控制之下的、强制性的“死记硬背”,如对于商品价格、电话号码的识记。此外还应当存在着一种凭借身心感受和心灵体验的记忆,理解记忆、机械记忆、情绪记忆,是分别建立在思维、意志、情感三种基本的心理活动功能上的记忆方式。三者相互渗透、相补为用,为每一个正常人所具备。但又因人而异,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人们来说,情绪记忆在其全部记忆活动中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不但是超出常人,甚至还会超出他们自己的理解记忆和机械记忆的能力。画家黄永玉在回忆表叔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说:表叔记性非常好,对于童年生活中许多琐事细节都记忆如昨,但谈起现代科学时所引用的数字却明显地不准确,常被膝下的孩子们抓住辫子不放。“文化革命”中,那些看管他的人员要他背诵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莫展。已故作家高晓声谈到当他度过20多年的坎坷岁月又重新执笔为文时,“连许多常用字都忘记了”,但农民生活中涉及的每一个角度,农民心灵中的每一丝悲欢,都深深地印上他的心头。一朝面对稿纸,“半生生活活生生,动笔未免也动情”,这就使他写出了一篇篇富有真情实感的优秀作品来。
情绪记忆是一种比理解记忆、机械记忆更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它大约具备下列一些显著的特点。
(一)古老的、原始的。从人类发展史看来,原始社会的人们最早的思维方式还不是周严地运用概念进行推理判断的逻辑思维,而更多地表现为在记忆的基础上展开的联想与想象。列维·布留尔(Levy-Brühl,1857—1939)在《原始思维》一书中通过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那些在不文明氏族的思维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前关联、前知觉、前判断根本不要求逻辑活动;它们只不过依靠记忆来实现。”“原始人的记忆有非常高度的发展”,“它既是十分准确的,又是含有极大情感性的。”他还引述罗特(W.B.Roth)对中昆士兰西北部土人们“惊人的记忆力”的记载:罗特亲自听土人们用整整五夜的时间才唱完一支歌”,而奇怪的是演唱者和听众之中没有一个人懂得一个词的意思,而歌词却记得非常准确。在列维·布留尔看来,原始人的这种惊人的、远远超过现代人的记忆能力,是一种带有极大情感性的记忆,而理解记忆只是在以后才渐渐发展起来的。[1]
从一个人的生长发育史来看,理解的记忆、机械的记忆都是出现较晚的,而情绪记忆的能力几乎在诞生伊始就具备了。沈从文先生对于自己襁褓中的记忆追溯得很早,他说他祖母死时他才刚刚活到这世界上四个月,他仿佛记得被谁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他说“若不是我在两岁以后做梦,这点影子宜应当是那时唯一的记忆。”沈先生的回忆也可能不准确,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婴儿心理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富有激情色彩的感觉,婴儿意识中首先出现的心理活动是与他直接领会的动作有联系的情感成分,其实这便是一种情绪记忆的活动。
(二)感性的、新鲜的。理解记忆和机械记忆的内容往往是抽象的或概念的,而情绪记忆的内容则总是形象的、生动的、活生生的。心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人的情绪活动基于主体的切身体验,与人类在维持种族生存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机体结构的活动密不可分。情绪活动比单纯的思维活动更直接、更充分地和人的感觉器官以及其他生理器官联系着。有人说,情感活动连结着人的全部的机体的活动,这也许并不夸张。沈从文先生忆及童年时代的生活时,曾生动地谈到湘西凤凰县的风物人情在他的视觉、听觉、嗅觉上永远留存下来的丰富而又新鲜的记忆,他说:
……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窖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出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刺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中拨刺的微音,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里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将近20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2]
不但情绪记忆中的识记是伴随着感官方面的积极活动,即使是情绪记忆的复呈也往往还需要一个感官方面的“诱因”,这个诱因仿佛是打开情绪记忆这座洞天仙府大门的“符咒”,有时是近乎神奇的。法国小说家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922)在《追忆流水年华》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这天,小说的主人公在茶里泡了一小块点心,点心的味道勾起了另一块泡在茶里的点心的味道。他记起这是儿时在贡布雷姑婆家曾泡过的这样的一块点心。于是,他所有的回忆便在这块点心香腻的味道中如死灰复燃一般地豁亮起来,使他重新寻到了失去的时间。普鲁斯特是柏格森直觉主义的信奉者,他的小说近乎玄奥,但他在这里描写的因感官受到刺激而追忆起往日情景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罕见。例如,美国杰出的诗人惠特曼说,他当年参加林肯总统的葬礼时,是一个四月的天气,棺材两边堆满了紫丁香花。他说,在以后的年月中“由于一种难以解释的奇怪想法,我每次看见紫丁香,每次闻到它的香味,我就想起了林肯的悲剧。”[3]我国现代散文家吴伯箫同志在他的传世名篇《歌声》中,对于听觉在情绪记忆复呈中的作用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像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会一幕幕放映起来。
这种充满了迷人的魅力的心理现象,在理解记忆和机械记忆中却是难以见到的。而在情绪记忆中,不只是文学家,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体验。
(三)可塑的、变形的。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概括的反映,具有客观的相对稳固的标准。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理解记忆总是要受记忆对象较严格的制约而凝聚成相对稳固的形态。至于机械记忆,则是一种“死记硬背”,自然更要和记忆主体所观照的客观对象精确吻合,比如电话号码,记错一个字就打不通。而情绪记忆却不然。情绪、情感是主体对客观事物和现象在态度上的反映,为主体自己的需要所左右,它不是客观事物的直接“映入”,而是染上了主体个性色彩的“折射”。情绪记忆的内容对记忆所观照的客观对象而言,可能是不精确的、不完整的、不固定的,甚至是被扭曲了的,甚或是一种错觉。在情绪记忆中,兔子可以变为豪猪,大象可以变为老鼠,土丘可以变为峻岭,水坑可以变为大湖。比如在鲁迅的记忆里,当年安桥头水乡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是那样“无与伦比的鲜美可口”,故居中一个分明是杂草丛生的荒芜的后院却变成了逸趣横生的儿童乐园。在马克·吐温的记忆中,他那位于偏僻的密苏里州的简陋的旧居,始终都是一座宏大的“宫殿”……然而这些与客观对象严重不符、被恣意变形了的“心造的幻影”,却不失其为一种堪加赞赏的“情绪记忆”。鲁迅谈到这种现象时说:“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4]
情绪记忆的这种可塑性、易变性,主要是由于记忆主体的个体差异造成的。比如年龄上的差异,所谓“少小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者;比如生活经历上的差异,所谓“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者;又如心境的变异,所谓“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者;还有健康状况的差异,像王熙凤病危时的闹神闹鬼,实为往日身受其害者所幻化。又如处境的不同,皇帝逃难中饥不可耐时吞下去的谷子面窝窝头,在情绪记忆中竟变成了甘饴无比的美食“黄金塔”。情绪记忆总是要受记忆主体个性和气质的过滤而叠映上主体自己的色彩。
(四)无意识的、不自禁的。理解记忆、机械记忆往往是确定了记忆对象之后方才进行识记的,而情绪记忆的对象是情感,是体验。显然,人在对某一客观事物或现象感受、体验之前,是不会有情感产生的。比如初次观看一出新编排的悲剧之前,你能预料到哪里将要流泪吗?一旦你不知不觉地被感动了,你才在实际上把它记忆了,而且,若干年之后,当你追溯起这个记忆时,对其内涵甚至仍然不十分清楚呢!人的记忆是很奇怪的东西。有些事,有些情景,有些话语,在你刚刚接触它的时候,也许并没有着意,但不知为什么,它却永远留在了你的记忆中,似乎就铭刻在那儿了。”鲁迅儿时曾亲手饲养过一只“隐鼠”,后来据说是被猫吃掉了,这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到了失去所爱的空虚和悲哀,无形中产生了对于猫的仇视,猫的一切表现——偷鱼吃、拖小鸡、恋爱时的吵吵闹闹,都使他感到不能容忍的厌恶。尽管后来已经弄明白害死“隐鼠”的凶手并不是猫,但这种仇猫的心理却始终未变。鲁迅一生也没有与猫和好处,即使在对“叭儿狗”进行鞭挞时,也没有放过猫。我揣测,这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童年时代的对于猫的情绪记忆。
在作家、艺术家看来,记忆,并不都像理论家所断定的,只是对于过去感知过的东西的重复和再现。记忆并不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种重建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心理活动,情绪记忆尤其如此。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
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所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甚至于很愁惨的现实的以及很粗野的自然主义的体验,过些时间,就变成更美丽、更艺术的了。[5]
这就是说,在记忆中“愁惨的现实”和“自然主义的体验”被诗化了,被变得“更美丽”、“更艺术”了。可以说,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进入文学作品之前,一旦走进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之中,便已经开始接受“记忆”这个熔炉的提炼。这使我想起一些自我标榜为纯粹自然主义的文学大师们:如左拉、福楼拜。他们像虔诚的信徒一样,相信自己的作品是对自然的如实描摹。有幸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充其量他们只不过是描绘了自己记忆中的自然。这种“自然”,早已在他们的记忆过程中心灵化了、诗化了、艺术化了。
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样,印象派绘画大师爱德加·德加(Edgard Degas,1834一l917)特别强调运用“记忆法”进行美术创作,他说:
把看到的东西摹写下来,这很好。把只能在记忆里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就更好,这是一种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想象必须同记忆合作。您只能表现使您感动的事物,也就是非表现不行的事物。那样,您的记忆和您的想象就都可以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6]
无独有偶,中国的老国画家关松房先生总结过一种“遗忘法”。他说,为对象感动之后不要急于画下来,而是进行长期酝酿,慢慢让纷繁的印象自我淘汰,最后把那些怎么也忘不掉的印象留下来,只要把这些画下来,就是鲜明的意境了。关先生的“遗忘法”和德加的“记忆法”,实则一回事,都是强调了记忆在艺术创造过程中自动的提炼和概括作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能进入艺术创造的领域,但是记忆中的一部分(包括部分理解记忆和机械记忆),尤其是关于情绪记忆的那一部分,却是整个艺术创造活动的基础和内核。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理论中是一个主情主义者,他在为艺术下义时说:“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紧接着他又举例说:一个遇见了狼而受到惊吓的男孩子如果把他遇到狼的经历和心情变化生动地复述出来,并感染了听他讲的人,那么这也就是艺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来,托翁的这一著名的关于艺术的定义便应该概括为:艺术,即情绪忆的审美表现。其要点为:情绪的识记——自己体验过的感情情绪的复呈——在自己的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情绪记忆的形态化——用某种外在的标志(在文学则是艺术的语言)表现出来。托尔斯泰的这种艺术见解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那里。当一些美学家们对于文学的定义争执不下的时候,歌德却说:“有什么必要下那么多的定义?对情境的生动情感加上把它表现出来的本领,这就形成诗人了。”人们曾经指责过托尔斯泰这一见解的偏颇,认为他忽略了思想的表现。单从字面看来,似乎确实如此。但在现实的、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中,感觉活动、思维活动、意志活动、情绪活动总是交织杂揉在一起的。尤其是感情,更是作为一种弥漫性的因素,滋润在精神活动的每一片土地上。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在精神活动的不同领域,比如哲学的、社会学的、艺术的、宗教的,人们的心理活动方式又是不尽相同的,又是各有侧重的。否则,世上就不会有不同门类的意识形态了。
情绪记忆,应该说是艺术创造过程中一系列感情活动的基本形态,它在人类的艺术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潜在的作用。
情绪记忆是哺育作家个性的摇篮。
记忆是人的反映机能的一个基本方面。有了记忆,人才能保持过去的反映和感受,才能积累经验、扩大经验,并使先后的经验融会贯通起来,使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一个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可以说,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他的全部记忆积累的结果。
儿童时代是人的性格形成的关键,儿童心理活动的主要方式则是感情的、直观的。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多半都是在童年时代情绪记忆的摇篮中便开始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早年的情绪记忆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是如此的重要,甚至在他们到了耄耋之年的时候,也总要竭保其童心不泯。这种在孩提时代体验过的情绪记忆,往往还会在无形之中渗透在他们终生的创作活动中,显示出他们的创作风格和作品的个性特色。卓别林在《自传》中回忆了他童年时代在伦敦兰贝斯的岁月留下的奇妙的印象:公共马车的车顶、紫丁香的树枝、有轨马车站花花绿绿的车票、玫瑰花的香味、脸色红润的卖花姑娘……并说:“我相信,我的心灵就是在这一切琐事中成长的。”他还详细地记述了在他八岁时发生过的一件小事在他整个的艺术生涯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们街尽头是一个屠宰场,经常有赶了去宰的羊经过我们家门口。我记得有一次一头羊逃走了,它沿着大街跑,看的人都乐了。有人跑去捉它,有的人摔倒在地。我高兴得哈哈大笑。但是,后来那头羊被捉住,回屠宰场时,悲剧的现实性控制了我,我跑进家门,哭喊着对母亲说:“他们要杀死它了!”“他们要杀死它了!”过了许多天,一切情景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常常猜想,我后来拍电影的主题思想——悲剧与喜剧的成分相混合,是不是受了那件事的启发呢?[7]
还有,以摄制紧张、恐怖影片而饮誉世界影坛的著名英国电影导演希区柯克说,他四岁时,由于顽劣异常,父亲为了惩治他,让他带个条子给自己一个当警察的朋友,条子上写着请朋友把这个无法无天的捣蛋鬼送进牢房一会儿。朋友照办了,小希区柯克在牢房中被关了几分钟,然而却终生留下了极为恐怖的记忆。他说,他后来的一切恐怖神秘的作品,都带上了这种恐惧心情的因子。当然,形成一个作家、艺术家个性和风格的因素决不会只有这么一件两件事。但如果没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记忆,作家、艺术家独自的个性与风格也就无从形成。
情绪记忆是感情积累的库房。
文学艺术家要想获得创作素材,就必须深入生活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到了生活之中,如何才能获得有价值的创作素材呢?到生活中去观察、搜集、提取、认识、分析、思索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因为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到了生活中也总是要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切莫忽略了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进生活的怀抱中去感受、去体验。在文学艺术家贮积素材的库房里,不但要有充足的生活事件、人物形象的积累,正确的思想认识的积累,同时还必须具备丰富的、高质量的感情积累。感情积累如何得以进行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来,这就是说文学艺术家要努力培养自己的情绪记忆的能力,培养一颗善于感受的心灵。要学会善于从自己的情绪记忆中筛选、淘洗、发现创作的因子和元素。在创作的过程中一方面把眼光巡视于万象缤纷的外部世界,一方面把眼光倾注于自己丰富充实的内心,去激发和复活自己心灵深处潜藏着的情绪记忆。这样的作品既是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更是文学艺术家心血和生命的结晶,有可能成为艺术的上乘之作。巴金的《家》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说: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著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到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8]
巴金曾不止一次地讲过,假如没有那20多年对自己家族中无数悲惨事件的观察、体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心灵始终忍受着“爱与憎烈火的熬煎”,那就决不会有《家》这部小说。小仲马是一个私生子,童年时代父母争闹不和。母亲的忍辱负重和父亲的放荡骄横,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感情上的创伤。直到他步入文坛之后,这些童年时代的伤口还在流血。他说他忘不了那一天,父亲因讨厌他的哭声而抓住把他扔到床上,他还忘不了那一天,父母离异,母亲时而把他藏在床下,时而让他跳墙逃走。那时他才七岁。这些自幼积累下来的痛苦的记忆,便成了他后来创作《克里孟梭的事业》、《私生子》、《放荡的父亲》等作品的素材。这些作品中渗透了他对不幸的母亲的同情,对自己卑屈的身世的悲哀,对他那个放荡的父亲的艾怨与愤懑。由此看来,长期积累下来的情绪记忆,就是文学艺术家灌注进他作品中的生气,一部作品,能否感动人,有无艺术的魅力,奥秘似乎正在这里。
情绪记忆是驰骋艺术想象的基地。
亚里士多德讲的“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记忆里的东西”,实在是一个古老而又朴素的真理。
情绪记忆与艺术的联想、艺术的想象就其本质而言,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必须加以区别,则可以说:情绪记忆(其中包括对于形象的记忆)是想象的低级阶段,而想象则是情绪记忆的高级阶段,一如数学中的算术,一如数学中的几何、代数。如果说,情绪记忆是一种自发的、自然的、散漫的、较被动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而艺术的想象则是一种有目的的、有定向性的、有意识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心理活动。艺术想象是对记忆的加工、改造、重新组合制作。而在情绪记忆基础上展开的艺术想象,往往以灵感触发的形式表现出来。列夫·托尔斯泰在1896年7月19目的日记中曾经记述过这样一个情况:
昨天,我走在翻耕过两次的休闲地上。放眼四望,除开黑油油的土地——看不见一根绿草。尘土飞扬,灰蒙蒙的大道旁却长着一丛鞑靼木(牛蒡),只见上面绽出三根枝芽:一根已经折断,一朵乌涂涂的小白花垂悬着;另一根也已受到损伤,污秽不堪,颜色发黑,脏乎乎的颈秆还没有断,第三根挺立着,侧向一边,虽也让尘土染成黑色,看起来却那样鲜活,枝芽里泛溢出红光。这时候,我回忆起哈泽一穆拉特来。于是产生了写作欲望。[9]
一个月后,描写高加索民族英雄哈泽一穆拉特的中篇小说写出了第一稿,题目就叫《牛蒡》。原来,托尔斯泰年轻的时候曾在高加索的炮兵部队中供职,并参加过战斗。在那里,他曾经接触了高加索的山民,听到了许多关于哈泽一穆拉特的传说,使他对这位民族英雄充满了敬仰之情。而在半个世纪以后的“7月19日”这一天,托尔斯泰偶然看到了那棵顽强不屈的牛蒡,留下了情绪上强烈的波动。这两种情绪记忆“撞击”在一起,便激发起创作的灵感,点燃了艺术想象的火焰。
综上所述,情绪记忆是一种既古老而又常新、既复杂而又单纯的人类心理活动机能,它具有自己显著的特征,在人类的艺术创造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潜在的、巨大的作用,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注释:
[1]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04-105页。
[2]《从文自传》,见《新文学史料》l980年第3期。
[3]转引自荒芜《惠特曼与林肯》,见《外国文学研究》l981年第l期。
[4]鲁迅:《<朝花夕拾>·小引》。
[5]《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二卷,第275—276页。
[6]全显光:《视觉记忆》,见《美术》l982年第2期。
[7]卓别林:《自传》,第3页;第34—35页。
[8]《巴金文集》第十四卷,第342页。
[9]《托尔斯泰评传》,第333—334页。
※ 此文为28年前的旧作,发表在《上海文学》1982年第3期,原文13000字,现已压缩。以此纪念我深为敬重的已故文学理论家、本文的责任编辑周介人先生(1942-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