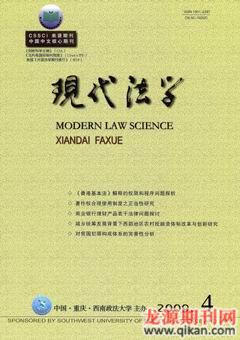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正当性研究
摘 要: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各国著作权制度中对著作权限制的主要内容。合理使用制度体现了著作权法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与促进知识与信息广泛传播的双重目的。合理使用的正当性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认识,包括激励与接近之平衡、宪法与公共利益、以交易成本和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等。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国颁布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合理使用的规定即是这种体现。
关键词: 著作权;合理使用;正当性;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DF5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04
一、引 论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各国著作权制度中对著作权限制的一种主要制度。“合理使用”概念的提出首先来自美国Folsom v. Marsh 案,(注:Folsom v. Marsh. 9 F. Cas. 342 (C.C. D. Mass. 1841) (No. 4901).)后来在美国1976年《著作权法》中被法典化。合理使用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后续的作者为了创作新作品如何利用先前作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合理使用制度已成为各国著作权法中通行的制度。
“合理使用”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而对作品所进行的使用。合理使用制度最直观的考虑是不允许使用他人作品会阻碍自由表达与交流思想,它最关注的是非营利目的的使用。换言之,“合理使用”原则允许在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对著作权作品进行使用。它服务于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是要确保著作权人对作品表达性方面的控制而又不会延伸到作品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方面。
合理使用制度作为著作权限制最重要的一种形式,自然可以定位于对著作权的限制。从各国著作权法的规定看,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这种专有权都规定了一些限制。其中有些限制适用于作品或者与作品相关的某些方面,如著作权人发行和展示作品的专有权受制于首次销售原则限制;而有些限制适用于著作权作品使用的特定类型,如引用方面的合理使用。对合理使用来说,该原则也是对所有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某些方面的限制。如计算机程序复制品的所有人为了备份而制作一个复制品,根据合理使用原则,没有侵犯程序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在合理使用原则下,本来由著作权人控制对作品著作权使用的行为如复制作品,可以由使用者自由使用。从各国著作权法的规定看,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学术和研究等性质的对作品的使用被划定为合理使用行为。也就是说,著作权法列举了一些特定的使用作为合理使用行为。但是,在具体涉及到合理使用判断的著作权案件中,无论一个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被列入有限分类的行为,都不能简单地确定是否为一种合理使用。没有在明确的分类中的作品使用也可能是合理使用,而在列举范围内的行为也可能不是合理使用。各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发展了判断合理使用的标准和方法。如在美国,法院首先考虑行为是否列入了一个或几个广义和模糊的对合理使用的分类中,然后考虑界定合理使用的因素。在确定被告行为是否为合理使用时,法院考虑的因素包括: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作品的性质、作为一个整体的著作权作品被使用的量和实质部分、使用效果对著作权作品的潜在市场和价值的影响。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侵权中基本的抗辩理由。当然,在制度设计方面,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很难进行精确的“数量标准”测试,这是因为在著作权法中要确定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人都认可的数量标准和程度并非易事。
合理使用制度也可以说是知识产权制度中对权利限制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一制度典型地体现了著作权法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与促进知识与信息广泛传播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著作权法以维护作者的权益为核心,对作者权益的充分保护始终是各国著作权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要求有利于促进知识与信息的广泛传播,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文化、科学事业的进步和繁荣。两者看似相互冲突,但这种潜在的冲突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加以解决。基本的思想则是,只有通过临时限制信息流动的方式,才能使广泛传播信息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目的得以实现。著作权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原则正是实现这样一个思想的机制,“它为著作权人针对信息传播中的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利益平衡的手段”,(注: New Era Publication Intl v. Henry Holt and Co., 695 F. Supp. 1493, 1499 (S.D.N.Y.1988).)确认了包含在著作权中的思想或者信息对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作用。设立合理使用制度不会对著作权法中激励创作和传播的制度结构产生负面影响,反而大大方便了公众对智力作品的利用。本文拟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正当性或者说合理性问题进行研究。
二、合理使用正当性之一:以激励与接近之平衡为视角
(一)著作权法之激励与接近平衡原理
1.著作权法激励创作与传播的立法宗旨与机制
通过为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提供充分的著作权保护,为作者创作作品和传播者传播作品提供激励,是著作权法的重要立法目的,也是著作权法的重要激励机制。在理论上,也可以将著作权法激励创作与传播的机理提升为著作权法的激励理论(激励论)。著作权法对创作与传播的激励还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到理解。
关于著作权法的激励理论,可参看笔者文著作权法之励理论研究——以经济学、社会福利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为视角[J]法律科学,2006,(6):41-49
2.对作品的“接近”:公众与著作权人对价的砝码
接近是指公众对著作权作品中的思想和表达的获得、使用。公众能够接近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实现著作权法宗旨的重要保障。公众接近作品能够使其从作品中所包含的知识和信息中受益,这也是实现著作权法社会目标的需要。对作品的接近因而成为著作权法理论的核心问题。公众接近著作权作品的能力通常可以理解为从著作权作品中获得思想、素材、知识、信息的能力。公众接近著作权作品的起码条件是:作者作品中的思想和表达能够以被理解的方式获得,并且公众能够获得作品的有形复制品。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公众则可以通过对数字化作品的下载、打印行为而获得这种复制品。不过,在技术急速发展的今天,公众对作品的接近会受到技术手段限制。
接近是实现著作权法目的的重要手段。对接近的关注和重视并没有改变著作权法促进作者创作激励机制的功能。著作权法非常重视公众接近著作权作品的重要性,原因是对作品的接近是保障其从被接近的作品中获得知识、信息和获得其他收益的前提条件。确保未来作者接近著作权作品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他人不能接近先前的作品,那么就难以甚至不能在原作品基础之上创作自己的新作品。接近对于实现著作权法的宗旨即在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基础之上增进知识、学习以及实现著作权法的民主文化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著作权法中激励与接近之平衡
合理接近著作权作品体现了著作权法中存在的“对价”机理——公众接近作品的可能和程度应与著作权保护范围和程度相匹配。著作权法授予著作权人以著作权,作为激励创作和传播的手段,同时著作权法也规定了著作权的限制和相关的公共接近问题,以作为对授予专有权的对价。对价集中于新作品的创作和对作品的公共接近。这种对价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著作权法赋予专有权的程度过高时,虽然能“激励”产生更多的作品,但会导致公共接近的障碍,使公众不能从早先作品中获得学习知识的利益,从而导致增进知识和学习公共利益的减少。
为了实现著作权法的宗旨,一般而言,公众应能接近著作权作品。也就是说,与著作权法为作者创作和传播者传播作品提供激励机制一样,著作权法必须为作品使用者提供接近著作权作品的机会。在设计整个著作权法时,在进行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和协调上,怎样保障公众对作品的适当的、必要的接近与保障作者的著作权同样重要。但是,由于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是以授予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形式出现的,而专有权直接体现为限制甚至禁止著作权人以外的人对作品的接近——在著作权立法上通常表现为未经著作权许可不得使用其作品——这就使得著作权法鼓励创作与传播的机制与接近的公共目标直接相冲突。这种冲突体现为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与接近作品之上的公共利益的冲突。为解决这种冲突,惟有对著作权这一专有权加以适当限制才能实现。著作权权利限制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便应运而生了。本文探讨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就是这种制度设计中最为重要的形式。
鉴于接近作品对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性,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是当代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关键。我们可以将著作权法视为对作者的激励和向公众接近间的平衡。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始终是协调著作权利益的杠杆。
(二)从激励与接近平衡范式看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正当性
在激励理论层面上,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是基于作品效用,特别是作品能够给著作权人带来利益。在制度安排上,以合理使用为核心的权利限制机制是建构激励与接近平衡范式的根本保障。换言之,权利限制机制也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著作权政策,即激励与接近政策。著作权政策经常涉及为了足够地激励作者的创作,但又不至于阻碍公众接近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程度究竟应当是多大的问题。可以认为,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基本限制旨在使一般的公众受益,而不仅仅是著作权作品的特定复制品所有人获益。也就是说,以合理使用为核心而限制著作权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公共利益比起对专有权的保护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解释德国《著作权法》第52条,即“在合理范围内所有权人必须容忍那些维护和促进社会共同生活所必要的限制”,就是一个体现[1]。
从著作权法的价值构造看,在著作权法中存在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在协调机制,并且著作权法表现为立足于著作权保护、在权利限制基础之上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平衡机制。权利限制的前提是权利的充分保护,这是因为确保公众能够获得作品的前提是存在大量的为社会公众需要的作品,这就需要通过激励作者创作来实现,而在著作权法中激励作者创作的重要机制则是对作者作品予以充分保护。没有权利限制,著作权法确保公众接近作品的目的将无从实现。以合理使用为核心的权利限制成为实现对创作者的激励与公众接近之间平衡的机制。
(三)激励与接近平衡范式透视合理使用正当性的微观分析
根据以上认识,著作权法价值目标要求激励作品创作的目标实现后,需要在进一步激励作品传播的基础上保障公众接近作品。确保公众接近作品从根本上体现了著作权法对公众利益的关注。在探讨著作权合理使用正当性方面,可以借用这种平衡范式进行微观分析。
合理使用原则在著作权法中的适用,是保障作品用户正常接近作品的需要。从鼓励作者创作的角度看,需要确保并适当增加作者受保护的利益。但是,作者受保护利益的增加可能会威胁到一些创造性活动的形式。这一风险连同相应的接近作品的需要,将提出包含三个特征的创造性形式:一是作品必须体现合乎需要的、创造性的形式;二是作品必须体现从早先作品中取走表达的创造性形式;三是作品必须体现作者不愿授权的创造性形式。这些因素的结合,建立了接近作品的强制性需要。如果后续作者通过其偏爱的某种创造性形式,必须借用先前作品的某些表达性因素,他却不能合理地获得许可,适用著作权的非正常保护范围将禁止后续作者利用其偏爱的创造性形式。如果作品是合乎需要的创造性形式,著作权法能够确保这种作品被创作的惟一方式将是为其保护范围提供一个例外[2]。根据激励与接近间的平衡范式,需要针对这三个与接近作品相关的标准来限制著作权保护范围。此时适用合理使用原则就具有必要性,因为它可以满足他人接近作品的需要。
在实践中,上述创造性活动形式不一定都同时具备。在不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对作品接近的正当性就不那么充分。就合理使用而言,由于它主要是保障对作品的适当接近,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合理使用原则将受到更多的限制。国外学者格莱恩•S•兰勒伊即以后续作品为例,讨论了合理使用原则受到限制的情形:当后续作品不是合乎需要的创造性的一种形式时,就没有多大的需要来确保对它的接近。如果后续作品的创作可以不用复制早先作品的表达,那么在没有复制早先作品的情况下也能创作它,也就没有接近作品的非正常需要。按照激励与接近之间平衡范式,由于此时接近作品的需要变得不明显,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法院偏向于不给予著作权以限制[2]483。
相反,如果与著作权有关的某一使用作品的行为体现了与接近相关的上述三个特征的创造性形式,确保对作品的接近就具有较大的必要性,而这就相应地需要对著作权予以合理使用形式之限制。在国外发生的一些关于“模仿”的案件就是如此。作为合乎需要的创造性的一种形式,模仿要求从目标的表达中借用一些形式,而这不是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所愿意许可的,除非某些条件将使这种创造性表达的某些形式变得不可行。由于模仿包含了与接近作品相关的这三个特征,它代表了一种对接近作品的不寻常的需要,因而根据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范式,为确保这种模仿形式的存在,著作权法应对其保护范围提供一个例外——允许合理使用。从国外著作权司法实践看,有关模仿的案件被从合理使用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运用,将模仿行为视为合理使用的案例屡见不鲜。
不过,体现与接近作品相关的上述三个特征的那些创造性形式在著作权实践中是需要严格适用的。对于批评、评论目的的使用作品的行为,司法实践中给予宽松的适用;而对于讽刺之类的使用,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在界定是否为合理使用时从严掌握,理由是讽刺性作品并不存在模仿、批评那样的接近作品的需要。总体上,体现了这三个标准的使用比通常的著作权法所允许的使用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从合理使用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来看,它本身是作为接近作品的一种手段。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合理使用原则逐渐发展为在侵权例外的案件中适用的标准,而不是作为是否侵权的主要标准。合理使用原则更强调对著作权的限制产生的利益平衡的效果。美国Wojnarowicz v. 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 案(注:745 F. Supp. 130 (S.D.N.Y. 1990).)比较有代表性。该案件涉及被告反对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一个艺术展览而出版了一个影集,该影集收录了部分展览的艺术品。法院考虑到美国政府的作品不受著作权保护,理由是政府提供了资金,著作权保护对于这种作品的创作方面的激励是不必要的。因而,法院将注意力转到考虑了合理使用方面的利益平衡问题。法院认为,在该案中由于联邦政府提供了资金并促进了作品传播,应更加宽松地解释合理使用问题。
如同作者受保护的利益膨胀一样,合理使用原则的演化反映了激励与接近之间平衡范式的另一方面——在缺乏对接近的非正常需要时,不应限制对著作权的保护。假定在确定后续作品是否与早先作品在表达性因素方面太相似方面,提出了在大多数案件中充分接近的需要这一问题,那么接近的需要以及进一步限制著作权相应地需要合理使用,这可能仅仅出现于特例中,但它依然反映了激励与接近之间平衡的需要。
三、合理使用正当性之二:以宪法和公共利益为视角
(一)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涵义
1.基本内涵
合理使用作为对著作权进行限制的最为重要的形式,它的确立也表明了著作权不是一种绝对的专有权,而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利。根据著作权学者的考察,合理使用的司法原则,似乎是在著作权法确立的专有特权中发展的,它确认了针对合法垄断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并进一步认为合理使用具有宪法性方面的正当性,值得被立法者和法院保护。
从宪法方面看,合理使用不是表现为对著作权的限制,而是在著作权法中实实在在地确立了合理接近著作权作品的权利,这一权利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宪法保护。也可以说,著作权法中体现了公众合理接近著作权作品的宪法权利。这一宪法内涵保护了对文化、教育、历史、科学、技术和知识继承物的合理接近。在实践中,由于没有赋予合理使用原则适当的宪法地位和保护,这样就背离了宪法保护的领域,结果导致对合理接近作品的放弃与排斥[3]。
合理使用具有的宪法保护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利平衡的需要,而公共利益对于著作权人的利益具有优先地位。换言之,合理使用在合理接近中的公共利益胜过著作权人的法定垄断权。二是举证责任从被指控的侵权人转移到著作权人。由于著作权只是制定法的一个创造,著作权人享有的著作权是一种专有权,这种权利本身不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权利。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也说明了作者不存在具有宪法性质的财产权。在平衡著作权人的法定权利与公众获得知识、阅读和视听的宪法权利之间,这种平衡的达成须偏向于公众的宪法性权利[3]。
将合理使用上升为宪法权利,有助于在不损害著作权人对作品进行专有控制的前提下确保作品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对著作权作品的适当接近。从宪法权利的角度可以更加深刻地看出,合理使用制度设计背后深层次的缘由。将合理使用上升为宪法权利,还意味着合理使用具有宪法性保护的效果。在这种宪法性保护和著作权人专有权的较量中,宪法性保护占据优势地位,如在考量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和著作权保护的平衡中,需要向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倾斜。这主要是因为,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代表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合理使用制度本身是对公共利益的宪法性保护来应对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设计。基于此,将合理使用的宪法地位在实践中的确认作为确保公众对著作权作品接近的保障,有助于在更大领域内进行智力创造和对智力加以使用,并促进著作权制度不断完善。
在上述确保对作品的适当接近中,确认合理使用的宪法地位特别有利于非营利性质的活动,特别是教育、研究、学术活动的开展。对非营利性质的知识产品生产活动而言,创造者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受限制地传播其创造性成果的愿望,而不大考虑经济上的收益情况。因此,比较而言,非营利性质的知识产品创造活动对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的“敏感程度”要低一些,但其重要性却越来越大。出于非营利性质的教育、研究或者学术目的而对著作权作品的合理使用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的传统观点在非营利性质的智力活动中体现得不够明显。
2.平衡意义上的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涵义
著作权法一方面保护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对作品利用享有的专有权,并对侵犯这种专有权的行为提供救济措施;另一方面,著作权法也具有确保宪法所确定的增进知识传播、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的目的。后者的实现是著作权法更高层次的境界和目的。为此,在著作权法这种“私法”中产生了针对专有权的公共利益。确立这种公共利益甚至被认为对于知识的增长具有实质性意义。
合理使用的实质涉及到对著作权作品的合理接近的权利,这种接近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宪法保护,原因在于合理接近著作权作品关系到宪法确保的发展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的公共利益。当然,在将合理使用纳入宪法视野考虑时,可能出现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与在著作权法中产生公众合理接近著作权作品的宪法性权利的冲突。解决这种冲突,需要明确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著作权这种专有权在宪法框架中的定位,二是合理使用作为宪法性权利的性质。从宪法框架看,著作权具有法定性,任何著作权都只是制定法的创造,其本身不是宪法性质的权利。从著作权立法的历史考察,作者宪法性质的财产权始终没有被确立过。但合理使用原则不同,在英美等国家,合理使用的司法原则和宪法性权利的提出通过司法原则和司法判例逐渐确立,在我国甚至在著作权立法产生前就被牢固地置于宪法原则和观念中。
“利益平衡精神是合理使用制度的合法动因”[4]。从宪法框架认识合理使用的正当性也可以基于利益平衡的理念与原则加以理解。在将合理使用视为一种宪法性权利时,需要在著作权人的法定权利与公众获得知识、阅读和视听的宪法性权利之间实现平衡;而且在平衡点的掌握上倾向于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这种宪法性权利与宪法确立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密切相关。如对著作权作品中的知识、信息的“接近权”在美国最高法院中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权利法案保护的完整权利的一部分。美国最高法院还认为,出版自由权利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印刷、出版和发行作品的权利,而且也是公众获得信息和思想的权利,是阅读和视听的权利[3]。
在平衡的层面上,合理使用的宪法性可以从著作权的严格限制以及著作权法对确保公众合理接近作品的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著作权被认为是一种垄断性质的权利,国外一些司法判例对此已有反映。如美国最高法院主张著作权是一种垄断,(注: Fox Film Corp. v. Doyal, 286 U.S. 123, 127 (1932). )著作权是垄断的形式。(注:H. R. Rep. No. 742, on H.J. Res. 676, 87th Cong., 2d Sess. 6 (1962).)甚至在最佳点上,“著作权有必要涉及限制权以及垄断知识扩散的权利”[5]。这种垄断虽然不同于反垄断法环境下的“垄断”,但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它有发展为后者的可能,因此,对法律保障的著作权进行严格限制是必要的。为获得利益之平衡,对著作权的保护与确保著作权法中公众合理接近作品的公共利益应当处于同一基线,而且在同一基线上公共利益对著作权人具有优先地位。
对著作权作品的接近主要是以确立合理使用原则为核心的。合理接近的公共利益体现为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这种宪法性权利受到保护,以防止著作权人对其作品利用的不适当控制。在确定专有权范围上,按照利益平衡原则,应当重视以下两点:一是应当对专有权作严格解释并严格限制;二是在权利定位上应使授予的著作权相对于通过合理使用的合理接近的权利而言处于次要地位[3]。其中“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十分重要。在认识合理使用的宪法性原则以及宪法层面上的正当性方面,这一原则依然值得重视。
3.合理使用宪法性权利对支撑著作权法的重要性
确认合理使用适当的宪法地位可以认为是保护著作权制度不致崩溃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著作权作品的利用中,典型地区分为商业性利用和与非营利性质的教育、研究、学术活动等有关的非商业性利用。在非商业性的教育、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智力创造者利用作品的重要特点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形成新的智力创造成果。这种活动是存续文化和科学所必须的。非营利性的知识创造活动离不开著作权合理使用的保障。在非营利性创造活动上,通常的著作权激励论的观点难以解释非著作权性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与非营利和非商业性使用相对应的著作权制度的实质性部分,是它作为对创造性活动的必要激励的假定错误。著作权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非营利性活动的关注。《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虽然具有垄断性,其中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却能保障公众必要地获得与使用著作权作品;并且,合理使用的这种宪法性保护相对于单纯的授予著作权人的垄断权具有优势。在平衡通过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和著作权时,这种平衡应向合理接近的宪法性权利倾斜。合理使用是实现对公共利益的宪法性保护应对著作权人利益的设计,也是支撑著作权法的重要机制[3]。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人的专有权有不断扩张的趋向,非营利性的教育、研究或者学术的目的而对著作权作品的合理使用比其他类型的合理使用更需要得特别保障。无论如何,将合理使用的地位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将其强化为确保社会公众对著作权作品必要的获取与利用,有利于更好地促进著作权法的改革和完善。事实上,即使是从著作权人的角度看,合理使用制度最终将被看成是有利于公众的使用,因为就使用其他作品而言,著作权人也是社会公众的一员。也就是说,即使是从著作权人方面考察,也可以理解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的重要性。
合理使用制度从根本上体现了著作权法对公众利益的关注。著作权法是我们社会文化权的一部分。著作权立法的一种重要思想即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著作权的存在甚至被假定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在著作权的宪法视野方面,如果公众在有些情况下能够优先获得复制品,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较少的作品被出版,公众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禁止公众复制它所需要复制的东西没有正当性。另外,在深层次意义上,著作权法也鼓励其他作者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新的作品,从而将表达延伸到新的领域。
(二)合理使用与公共利益
当代的著作权法与其他知识产权法一样,在利益的天平上存在着向权利人倾斜的趋向。公共利益的精妙平衡是著作权立法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在著作权法中保障公共利益的关键,是确保公众对作品必要的接近,包括确保不被保护的要素成为后续作者创作的素材,从而使这些未来作者使用那些要素创作出新的和不同的作品。
著作权法中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如增进知识和学习、保障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增进民主文化等。确保这些公共利益需要由具体的制度建构来实现。合理使用原则就是其一。对作者表达的保护在合理使用框架下给不同利益主体使用作品带来收益,实现文化繁荣的公共利益就建立在这种对公众使用作品利益保障的基础之上。通过确立合理使用原则来避免过度的著作权保护或者著作权保护不足,满足了公共利益的要求。在国外有关涉及合理使用的著作权司法实践中,法院主张著作权人的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宪法要求。(注:Berlin v. E. C. Publications, Inc., 329 F.2d 541, 543-44 (2d Cir. 1961); Rosement Enterprises Inc. v. Random House Inc., 366 F.2d 303, 309 (2d Cir. 1966). )合理使用与宪法性权利联系起来,甚至被法院看成是宪法制度的一部分。这本身体现了合理使用确保公共利益的价值所在。在著作权制度的早期,关于一个使用是合理使用而适用公共利益的情况很少,没有赋予合理使用原则适当的宪法地位和保护侵害了宪法保护的领域,结果导致对通过合理使用而接近作品的放弃与排斥。
有关判例表明,合理使用原则分析了先前作品的表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竞争者和公众所利用。(注: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114 S. Ct. 1164 (1994).)但是,合理使用也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公众和竞争者能够接近先前的作品。(注: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114 S. Ct. 1177 (1994).)有学者主张合理使用产生了两类公共利益:第一类是直接发生的公共利益,因为公众能够从原创的作品中获得思想和表达。第二类是附加的公共利益,该利益是公众从需要接近最初作品的竞争者所创制的竞争性表达和思想中获得的。简单地说,作为用户的公众和竞争者都需要接近著作权作品,以进一步实现著作权法增进知识和学习的目标。这里的接近必须是对著作权作品中的表达的接近,并且通过对表达的接近,接近了这些作品中的思想[6]。简单地说,合理使用是通过对作品合理接近的保障而实现公共利益的。
四、合理使用正当性之三:以经济学为视角
在经济学看来,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体现了著作权法实施的社会成本和收益间的平衡。从成本的角度看,授予著作权会产生与垄断相关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作品的使用者承担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使用作品的义务。当然,实施成本还包括制止侵权的成本、著作权行政管理的成本等。从收益的角度看,它表现为著作权法激励了作者进行智力创作,增加了社会知识共有物的含量,并通过其一系列制度设计促进了思想、知识、信息的广泛传播,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平衡离不开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其中合理使用占据了核心位置。对于著作权作品的用户或者说使用者来说,随着近些年来对著作权限制其他形式的严格控制,他们更依赖于通过合理使用原则解决对作品的利用问题。
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合理使用的正当性,实际上是透视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经济理性。在这方面,可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合理使用制度可以看成是制度安排下的特定智力作品创作者和不特定作品使用者之间就信息资源分配所进行的交换。合理使用制度既可使智力劳动者获得报偿,也维护了公众使用公有资料的自由,这正是其合理性或者说正当性所在。以下将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方法和新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或者说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理论。根据该理论,产权界定的程度直接受制于交易成本的高低。产权由交易成本决定,但产权界定也影响到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外部性问题;认为产权界定和制度安排对于资源分配具有关键性作用,合理界定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并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则有很大的不同,它重视在完全竞争情况下的经济运行情况。方面加以研究。
(一)合理使用的交易成本方法分析
在公众对作品的接近没有合理使用制度保障时,公众可能需要与作者等著作权人打交道而增加过度的交易成本,从而可能导致市场失败。例如,在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案中,法院提出著作权法是否应限制对录像机私人性质的使用,这种私人性质的使用影响了公共广播电视节目的使用。其正常使用可以假定能获得许可证。但是,获得许可证的交易成本和许可证的实施将超过从许可证获得的收益,这种许可证的运用将导致市场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激励与接近间的平衡范式,应考虑被告的行为为合理使用。法院遵从了这一主张。
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运用于合理使用制度中,侧重于交易成本损害了自愿许可协议的达成从而导致市场失败的情形。换言之,合理使用限于交易成本损害了许可交易的情形,并且它是克服市场失败的途径和方式。交易成本方法与知识产权的市场弹性直接相关。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学理论被冠以对著作权的财产权分析方法[7]。在有关司法观点和学术评论中,它仍然是一种被推崇的方法。例如,学者斯戴芬•M•迈克恩对之作了较透彻的阐述[8],以下将从交易成本方法分析入手审视合理使用的正当性及其经济理性。
1.关于合理使用的交易成本方法
运用交易成本的观点阐明著作权合理使用理论,与“市场失败”相关联。市场失败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是因为某种原因使得市场交易没有或者不能完成。在这里的分析中,很显然交易成本因素是导致市场失败的原因之一。就著作权法来说,如果著作权作品的使用者能够从著作权人那里获得许可,并且获得许可的成本比从许可证获得的收益相比要小,合理使用原则的适用将是不当的。但如果因交易成本或其他被狭窄定义的市场失败而阻止自愿交易,那么合理使用适用的机会将会更多。市场失败特别地出现于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之间就著作权作品的使用谈判许可问题的成本很高的情形。这种交易成本的存在阻碍了交易的形成,为合理使用提供了经济学上合理性的基础。在缺乏合理使用的情况下,使用者使用著作权人作品将受到限制。此时引进合理使用规则可解决因交易成本而阻碍接近作品的问题。
交易成本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学分析方法。该方法关注的是资源分配由市场机制来选择。即它不是判断使用作品的利益是否会超过对作者激励的减少,而是将分配留给市场机制解决。交易成本方法显然涉及成本与收益问题。在交易成本大于使用作品的收益时,合理使用的条件可以得到满足。但使用者使用作品获得的利益超过因使用作品而对著作权人的损害,却不是合理使用的理由。相反,如果使用的盈余存在,使用者还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
交易成本方法也是一种市场分析方法。这是因为,市场在使用和传播独创性作品方面具有独特价值。无论是在作品中受著作权保护的方面还是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其他方面,市场都是使著作权作品中的资源分配和分享得到实现的基本保障。在这种市场分析方法中,交易成本是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的。
合理使用的交易成本方法分析在著作权制度领域还具有一定的功能性目标。当交易成本的存在阻碍了作品许可使用机制的发挥时,合理使用被认为是对作品的更富有效率的使用。这种更富有效率的做法也可以认为是合理使用制度在经济学上成立的正当理由。当然,其他相关的分析方法也具有相当的价值。其中劳动学说中的自然权利分析方法即是一例。有人甚至主张在民主市民社会自然权利分析比起经济学分析可能会为著作权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如此,在合理使用方面,自然权利的分析方法难以提供一个具体适用的指导规则。
2.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中合理使用界限之确定
根据迈克恩的观点,合理使用的交易成本方法假定著作权中的边界是可以识别的,并且运用该方法需要确定类似于不动产的财产边界范围。但是,确定著作权的边界范围与有形财产不同[8]。我们知道,有形财产产权化的前提是有一个稳定的可以被识别的边界。例如,不动产的边界可以通过测量等方法很清楚地描述,个人动产的边界也较好测定。边界难以划分问题只是一些例外的情况。尽管著作权的存在依附或者体现于一定的有形的物质载体,但有形的物质载体本身却不是著作权调整的对象,而是物权调整的对象;因此,通过著作权作品的复制品确定合理使用的边界范围是不适当的。在运用交易成本的方法确定合理使用的边界范围时,严格区分著作权作品和著作权作品的有形复制品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确定著作权上述边界范围的因素在实践中存在一定难度。在独创性方面,一般而言,任何作品中都包含了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和因具非独创性而不被著作权保护的因素。虽然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的基本条件,每一个独创性作品却同时也包含了非独创性因素。在理论上,尽管可以将独创性的界定阐述清楚,在实践中独创性与非独创性的边界却具有相当模糊。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方面,对于一个著作权案件来说,对可著作权的表达和不可著作权的思想之间的界限进行划分也具有较大的困难。正如勒德•海恩德法官所指出的一样:这是一个必要的和特殊的考虑:没有人曾经确定过这一边界,也没有人能够。(注: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 45 F. 2d 119, 121 (2d Cir. 1980).)随着技术的发展,作品中一些因素是应当属于表达性因素还是思想也变得模糊起来。以作品中一般认为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功能性方面而论,计算机软件方面的争论出现了。在软件保护司法实践中,一般观点是主张软件的功能性方面不能受到著作权保护,认为软件固有的功能性方面与独创性作品存在区别而要求它采用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但区分功能性方面与表达性方面也并非易事。如在Computer Associates Inc. (注:Computer Assoc. Inc. l v. Altai, 982 F. 2d 693 (2nd Cir. 1992).)案中,法院进行的测试也只是重述了抽象分析。
应当说,著作权边界确定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既对作品赋予专有权,也对通过缩小合理使用来扩张著作权的边界范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因为当边界的范围不确定时,赋予著作权作品以权利将失去基础;同时,即使对著作权予以扩张,也不一定能够激励著作权人的创作。对作品使用者来说,则因为难以准确判断自己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作品著作权而可能会影响其使用。这一情况在实践中的体现是,在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以牺牲公共领域为代价而被扩张时,边界线不确定引发的纠纷也将增加。
(二)合理使用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
著作权法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扩大对著作权的保护以支持商业的发展。从作者和著作权人的利益出发,应当穷尽开发著作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对著作权因技术进步而遭受到的损失应当尽量给予补偿。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作品纯粹是一种商品,著作权纯粹属于市场。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为“可以销售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延伸到每一个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使用。著作权就是作为在现有作品中直接投资的设计。著作权法在本质上是服务于作者和出版者识别和适应消费者偏好的机制,消费者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越多,投资回应消费者市场的创造性作品的人也将越多。从著作权法的经济方面说,市场价格在一个理想的有效率的方式上能够指导直接资源分配和现有创造性表达的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强调在避免市场失败的情况下,著作权法能够保障作品在整体上的有价值地得以使用,以及著作权人从作品的流转中获得必要的利益。当市场能够引导创造性作品做最有价值的使用时,著作权法为创造性作品提供了适当程度的保护。这样,著作权法的激励理论集中于激励与接近之间平衡,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旨在创造和完善创造性作品的所有潜在使用市场。对这些创造性作品来说,可能存在很多自愿购买者。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视角看,根据市场被转让的价值来分配创造性作品可以看成是著作权法的重要目的[7]。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重视市场机制作为自由分配资源的手段。根据该理论,作品创作和传播都定位于市场,而市场离不开作品的消费者。
消费者对作品的需求既决定了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的价值,对未来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当然,这主要是针对那些与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的作品而言的。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很多作品来说,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更主要是基于其社会价值和影响,而不是市场消费者的大众化需求。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看来,提高作品市场效率的先决条件以及重要保障取决于清晰界定的财产权,理由是为实现著作权法的有效率的分配目标,确立广泛的并且可以被交换的财产权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关于著作权法的正当性,必须为创造性表达的作者提供广泛的、能够延伸到每一个有价值地使用的财产权。
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分析“合理使用”问题时,使用作品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是考虑的重要方面。以下将通过分析几个典型案例需要加以说明。
在一些牵涉到合理使用的著作权案件中,法院似乎认为应将著作权扩张渗入到更广泛的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财产权上。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出发,法院重视合理使用作为作品使用者为创作新作品而需要适当接近原作品的特点[9]。 以国外的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案(注:464 U.S. 417 (1984).)为例,美国法院肯定了私人性质的、非商业性质的家庭录制作为合理使用,其分析路径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上的正当性。法院承认商业性使用著作权作品作为合理使用对著作权人是不公正的;但法院主张,当使用者的行为对潜在的市场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时,可以考虑允许这种使用。在该案中,家庭录制不但不会产生这种影响,而且还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利益,因而应视为合理使用。法院认为,著作权不应限制录像机的私人性质的使用,这种私人性质的使用并没有影响公共广播电视节目。在该案中,法院还同时采用了合理使用的市场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法院推理:被告这种私人性质的使用一般是知道录制过的节目的,因而可以假定能够获得许可证。但是,获得许可证的交易成本和许可证达成后的实施成本将超过实施许可证获得的收益,这种许可证将导致市场失败[10]。同时,法院还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除了增加过度的交易成本将导致市场失败的可能外,作者受保护利益的增加也会威胁到一些创造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对作者的著作权给予合理使用限制也是正当的。
美国的另一案即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v. Nation Enterprises 案件[11]更是法院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适用到合理使用的例子。该案法院将市场理论列入了合理使用原则。沿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路,法院进一步限制了合理使用原则的适用。该案件转向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路方面,葛德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在该案中适用合理使用应受到限制,原因是被告证明市场失败是不可能的,对使用的控制服务于公共利益,而著作权人的激励不会被实质性地损害。根据他的观点,合理使用的狭窄作用在于避免市场失败和保护不会影响著作权价值的合乎社会需要的使用。在该案件中,法院将对原创的、创造性作品的市场影响作为合理使用最重要的因素。这样,对潜在许可收入的影响对合理使用具有决定性影响。适用葛德的市场模式和来自这一模式的限制性条件,法院认为适用合理使用仅在于单独的市场失败的案件,以及在缺乏对著作权作品相反的潜在市场影响的情况下,不仅来自于使用,也来自于其他方面[9]。 法院通过引进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肯定了实际和潜在的经济价值在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中的地位,并据此认定被告的行为不符合合理使用的条件。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案件(注:510 U.S. 569 (1994). )则涉及到模仿是否为合理使用问题。美国法院在该案件中也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适用到合理使用方面。法院立足于市场失败而主张成立合理使用。在该案中,法院认定被告的歌曲尽管是对原告歌曲的模仿,并且具有商业目的,但由于它不会替代原告作品的市场,这种使用仍旧是一种合理使用。考虑到著作权人一般不会授权第二个人模仿他的作品,而且潜在的演绎性市场仅包括原创性作品的创作者将一般性地许可他人进行演绎,法院主张模仿构成了支持合理使用判决的市场失败的类型。同时,法院也认为,合理使用的分析必须确认著作权人利用演绎作品的市场,并在其权利范围内对演绎作品市场的利用不是合理使用。另外,在运用市场因素推导合理使用方面,市场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当使用著作权作品的行为是一种对著作权人潜在许可使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商业性使用行为时,这种使用就不是合理使用。
四、余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之正当性
(一)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仍存在必要性
网络环境中利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与模拟环境相比具有新的特点,相关的著作权立法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同时,传统上维护了公众广泛接近作品的权利限制和例外,在信息网络空间仍然具有重要的生命力。以数字化为主要特色的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限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合理使用。网络环境一方面增加了著作权人控制作品的市场范围,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作品在网络空间的失控而影响到其利益。例如,当可以从公共服务中找到所需要的著作权资料时,使用者将可能不再购买著作权人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数字图书馆将他人图书作品数字化前需要获得著作权人同意的重要原因。在网络环境中,适用著作权合理使用等限制著作权的形式,能使著作权法在新的环境下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对著作权法中公共利益的考虑,也能有力地支持将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原则适用到信息网络环境中。
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用户复制和分享作品变得更加容易。作为用户意义上的公众对于著作权作品同样具有阅读、浏览以及其他形式使用著作权作品的权利。调查发现,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图书馆等对这一使用权表示了充分的认同,相关部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如英国电子环境下合理使用共同信息制度委员会和出版者联合工作组报告将对印刷物的限制适用到了网络环境中。国际上也对网络环境中合理使用的适用给予了充分考虑。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第10条允许成员国在它们自己的、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可以被接受的法律中将限制与例外适用到网络环境中。这些规定应理解为允许成员国设计出适合于网络环境中新的例外与限制。
在网络空间,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仍然适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偶尔在软盘中的复制,不论是电子出版物的部分还是全部;为浏览目的偶尔复制而不是出于为永久性储存目的的复制;个人为永久性储存的需要,把电子出版物的一部分复制到磁盘;应个人的要求,为永久性电子储存的目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将电子出版物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等,均为合理使用。但是,与模拟空间相比,网络空间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种类和方式以及用户使用作品、传播者传播作品的方式都具有独到的特点,传统的合理使用不能简单地移植到网络空间。现在的问题是:在网络空间,合理使用范围是应当扩大还是缩小。笔者认为,简单地主张网络空间合理使用应当扩大或者缩小是不必要的,因为网络空间著作权的范围和用户使用作品的范围都相应地得到了很大拓展。权利扩张后权利限制也相应地被扩大了。关键是要针对网络空间不同著作权来确定对应的、适中的权利限制,特别是合理使用。当作品延伸至网络空间后,并不是所有的著作权权能都扩大或者缩小了,而是有的可能被扩大,有的则有可能缩小。探讨网络空间合理使用问题时,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著作权权能作出考察。如网络环境下的复制权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网络环境下复制权的合理使用也同样值得研究。以复制权的合理使用而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临时复制,远程教学中产生的复制,为个人学习、研究、欣赏目的的复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计算机系统在提供信息网络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复制等应纳入合理使用范围。
(二)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经济学分析:以交易成本为视角
前面分析过的交易成本方法也可以透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在当代,数字技术的出现深刻地影响到了著作权保护,甚至对著作权保护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是因为,在数字化环境下著作权作品可以通过网络特别是因特网的形式被自由地传输、复制、下载,只要具备起码的计算机知识的人都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形式获得数字化作品的电子版本并进行远距离电子发送,而著作权人却很难控制网络空间大量未授权使用作品的行为。网络空间的失控无疑会极大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为此,网络空间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被提出来了。在实践中,著作权人为了在网络空间保护其著作权不受损害也往往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防止他人随意接近和使用著作权作品,技术措施、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等技术手段还得到了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的支持。技术措施对网络作品的限制比起硬件环境中要强,这相应地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技术上的人为割断产生了著作权人单方面控制的合理性的疑问,如何在网络空间既做到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也使合理使用原则继续发挥效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数字技术的发展无疑使著作权的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对作者创作的激励和公众接近作品之间精妙平衡的传统平衡机制在网络环境下也同样遇到了挑战。在网络环境下,传统作品被以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空间被储存、传播与利用。在这一虚拟空间中,新的著作权问题很多。由于著作权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便捷地与作品使用人进行作品使用许可,一些学者认为网络空间著作权授权使用的交易成本将大大减少,根据合理使用的交易成本方法分析的原理,这必然会要求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如本杰明•R•库海恩主张,数字技术的使用将会戏剧性地降低交易成本,而这为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提供了正当性[12]。还有学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中的交易可以达到几乎没有成本的地步。权利管理机制所带来的主要经济利益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交易成本的减少。由于计算机技术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合理使用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被缩小了。由于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市场失败的例子,将会随着技术降低交易成本而减少。技术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是通过增加在市场和使用之间巨大的和急速的市场交易来实现的[9]。其实,类似观点在美国早些年颁布的《信息高速公路白皮书》中即有体现。该《白皮书》建议合理使用范围根据著作权保护之需要应当缩小,并且合理使用的举证责任在用户一方。
诚然,在数字网络空间,著作权人可以通过事先拟订好用户接受的使用作品条件和用户“达成”许可交易协议。用户通过网络点击一下鼠标即可以完成许可事宜。表面上看来,这种授权许可的交易成本非常低,以致戏剧性地减少甚至消灭了合理使用和对著作权人专有权的其他形式的限制。但问题是,如果用户不愿接受著作权人开出的使用作品的条件,就将无法继续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而这种使用在现实空间很可能被当成是合理使用。著作权人通过网络空间的技术手段甚至可以排斥在非网络空间正常的合理使用,从而使其著作权在网络空间被不适当地扩张。这种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或手段对作品在网络空间利用的限制,会对合理使用制度带来冲击。技术措施的存在使得合理使用被限定于一部分人,这可能会影响著作权制度的宗旨在网络空间的实现。也就是说,网络技术也导致对合理使用的限制。由于在网络环境中,那些本来游离于著作权人的专有权控制的用户现在却面临技术措施的壁垒。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合理使用对于阻止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非著作权性方面进行不适当的控制是很有必要的。
进一步说,在网络空间使用作品不能简单地说交易成本必然会降低。主张在网络空间限制合理使用需要证实这种限制会促使表达多样性的实现。从理论上讲,对著作权作品的市场影响程度对合理使用是否成立具有关键性意义。不能为了保护网络空间这一部分市场而限制合理使用,也不能使一个小范围使用作品的行为威胁到整个作品的使用市场,而小范围的使用对于大的市场具有较少的影响才是公正的[13]。ML
参考文献:
[1] 韦之.知识产权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362.
[2] Glynn S. Lunney, Reexamine Copyright Incentive Access Paradigm, 49 Vanderbilt Law Review 500 (1996).
[3]Harry N. Rosenfield, Constitutional Aspects of Fair Use in Copyright Law, 50 Notre Dame Lawyer 790 (1975).
[4] 李扬.网络知识产权法[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112
[5] Hudon, The Copyright Period: Weighing Personal Against Public Interest, 49 A. B. A. J. 759 (1963).
[6] Robert A. Kreiss, Accessibility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Copyright Theory, 43 UCLA L. REV. 13-14 (1995).
[7] Neil Weinstock Netanel, Copyright and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106 Yale L. Rev. L. J. 283, 306-14 (1996).
[8]Stephen M. Mcjhohn,Fair Use and the Privitalization of Copyright, 35 San Diego Law Review 61 (1998).
[9] Maureen Ryan,Cyberspace as Public Space: A Public Trust Paradigm for Copyright in a Digital World, 79 Oregon Law Review 647(2000).
[10]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60 F. 3d at 930 n.8; Richard P. Adelstein and Steven I. Peretz, The Competition of Technologies in Markets for Ideas: Copyright and Fair Use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5 Intl. Rev. L. & Econ. 209, 230-33 (1985).
[11] Pierre N. Leval, Ninmmer Lecture: Fair Use Rescued, 44 UCLA Law Review 1456 (1997).
[12]Benjamin R. Kuhn, A Dilemma in Cyberspace and Beyond: Copyright Law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tributed Over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s of Today and Tomorrow, 10 Temp. Intl. & Comp. L. J. 171 (1996).
[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641-642
Justification of Fair Use of Copyright
FENG Xiao瞦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Fair use is a main way to limit copyright in the copyright regime in all states, which intends to pursue double aims of protec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author and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encouraging a wide spread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e justification of fair use can be understood in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balance of stimulation and access, constitution law and public interest, economic analyses based on transactional cost and classic economics. Even in the context of network, the existence of fair use can be justified. The fair use provision in the Regulations of Protection of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n Networks enacted and enforced in China is such a good example.
Key Words:copyright; fair use; justification; public interest
本文责任编辑:汪世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