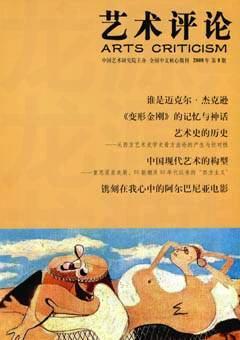从“天下一家”到“我们是世界”
刘 斐
美国流行音乐人迈克尔·杰克逊的突然离去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引发了一波纪念热潮,在中国,其浩大声势和热烈程度尤其引人瞩目。透过媒体展现给我们的诸多哀惋之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缅怀和赞叹,这种看上去似乎是跨越种族、超越了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认同的热切姿态本身显现为一个症候,它不仅表征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大众文化产业全球化整合的深入程度,而且特别以其错落有致的层次凸显出流行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为我们反观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考察今日中国人的情感结构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切入点。
迟到的流行
如果“流行”这个词的本意暗含着时间坐标的原点放置在永远流动而封闭的当下这一意味,那么“流行音乐之王”的称号之于迈克尔·杰克逊只是一个象征。尽管可以想见,他的离世必然会带动其唱片销量再创新高,他却显然并不是近十年来活跃于人们口头和耳边的最流行音乐人。2001年他发表了最后一张新歌专辑《Invincible》(《无敌》),不仅销量不甚理想,而且最终也没能留下一首堪称经典的单曲,人们往往用他之前获得的成就来弥补这张专辑的失败,以至于其中的新歌也只能通过比附于诸如《You are not alone》之类的先例获取些许光芒。换句话说,作为一名音乐人,他的创造才能和引领音乐潮流的惊人影响力至此已经成为了过去的辉煌。总体说来,杰克逊自年幼出道从艺直到生命终结一直都笼罩在明星的光环之下。从更为客观的角度考察他的风格演变、艺术成就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一味追捧天王神话,其艺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可以限定在19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之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杰克逊在1985年之前发表的两张个人专辑《Off The Wall》(1979)和《Thriller》(1982),主要是以其黑人音乐特色在美国社会内部获得了主流音乐界的认可。第二阶段是1985年的“天下一家”演唱会,不仅对杰克逊个人的演艺生涯、而且对整个世界流行音乐的面貌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的五年时间里,杰克逊只出过一张专辑《Bad》,但是从1987年开始,他的巡演活动却由美国扩展到了全世界,其影响力和知名度也由此通过演唱会现场以及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多重媒介而获得极大提升。
第三阶段的开端应该以1990年杰克逊与索尼唱片公司签约为契机。仅仅在此一年以前,日本索尼集团收购了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标志着冷战格局结束,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奠定了演出和唱片销售的全球化格局,也使得这个时期之后的杰克逊逐渐淡化美国色彩,而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有意思的是,代表杰克逊艺术成就的专辑被命名为《历史》[1],在该专辑的MV里,场景设置和军队的装束都令人联想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场面调度和镜头切换则明显借用了德国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但最终我们看到,步调整齐的军队和狂热的群众实际上只是要欢庆广场上竖立起一座杰克逊的巨型雕像。大众文化随意挪用并游戏历史,这堪称是文化产业借助历史表象的碎片所实现的自我经典化过程与行销全球的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奇妙混合。《历史》本身作为一张回顾性和总结性的专辑,其中有一半曲目都是以往歌曲的选辑和再收录。1997年的专辑《血染舞池》中更有一半以上都是以前发表过的歌曲的重新混音版,该张专辑的销量在杰克逊的唱片销售史上也首次出现下滑而难与之前的作品比肩。可以说,就在杰克逊用《历史》向全世界展销“历史终结”这一意识形态的同时,他的艺术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与此相对照,眼下发生在中国的纪念热潮呈现为一个耐人寻味的滞后——杰克逊正当红时显然并没能在中国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他尚在世时,其音像制品在中国的传播也一直是潜流般地仅限于欧美流行音乐爱好者的范围,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公共话题。要想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迟到的“流行”何以产生,我们首先需要对杰克逊艺术活动的价值内涵给予简要分析。
音乐、舞蹈与MV:形式的混杂性
面对欧美流行音乐,人们常常会困惑于风格标签的繁杂多变,杰克逊也是如此,我们一向很难用单一的风格来对他加以界定。在用以描述杰克逊音乐风格的诸多标签当中,惟一算得上独创的要数"new jack swing"(新杰克摇摆乐)了,然而这个标签与其说是标志着杰克逊的伟大天赋,不如说是反证了黑人音乐自19世纪爵士乐兴起以来突破既定社会文化规则、寻求自我表达的顽强生命力和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如果把杰克逊纳入一百多年以来黑人音乐传承与流变过程中,那么他更多地继承了融合于社会的一面[2]。从音乐形式上看,他的风格核心是承自1960年代的摩城之声(Motown)[3]和更为源远流长的节奏布鲁斯(Rhythm &Blues),他的主要唱腔是灵歌(Soul)唱法,然而在配器和编曲方面他也成功地吸收了七八十年代以来的重金属(Heave Metal)、新浪潮(New Wave)和迪士高舞曲(Disco)风格。与他合作过的摇滚乐手从范·海伦(Van Halen)乐队的Eddie van Halen和枪与玫瑰乐队(Guns &Roses)的Slash到桑塔纳乐队(Santana)的Carlos Santana等,不一而足。然而摇滚乐激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始终是他音乐创作中的一个他者,仅就直观印象来说,他的大多数歌曲曲风也很少像同时期的朋克或金属乐那样吵闹。
虽然我们是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内讨论杰克逊的艺术成就,但实际上他的音乐从来都无法与其舞蹈表演相分离。这一方面取决于布鲁斯风格节奏感强烈、适于舞蹈的内在特性,另一方面也与杰克逊本人杰出的舞蹈天赋有关。1980年代是舞曲风行全球的年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阿巴(ABBA)、欧韵(Eurythmics,也译作韵律操)、洛克赛特(Roxette)、香蕉女郎(Bananarama)等乐队都是这个时期的弄潮儿。与出身欧洲的他们相比,只有承袭了黑人悠久歌舞传统的杰克逊以他灵活而富于想象力的舞蹈,才为这种原本是要诉诸身体的音乐形式赋予了真实可感的形体。然而就现代跳舞音乐的发展规律来看,舞曲经历了由繁到简、又由简到繁的变化过程,原则上说是为了解放人们的身体,使得舞蹈没有一定之规、成为人人可为的娱乐活动。但是杰克逊的走红又似乎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他的舞蹈极度个性化,每每表现为一种视觉奇观,而且其崇拜价值远远高于模仿价值,这也与流行音乐文化追求平民化的倾向形成有意思的对比,提醒我们注意媒体既可以民主的方式传播文化、又会塑造出新的神话。
此外,杰克逊的音乐成就不仅代表了美国流行音乐尤其是黑人音乐传统的文化独特性,而且在极大程度上是通过其现场舞蹈表演以及相关的影像产品创造出来的。他的音乐从来就不单纯是音乐,他的歌曲也从来都不能脱离开MV(音乐电视)而独立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他并不是MV的最初受益者,但是他却运用MV技术有效地改造了歌曲的基本面貌,使其得以成功地借助好莱坞工业生产出来的现成叙事元素,用大量的意象来填充歌曲本身所缺乏的情节性和戏剧性。事实证明这对流行音乐产业和影视行业都是一个双赢的举措,但是就歌曲本身而言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某种程度上的退化,尚有待进一步考察。
综上所述,杰克逊音乐形式的混杂性不仅表现在风格方面,而且也渗透到了表现形式的一切细枝末节,而这种混杂从根本上说是为其音乐价值观服务的。
爱的哲学与作为工具的音乐
作为战后婴儿潮一代的一员,杰克逊的音乐无可避免地浸染了60年代的色彩。以他走出美国、扬名世界的公益歌曲“天下一家”为例,其中就显然可以听到披头士乐队发表于1967年的歌曲《All You Need Is Love》的回响。但是,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和人类之爱的60年代同时还有坚持反抗、批判社会不公的一面。在美国,这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特别与黑人民权运动相联系。随着1960年代的逝去,这种批判精神却在摇滚乐中保存了下来。一系列总题为《西方文明的衰落》[4]的纪录片可以多多少少向我们展示七、八十年代美国音乐的另一面,其中展现出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深深的厌弃,与此同时60年代那种对于东方文化作为拯救性力量的幻想却已不复存在,而这种批判态度在杰克逊那里则付诸阙如。
杰克逊个人第一张专辑《墙外》(Off The Wall)很难不令人想起同年面世的英国迷幻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概念专辑《迷墙》(The Wall)。虽然二者都将外在于人的压制性存在比喻为僵硬死板的墙,但是后者对于社会建制深刻的质疑与批判以及自毁式的反抗在杰克逊那里则换成了一种对于爱的力量的呼唤甚而对于爱的信仰。显然,对杰克逊而言,离开日夜劳作、朝九晚五的疯狂生活而暂时地沉浸于情爱/歌舞的自我享受才是他希望透过音乐带给人们的最大启悟。与大多数流行歌曲没有什么不同,杰克逊大量歌曲的主题也集中在青少年对于理想化爱情的渴望以及爱的失落所造成的孤独感等方面。这类“小爱”演变成胸怀世界和平、环境安全的“大爱”,既是中产阶级伦理观的自然发展,也是文化工业全球扩张对于无害化的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
其实,杰克逊的音乐世界中并不是不存在冲突,但是他的处理方式却依然遵照着“爱”的原则。例如发行于1991年的专辑《危险》中有一首名为《黑或白》(Black Or White)的主打歌。这是一首以呼唤种族平等、和谐共处为主题的歌曲。在这首歌耗费巨资制作的MV中,最令人过目难忘的景象莫过于摄影机镜头掠过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种族的人们都在镜头前对着口型同唱这一首歌,通过电脑特技叠化的头像仿佛展示给我们一个平面化而均质的世界图景。然而在影片的后半段,MV的拍摄机制却自我暴露,场景被还原到制造以上影像的摄影棚,我们甚至看到了标志着美国本土的灯光昏暗的街区。其后的超现实主义场景中,一只黑色的豹子悄然穿行,杰克逊则以近乎癫狂的神态完成了数分钟无配乐的舞蹈,并在高潮部分拆毁一辆汽车,砸碎了写在街边窗户上的种族歧视的标语,一阵声嘶力竭的嚎叫之后,他本人则变成了那只黑豹。众所周知,黑豹是60年代激进的黑人争取民权组织黑豹党的标志。杰克逊在这里化身黑豹的举动可以看作是反抗精神的显影和附体。然而,有趣的是,整个MV的故事被放置在一对白人父子因为生活方式差异产生冲突的情节框架之中,因此,种族意识先在地即被更具重要性的父子关系所限定,进而取代[5]。
总而言之,杰克逊的艺术创作试图表明,音乐本身是一种建构性的社会工具,最低程度也是社会的粘合剂。从《住手》(Beat It)等歌曲我们不难看出,歌声可以化解争端,舞步能够消弭暴力,音乐变成了由它自身之外的功能所定义的东西。
从“天下一家”到“我们是世界”
前面已经提到,眼下纪念杰克逊的热潮是一个历史性的滞后。虽然来势迅猛,但是它却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媒体的重复报道和大众的从众心理所共同造成的舆论泡沫。很难说中国人对于杰克逊的纪念不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更不能由此简单地断定我们是在杰克逊死后才重新发现了他。
杰克逊进入中国的时机并不滞后。中国摇滚乐的开端常常被追溯至1986年《让世界充满爱》大型演唱会的举办,而这场演唱会就是在杰克逊《天下一家》的直接刺激之下产生的[6]。但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中国流行音乐受到迈克尔·杰克逊的直接影响则是少之又少的。这首先是因为上文所述杰克逊本人艺术风格的混杂性导致他的音乐风格很难复制(若是考究霹雳舞、太空舞、街舞在80年代的盛行,或许还能找到杰克逊产生影响的踪迹);其次,对于思维较为活跃的中国摇滚乐手而言,他的音乐又不如那些有着激烈社会批判立场的艺术家那么有吸引力;第三,华语流行音乐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历史延续性,与欧美流行音乐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文化差异。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杰克逊的去世所引发的社会性关注并不局限于他的音乐成就,而是涉及两起多少有些令人尴尬的事件,即与肤色相关的种族身份问题和娈童丑闻。仅就音乐之外的社会关注而言,后冷战时期的文化接受并没有完全摆脱冷战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认识论氛围,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导致的艺术物化和人的异化继续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文化结构和世界想象当中,作为冷战镜像之一的美国社会的非正义性等级建构是和受压迫的黑人形象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杰克逊音乐爱好者身上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道德的优势。
从杰克逊一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他的影响就并不单纯是音乐,而是裹挟着所有关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想象以及随后发生的震惊体验一起到来的。所以,原本是美国艺术家支援非洲的义演,其混合了责任感和优越感的标题“We Are The World”却被翻译成了更具乌托邦色彩的“天下一家”。这就形成了一个富有趣味的错位——当杰克逊被当作美国文化的象征加以接受的时候,中国人同时把他想象成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秩序的代表——而当杰克逊已然借助跨国文化工业成为全球头号明星的时候,我们则仍然忽略掉他的美国人身份而把他当成一位世界公民来看待。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杰克逊的身份是否与自由世界代表或世界公民相称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如何体认杰克逊实际上紧密地联系着中国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和想象。
因此,杰克逊之死引起的关注正好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改变正在生产出强有力的文化表征。由于流行音乐自身呈现为一个价值中立的名利场,对于巨星热切的怀念无疑将有效地消除过去30年来中国追赶世界潮流的足迹,同时使前者得以以一种崇拜和接续的姿态寻求更进一步的自我表达。如果其中的自我表达成分足够真诚,那么这将不仅是对一位昔日巨星的怀念,同时也是这个时代对逝去的80年代充满复杂情感的回望。既是借怀他人之旧而怀自己之旧,也是对于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和希望、不需要怀旧的精神状态的怀旧。
注释:
[1]发行于1995年,全名为《历史——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书》,为杰克逊第五张个人专辑。
[2]试比较从Rap到Hip-hop和Trip-hop的发展历程,流行音乐分类学本身在遮蔽社会历史背景的同时,指示出了黑人在音乐形式不断被主流商业文化吸纳的情况下努力寻求异变和疏离的路径。
[3]原本是成立于1960年的一家黑人唱片公司,由于培养出了一批成功融合灵歌和流行音乐的艺人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音乐风格的代名词。灵歌当时只在黑人中流行,这与六十年代民谣歌手追求种族平等的倾向相悖。可参见钟子林编著《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第五章第三节《摩城》,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4]也译作《朋克简史》,目前共有三集,分别出品于1981年、1988年和2003年
[5]MV的最后一幕,是杰克逊所变的黑豹走向路的尽头,后面跳接的镜头则表明这一切都是儿子正在观看的电视节目的内容。
[6]见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第七章《崛起的1986》,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刘斐:北京大学中文系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