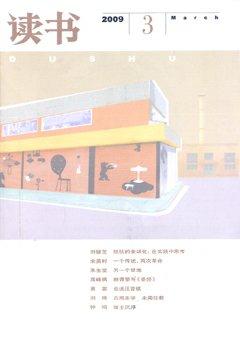伏尔泰与里斯本地震
吴 飞
汹涌的波涛扑进港口,打碎了所有停泊的船只。火焰和灰烬盖住了大街小巷;房屋倒塌了,屋顶被掀跑了,房基也毁坏了;男女老少共三万居民,被压死在这些废墟之下。
这是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描述的里斯本地震。面对如此凄惨的景象,刚刚到达里斯本的哲学家庞格罗斯困惑地说:“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如此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相信“存在的就是最好的”的哲学家显然也怅然若失,一定要为这件事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说明地震的发生是有意义的。他在看到水手竟然趁乱打劫,甚至用不义之财去嫖妓的时候,似乎更是感到自己的哲学受到的挑战,上前劝他说:“朋友,这样可不好,您缺乏如此行事的理由,您选错了时间。”
水手不会听哲学家的劝告,但当庞格罗斯看到在废墟底下呼救的老实人时,却已经恢复了他的理性:“地震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去年美洲的利马城也发生过同样的震动;相同的原因,相同的结果:从利马到里斯本地下埋着一条硫磺带。”
庞格罗斯在救出更多的灾民之后,似乎进一步恢复了他的哲学自信心。他向那些感谢他的灾民演讲说,事情不可能比现在更好,由于里斯本有座火山,它就不可能在别处,因为事物不可能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一切都很好。
庞格罗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全被宗教裁判所的人听了去,而里斯本的教会对地震原因早已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庞格罗斯的说法要么会推论出没有原罪和惩罚,要么推出没有自由意志。地震完全是上帝的惩罚,只有对异端处以极刑,才能平息上帝的愤怒。于是,庞格罗斯、老实人和别的几个异端一起被抓了起来。而就在刑罚执行完之后,大地却再次颤抖了起来。
发生在一七五五年万圣节的里斯本地震,被称为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地震”。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规模巨大,破坏性极强,从而催动了现代地震学的诞生,而且因为它处在思想启蒙的中间,伴随着很多重要的思考。伏尔泰、卢梭、康德、歌德等都曾经评论过这一事件,而伏尔泰和卢梭在地震发生时都处在思想的成熟期,围绕地震的争论甚至直接导致了二人的最终决裂。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场地震的看法与他们一些最根本的哲学思想相关。
伏尔泰在地震发生后第二年就写了两首长诗《里斯本的灾难》和《自然法》,卢梭在看到诗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就是著名的《论神意书》,但伏尔泰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此信。几年之后,伏尔泰匿名出版了小说《老实人》,卢梭认为那就是对他的回应;而卢梭后来在《爱弥尔》中所写的萨瓦神父的告白,据说又是对伏尔泰的回应。这些芥蒂终于导致了二人最终因《论神意书》的出版纠纷而彻底决裂。
在地震发生之时,确实颇有宗教人士像《老实人》中描写的那样,把地震当成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虽然并不像小说中讽刺得那么可笑。不过,伏尔泰严肃对待的,并不是这样的天谴论者,而是像庞格罗斯那样的哲学家,或者说,他真正挑战的乃是曾经相信一切皆善的过去的自己。而这恰恰触及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中争论非常激烈的神义论问题。导致伏尔泰和卢梭决裂的思想原因,正是对神义论的不同理解。
一七一○年,莱布尼茨以法文出版了著名的《神义论》(Theodicée),明确以乐观主义的“神义论”概念诠释基督教传统中“存在的巨链”的说法。在他看来,现存的世界是上帝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世界,其中的一切存在物都严格按照上帝规定的秩序排列,形成一个连续的、充盈的巨大链条,并不存在真正的罪恶和不完美,表面上的不完美都服务于整体的和谐完美。莱布尼茨的观点很能代表十八世纪前半期的乐观主义思潮,而英国诗人蒲柏于一七三三至一七三四年完成的长诗《论人》(Essay on Man)则是对莱布尼茨神义论思想的诗歌图解,其中的名言“存在的都是对的”(Whatever is right)代表了十八世纪欧洲人天真的乐观主义思想。他甚至谈到,如果地震或风暴毁灭了整个城市乃至整个民族,那也遵循宇宙间普遍的大法。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
早年的伏尔泰非常推崇蒲柏,说他的《论人》是“任何语言中不曾有的,最美、最杰出、最高贵的教育诗歌”,甚至还亲自作诗模仿。但是,身边的苦难使伏尔泰就像老实人一样,逐渐对自己曾深信不疑的乐观主义发生了动摇,而里斯本地震使他最深地表达了这种怀疑,《老实人》则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不过,伏尔泰在《里斯本的灾难》和《老实人》中是否真的与乐观主义彻底决裂,学者们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里斯本地震后的伏尔泰彻底否定了乐观主义。但也有人认为,前后期伏尔泰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的断裂。比如卡尔·贝克尔就说,伏尔泰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只不过不再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按照这种观点,伏尔泰只不过修正了蒲柏的乐观主义中过于天真的部分,但并未放弃乐观主义本身。
《里斯本的灾难》的副标题是“对‘存在的都是对的这句格言的探询”(examen de cet axiom: Tout est bien)。伏尔泰在诗序开始就谈到了他的用意:“对于那些亲眼看到这些灾难的人来说,‘存在的都是对的这句格言就显得夸张了。无疑,万事都是神意安排的,但很久以来就很明显,神意对万事的安排并非意在提升其尘世的快乐。”
随后,伏尔泰列举了对蒲柏的名言的种种误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些要绞死庞格罗斯的教士们的观点,然后这样阐释自己的立场:“《里斯本的灾难》的作者并不想攻击伟大的蒲柏,而是自始至终热爱他和崇敬他;他几乎在所有细节上都同意蒲柏,只是更同情人的悲惨;但他要攻击那对新格言‘存在的都是对的的滥用。他指出这样一个古老但可悲的事实,这也是所有人都承认的,即世上存在罪恶;他承认,‘存在的都是对的这句话,如果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而不将对快乐状态的希望放到未来,只会伤害我们当前的悲惨。”
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专门有一个辞条解释“存在的都是对的”,对蒲柏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说,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切都是被安排的,一切都有秩序”,那是对的。但如果把这理解为,“谁都过得很好,没有人受苦”,那就不对了。而这后者,正是蒲柏自己的理解。
如果就在地震吞噬了那么多城镇的时候,有哲学家面对那些好不容易从废墟中跑出来的人大喊:“这些都服务于总体的好;那些死去的人的后代将提升他们的命运;泥瓦匠将会在重修房屋中赚钱,野兽们可以去吃废墟下掩埋着的尸体;这是必然的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你自己的不幸不算什么,但会有助于总体的好。”如果是这样,这种演说无疑和地震一样残忍,《里斯本的灾难》所针对的,正是这样的滥用。而这就是庞格罗斯那种天真的乐观主义,也是蒲柏的本来意思。曾经极为崇拜蒲柏的伏尔泰借着纠正误解的借口,无疑是想重新诠释蒲柏的名言。他已经无法赞同蒲柏的理论,但仍然欣赏这句话中体现出的乐观主义。
在伏尔泰看来,庞格罗斯那样的神义论表面上是乐观主义,实际上却是非常冷酷的。因为,按照这种思想,所有的灾难和痛苦都罪有应得。面对地震之后的惨象,这样的思想将是极为可怕的:
比如,当你听到他们那可怜的、断断续续的呼喊,
当你看到他们的骨灰上冒起的青烟,
那么,你会认为这就是永恒之法吗?
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这恐怖的景象,
你会认为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吗?
那被抱在母亲的胸前,流着血的婴儿,
你能说他们有什么罪过吗?
难道在这坍塌的里斯本,
你能找到比花天酒地的巴黎更多的罪孽?
比起崇尚奢靡的伦敦,
里斯本的放荡岂敢媲美?
但大地吞噬了里斯本;法兰西的轻狂儿女们
还延续着无度的宴饮,跳着疯狂的舞蹈。
伏尔泰说这种神义论是对蒲柏的乐观主义的歪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蒲柏的原意,是让人们对幸福生活充满更大的希望;但若以蒲柏的“存在的都是对的”来解释里斯本这样的灾难,则无异于为灾难和罪恶正名,反而陷入了一种冷酷的宿命论,与蒲柏的初衷相去甚远。伏尔泰质疑的,并不是乐观主义本身;但他从莱布尼茨—蒲柏的神义论中确实发现了自相矛盾之处。
莱布尼茨的神义论建立在他对“存在的巨链”的重新理解之上,而伏尔泰对这一神义论的扬弃,也正是基于对存在巨链的又一诠释。他在《里斯本的灾难》的一个长注里讲出了自己对于存在巨链的理解:
宇宙间的那个链条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个连接所有存在物的规则的阶梯。非常可能,在人和野兽之间有巨大的距离,就像在人和更高的自然之间那样;同样,在上帝和所有被造物之间,也有无限距离。
按照启蒙时代比较流行的理解,存在的巨链应该是一个不间断的、规则的链条,从最高的存在到最低的存在物之间,按照规律逐渐下降,在两个差别较大的物种中间不可能有空缺,必然存在过渡物种。这一观念曾经使洛克感到不安,因为在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而人们只知道这之间有天使。因此他推论出,如果有存在的巨链,则在人与最高存在物之间,必然存在很多物种,是人所不曾知道的。而今,伏尔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质疑这一说法:既然各种物种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那么,存在的巨链就不是一个规则的阶梯。这无异于否定了莱布尼茨—蒲柏神义论的宇宙论基础。如果万物之间不是规则地逐层排列的,而是杂乱无章的,那还谈得上什么“预订和谐”?伏尔泰明确地指出,“说任何一颗原子被拿走,世界就无法存在,那是根本不对的”。随后,他更系统地批驳了莱布尼茨的宇宙论:
杰出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凭着无与伦比的天才,认可和捍卫了事件之间的关联;这需要解释一下。所有的物体依赖于别的物体,所有的事件依赖于别的事件。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物体都是支持宇宙和维护其秩序所必需的;在事件的总体系列中,也不是每个事件都必不可少。一滴水或是一粒沙并不能在整个体系中带来革命。
不仅自然世界是这样,历史事件也是一样。伏尔泰举例说,如果恺撒的母亲不生恺撒,世界历史恐怕就会非常不同,但恺撒究竟向右边还是向左边吐痰,却无关宏旨。由此可见,有些事件会有结果,但有些没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就过去了,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某种物质若有一小点增加或减少,稍微偏离规律,根本不会影响到存在的巨链。
这条巨链并不是绝对的充盈(plenum)……不是每个空间都被充满。因此,物体并不是从原子到最远的恒星这样过渡的。因此,在有感觉的不同存在物之间,可能就存在极大的距离,没有感觉的物体之间也可能有。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人一定要被放置在如此环环相连的不间断链条中。所谓万物都被连在一起,只是说明,万物都被规则地放置在其各自的秩序上。
推论到最后,伏尔泰所能接受的只有,万物各有其应该的位置;但万物之间并不存在可以辨识的联系。宇宙间和人类历史上都有各种偶然性,并不是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即使是必然的事情,由于并不严格遵循规律,也是人所无法认识的。他在另外一个注里又说:
很显然,人若没有外在的帮助,不可能得到这种知识。人脑都是从经验获得知识的;但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帮我们看透我们的存在之前有什么,看透这之后有什么,甚至看透现在是什么在支撑这一切。我们怎样获得了生命?它所依赖的生命之泉是什么?我们的头脑怎么会有观念和记忆?我们的四肢如何遵从意志的每种运动?对这些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的星球是唯一有人居住的吗?它是在别的星球之后被创造的,还是同时被造的?每种植物是从第一种植物变化来的吗?所有的动物物种都是第一对动物的后代吗?最深邃的哲学家也不比最无知的人更能解决这些问题。
既然宇宙不是那么规则的体系,既然有很多偶然的事件发生,既然人根本没有能力理解万事之间的关联和规律,这无异于彻底否定了“预订和谐”的可能。这样,地震的发生完全可能是偶然的,它发生在哪里,会砸到哪些人,也是完全无缘由的。如果真是这样,则人们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生死祸福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好人完全可能遭受无妄之灾,坏人完全可能享受颐养之福,没有什么根据可言。那岂不是比蒲柏还要无情吗?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受偶然性主宰的世界。小说中的每个人都会被毫无缘由地卷入一个又一个的厄运当中,都自以为是命运最悲惨的人。没有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庞格罗斯自始至终都坚信蒲柏的信条,但他自身的遭遇却一次次摧毁这一理论。
尽管如此,伏尔泰还不愿意像休谟和康德那样彻底否定充分理性原则。他之所以修正莱布尼茨—蒲柏的乐观主义,就是因为他们乐观得不够彻底。就像他在《哲学辞典》中所说的,“存在的都是对的”这一教条“根本无法安慰人,反而给人们带来绝望”。但他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却走到了更加残酷的一个结论,使他自己都不敢接受。于是,他在前引的论存在巨链的长注中继续写道:“上帝是这秩序的原因和管理者。荷马笔下的朱庇特是命运的奴隶;但是,根据更理性的哲学,上帝是命运的主宰。奥古斯丁说:‘在正义的上帝面前,没有人会无辜受苦。这位圣徒的格言的意思是:在正义上帝的管理下,凡是受苦的,没有不是罪有应得的。”
伏尔泰似乎又绕了回来。既然受苦的人都是罪有应得,那些惨死在地震中的婴儿岂不还是有罪的吗?正如他在诗中说的:
这是你应该解开的命运的纽结,
你若否认我们遭受的恶,你怎么来治疗呢?
伏尔泰仍然坚决认为,世界上确确实实存在着罪恶。既然如此,上帝为什么会允许那么多人无辜受苦呢?伏尔泰回到了曾经困扰莱布尼茨的那个基督教的神义论问题:万能而至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允许罪恶的存在?
上帝曾经在地上与人类住在一起,
而今罪恶却充满人心;
一个高傲的智者喊着说:他无力做到;
另一个回答:他能做,但他不愿意。
万能的上帝怎么可能无力消除罪恶?如果他可以做到却不愿,那就不是至善的?面对这样的争论,伏尔泰甚至像培尔(Pierre Bayle)一样,考虑过摩尼教的二元论。他在《老实人》中借马丁之口说:“先生,我们国家的教士们指控我是索尼齐教徒,但事实上我是个摩尼教徒……魔鬼到处插手人间事务,我肯定,他附在我的身上就像附在其他人身上一样。我要告诉您,放眼全球或者说这个小球,我认为上帝把它交给一个专干坏事的家伙。”
但伏尔泰也像培尔一样,并不甘心接受这种异端邪说。他在《里斯本的灾难》中举出了各种神义论的解决方式之后,认为这些都比不上培尔的,因为培尔推翻了一切解决方式,认为恶的存在问题根本不可能有理性的解决。当年莱布尼茨写《神义论》,就把培尔当成了自己的批判对象;而今,曾经盛赞蒲柏的伏尔泰竟然转到了培尔那边,可见他确实改变了立场。
不过,对于培尔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伏尔泰仍然不愿意全盘接受。他认为,虽然培尔成功地推翻了所有体系,但他同样也在反对自己的信念。或许真正令伏尔泰不安的,并不在于培尔无法建立一套思想体系,而是因为,追随培尔势必彻底背离乐观主义。满怀悲悯之心的伏尔泰,还是希望为人类的幸福找到依托。
对存在巨链的逼问已经使伏尔泰无法回到莱布尼茨的预订和谐论,因为这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已经不可能是好的了。在《老实人》中,人们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并没有回到乐园里,过起幸福的生活,而是陷入了无休止的空虚和无聊当中。不仅颠沛流离的生活是悲惨的,就连和平安静的生活也毫无幸福可言。伏尔泰要为乐观主义留一块地盘,已经不可能在尘世中找到:
“一切都会好的”,这个希望足以支撑人类;
“一切都是好的”,这却只是虚妄的幻象。
现实永远是悲惨和不确定的。唯一支撑人们的,是对于来世的美好生活的希望。伏尔泰把蒲柏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都会好的”,似乎保留了乐观主义的基调,但其含义已大不相同了。
在《里斯本的灾难》的末尾,伏尔泰总结了他思想的变化:
我谦卑地叹息着,柔顺地承受着痛苦,
不再攻击神意的道路。
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艰苦中更轻松地歌唱
温柔享乐的律,但这律却把人类带入了歧途。
时过境迁;年龄和操劳教育着我,
我虽然错解了必朽者的软弱,
我在这黑暗中还在寻求真理之光,
没有什么抱怨,我服从命运。
就连庞格罗斯都意识到,原来伊甸园中的人不是要享乐的,而是要劳动的。于是,《老实人》中的人们都认真地过起日子来,在辛苦的劳作中慢慢培养起一点点希望。在尘世中,并不存在可以安享的幸福,只有追求幸福的劳作。一旦人们以为这劳作已经带来了幸福,那就立即犯下了又一个错误。所以,每当庞格罗斯心满意足地说什么“最完美的世界里,事事相连”的时候,老实人就提醒他:“讲得很对,不过,还是把我们的园地种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