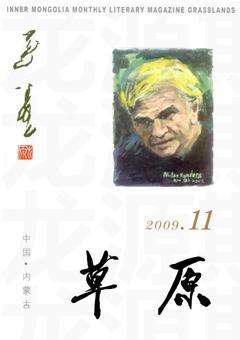忘不了的古鲁玛奈
刘振国
人老了,记忆力减退了,刚刚办完的事,转过身就忘了。但是,四十五年前的往事在记忆中却越来越清晰了。这几天,忽然记起了古鲁玛奈。多好听的名字呀,像一个纯情的少数民族少女的名字,像一朵艳丽的鲜花的名字,可是它却是一条小河,一条深藏在高山密林里的小河,一条鲜为人知的小河。大兴安岭上这样的小河不计其数,不过大多数没有名字,它是个例外。许许多多条这样的小河汇集起来,冲出原始森林,河面宽阔了,河水平静了,在水滨有了星星点点的村落,人们才想起给它起个名字。在没有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要个名字有什么用。但是,它有。三年前,我曾回到那个林业局,向人们打听过那条河,许多人都说不知道。可是那里曾经人欢马叫,喧闹一时,我们曾经张开理想的翅膀,艰苦创业了一阵子。如今却销声匿迹了。
“金山银山花果山,老百姓一定胜过苍天,快马一去千万里,一天等于二十年。”我就是唱着这支歌进入那片原始森林的。森林小火车把我送到五十一转运站。那里是小火车的尽头。下了小火车,到转运站喝点水。转运站只有一个老头,看守转运的物资。老人见了我便问:“孩子,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荒山野岭的,有啥好玩儿的!”我说:“我是分配到古鲁玛奈工作的。”他又说:“这么点的孩子,家里怎么舍得让你到那个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去呀?”我说:“我是主动要求来的。”他说:“今天没有进山的人了,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在这住一宿吧。”我说:“那里正缺人,我必须马上去。”“你自己能行吗?”“能行。”他指给我看:“往古鲁玛奈去只有这么一条小路,是倒背工运送物资趟出来的。路上不贪玩儿,不采野花,就走不错。”我说:“记住了。”于是,背起行装,向古鲁玛奈挺进。
第一次走进原始森林,一切都感到新奇。树木那么茂密,遮天蔽日,又那么粗壮,一个人搂不过来。这是在预想之中的。没有想象得到的是,这里看不到成群结队的獐狍野鹿,也感觉不到黑熊野狼的威胁,连树上的鸟、草里的虫,都不肯鸣叫,好像生怕破坏了大森林的寂静。那条森林小路,草还是青青的,只不过被人趟得倒伏下来。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匆匆地走着,在寂静中,想起了儿时的童谣:“小板凳,歪歪歪,里头坐个秃乖乖。乖乖出来买菜,里头坐个老太。老太出来烧香,里头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磕头,里头坐个孙猴。孙猴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由此想起了姥姥。姥姥常常拉着我的手,坐在板凳上,晃着身子,唱着这个童谣。他说:“秃乖乖就是你呀!”我说:“怎么会是我呢?我的头发多厚哇!”姥姥说:“你刚刚出生时一根头发也没有,就是一个秃乖乖嘛。”我说:“怎么我一出来,就有一连串儿的故事呢?”姥姥说:“我外孙子能呗!”我想,能什么呀?进了原始森林,兔也不跑了,鸟也不唱了,什么山猫野兽都没了,哪里还像个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哪有什么童话!
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走得满头大汗。累了。累了也得走。因为我忽然觉得山林里寂静得可怕,不仅隐藏着奥秘,而且隐藏着杀机,这满头大汗就立即变成了冷汗。我越走越快,以致于跑了起来。跑着跑着,嗓子眼儿又干又痒,冒烟儿了,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脚下一滑,摔倒了。正巧,两个采伐工看见了,急忙跑过来,把我扶起来。见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便问:“你这是到哪儿去呀?走得这么急。”我定了定神,说:“工段。”“哎呀,你是从五十一来的吧?”我点点头。“多远那,十八里路呀,你怎么还跑呀?”我没有回答。其中一个高个子对我说:“我们都是这个工段的。我姓白,山东人,大家都叫我‘棒子。”我仔细看了看他,心想:他姓白,长的可够黑的。满身的肌肉块,挺壮实。那个矮个子也发话了:“我姓兰,四川人,大家都叫我‘槌子。我们都是这个工段的采伐工。”我又看了看这个人。他姓兰,眼球可黑的发亮,额头很大,一定很聪明。说话间,我放松了,喘气也匀了,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儿到了工段。
他们赶紧给我铺好行李,让我休息一下。棒子去找段长,槌子给我从水筲里舀了一瓢水,递给我。我赶忙说:“不,不喝。”他说:“出了那么多汗,不喝水哪行?”我说:“我不喝生水。”“在大森林里,哪能常有开水?咱们这里的水可好了,又清凉又爽口,还不闹肚子,你少喝点试试。”好意难却,我接过水瓢,看一眼瓢里的水,清澈透明,喝了一口,透心儿凉,还有点甜。于是,咕咚咕咚把一瓢水全喝了下去。这时,段长来了。我赶忙坐起来,下铺。段长说:“走了一天,累了,别起来了。十八里山路,累坏了吧?”我是瘦驴拉硬屎,强挺着说:“这点儿山路没问题,梁山伯送祝英台,溜溜达达就走了十八里。”段长笑了:“这小子还挺风趣呢。”我接着问:“段长,这里的水怎么这么甜?”段长说:“源头活水,能不甜吗!你先休息一会儿吧,明天上班。我走了。”
段长走了,我躺在铺上睡不着,心里就想着这里的水。我小时候,住在小兴安岭铁力森铁处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那个小山村只有四五户人家,村头有个老道庙,庙前有棵歪脖树,树下有口辘轳井。姐姐和二哥放学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井沿去抬水。抬回来的水又浑又红,喝下去就肚子疼。所以我家买个黑铁壶,我们总是用黑铁壶烧水,使我对黑铁壶有了很深的感情。一次,二哥给我出了个谜语:“一个老头黑大黑,见了人就哭衰衰。”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黑铁壶。”“对了,就是黑铁壶。一百分!”烧开的水盛在碗里,清凉一会儿,碗底就沉淀出一层铁锈一样的东西,水面上还漂浮着油污一样的东西,喝到嘴里又苦又涩。因此我常说,我是喝苦水长大的。没想到,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深山老林里,竟然喝上了甜水。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同小乔一起上山检采伐尺。初秋,匍匐在地面上的一种小植物叫雅格达,结的果实可好看了,圆圆的,白里透红,满山满野,到处都是。我们检尺归来,架不住野果诱惑,蹲下来采摘雅格达的果实。这种果实,大家叫它“红豆”。但不是王维诗里写的那种红豆,那是南国红豆,树上长的;这是北国红豆,草里生的。我们一个向东,一个向西,采着采着,就分开了,而且越来越远。我一边往饭盒里装,一边往嘴里放。饭盒满了,吃得也倒牙了,才想起抬头看路。这一看不要紧,傻了。距我不到十米,一只黑瞎子也在吃红豆,我一下子坐到地上,想喊却喊不出声来;想跑却抬不起腿来。这时,黑瞎子忽然发现北面有喊声,竖起耳朵听了听,就向北奔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乔跑过来,使劲推我一把,我才醒过来,他说:“刚才黑瞎子到你这边来过吧?”我“哦”了一声。他说:“没伤着你?”“没有。就在我身边吃红豆。不知怎地,它就向北跑了。”小乔告诉我,他在远远的地方看见一只黑熊向我这边走来,就去找棒子和槌子。棒子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观察,如果发现黑熊离开了我,立即跑去找我。他和棒子往北跑,让棒子伐一棵树,这棵树不可太粗,太粗,需要的时间过长;也不可太细,太细,树倒时发出的响声太小。槌子负责把黑熊引过来。棒子开始伐树时,槌子就呼喊“救命”,喊着,喊着,熊真的向他扑去,他灵巧地在树缝里转弯,引诱熊跟着他。忽然,棒子伐的树“轰”的一声倒下了,熊顾不得追赶槌子,慌乱的向密林深处逃窜。小乔看到这种情况,这才过来找我。他把我拉起来。我惊魂未定,怔怔地跟着小乔回到工段。回到工段以后,大家不称赞槌子的机智,反而夸奖我的勇敢:“小刘真行,差点和黑瞎子亲嘴。往地上一坐,黑瞎子就被吓跑了。”我也捋杆爬:“知道吗?那叫‘坐禅。佛法无边啊!”
夏天是不知哪块云彩有雨,秋天则是有云就有雨,秋雨连绵!秋雨终于把森铁的路基冲垮了,粮食、蔬菜、一切物资都运不上来了。我们眼看要断顿了。大家顶着雨到森林里采野菜、下兔套。我们真的吃盐水煮野菜了。大家都盼着能套住几只兔子,开开荤,天天都跑出几次溜兔套,总是空手而归。烦了,索性不去溜了。一天馋鬼茹毛非要出去找一找,谁都不愿跟他去,他就自己去了。出去两个小时不见回来,大家有些后悔,相跟几个人好了,这要是出点什么事,咋办!正打算派人去找的时候,他推开了门,没等人进来,喊声先进来了:“套住了,套住了,还套个大的呢!”大家将信将疑:“既然套住了,你怎么没拿回来呢?”“太大了,我拿不动。”“真是鹰嘴鸭爪子,啥也干不了。”“谁能谁去呀!”他这么一说,都认为他在瞎说,啥也不说了。可是他在火炉旁,一边拧衣服,一边说:“棒子,找几个棒小伙子,抬去吧。你在下雨前下的油丝绳套,套住了一头大狗熊。”棒子赶忙说:“真的吗?狗熊死了吗?”“我看是死了。我用棍子捅了两下,一动不动。”棒子点兵了,可人们还怀疑,兔子套怎么能套住黑瞎子呢?棒子说:“很有可能,那个套上的油丝绳是双股的。”大家相信了棒子的话,带上绳子、杠子,走了。一袋烟工夫,他们闹闹轰轰地抬回来了头大狗熊,足有六百斤。
大家冒雨给黑瞎子剥皮、开膛,去除内脏,摘下苦胆。大家认为熊的苦胆能够医治多种疾病,于是把它收藏起来。至于要不要熊掌,我提出:“熊掌是个好东西,千万不能扔掉。孟子把鱼同熊掌相比较,说,‘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可大多数人持不同意见,特别是棒子,说的更狠:“什么孔子孟子,什么者呀也呀,熊掌上没有多少肉,毛也褪不净,把它留下来谁会做,还不是放烂它,让它生蛆下蚱。扔了吧!”别看他不是官,他说话是人们都听他的。于是,四个熊掌被扔得远远的。我们按小组,一个小组一洗脸盆肉,不够再去割。这主要是为了解决盆多炉子少的问题,如果一人一盆,到哪儿去炖肉啊。我们把肉切成大块,放到洗脸盆里,浇上水,撒上盐,放到铁炉子上炖。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比过年还热闹。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啊!
森铁路基修复了,森林铁路通车了,冬天也来了。林场决定在我们工段召开创高产、放卫星,比武打擂大会。大会在晚上召开,各个工段的段长都来参加大会。林场主任说:“为了给冬运生产提供充足的木材储备,林场决定明天为木材生产高峰日,今天在古鲁玛奈工段搭了擂台,是英雄,是好汉,登上擂台比比看!”就这样大会开始了。段长们纷纷登台,你说日产三百米,他说日产四百八。越抬越高,还是我们段长有魄力,登台就喊:“战鼓一打咚咚咚,五更半夜搞高峰,明天高产一千米,放颗卫星大家看!”大家一听都傻眼了。弯把锯采伐,一天生产一千米,不可思议。
会议开了半个小时就散了。各段段长都回去安排明天的高产日。我们咋办?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段长说:“咱们研究一下自己的事情吧。”许多人说段长的牛吹大了,以前日产百米就算高产了,现在高出十倍,咱也没有三头六臂,调动不了天兵天将!段长是不是发高烧了?怎么说起梦话来了!可段长却很镇静。他说:“咱们过去采伐是四道锯俩人一组,一人扛斧子一人拿锯,明天改为一人一组,既扛斧子又拿锯。”棒子立即跳起来喊:“任务重了,怎么反倒减人了?”段长说:“听着,你们四个人只要把树放倒就行了。减下来的人造材。”棒子又喊:“说来说去,大嫂子还是个娘们。原来两个人既伐树又造材,现在分开了,工序不衔接了,速度能提高吗?”“你这个人怎么不动脑子?过去是俩人一把锯,现在是一人一把了!现在就出库四把新锯,由大老黑把它锉好,分给造材工。检尺员不仅要检尺,还要协助造材工量材。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大老黑马上进入角色,大家都说你锉锯锉得好,明天这锯好不好使,就看你的了。其他人都睡觉。我要当一回周扒皮,半夜把你们赶上山去。现在是下弦月,后半夜有月亮,在月亮底下采伐,千万要小心,注意安全。命令你们,睡觉!”
我们这支队伍,别看平时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呲缨子,扯大栏,关键时刻还真能叫一号。段长那公鸡嗓子一叫,全都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裳拿起工具上山了。那速度不比军人差。工人上山了,伙房也忙起来了。八两一个的大面龙,白肉片土豆汤,由打柈子工、烧炉子工、伙夫分别送上山去。大家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笑了:“天天搞高峰多好,不用啃冻窝头了。”“天天搞高峰不累死你呀!快干吧,晚上给你们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段长和大老黑都拎着一把锯上山了,和大家一样干,给大家鼓劲,大家干得更欢了。下午五点左右,段长估计伐倒的树已经差不多够了,让伐木工停下来,去造材。这时天渐渐地黑下来,打柈子工把平时积攒下来的明子全部运上山,段长又告诉他回去以后把工棚子里里外外都点上油灯。这样,整个古鲁玛奈,山下点灯,山上点明子,有点儿像威虎山了。不过,那时曲波写的《林海雪原》还没发表。点着明子造材,擎着火把吊峁,干得欢着呢!晚上八点收工,天上飘起雪花来。落到头上脸上就融化了,与汗珠子搅在一起,变成水。回到工棚里互相一看,像小鬼儿一样,都忍不住笑了。统计数字出来了,高产日完成一千零一十三米,段长立即用电话向林场报捷。林场主任接过电话:“感谢你们!咱们林场今天的总产量突破了五千米大关,放了一颗大大的卫星。得给你们记一大功啊!”为了庆功,我们吃上了猪肉炖粉条子,每人还有二两白酒。我们帐篷里热乎乎的捏着酒壶,外面的寒风卷着雪花敲打着帐篷。第二天早上,大雪封门了。段长说:“近一个阶段,我们除了维持正常的木材生产之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牛马套子上山的准备工作上。”于是,我们在工棚子对面又架了一栋帐篷。帐篷里安装了铁炉子。帐篷北侧盖了长长的一溜马厩。马厩里放了马槽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盼着,盼着,牛马套子终于盼来了。那年的套子队是从依安农村来的。东北农民,入冬以后一般都在家里猫冬了。人吃马喂,花销不小。他们愿意带上牛马到林区来,干上一冬,比他们在地里干两三年挣的还多。套子队来了四十多人,十八匹马,四只骡子,八头牛。寂静的山林里一下子就变得人欢马叫了。
工段里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吃水就成了大问题,入冬以来,工段只用一个运水工,他一个人到河里刨冰,装到麻袋里,用扒犁运到工段,放到缸里、锅里,化成水。洗脸刷盆、淘米饭都用它。本来就忙不过来,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牲口,虽然套子队也派了一个运水工,还是不够用。我们收工以后就到河里义务刨冰。大家都愿意去,刨冰是个挺有意思的活。古鲁玛奈河虽然很窄,河水却很深,能刨出大块大块的冰。当然化水用的冰不需要大,应该说越小越好。但我们愿意刨大块,大块冰可以直接装上扒犁,不用麻袋。大家宁可运到工段把冰砸碎,也不愿往麻袋里装碎冰。套子队里有个自愿运冰的小伙子,每天晚饭后,他都赶着牛爬犁到河里拉冰。这个农民少言寡语,绵和厚道,个子不高,力气不大,衣着破旧,长相一般,他的牛也和他一样,个头矮小,身单力薄。可是,却很勤快,总是把刨冰现场打扫干净,才最后收兵。所以我很注意他。都是年轻人,很快就熟悉了。我觉得他的那头小牛挺好玩儿的。就说:“大哥,让我骑一下你的牛,行吗?”他说:“嗯哪。”嗯哪是什么意思?我愣住了。他走过来,把我往牛背上扶,我才明白。牛脊梁上的皮真滑,我上了几次都没上去。有一回我都爬到牛背上了,正高兴着,牛皮一抖,我又被摔下来了。他告诉我:“骑马前腿跘,骑牛屁股蛋。你得往后屁股上坐。”嘿,真灵!从此我会骑牛了。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任喜元。他告诉我,在农村,干一年农活,秋后分得的粮食还不够吃,一点现钱也看不到。只有争取参加套子队,才能挣得一点活钱。他家老人多年患病在床,无钱医治。他有一个孩子在襁褓之中。日子过得很艰难。
几天后,他们做好了那种长辕子、短雪橇式的牛马拉的爬犁之后,就开始上山运材。任喜元总是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收工。他说:“牛比马慢多了,我赶牛套就得早出晚归,争取多拉几趟,才能达到一般水平。”有一天傍晚,人家最后一趟套子都开始下山了,他还非要再上山拉一趟不可,我只好在楞场等着他。天太冷了,我身边生着一堆火,还是冻得直跳脚。天太黑了,那堆火发出的光太有限了,山林草木什么都看不见。偶尔听到风吹树梢发出的尖叫声,令人心颤。不是那堆火给我壮胆,我早就吓瘫了。因为我知道,凶猛的野兽都怕火,有火它们就不敢上前。我等啊等,提心吊胆的等,我真怕他在山上遇到什么野兽,对付不了。也担心他的爬犁坏了,收拾不好。我没有手表,估计到了子夜,才听见他赶牛的声音。我兴奋极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兴奋得抱住他亲了又亲。我这回算尝到了人等人的滋味。他那次拉了六根六米圆木,径级又很大,那么一头又小又瘦的牛,被又小又瘦的人赶着,真难为他们了。我迅速给他检尺,收起野帐,准备回家,他忽然喊住我:“记好了吗?是六根吗?”我真的烦了。“六根,差不了!”其实,计算木材材积不仅是看根数、材长,还要看径级。如果在径级上给他压尺,木材材积就会大打折扣。你非得看我记了几根有什么用,傻狍子一个!气得我一路上没有搭理他。因为你一人,我等了大半夜,不说一句感谢话,还怀疑我的验收水平。什么人!我回到工段,躺在铺上,睡不着。想来想去,觉得他也很不容易。那么晚,那么累,又有那么多的危险,当然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了。想到这儿,心情才平静下来,入睡了。
工段里有人下山,我托他捎个马蹄表。那马蹄表可漂亮了,双铃的,上发条的,我有些爱不释手了。但我还是送给了任喜元。为的是让他有个时间观念,别总是半夜出工或者半夜收工,不仅损害自己的身体,而且弄得我也没法休息。他接过马蹄表,表情很淡漠,以后也没有照我说的那样,看着时间上工,看着时间收工。我花掉半个月工钱给他买的马蹄表,打水漂了。不过,我听套子队的农民说,他把这个马蹄表当成了玩儿物,一有闲空就拿出来把玩,甚至还搂着它睡觉。
转过年三月,山里的雪已经有些发粘,东北农村也开始往大田里送肥了,于是,牛马套子下山了,人欢马叫了一个冬天,终于平静下来。我们忙了一冬,本来可以休息一下了,可是心里空落落的,大家都觉得人气还是旺一些好,工作还是忙一些好。
大约过了半年,我忽然接到一个邮包,上面写着“任喜元寄”,打开一看,是一块布料,趟子绒的,十五尺。包裹里没有留言,看来他是让我做一身趟子绒了。那时候没有化纤产品,人们做衣服只能用棉布,而棉布的加工技术还不过关,普通百姓谁身上没有几块补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喜欢趟子绒,因为它抗磨,禁黵,美面,大方。有个民谣中说:“老农进城,一身趟子绒。”那是他们的礼服!我想他买这十五尺趟子绒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买布需要布票,布票是按人头定量供应的。他得从自己身上节省下来,送给我。我想到这儿,觉得这不是一般的趟子绒,这是充满深情厚谊的宝啊!于是,我就把它包了又包,裹了又裹,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做个永久的纪念。
一晃,四十五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不知现在古鲁玛奈什么样了?我们工段撤点以后,那里便开始封山育林,逐步成了无人区。那里的树是不是又那么密那么粗了,那条河是不是还那么清澈那么甘甜,当年那些老友是不是还能记起当年的封尘往事,新的开发计划是不是已经实施。记得那时候我们爱唱“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么,四十五年就等于三十二万八千五百年啊,让考古学家去研究吧。
〔责任编辑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