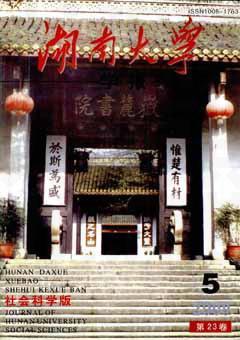时制,时态和情态条件触发的作格一分裂现象探讨
鲁 曼 陈 姻
[摘要]由时制,时态和情态(TAM)因素触发的作格一分裂系统在作格语言中倍受关注。其中影响参数理论,给物性参数理论以及视点角度和自然关注点理论极具代表性。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倾向于Delancey,认为在许多语言中主格和绝对格与动词的一致关系是一种“视点”的类别标志,即说话者描述事件的角度。作格一分裂系统中格标记的模式反映了最自然的视点与关注点之间的冲突。但同时指出,对作格一分裂现象的探讨不应排除语法因素。
[关键词]作格一分裂;影响参数;给物性参数;视点和关注点参数
[中图分类号]H0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5-0103-04
一引言
作格(Ergative case)是指一种语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给物动词的主语与给物动词的宾语具有相同的格标记,而与给物动词的主语不同。主格/宾格和作格/绝对格在作格语言之间交替使用。比如在一些澳大利亚语中,一种语言中既有宾格标记也有绝对格标记。这在语言学上被称为“分裂作格”(split—ergative)。根据Delancy,格标记分裂形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是:给物动词的主语标记为作格或者不标记:由句子的时制,时态和情态触发的分裂式模式;以及活动/状态分裂模式。在活动/状态分裂下,不给物动词的主语标记与给物动词的施动者或受动者相同。本文主要探讨由时制,时态和情态触发的分裂形式。也就是说,在作格语言中,完成体(有时候也涉及过去时态)引发作格的分配。而非完成体(现在时/将来时)则激活宾格的分配。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时态,时制,时态与情态对作格分裂的影响。相关的问题包括:时制,时态与情态(TAN)为什么会触发作格的分裂?作格分裂现象与此三种语法形式之间有什么关系?
二格标记理论
在处理作格语言中的作格一分裂(spilt—ergative)现象时,语言学家们众说纷纭。其中有效果参数,给物性参数以及视觉点和关注点参数分别从受动者受影响的角度,给物性传递的角度以及事件表征的角度(语法体)进行了分析。所有这些理论对于揭示TAM条件下和作格分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一)效果参数
一个事件被表征时,某些语义条件会引发动词一分裂(verb—split)和TAM一分裂(TAM—splh)现象。Tsunoda把这种现象叫作效果条件(Effect—Condition),主要关注的是二元谓词的事件/情景中施动者对宾语所产生的效果以及动作的实现等状况。当效果得到满足,作格语言中会出现作格一绝对格的格分布形式,而不管是否出现动词分裂或TAM分裂。但是当效果条件没有满足时,作格一绝对格的格分布形式就不会出现。这时会出现其他形式的格分布情形。效果条件包含许多密切相关但并不互相雷同的语义参数,例如:
(A)动作:状态
(B)对宾语产生影响:对宾语没有影响
(c)宾语实现预期的目的:宾语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
(D)宾语完全受影响:宾语部分受影响
(E)事件已完成:事件尚未完成,还在进行中
(F)即性的,短暂的:持续的
(G)有内在终点的:没有内在终点的
(H)有结果的:没有结果的
(I)具体的或单个的事件或状态:习惯性的/一般的/习俗性的事件或状态
(J)宾语是有定的/具体的所指:宾语是无定的/不具体的并且无所指
(K)现实的/被实现了的:可能的/没被实现的
(L)实现了的:未曾实现的
(M)肯定的:否定的
上述这些参数互相联系,显示动词分裂的等级性,这种等级取决于施动者对受动者所产生效果的程度。就格标记方面而言,动词类型等级呈现出一种给物性的阶梯形式:分别是作格和宾格的排列。比如,动词“打,打击”出现在左列,那么作格分配给施动者,宾格分配给受动者。对这些效果参数的仔细思考表明,将动词一分裂和作格一分裂相提并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具有其合理性,主要是因为这两种模式事实上都以句子的给物性为基础,而后者其实是句子的一种内在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者都是在解构施动者和受动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分析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在上述所列出来的条件中存在许多重复的现象(尽管Tsunoda强调说这些参数并不互相雷同),例如(G)和(I)之间涉及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我们的理由是,一个具体的或者说是单数形式的宾语通常会产生具有内在终结点的解读(telic),因此就没必要将(G)和(I)分别列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很难将施动者和受动者从感官动词和心理动词区分开来。比如,在句子John liked Mary(约翰喜欢玛丽)和John expected Mary to marry with him(约翰希望玛丽和他结婚)中,我们就很难从有效参数的角度来分辨这两个句子中的施动者和受动者角色,从而来确定是否给它们分配宾格或作格。
(二)给物性参数
Hopper and Thompson从语义出发,指出动词分裂和TAM条件下产生的作格一分裂存在一定的联系。“……给物性在传统上被解释为动作行为从施动者‘搬运或‘传输到受动者。”他们还指出,名词短语格标记的功能就是标记出施动者的施动角色,而表示受动者的名词短语的格标记功能则是将受动角色标记出来。主语有时标记为施动者,有时候标记为受动者是因为主语在某些方面与施动者相似,而其他方面与受动者相似。
Hopper and Thompson说,就象效果参数一样,给物性参数同样包括10个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涉及到效果参数的不同方面。这些参数的强弱不同而形成的阶层使得动作行为被从一个参入者传送到另一个事件参入者,这些参数共同作用以加强或减弱语句的给物性。比如,具有两个事件参入者的语句就比只有一个事件参入者的语句的给物性强,因为后者情况下不会有“传送”发生,除非整个事件涉及至少两个参入者。再比如。就受动者角度来说,一个受动者完全受到影响的语句,其给物性就比受动者只受到部分影响的语句的给物性低。
Hopper and Thompson还注意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完成体的句子比非完成体的句子给物性高,因为动作行为从施动者到受动者的传送已经完成。
根据Hopper and Thompson,动词语法体的差异在概念上与完全受影响的宾语和部分受影响的宾语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也就是,完成了的事件就是已经将动作行为完全传送到了受动者,而这对于非完成体或进行体来说,则并非如此。根据这个思想建立起来的参数等级就被用来解释作格语言中作格的分裂现象。表面上看来,Hopper and Thompson似乎
合理的解释了TAM条件触发的作格分裂。但是,我们认为Hopper and Thompson的分析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标记为主格的施动者与标记为作格的施动者之间存在施动性差异。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标记为宾格(accusative)的受动者又是怎样并且又是为什么与标记为绝对格(absolutive)的受动者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时都具有受动的特性。并且,人们对体的研究发现,完成体的性质并不一定表示动作的完成(实现了事件固有的终点),一个用完成体标记的事件可以是实现了终结点(completed),也可以是截止了的(terminated)。如果只是截止了的话,就不能保证该动作行为已完全传送到了受动者。再者,相对于有一些事件,我们无法根据他们的参数理论来区分施动和受动者。例如,John met Mary in the street在这个句子中我们根本无法将施动和受动者区分开来,自然也就无法去区分他们之间的给物性。
(三)视点角度和自然关注点
就给物性特征这一点来说,Delancy与上述理论(给物性参数)观点相同。他声称,一个作格结构就是一个给物性句子。在这个句子里语义上的施动者标记为特殊的格形式或是通过将其后置而标记出来。与上述不同的是Delancy提出,作格的分裂是基于两个心理概念:视点和自然关注点(Point 0f view and attention flow)。自然关注点指的是感官的策略,而视点是一种语言机制。句子里名词短语的顺序是自然关注点的反映。该顺序表明说话者希望听话者根据此自然关注点来关注话语。任何事件具有内在的自然关注点,对说话者来说它是指事件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展开。视点和自然关注点是基本的参数。它们决定事件中各参人实体的受关注程度。换句话说,语言结构再现人类认知结构(i.e线性顺序)。这些概念以语义为基础,在人类语言的语义结构中占重要的一部分。可以将它们看作是事件的原型。在实际的言语交流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原型事件都引起人们同样的兴趣,所有的语言都有各自的机制来标记话语中重要的事件或重要的实体。
就像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一个原型情景一样,事件也可以从许多可能的角度来考察或讲述。这些角度可以是一个对此事件没有什么兴趣的观察者的视点,也可以是从每个事件参入者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允许或要求说话者明确他/她对所表达事件的角度,并且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假设在所有的语言中存在语法和词汇的机制,以便说话者明确他/她所表达的视点。事件参入者作为话语的中心所在,而视点就是对事件参入者的关注,因此也就构成了自然视点(natural viewpoint)所在。
关注点的流动和自然视点有时偶然会重合,而在其他时候也可能不会。根据Delaneey,作格分裂模式是解决关注点的流动和自然视点二者之间冲突的办法。如果二者一致,所描述的就是一个自然的事件,而如果二者相互不一致,所描述的事件就不是一个按自然顺序展开的事件。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对事件参入者的格标记不一样。例句(1)和(2)可以说明这一点。
(1)nurra-φ bayi-φ yara-φ balga-n
you all-NOM M-ABS man-NOM hit—NFUT
(你们都打了那个人)
(2)nurra—na bagul yara—gu balga—n
you all—ACC M—ERGman—ERG hit-NFUT
(那个人打了你们大家)
在例句(1)里,关注点和视点巧合一致,因此事件中的两个名词短语都没有标记,也因此表示该情景是自然的描述。而与(1)不同,例句(2)里,两个参数并不一致,两个名称短语都有不同的格标记。这表明(2)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按正常顺序描述的。
根据这种理论,在TAM条件下触发的作格分裂,可以根据自然视点和关注点二者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在这个理论里格标记的倾向分别是主格一宾格系统出现在完成体或过去时句子当中。作格一绝对格出现在非完成体,进行体或非过去时里。给物性事件可以看作是行为动作从某个时候从施动者出发,经过一些时间后在受动者处终结。作格语言中体的分裂不允许体和视点分配之间存在冲突:完成体要求视点落在和终结点的时制一致的名词上,即受动者。体模式和作格分裂模式因此可以相提并论。二者当中,视点的确定都受限制;当限制阻止自然出发点被选为视点时,那么就必须用作格来标记视点。非过去时和非完成体与施动有关,因为事件还没有终结,动作行为的传递还在进行当中。因此在非过去时或非完成体中,自然视点与出发点一致,还在施动者上。在过去时或完成体里,事件已经结束,因此自然视点分配到了终结点,即受动者上。
三重新思考
从上述三种参数的讨论来看,在处理格标记的问题时。首先需要考虑名词格标记的目的。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需要进行格标记(case-marking)。根据Comrie,格标记不是用来标记语法关系,而是直接用来表明哪个成分是施动,哪个成分是受动。格主要是用来解构论元和谓词之间的关系,其主要的目的是表明“谁在对谁做什么”(Who did what to whom)这种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成分之间的格标记为什么会呈现如此大的差异(一共有五种类型的格标记以及我们讨论所涉及的格分裂系统)?而各种语言又是如何来处理事件中的种种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格分裂(case—split)只出现在作格语言中,而在其他语言中则没有类似的现象?格分裂的出现对该语言的语法系统有什么样的指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格分裂的研究就必然要涉及到相关语言的整个系统。结合这些思考我们认为对格分裂的研究有必要从语法和语义两个角度着手,这样才能真正揭示格分裂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已经提到的关于此问题的三种理论。毋庸容置疑,这三种参数(效果参数,给物性参数和视点以及关注点参数)的提出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各自解决的方案。其中效果参数和给物参数从动词的语义分析出发来进行探讨。他们的假设的基础是,给物性句子里施动者影响受动者(影响参数)或者说是将动作行为传送到受动者(给物参数)。在效果参数理论里,如果施动者成功地实现了对受动者的影响,那么它就无需格标记,因为这属于默认的机制。否则,它就会标记为主格或其他格形式。根据给物性参数理论,如果施动者成功地将动作行为传送给了受动者,那么前者为零标记。反之,则标记为主格或其他格形式。施动者对受动者完全产生了影响表示动作行为已从施动者成功地传送到了受动者。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影响参数和给物性参数实际是从相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分析——以语义分析为出发点。然而我们发现这种分析中,最大的问题是如
果我们承认这些是语言的共性的话,我们很难根据这两种参数来解释是否是受动者受更大的影响或更具有施动的特性只表现在作格语言中。并且,我们的分析还提到,当事件的谓词是心理动词或感官动词时,这两种参数理论就难以用给物性或影响性来区分施动者角色和受动者角色。比如在句子“张三喜欢李四”里我们就很难根据该两种理论来判定说张三和李四之间哪个名词更具有施动的角色,哪个名词又该是受动的角色,因为我们无法从施动者或受动者的角度来明确影响性或给物性。显然,由谓词“喜欢”所产生的影响从施动传送到受动者时根本不能与句子“张三打了李四”中由谓词“打”所产生的影响相提并论。
比较而言,我们认为视点和关注点参数更有解释力。虽然同样也强调语义分析的作用,Delancy基于认知的机制,将分析从语义扩展到语用,着重关注事件的视点如何被表征。根据他的理论,句子的内在属性就是将句子的信息——自然的时间和空间顺序表现出来。如果行为的描述视点是从施动者到受动者,那么零标记的施动者就是默认了的。而如果事件的描述视点是从终结点或者说是受动者出发,那么施动者就应该受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Delaneey实际上就是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事件中名称短语的标记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事件都具有其内在的特性。一个有内在终点的事件(telic),比如说John ace the apple(约翰吃了那个苹果),被描述为已经截止。但是我们知道截止并不表示事件已实现了它内在的终点(completed)。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句中我们无法确定究竟约翰有没有吃完那个苹果,我们只知道他实施了吃那个苹果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无法根据参数理论或给物性理论来确定施动或受动的关系[苹果被约翰吃过,宾语(受动者)无疑是遭受了影响的,同时吃的行为也已经传送到了苹果上]。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视点和关注点参数理论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它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在作格语言中一个给物动词会有一个更受影响的受动者或一个更具有施动角色的施动者。不管事件实现后的结果如何,该事件总要以一种或某种方式被里现。要么从施动者到受动者或者从受动者到施动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Delancey对作格语言里作格分裂现象的分析更全面也更深刻。
我们坚持Delaneey分析的另一个理由是,他所提出的视点和关注点这两个概念都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的。这两个概念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结构是人类认知/概念结构的映射(即时间或空间的顺序)。在作格语言里,体貌系统的分裂和事件视点的分裂被统一。同时,又根据事件参入者的实际关注点来确定视点。出发点表现了事件被实现,终结点指向事件的结果。在作格语言中,视点在事件出发点则表明事件的描述从出发开始,而如果描述从终结点开始,当事件一日被实现,官就会有一套格标记的机制来表示出施动者和受动在者。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说Delancey的分析毫无瑕疵。比如,关注点的分析就遇到效果参数和给物参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关注点这一现象只存在于作格语言中。如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整个人类语言的格标记系统的话,我们所讨论的视点和关注点参数就不能排除其他的语言。另一个问题是,他所讨论的格标记现象没有涉及到语法现象,我们已经看到格分裂只出现在作格语言中,这是否意味着它与这些语言的其他语法现象相互影响呢?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对格分裂现象的分析就不应该排除从语法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事实上语言学家如William,B.McGregor已经指出格标记不仅仅是用来标记施动者A和受动者P。
四结语
本文分别讨论了三种分析TAM条件触发的作格分裂理论。这些理论包括:效果参数、给物性参数以及视点和关注点参数。效果参数理论强调TAM触发的作格分裂与动词的分裂没有本质的不同,二者都与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语义和格标记机制有关。给物性参数关注的是动作行为从施动者到受动者的传送。视点和关注点参数则是从心理学和认知的角度,认为作格语言中作格的分裂与对事件描述的视点有关。如果描述的角度遵循自然的顺序,则施动者无须标记;如果对事件的描述从终结点开始,那么就会出现作格的分裂现象,则施动者在作格语言中标记为主格,受动者标记为宾格或其他格形式。我们的分析指出,视点和关注点参数更具有解释力,因为它的分析不仅涉及到语义,而且将心理学和认知学纳入讨论的范畴。最后我们还提出语法可能对格系统的分裂产生影响,后者不应该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