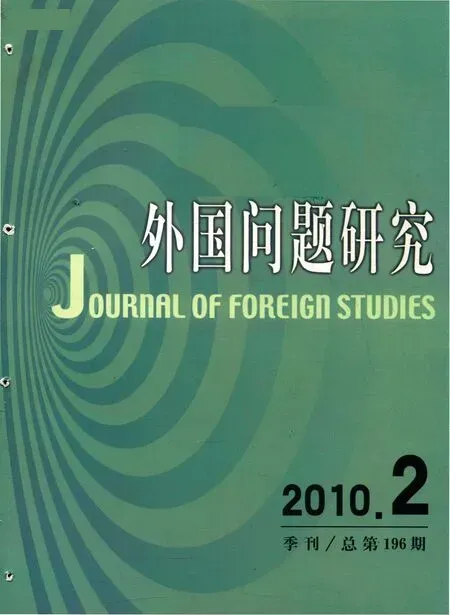《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的电影化努力
董奇昊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24)
一
村上龙曾这样认识自己的处女作《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当时《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被认为是极其丑陋的。麻药、乱交等成为话题,这种东西并不是文学等声音也不乏存在。可说其不是文学的批评是错误的。‘这种东西并不是日本近代文学’、就应当对其进行如此批评。既存在没有人物的内心描写等批评,苦恼、悔恨、悲哀都没有的批判也很多。我并没有写到现代人的不安,连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家族的牵绊、普遍的青春都没有写到。四半世纪前期,我不自觉地想要表现的是丧失感。70年代中期,我的母国日本完成了近代化,可取而代之的却失去了某些东西。那并不是日本固有的自古以来的文化,而是近代化达成的大目标。日本民族失去了目标。”[1]
“美国的绝对影响,波及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学问、大众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日本国依存于特定的外国,这种事在1945年以前是没有的。大陆文化对古代日本的影响虽然远为广泛,远为深刻,但中国方面并没有军事的、经济的压力。19世纪的‘开国’,确实是在军事的压力下进行的,但在其后的‘西方化’的过程中,作为样板的先进国没有集中于一国。其影响也没有及至大众的风俗习惯,在这点上也和战后三十年的状况大不相同。”[2]
二
《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作为小说,后现代主义倾向和因素、或者说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对电影艺术的诸多借鉴和整合,并且从中找到了小说文本的全新形态。
村上龙多才多艺,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位电影导演。高中尚未毕业,便开始尝试电影摄制,那一年他只有18岁。1977年,村上龙从武藏野美术大学休学,同时开始了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1979年,他把自己获芥川奖的小说《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改编成电影,并亲自担任导演。那以后在电影领域一发而不可收,从1979年至今源自村上龙作品的电影已有十多部公映。其中包括他在意大利电影节上获导演奖的《黄玉》。此间作为作家,他涉足电影的文字也大抵与创作保持着同步状态。1978年和1983年,村上龙分别有《亭午映像,夜半话语》和《别担心,我的朋友 》,以摄制日志的体裁问世。1992年出版的《黄玉的诱惑》,则是一本关于荧屏幕后的对话集。1995年又有《村上龙电影小说集》推出,作为《69》的续篇并且于次年获得了平林泰子文学奖。或许可以认为,村上龙对于小说和电影的执著,是很难分出伯仲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在小说创作中,把电影艺术的长处信手拈来,融汇期间,为自己的文本找到全新的叙事模式。
《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的文学电影化的努力,首先表现在以蒙太奇的手法、用画面的组合取代传统小说的框架结构,从而使小说叙事、情节发展的文字被大量削减,有效地张扬了画面的冲击力量和形象效果。作品全文计八章,第一章因此可以理解为第一个画面,亦即丽丽的家。第二章可以看做是丽丽的店。第三章可以分解成两个主要画面,一个是关于良山和阿开的;一个是奥斯卡家里与美国兵的聚会。第四章又回到了丽丽的家,这是一个聚会次日,日美青年群体混居的描写。内中还有聚会的场面作为倒叙蒙太奇继续出现。最后的一幅,是阿龙和丽丽的驾车兜风。第五章是横田基地、和警察出现在丽丽家的画面。第六章是日比谷的露天音乐厅,良山打警察的画面。第七章、也就是第七个画面的主要内容,是良山与阿开分手。第八章是作品的尾声,画面里的主人公是阿龙和丽丽。从画面的设置中也不难看出,作品主人公的阵容,除阿龙外还应该包括丽丽、良山和阿开。
每一章的大画面,又被分切成若干小画面,服务于人物出现、人物关系的冲突与发展、人物命运的起伏和归宿。这样,整部小说便在八个大画面和若干小画面的构架中,讲述了一个美军基地周围一群年轻人颓废的日常生活。除了作为作品情节和人物塑造所必需的交待画面,作为作品的整体图示,第三和第八画面又是重点。也就是说,全部画面是以聚会的性活动与男女主人公意识改变为核心而设置的。这样的读解,看上去与其说像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提纲,莫如说更像一部电影分镜头的脚本。村上龙的叙事艺术就这样出现在写作提纲和电影脚本有机结合的土壤中,作为叙事艺术它的面目与风格也必然是独特的。
在品味大小不同的画面时,人们仍然可以从小说语言中发现电影的近景、中景和远景的差异。第一章画面上“丽丽一边擦着滴在大腿上的桃汁,一边和我聊天,挂着拖鞋的脚背上,红色和青色的脉管清晰可见。在我的眼里总是很美的。”这段描写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镜头由近景推向特写的移动效果,否则便很难感受到女性脚背上脉管的“颜色”。“菠萝的切口发黑,已经完全腐烂了,成了一盘稀泥。”把腐烂的菠萝比喻成稀泥,这是文学表现的常用的手法。但是在腐烂的菠萝中发现“切口发黑”,显然也是只有特写才可能确认的存在。就像聚会的场景可以看到“红色的地毯上到处可以看到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内裤、烟蒂、烟灰、面包渣。西红柿的根蒂,还有各色体毛、染有血迹的纸,酒杯、酒瓶、葡萄皮、火柴、沾了灰的樱桃”一样,大都淆杂着村上龙的小说细节表现的电影化的质感,这种功力分明也是源自对后现代电影艺术的熟稔。仅就地毯上的体毛而言,生活之中一般是要借助放大镜才可以发现。
在描写聚会的男女杂交场面时,作品的处理是:“我望着房间里淫荡的扭动着身体的三个日本女人,一边喝薄荷酒,一边吃点心”。这里的我,分明就是“机位”;我的眼睛,不消说就是镜头。铃子笑眯眯地找餐巾纸擦脸时,沙布洛把她轻轻抱起来,像给小孩把尿一样叉开她的双腿。他用左手按住铃子的脖子,右手抓住她的脚腕,让她全身的重量压在自己的阳物上。铃子直喊痛,手拼命挥动,想要离开沙布洛,可是无济于事,铃子的脸渐渐发青了。沙布洛仰靠在沙发上,支撑着铃子的身体开始旋转。”这是全作遭到批评界否定的、最露骨的性画面,也是这部小说的色情效果之最。机位的移动迅速而不留痕迹,画面的切换层次清晰,俨然村上龙作为导演在现场拍片一样,就连作家本人也直接写到,当时的玲子发出的是像“恐怖电影”里的演员一样的尖叫。
在表现阿龙注射海洛因后的状态时,针对一个嗜毒不深的青年人,小说从身体反应和梦幻心理两个视角,同样借助电影手法,收获了仅凭小说心理叙事很难达到的艺术效果。“无论我怎么用力,也只能吸进一点点空气。而且还不是从嘴或鼻子吸进来的,好像是从胸口上的一个窟窿里漏进来的。我腰部发麻,不能动弹,心脏一阵阵绞痛,太阳穴的血管一蹦一蹦地直跳。闭上眼睛像是要掉进一个快速旋转的漩涡之中,可怕到了极点。全身有一种被人爱抚的感觉,像汉堡包上的溶化的奶酪。如同试管里的水和油,身体里冷却的部分和发热的部分泾渭分明地旋转着。燥热传导到了我的头部、喉咙、心脏和性器。”
阿龙吸毒后的幻觉,是电影的幻想蒙太奇的文字翻版:“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从大厦屋顶跳下的女人。她的脸因恐怖而扭曲,眼睛望着远处的天空,手脚像游泳似地不停地划动,挣扎着想回到屋顶。束着的头发在空中散开,像水藻似地在她头上漂着,放大了的街树、车辆和行人,被风刮得变了形的五官,这些情景就像在酷热的夏天做了一个噩梦,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楼顶上掉下来的女人的动作,简直就像黑白电影里的慢镜头。”
作品中强化画面的艺术效果的处理还有很多。第五章里那个基地的黑夜,当阿龙和丽丽看到探照灯巨大的橘黄色光柱将黑夜层层剥去时,作品描写道:“铁丝网突然变成了金色,射过来的灯光,与其说是光束更像是烧红了的铁条。光环迅速逼近那里,地面升起了水气,大地、绿草、跑道、都变得像烧化了的玻璃一样白晃晃的。”这个画面效果中,金色的铁丝网,烧红了铁条般的探照灯光,白晃晃的烧化了的玻璃的比喻,都源自电影的照明艺术和特殊的全景处理。它在小说描写中的出现,很有一点不重复别人的全新品味。
三
当然,《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对电影艺术的借鉴,除去带来了上述的小说艺术的新感觉之外,也必然面临小说与电影结合的一些难题。即如画面的简捷在大量削减文字的叙述内容的同时,也往往会伤及叙述的缜密与必要性,从而有时不得不把必要的叙述排挤到补充说明的地位,这无疑也便破坏了小说叙述的完整性与美学效果。作品的片段感和时隐时现的阅读障碍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便产生于这样的改变之中。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而言,这部完成于7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在阅读上明显存在着进入艰难的问题。如果不是一边阅读、一边停下脚步、去整理和思辨人物关系的复杂性,那么除了一幅幅画面的印象之外,面临的也许会是一种不尽人意的阅读享受。
即如作品第二章是参加和美国人的聚会之前,阿龙和他的群体的生活方式的一次集中描写。丽丽、阿开、和夫、莫卡、良山都在这一章先后登场,由于人物形象和彼此关系主要是通过动感很强的画面体现的。作为小说手段除了与场景相关的人物对话以外,其他因素介入过多无疑会妨碍作品风格的形成。然而,这样的艺术抉择,无疑对人物对话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有些内容甚至是仅仅依靠对话很难表现、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包括丽丽在内的这些人物的个性的模糊和雷同,因此成为很明显的弱点。在电影画面中,镜头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明“店”的性质,或酒吧、或聊吧,抑或是咖啡馆之类。而在小说叙述中,忽略了文学和电影艺术形式的区别,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店,经营这样的店之于经营者、之于这个群体的生存有着怎样的形象说明作用,无不入坠雾中。
作品的人物对话,也可以看出明显的电影化的影响痕迹。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第一,人物语言整体上的生活化要求。简单直白的口语体短句子,畅晓自然的倾诉方式,是阿龙和其他人物对话的共同特征。这也可以看做是小说的做法,但对电影而言却是一种硬性的框定。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的处理既在符合了人物身份的要求的同时,也模糊了不同人物之间语言表述的界限。人们有理由提出,这些来自日本各地,教养状态、学习经历和地域背景并不相同的年轻人之间,在寻找到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又很难在短时期内摆脱既有文化的惯性,然而仅凭对话方式很难看出这样的区别。“你和你爹也乱来吗?问你那,听见没有?”训斥阿开的这话,一听就是从警察口中说出的。“抓住这帮家伙!”,这样的讲话方式,可以清楚地断定从电车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喊的中年男人,肯定不是阿龙们的同类。“玲子,出卖色相就有钱买海洛因了,这是杰克逊告诉我的”;“我要存钱去印度,然后打工挣钱,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了”;“那个男人在一个早上,开车去了内华达的沙漠”。这是冲绳、良山和丽丽在三个不同场合的公式般的话语,就中除了共性、很难体味出个性化的区别。可见,人物对话的电影化倾向,处理不善也会成为小说艺术的一把双刃剑。
第二,人物动作的设计在电影创作中是一个宽泛的空间,可以找到诸多的表现途径;然而在小说中则被局限为单纯的语言描写,使用过多不免失衡、与小说情节的发展需要形成对峙。为了协调这种矛盾,作品中的对话虽然满足了生活化的要求,但同时因为要承担动作之外的叙事内容,并把它分散到不同的场合和人物身上,这样在整个作品中人物对话总量实际上不能不膨胀起来。之于对小说对话,这种情形的大量出现,由于并不是出于人物性格塑造、而是文本整体的要求,所以实际上不能不导致以己之矛、击己之盾的尴尬,使小说人物对话的诸多努力相互抵消,最终不免弥漫着一种平庸和泛泛之感。
《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中出现的音乐符号、色彩符号和食品符号,同样与电影手段不无关系。阿龙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美国军事基地极为抵触,小说以幻想蒙太奇的手法,把主人公想象中的城市装入一张照片里,渐入的镜头分层次地表现了这个都市的样态,大大地改变了小说叙事的传统模式:“那场面比电影还要盛大、精细,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这里。有瞎子、乞丐、佩戴金质奖章的将军和满身鲜血的士兵、还有食人的土著、男扮女装的黑人、女歌唱家、斗牛士以及在沙漠中祈祷的游牧民”。
类似作品第八章中的文学介质的描写,作品中也很容易看到。在以小说描写为主体的同时,同样通过以电影画面的处理方式,把镜头里的发现融入了纸笔上的表述:“地上掉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结成一团儿的头发,一定是莫卡的;有丽丽买的蛋糕的包装纸和面包渣。红色或黑色的指甲、花瓣、弄脏的卫生纸、易拉罐的拉环、女人的内裤、良子的凝固了的血块儿、袜子、折断的烟、杯子、沙拉酱的瓶子。”需要说及的是,在符号介入时,作家采取的往往并非是大众化的手段。作品开篇的:“我曾打死过一只在调色板上爬的蟑螂,流出的是鲜紫色的液体。当时调色盘里并没有紫色的颜料,我想大概是在它那小小的肚皮里把红色和蓝色混合成紫色的吧。”这样的写法,在活化了颜色的物质性的同时,也把美军飞机像蟑螂一样可恶的寓意,通过象征手法隐约地体现了出来。
四
无论是六、七十年代的“反安保”运动、还是发生在1968年的“全共斗”学潮,均给予了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一代以巨大的内心伤害。生存的失落感、茫然感和颓废感像瘟疫般在这一代人中恶性蔓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主人公们的放浪形骸,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说得更准确些,这部作品又是战后,美国与日本社会某种互动的文化现实,以及世界性的政治动荡所导致的文学影像。“从旧金山和约(1952年)至安保斗争为止,贯穿这一社会能量之中的巨大的思想源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3]。这种文化演进自然会牵及到村上龙及其一代人的美国情结。
[1][日]村上龙著.竺家荣译.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M].珠海出版社,1999:2.
[2][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叙说(下)[M].筑摩书房,2007:444.
[3][日]丸山真男.现代日本的革新思想(上卷)[M].岩波书店,20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