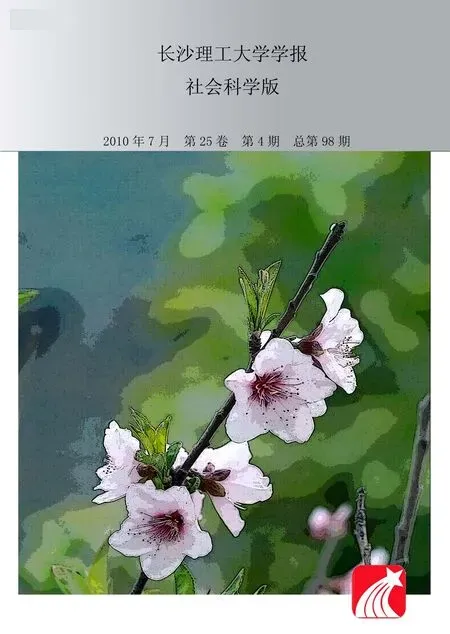“小平之虑”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钟武强
(1.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一、“小平之虑”:“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根据《邓小平年谱》提供的资料来看,邓小平同志在1990-1997年的晚年生活中关注国家稳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香港回归、抓住机遇发展生产力、浦东开发、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经营、共同富裕、金融、人才、中美关系、外交原则等一系列的问题,但关于社会财富分配、共同富裕则是他重中之重的少数几个主题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六次谈到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强调这是一个大问题,处理不好,要出乱子,强调要用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个原则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有相对差距的财富分配。1993年8月,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曾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1](P1362~1363)在他的心目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是他的“政治交待”了。1992年6月12日,在同江泽民同志的谈话中,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从而确定了党的十四大主题[1](P1347~1348)。由此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可称之为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改革交代”。在“政治交代”、“经济改革交代”之后,邓小平同志的眼光既着重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命题,更着重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怎么办的主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4)“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1](P1356~1357)。
关于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财富相对公平,“小平之虑”是小平同志当时跨越时空考虑的一个命题,这是一个大智慧的命题,这更是一个关系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生命题,是人民领袖之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者之虑。
分配问题之所以大得很,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则性问题。首先,就社会秩序层面说,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社会就不会稳定,就可能出现动乱层面。小平同志指出,不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穷人就可能起来“革命”,就会全方位影响和破坏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改革开放的初衷背道而驰。“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1](P1317)。“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1](P1312)。
其次,从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外表象征。“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1](P1312)。“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致富,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P1324)。正如马克思所说,“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十七、十八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十九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2](P175)。同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财产问题是劳动者阶层的切身问题,不是简单的“契约”或“交易”能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制度层面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正是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远见。
再次,分配问题是当代民生工作的关健。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有恒产才会有恒心,才会从内心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分化的现实已相当严峻,必须找到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才能解决因利益分配不公而产生的显性的特别是隐性的不和谐矛盾。“中国情况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1](P1312)。收入分配不仅仅是指资本所有者、特殊阶层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同时也包括不同行业之间劳动者的差异。“官方数字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三成五,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比印度还低一成多。勤劳者不富有,……多数民众感觉口袋中的钱不够用,原因包括工资涨速低于物价涨速,‘工资在爬、物价在飞’;社会分配不均,占职工8%的国企高管及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五成五,其余九成二职工收入只占四成五,使得大部分职工实际收入负增长。国民财富收入就像是个大蛋糕,普通百姓‘干多挣少’,是因为有人‘干少挣多’,分走了蛋糕的大部分”[3]。这些简单的“大数”背后,实实在在隐藏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
最后,分配是现代大生产体系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四环节之一,如果社会财富分配原则不遵循现代大生产体系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那么,遭受损害的不仅仅是劳动者阶层本身,同样,生产社会财富的现代生产力体系自身也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二、返本开新:重建劳本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体系
“小平之虑”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出了一道世纪题目,就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重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理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新回到一百四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去吸取营养和智慧。
马克思经常批评那些只在分配圈子之内打转转的人,仅仅从分配本身来谈分配,那根本不是解决工人阶级的地位和收入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必须站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互为一体的角度,同时突破交换、分配、消费的局限,站在生产领域的角度,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原理来分析现代大生产的价值创造过程,才能从根本上抓住如何分配社会财富的科学法则。这就要求大家必须回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重新建立以劳动者为本即劳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体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认为,“商品体”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体的“物的有用性”,“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价值则是商品体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商品体的二重性;商品体的价值量是由“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量又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构成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商品之间的交换实行等到价交换原则。马克思特别强调“商品中的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P47~100)。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历史性地发现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中,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称之为不变资本,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称之为可变资本。劳动力的价格是由“维持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所创造的价值是二个完全不同的量,在通常条件下,后者一定会大于前者,这其中的差额便是剩余价值。因此,“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2]。在以马克思劳动价值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中,人们清晰地发现,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资本则是能带来价值的价值。“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P243~244)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过程中,企业剩余是由全体劳动者所创造的。在承认这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尊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兼顾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但是必须突出劳动者集体利益原则。劳动者集体利益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经济法则。而这一法则是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劳动者集体利益至上的法则,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离开劳动价值论理论的这个根本,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将变成一堆空洞的、唯心的、自欺欺人的说教。这是被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历史清清楚楚“说明”而不用去“证明”的事实。要很好地解决“小平之虑”这一政治经济学难题,必须返本开新。“返本”,就是要返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去,“开新”,就是要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中 “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
三、共同富裕:从制度上确保劳动者集体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
马克思对雇佣工人、劳动人民充满着无限的关心,但他的这种关心是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雇佣工人和一切的劳动人民都发自内心爱戴马克思,也许他们没有读过《资本论》,但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能给他们带来具体的利益。对待劳动人民不仅仅是一个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劳动创造价值这一事实的科学态度问题。离开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永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在现代大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收入分配问题。顶多是等待国家的福利和资本所有者的开恩施与。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的基本原理,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别是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来看,企业的剩余价值不是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创造的,而是工人阶级集体创造的,是工人阶级养活了资本家,而不是相反: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个基本事实,至今没有改变。最重要的,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劳动者直接参加企业剩余的初次分配,是增加劳动者收入最重要的手段。离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国家的扶持政策,在一定的程度能缓解这一矛盾,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居民的需求,但从长期和整体来看,这一定会相当有限。因为,国家政策扶持所扩大的内需,是外在因素拉动的内需,可称之为外在内需,这是求人消费的“需求”,具有“泡沫性”,是有风险的需求。只有当劳动者的直接收入可持续提高后,自己的腰包能长久地鼓起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真实购买力,劳动者的真实自信、幸福感才可能自然流露,到那时,该消费的他会自然消费,也就用不着国家政策大力去号召了。只有那时的消费,才可称之为内在的内需了,“内需”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消费需求。“把所谓的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4]。所以,要从现实中彻底解决“小平之虑”这一难题,国家必须从制度上建立一套劳动者集体直接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经济法律制度和规范,具体落实“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这一前提。至于劳动者集体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直接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那是劳动者集体自组织内部的事情,关健的是国家要从法律的高度确立这一生产关系的权利并强制监督执行。在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分配方式的微观基础上,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到那时,和谐民生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1]冷溶,汪作玲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郜捷主编.内地民众何以“干多挣少”?[N].参考消息,2009-12-7(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