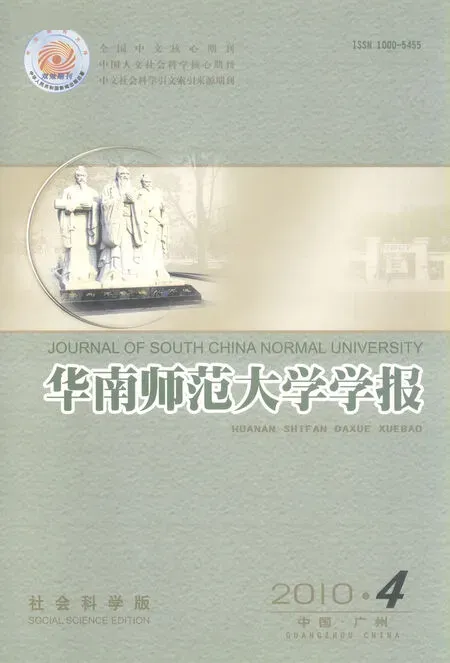交往教学的建构性——一种在教学过程中表征的价值
魏 薇,陈旭远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真正的理论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精华,真正的教育需要切合价值精华的理论。交往教学作为一种理想的教育形态,对于改善传统教育实践,促进我国当前教育理论与教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它重要,主要是因为它蕴涵了一定的重要的价值精华,而这些价值精华对于治疗传统教学的弊端、提升教学改革的理念都起到了积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建构性作为交往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蕴涵了丰富的力量和意义,尤其从教学过程层面看,交往教学的建构性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
一、交往教学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建构性的过程
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积极倡导交往的教学过程观以来,广大学者在“教学过程是一种交往的过程”、“教学过程的本质首先在于这是一个教师与学生相互作用的过程”[1]等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随着教学研究与实践的深入及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推进,交往教学的问题已越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教学研究和实践领域开始转向,将教学过程视为“师生交往”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教师把知识传递给学生的单向程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教育学者小威廉姆·E.多尔(W.E.Doll)认为:“作为教师我们不能,的确不能,直接传递信息;相反,当我们帮助他人在他们和我们的思维成果以及我们和其他人的思维成果之间进行协调之时,我们的教学行为才发生作用。这就是杜威为什么将教学视为交互作用的过程,而学习则是那一过程的产物。”[2]
交往教学作为一种富有生机的教学理论形态,其本质属性是互动交往的,而这种互动交往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交往教学是在建构性的实践活动中开展并实现的。因此,交往教学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建构性的过程。换言之,建构性是交往教学的一种重要价值精华,而其特性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得以实施和展现的。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怎样落实交往的教学理念?交往教学的建构性如何展开,如何在交往教学理论及其特殊的价值指导下改变当下教学行为,成为许多教育实践者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探究交往教学的一种建构性的价值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
与相关的教学理论尤其是与传统教学理念相比,交往教学的建构性在教学过程中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建构性作为交往教学理论必要的价值所在。
(一)建构的涵义: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与生成的实践特性
知识和意义的产生,社会交往能力和生命价值的表征都是在互动的交往中形成和重构的。在这一逻辑旨趣上,“知识”不能简单地移植,不能简单地“授—受”,而必须经历一个学习主体的自主构建的过程。对个体而言,建构知识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也是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意义也随之孕育而生。同时,建构性的教学过程重视学生对过程的参与、亲历,关注学生的经验背景和意义网络,注重情境的创设。[3]此时,交往教学的过程被看作与他人的交互作用实现的社会建构过程,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交往意义得以提升,这些都将渐臻教师和学生的生命价值的完满和幸福。
(二)建构的过程:教学过程是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的统一体
教学过程有很大一部分建构的意味。那么,建构性的价值视角就便于我们重新审视教学过程:教师的教授不再被看作仅仅是传递知识的流水式进程,教学的过程也不是学生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积极地参与。同样,学习也不仅仅只是对知识的被动接受,而是通过与先前经验和知识的联系建构有意义的知识(不只是零碎的客观事实)。课堂交往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输与接受的单向过程,而是师生、生生之间双向交流的互动的过程。
(三)建构的目的:通过知识,得到智慧
教学过程不再是只传授知识,交往也不是为了占有知识,而是懂得知识,最终通过知识得到智慧。这个过程使学生从无知到有知,在其中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批判精神,鼓励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辩证观。而且,知识的建构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学习者的广泛而丰富的知识背景会参与到这种相互作用中来,从知识的建构提升到意义建构的境界,从而使学生获得生命的体验、智慧的成长、人格的完善。
二、交往教学的建构性通过三个范畴表征其价值
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方法取决于我们自身拥有怎样的理论解释方法,即我们对于现象和价值的认识不是客观世界直接反映的结果,而是我们所拥有的解释世界的框架——“概念框架”(conceptual scheme)。这种立场也是古德曼(N.Goodman)在《世界制作的方法》中秉承的“世界是借助适当的概念框架而制作的一种虚构的产物”的基本立场。因此,从建构性出发来理解教学过程的“交往属性”,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通过什么“概念框架”从而更好地表征交往教学过程的价值。
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属性、机理与样态是任何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三维层面。建构性对于交往教学过程的价值也是遵循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建构性的哲学基础深深扎根于认识论的属性,这使得它能够冲破康德(I.Kant)的认识论的藩篱,以主客体、主客观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认识论为指导,对交往教学作以新的解释,建构新的设想;建构性的机制原理旨在强调事物通过交往、交互的协商过程,得以共享对象、事件和观念的意义,这也是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产生新思想的源流;建构性的样态最终体现在个体价值上,即自我主观的内部伦理意义,这也正是卡米伊(C.Kamii)、科布(P.Cobb)和亚克尔(E.Yackel)等社会心理学家期望的个体凭借自己的力量建构知识、判断适当与否(反省性思维)来发展起个体的“意义性”和“自律性”,而这与交往教学特有的认识系统的内在逻辑展开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哲学的层面上分析也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曾有学者提出哲学教育的三种类型:“作为思维训练的哲学教育”、“作为智慧探求的哲学教育”和“作为文化陶冶的哲学教育”。这三种类型分别对应着哲学的价值维度:即思维形式维、智慧内容维和社会历史维。[4]184这种观点很有意义,基本上所有哲学教育和哲学活动均是如此。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我们可以借鉴这种观点作为一种表征价值的“范畴框架”。
建构性对于交往教学过程的价值,正是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哲学的使命和教育实践的意义。因此,交往教学建构性的价值图景可以在教学过程的三个范畴上得以表征。第一范畴为反映认知过程的“认识价值”。这一范畴是以认识论层面的知识及其意义的生成为基础的,这说明,“认识价值”是建构性的价值的基础。第二范畴为反映社会交往、社会实践和社会交互能力价值过程的“社会价值”。社会交往意识和社会构建能力是教学过程中智慧生成的象征,也是交往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意识和主体结构必由路径。而第三范畴即实现自我内过程的“伦理价值”。在第三范畴上,学生主体得以自我建构,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得以彰显,在自我内过程的“伦理价值”层面上回归个体的精神自由、教育的终极旨向。
三、交往教学建构性的价值旨趣
一个世纪前,英国诗人艾略特(T.S.Elliot)关于智能与人生本质的一个疑问“在信息中,我们的知识哪里去了?在知识中,我们的智慧哪里去了?在生活中,我们的生命哪里去了”[5]71似乎引导着我们深入思考:建构性作为交往教学过程的重要价值精华,其基本的价值旨趣应该是面向认知、体现生活智慧和指引生命意义的。所以,我们依据认识价值范畴、社会价值范畴和伦理价值范畴“架构”了交往教学的价值图景。而深入地阐释上述三个范畴的价值旨趣,准确地理解其价值内涵才会更有意义地表征交往教学的建构性。
(一)认识价值范畴——知识意义的产生
认识价值范畴是表征价值的第一范畴。这一范畴是以认识论层面的知识及反映认知过程的意义生成为基础的。这说明,“认识价值”是建构性的价值基础。
1.知识教学观念的转变
知识的问题是认识论的首要问题。因此,交往教学过程中建构性的实现首先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建构”。它源于对传统认识论和知识观的反思和批判。这就涉及知识观及其知识教学观念转变的问题:从知识观的发展来看,大致经历了理性主义知识观、经验主义知识观、建构主义知识观和后现代主义知识观。通常意义上我们认为前两种知识观是传统知识观,而后两种是新型知识观。
传统知识观认为学习就是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所给予的知识。教师呈现知识,学生接受知识。而知识是客观的固定物,因此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呈现知识、接受知识和测量知识。知识成了学校教育的轴心。“知识本身成为目的,它控制了课程,同时也控制了教育,控制了人。……人和学校都成了围绕知识运转的机器,服膺知识的权威,由人引入的知识反倒成了学校生活和人生存的异化力量。”[6]建构主义知识观和后现代知识观吹响了解构传统知识观的号角,更为我们解读交往教学过程中建构性的价值打开了一扇窗户。建构主义知识观和后现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开放性、变革性、整合性及个体主观体验的重要性。与传统知识观相比,新型知识观视知识为动态发展的过程,从强调积累知识走向发现和创造知识,试图以此建立一种新的知识教学理念。这个理念承认和尊重人们的意见和价值观的多元性,不以权威的观点控制教学过程,试图在师生交往的各种观点、观念相互冲撞、融合的过程中寻求一致或理解。这种观念的转变鼓励学生的独立探索和创造,与旨在传递知识的传统教学观形成鲜明的对比。
基于上述的分析,知识观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对待知识的态度:是单纯地授受,消极地接受还是积极地理解它,甚至建构出更多的知识的意义。那么,从对待知识的态度上,也体现出师生交往的建构性的价值取向:仅仅单纯地传授知识和消极地接受,是传统的知识教学观念视野下的教学过程,它强调并关注的是准确、系统、确定地实施与传授,目的是简捷、高效的、系统地传授前人所创造的文明和文化,缩小个体认知经验与人类知识之间的差距,以确保知识和技能系统能被准确地掌握。相反,积极地理解知识,甚至建构出更多的知识的意义是当前知识观转变下截然不同的建构性的价值取向。建构性的意义就在于,把知识的教学看作是动态的、可生成的、可建构出意义的过程,而不是凝固化了的存在。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流动性的超越,所以这种建构性的价值超越就是要通过师生的交往,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移到知识意义的建构,通过师生与教学资源的互动,来对待知识,理解知识。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知识意义的产生,这是认识价值范畴的落脚点。
2.知识的意义产生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教学观念的转变对于教学本身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影响。而知识的意义问题是知识教学的核心问题,因此知识意义的产生是交往教学建构性价值旨趣的最主要表征形式。
我们说知识是有意义的,是主体对经验世界的建构,这是因为意义不是事物自身的本质属性,而是通过“建构”生成的。交往教学的价值追求要求知识必须对人有意义,那么,“知识的意义性实际上就是知识与人建立起的意义关系”[4]64。目前教师所持有的知识教学的观念,师生双方对于知识的理解、知识的考察及其知识的意义化的追问,这些本身都成为了交往教学建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知识意义的产生是交往教学在教学进程中的建构性的体现和表征。这也预示着教学交往关注的不只是学生对已有知识的学习,而且更加关注在交往中促进学生参与建构新知识和生成知识意义的过程。
在交往教学过程中,知识是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建构又是促进知识增长的重要方式,它可以提高知识获取过程的趣味性、动态性和应用性,从而促进知识的持久性。而知识的获得不能终止于知识的占有,而必须进一步提升到产生意义的层面才具有价值。也就是说,知识的获得不能停留于“掌握”上,必须上升到“意义的生成和构建”上。[7]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所谓知识意义的建构是指学生知识的获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受与记忆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内化与主动生成的过程。相应地就要求教师对于知识的理解和呈现要有自己的建构和加工。因此建构性的教学过程就是强调知识的能动性和学习者在获取知识过程中的自主建构的必要性,最终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意义建构。
知识意义的产生不是由知识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是一个情境与建构的产物,是知识与学习者相遇时,学习者个体精神世界与知识之间所产生的效果。只有学生与自己“相遇”的知识发生兴趣并积极主动地建构出个人意义时,知识才能产生意义,学生才能获得新的知识的意义并形成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巨大力量。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知识意义的获得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是人们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解释的主观建构过程。学生获得的新的知识意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忆的过程,而是一个把知识融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在这种知识的生成过程中,即个体在已有经验基础上建构新经验的过程中,学生借助中介(教学资源)系统与客体相互作用,把知识纳入自己的解释系统,形成他们自己对知识的看法与观点,从而实现知识意义的产生。
“建构性的”意义的表征意味着教学过程中师生主体对于知识和“存在的意义”的处理应该有自己的理解和呈现。一个学科、一本教材、多个学科的知识在与不同学生个体相遇的时候,学生所获得的知识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学习者不同,即使是相同的知识内容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性。因此,交往教学的建构性要求将静态的、客观的、普遍的、中立的知识的关注与对动态的、主观的、境域的、价值的知识的建构协调统一起来。在师生交往中教师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意义建构,更赋予“意义”“建构性”向度,这才是交往教学建构性的认识价值的真正过程。
(二)社会价值范畴——社会交往和社会建构
交往教学的建构性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实现对知识的意义建构的过程,更被看作是一个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作用实现的社会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价值在于反映社会交往、社会实践和社会交互能力。因此,“社会价值”范畴把教学看作是一个社会建构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促进学习者的主体精神和自主意识。
1.教学是一个社会交往和社会建构的过程
我们认为,在“社会价值”范畴里,教学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建构和社会交往的过程,即教学是一个通过与他人和自己的交互作用而实现的社会建构的过程。在这个价值范畴里,学习者的学习和活动经验,不仅是一个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建构过程,更是学生主体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双向建构过程。这实质上指出,建构性的“社会价值”范畴认为个体应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各类工具和符号中介,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与社会的协商,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经验并获得知识。
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指出,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和知识。[8]其主旨是:(1)个体与社会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2)意识来源于社会的建构;(3)学习与发展是有意义的社会协商;(4)文化和社会情境在儿童的认识和发展中起巨大作用。[9]受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辐射,关注交往教学的建构性就潜在地将由师生们所构成的群体视为一个小型社会,默认了教学是一个社会交往、社会协商和社会建构的过程。在这个“社会”中的微观和宏观背景与个体自我、信仰和认知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知识、经验、意义、交往能力的获得都是在这种社会范围和社会环境里建构的,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同时强调,知识、经验、意义、交往能力等为不可分离的、循环发生的、彼此促进的、统一的社会过程。
2.主体精神和自主意识通过社会交往得以完善
交往教学的建构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哲学思想催生发展的,它在认识论上否认客观主义,主张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强调主体间性和主客体间的互动。社会交往意识和社会构建能力是交往教学过程中智慧生成的象征,也是交往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意识和主体结构的必由路径。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人境交互决定论”认为,“人和环境并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它们都仅仅是一种潜在的性能。环境的潜能只有在特定的行为使之现实化之后才能起作用。同样地,人的潜能在未被激发之前,也并不发生作用。”“在社会交往中,一个成员的行为会激起另一成员的特定的反应,反过来,这种特定的反应又促进了交互的对应反应,从而共同形成社会环境。”[10]因此,学习者的潜能只有在特定环境中才得以激发,其主体精神的发挥和自主意识的现实化是与其环境的不断地交互作用的结果。学习者也通过社会交往和社会构建赋予自己和他者共享精神、智慧、知识和意义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学习者”的内涵得以延伸,即“社会性的学习者”,指学生的知识和理解是社会建构的,发生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知识和理解是高度社会性的,我们不只是个人化地建构,而是在与别人的对话和交流中进行建构的。[5]65
我们往往也发现,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中,尤其是社会交往层面,学习者才能大胆地将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而且在深入地社会建构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也只有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学习者更愿意发现与比较自己和他人的差异性,更容易摆脱权威,形成辩证性思维惯式,进而学会互相协商、相互协作。这一过程也很好地培养了学习者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交往教学要顺利地进行,就要求各主体具备一定的交流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指要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学会去倾听他人的观点和立场。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学习者还要深入感受“表现自我”“尊重他人”,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是在封闭的自我中生成的,它是在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和交往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当教学渐变为一个社会交往、协商和建构的过程,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三)伦理价值范畴——学生主体的自我构建
交往教学的价值表征在第三范畴即实现自我内过程的“伦理价值”。这一范畴的价值是一种指向学生主体得以自我建构、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得以彰显的可持续性发展过程。在学生自我内过程的“伦理价值”层面上回归个体的精神自由、教育的终极旨向。
1.学生主体的自我构建的必要性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自我生存过程中要冲破三重阻力:人在本质上有不可改变性 ;同时由于人的先天不足,又具有内在可塑性;人是独立的自我存在。与这三者对应存在三种教育方法 :(1)训练;(2)自我教育和纪律,即一种相对开放的教育;(3)存在交往。而他认为教育的最好的方法是第三种方法,“因为训练使心灵隔离,教育使精神契合、文化得以传承,而存在的交往则能使人了解他人和历史,理解自己和现实,使人类的历史文化得以延续”[11]。因此,要实现学生主体自我内过程的建构就要重视交往教学价值中的内在超越。就教育的建构,鲁洁教授提出教育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这说明,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主体的自我建构、自我发展的过程,是以‘理想自我’为目的的主体性实践过程,是主体的自我超越过程。”[12]需要说明的是,教育虽然存在一种外部施加影响的过程,但是其主题却应是促进、改善受教育者主体自我建构、自我改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作为教育学细胞的教学过程其本质也不在于认识而在内在心智结构的建构。[13]交往教学的建构性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主体的自我建构和自我发展的内过程。
其中,自我价值实现的建构性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师生互动中,教师以信息变换的方式经过改造而作用于主观世界,学生通过主体的活动将之纳入自身的心智结构而获得发展。例如,师生的对话并不总是预先设定的,它在进行过程中不断地变化和被构建。在对话互动中,教师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而且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素质和修养的提高,学生也不仅仅获得知识,而且也以个体的认知、情感等个性特征影响他人。交往主体总是根据自己交往的需要和对话对象的反应来采取对话行为,通过相互质疑不仅可以确定对话的主题,而且使对话不断深入,不断拓展,通过相互讨论增强双方的相互理解,实现知识的共生共建。这里的“对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启发、相互联结、相互反馈、相互调适、相互评价的过程,是一种交互作用的互动过程。
另一方面,学生是一个不断能动发展的生命体,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创造者,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学习者。学生主体通过自我意识将自己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并不断发展这种存在于自我之中的主客体相互关系,在内在相互的改造活动中,主观能动地建构新的主观世界。这就意味着在互动与生成中学生“投入理解”和融合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不是以理性推理和实验的方式进入,而是带着个体的经验、批判的眼光和主观情感展开理解和沟通,以期达到超越事实材料、拓展自己的视界。[14]所以说,“学习是学生的自我调节,是学生通过自己的反思和抽象建立概念结构”[15]。学生的认知过程是自我建构的实践过程,在参与、体验的过程中获得个人的完整性。
2.内在超越——关注人的生命意义,精神自由
交往教学的建构性的伦理价值最重要指涉的是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意义的关切,它呼吁教育关心人的自我生存,关心人生存的精神自由,实现教育由外在目的性向自身意义世界的回归。
学生主体的自我构建是自我内过程的教育价值反思,通过对当下教学和主客体问题的审视和反思,从而倡导交往教学的生命和精神伦理范畴的价值向度。在传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像搬运工一样输出和传递知识,学生相应地线性地被动接受知识。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无从体验到知识的快乐和幸福,更感受不到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要知道生命的本色不仅应是全面的、和谐的,而且是自主的、自由的。而禁锢心灵和精神自由的知识原本是源于自由心灵的积极探索,是保证学生个体精神自由的中介。因此,交往教学的伦理价值范畴试图通过对教学过程的重新定位而使教育、教学、学习主体回归个体精神自由,在交往为旨趣的教学过程中促成学生获得精神愉悦和生命健康成长的精神自由家园,在这个创造生命意义的过程中找回原本属于人的内在超越本质——自我建构和自我提升。
交往教学的“建构性”是渗透着人们的主观意趣的建构,是以主体间理解和意义建构为目的的。师生在教学过程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和生成中,完成着学生的自我建构和自主发展。这时的师生之间是一种“参与—合作”的关系。这样的交往是一种指向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交往,它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加深对世界的理解,也更能加深交往双方的理解,最终达成自我潜能的实现。
交往教学的建构性不仅是社会价值、社会过程的意义和使命,更是社会文化、心理过程的意义和使命,也是个体的内在价值的意义和使命。作为一种价值精华的交往教学的建构性不但发挥着师生双方的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激活教师的教育实践智慧,催化学生经验的改造,而且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建构性的交往教学本质上是一个互动协商、动态开放的、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创造与发现、意义与思想共享的情境,更是一个指向学生真正生命意义上发展的教育旨趣。
[1]朱佩荣.季亚琴科论教学的本质:上.外国教育资料,1993(5).
[2]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57.
[3]肖川.“建构知识”之意含.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
[4]郭晓明.课程知识与个体精神自由.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辛自强.知识建构研究:从主义到实证.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6]周燕.从知识的外在意义到知识的内在意义——知识观转型对教育的影响.全球教育展望,2005(4).
[7]郭晓明.知识意义的获得性与知识意义的新标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6).
[8]钟启泉,高文,赵中建.多维视角下的教育理论与思潮.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6.
[9]王文静.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01(10).
[10]张锦堂.互动式教学模式及其实施策略.上海教育,1996(5).
[11]雅思贝尔思.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24.
[12]张应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310.
[13]鲁洁.教育: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教育研究,1998(9).
[14]胡芳.知识观转型与课程改革.课程·教材·教法,2003(5).
[15]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高文,徐斌艳,程可拉,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