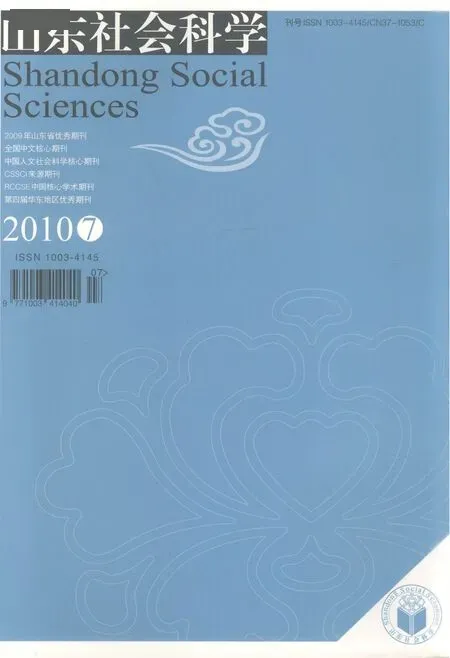非遗保护与利用的动态博弈*
党红星 公学国
(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山东济南 250002)
非遗保护与利用的动态博弈*
党红星 公学国
(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山东济南 2500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化的追求,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的始终。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化追求的过程,也是与背离本真的认识和行为即失真进行斗争的过程。失真与本真斗争的焦点集中于传承人、文化空间以及传承人与文化空间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传承人及文化空间,这在理论上已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上却常常出现背离本真的认识与行为。含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中主要表现为文化空间的本真传承与文化空间破坏或断层之间的搏弈。原生态民俗艺术,主要表现为传承人对传承艺术的本真化坚守,与损伤艺术品质的失真化演出之间的搏弈。这些搏弈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阶段性搏弈,解决这些搏弈,一靠研究,二靠寻求积极有效的方法。每一个阶段性搏弈的解决,意味着另一个阶段性失真与本真较量的开始,每一次解决都是一次对失真的舍弃修正和对本真的更加深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失真;搏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国家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是民族传承的文化基因和密码,是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更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根本性标志。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质、保护目的的认识似乎越来越清晰,这些实质和目的最后都应归结为本真性的保护,这是当前学界关注和实践利用的终极目的。如果割裂的、碎片化的、商业化的、自身基因谱系损伤甚至断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代、下下代的话,将是人类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灾难和悲剧,这不仅不是一种本真性的保护和传承,而是一种严重失真的传承和传承上的失真。对于“失真”,我们可将其理解为背离本真的认识和做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时间链条上,本真与失真不会和谐的共存在一起,而是始终处于一种较量和搏弈的动态之中。较量和搏弈的结果,必然是积极寻求有效的方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使之更趋向本真。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本真与失真双方力量的较量,大致缘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之初。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的认识,就是一种浅薄的模糊的片面的失真的认识,如果计算再精确一点的话,这种失真性的认识实际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出生前就已孕育,这可以从 1972年通过的仅仅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遗产公约》文件中得到充分印证:“在当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尚未正式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尚未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文件的视野。”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4页、第7-8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提出的,是作为“充实和补充《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于非物质文化形态的文化遗产保护的遗漏的”②王文章:《非物质文 化遗产概论 》,文化艺 术出版社 2006年 版,第4页、第7-8页。角色而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婴儿期”也是屡遭不幸,频频受到失真的不公正待遇。“在中文中,则先后使用过‘非物质遗产’、‘无形文化遗产’、‘口传与非物质遗产’、‘口述与无形遗产’、‘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词语表述形式”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9页、第9页。,这些表述形式让学界和社会层面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没有物质表现形式,不需要物质的载体加以呈现之类的联想。”②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9页、第9页。这些表述形式和脱离本真性的认识一度在学界产生了层层涟漪,众多学者就此纷纷展开讨论和研究。讨论的焦点集中于无形与有形、有形与非物质、非物质与载体等若干方面,讨论的结果也逐渐向本真性靠拢,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载体是人的观点逐渐从众多失真的认识中分离出来。这一本真结论趋向一致的意义非常重大,使得众学者不再纠缠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使得理论和实践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核心的认识得到了统一。这一认识,在实践层面还得到了具体的展现。如目前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地分级管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评定和保护,以及社会层面开展的“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民间文化十大守望者”等等,就是极好的佐证。这一本真性结论,使得另一个本真性认识也开始明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人,人是社会的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作为“具有很高知识水平、掌握实施或创造非物质遗产某一方面所必需技能的”③卫才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传承人,不会也绝无可能脱离文化空间而独立于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特定时空环境中产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定时空环境中的精英和佼佼者。随着文化空间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文化空间的本真性认识更加深入。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活动都有传承人,类似于河北任丘妇女七月七日焚烧天棚地棚的民间祭祀信仰活动,类似于胡集书会或周期性举办的庙会等民间集会活动,谁也不敢说张三还是李四或是王五就是这些民间活动的集大成者。这些活动的传承是一种集体化的传承,是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传承。由此我们非常庆幸,经过多次较量,对文化空间的本真认识更加清晰,文化空间是传承人孕育的土壤,传承人赖以文化空间而存在,文化空间可单独传承也可携传承人共同传承。我们都希望理论的认识与实践的做法一致起来,但往往事与愿违。传承人尤其是文化空间的本真认识,理论上达到了一定高度,但现实却常常是跌入失真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或陷入失真与本真互相纠结彼此消长的白热化对抗中,其对抗的焦点还是集中于传承人、文化空间以及传承人与文化空间三个方面。
二
实践上的失真表现在若干层面,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的割裂、文化空间的破坏或断裂就是典型的失真。以新农村建设为例,当下新农村建设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流。无可厚非,新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决策。但新农村建设绝不仅仅是经济的、产业的、职业的、技术的、信息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文化观念上的、文化保护上的、文化传承上的建设和再构。尤其是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乡土文化,将之放置于新农村建设的何种地位,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抛弃要么有条件有限度的继承。可惜的是,很多地方政府选择了前者。“每个村落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库,储藏着极其丰富的非物质的精神文化遗产”,④冯骥才:《保护古村落是当前文化抢救中的重中之重》,《本期策划》2009年第11期。尤其是古村落更是以“曾经负载或内涵的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深植于中国农耕文明土壤的儒教式‘耕读’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理念、天人和谐的人居空间与文化景观、恬淡而平和的民居乡情和生活态度、与风水美学密切相关的田园环境和乡村生活形态等”,⑤周星:《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成为解读中国人文化传承基因的巨大储存库。因此,学界主流纷纷呼吁和主张先保护后利用,并且在保护基础上必须是有条件的利用。学界的共识目前业已成为官方、社会、民众的共性认识。反观现实却并非如此,本真的认识在很多情况下面对实践上的失真是很无奈的。换言之,官方、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本真认识虽然基本达成了一致,却撼动不了实践上种种背离本真行为的频频出现和发生。一座座含有大量“建筑形式、相关的民情风俗以及村民行为生活方式”⑥崔婷:《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今日评论》2009年第11期。的古村落,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显得是何等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推土机和拖拉机在数日或数十日内就可将一座几百年的古村落消灭殆尽,笔者在山东平阴孝直镇孔庄古村调研时对这一幕深有感触。这种彻底的完全的毁灭式的利用方式,犹如大树连根拔起。意味着乡土中的民歌、诗歌、故事、饮食、服装、民风民俗、戏曲戏剧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诞生和发展的土壤再也不复存在,再也不能复原和逆转。一座座储存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古村落的倒下,意味着乡土生活中最活跃最具吸引力最有传承能力的文化空间的彻底抹去,更意味着后世子孙再也无法回首和瞻仰前世的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他们只能凭借着有限的文字资料去想象和猜测。经过空前的失真化的毁村运动,前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即使再丰富也难以传至后世,缺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和源泉的后世,文化上的真空和文化上的苍白将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怨恨并痛骂蒙羞于地下的我们也极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政府对于含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古村落的抹杀,可能是迫于土地整理政策的压力,也可能是迫于实现民生目标的压力。调研中发现民众对于从祖上传下来的古村落的推到,绝大多数人居然是弹冠相庆,乔迁楼房搬迁新居、获得数量不等的补偿款是古村落居民拍手称赞的主要原因。在实践当中,将古村落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抛之于脑后等等失真的认识,官方和民众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更可怕的是,民众背离保护古村落本真性的做法,有时候更甚于官方。发家致富是所有村民的愿望和目标,而村民一旦“发”起来,即使政府还未对古村落加以拆除,村民也往往会先于政府进行自我拆除或部分改装,或干脆弃之不顾,目前不少的古村落出现的空巢化即缘于此。弃之不顾导致的家庭空巢化,实际是一种房屋个体和文化个体的慢性自杀。这种慢性自杀的个体,随着致富家庭的逐渐增多定会逐渐蔓延,蔓延的结果是骇人的,僵死的与缺少人气的古村落必将成为非物质文化及文化空间的坟场。政府对于古村落的拆除还有些无奈的成分,从这一点来看,政府还不十分情愿背离保护好古村落的本真性。相对于政府而言,古村落村民对于自家房屋的拆除和放弃,却没有半点无奈的成分,他们是心甘情愿的义无返顾的和热情高涨的。我们必须明确,村民对于光线明亮卫生舒适的楼房的本真性追求没有错。但是,在追求幸福的本真目标时,以牺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价、以抹杀文化空间为标志的失真做法,却是极不明智和愚蠢的行为。对于这一点,常常令我们无比的心痛和深深的忧虑。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纯粹的“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是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核心是传承人的认识,虽然在理论上已是学界、政界、社会乃至民众的共识,现实中对传承人保护传承的种种做法却往往表现出在失真的旋涡里回旋,导致种种背离本真的认识和行为不断出现。实践中种种背离本真的认识和利用,又会折射到传承人保护传承的本真性认识当中去,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究竟如何保护?是封存起来原封不动的保护传承下去?还是有条件的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延续下去?实践中失真与本真的较量,将会进一步澄清和深化原初的本真性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必须要保护传承下去,但在保护传承的具体方法上、在保护利用的程度上、在保护利用方式上常常出现失真与本真的不断纠结,成为失真与本真较量的焦点。不少学者经常羡慕而且肯定韩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定位和传承利用方式:“那些被韩国指定为国家级文化财的表演者,他们随时随地的都会被搬上‘舞台’,每天都要忙着去不同的演出场地赶场,韩国农乐乐团的演出经常是一场接一场。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有者们的精彩表演常常吸引无数的国内外观光客,促进了韩国旅游业的发展。”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258页、第257页。羡慕是有充分理由的,说明我国还没有很好的摆正“国家级文化财的表演者”的位置,至少与当前众多影视歌三栖明星、歌坛大腕相比是这样。韩国将“文化财的表演者”抬高到明星大腕的地位,主要得益于政府和媒体的广泛宣传,如在韩国“各类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保有者在电视上露面,这些人都有一个出场的价目表。”②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第258页、第257页。在我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的漠视,与对歌坛乐坛明星不分好坏、死缠烂打的宣传和追踪报道,导致众多企业的广告资本迅速而持久的流向娱乐明星。媒体的导向在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计都难以维持,何谈传承与保护?由此看来将文化财的表演者等同甚至超过当前娱乐明星进行定位和宣传,频频走穴并在媒体面前频频曝光,不失为一种本真的做法和认识。果真如此,众多学者又会产生新的担忧“当表演者经过多次的远离乡野,他们的内心肯定会发生变化,而其原本保持的原生性艺术是否因此保持最初的艺术魅力就大打折扣了。任何艺术家,一旦离开风俗文化的航道,离开了社会生活,正如离开了水土阳光的草木一样令人不可思议。远离乡野的具体产生背景,艺术的商业化表演方式必然会损伤原生态艺术的品质和魅力。”③马致遥:《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民间艺术的表演离不开民俗生活,离不开民众的精神,一旦离开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一旦离开,那些“原本只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场合下,按传统内容和方式才能举行”④周冰琦、程励:《“藏彝走廊”民族音乐遗产及其保护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的众多民族歌舞,就成了随时可以展演的廉价商品。民间艺术离开文化空间脱离民众生活会枯萎,民间艺术没有经济支持和经济基础同样也会走向衰落、变异、萎缩甚至消失,如当前国粹京剧的振兴需要资本,不少民间工艺因处于濒危境地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需要经济,传承人因维业艰辛收入微薄或负收入找不到弟子,甚至自家子女也强烈反对子承父业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讲,民间艺术和民间艺术表演者的知名度与传承力度,与舞台化的演出和演出的经济收入多数情况下是成正比的,当下代表性的例证就是二人转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本山。民间艺术的传承,传承的是艺术的原生态。艺术原生态只有在活态化的民俗生活中,才能不损伤艺术的品质和魅力。民间艺术的传承,没有经济是不行的,传承人经济上的收入和收入的逐渐增加,民间艺术的传承费用和传承弟子的培养,更多情况下更须依靠超出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合下的演出,而易地演出、远离文化空间的演出、频繁的走穴式的演出,或本地舞台化的演出,或在本地将原生态民间艺术打包压缩式的演出,都会成为肢解民俗艺术的演出,都会成为功利化、商业化、庸俗化的演出。在此,原生态民俗艺术的本真化要求,与失去传统文化特性的失真化的演出,传承人窘迫经济条件下传承技艺本真化的艰难坚守,与为了赚取噱头和利润大大损伤艺术品质的失真化演出,现实中又相互缠杂纠结在一起。
四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永恒的,只要人类不灭绝。古村落文化空间的抹杀与传承,传承人传承技艺品质的坚守与丧失之间的搏弈,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阶段上的搏弈。面对这一阶段上失真与本真之间的搏弈,我们不能充当看客的身份。相反,我们是研究这些搏弈的研究者,更是终止一个个阶段性搏弈的救世主。新农村建设中,对古村落及古村落文化空间的保护应掌握好“度”。既不能“因过去的贫穷,便否定古村落文化的价值,平旧地起新村……割裂现实的发展与历史的联系,走向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歧路。”①崔婷:《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今日评论》2009年第11期。也不能“忽略古村落村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和新农村建设福祉的权利,”②崔婷:《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今日评论》2009年第11期。对古村落一味的“保持现状、机械维持旧有生存模式”③崔婷:《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今日评论》2009年第11期。。我国大致有 55万个古村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保留下来,应该在“文博工作人员指导下,选择有代表性的建筑或古村落妥善保存下来,维护古村落个性化的风貌和气质”④崔婷:《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今日评论》2009年第11期。。保护利用措施十分明确,应将最具代表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的古村落保留下来,让那些真正含有中华民族传承基因的古村落保留下来。对于拥有民间技艺和民间艺术的传承人的保护和利用,应用“标准”进行衡量和把握:一看传承人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是否得到完好的传承,二看传承人坚守本真技艺的程度。不离本土,在传承人生活的民俗文化土壤上,无论怎样演出,无论怎样利用,都不应成为传承人舍弃或改易原生态艺术的理由。远离本土,无论多少次演出,演出的利润有多丰厚,都应以艺术的坚持为演出的本真性追求和目标。无论多少次演出,展现给观众的都是最原初的最本真的艺术,绝不能让艺术魅力打任何折扣。非物质文化遗产失真与本真搏弈的终止权掌握在我们手中,而每一次终止,都是一次升华,都是一次对失真的舍弃修正和对本真的更加深化。每一次终止,又都是一个阶段性搏弈的终止和另一个阶段性失真与本真较量的开始,如将那些真正含有中华民族传承基因的古村落保留下来,将最具代表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的古村落保留下来,这里所说的最具代表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的古村落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又如对传承人民间艺术品质坚守程度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及实践上的做法,又必将导致新一轮失真和本真的搏弈。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就再也不会担心是否留住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和文化记忆,再也不会担心民族文化精髓和文化记忆能否传至下代、下下代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红星)
G05
A
1003—4145[2010]07—0040—04
2010-05-30
党红星,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公学国,济南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