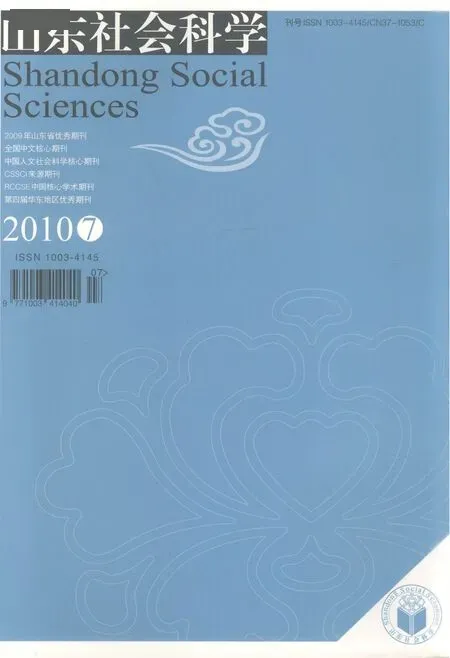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
夏泽祥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
夏泽祥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一文将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归纳为“求诸传统的认定方法”、“‘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和“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三种,这一归纳是不全面的,而且存在着混淆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的嫌疑。美国学者提出的原旨主义方法、文本主义方法、建构性的方法、推定的方法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标准和评价标准,可以视为对该文的补正。
未列举权利;认定方法;判断标准
2007年第9期《法学》发表了屠振宇博士的《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一文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该文结合美、德等国的实践,将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归纳为“求诸传统的认定方法”、“‘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和“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①参见屠振宇:《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法学》2007年第9期。该文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两点不足:(1)对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的归纳是不全面的,在以上三种方法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方法;(2)存在着将“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混为一谈的嫌疑。为深化对未列举权利保障制度的研究,现将美国学者围绕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 (以下简称第九修正案)的适用而提出的认定未列举权利的四种方法作一简要述评,同时把中、美两国学者在未列举权利的判断标准问题上的看法作一归纳,供学界和实务部门同仁参考。
一、原旨主义方法
这种方法意在探求制宪者们对于第九修正案文本的理解,进而弄清一项具体的未列举权利究竟是什么。由于制宪者们对于某些未列举权利的描述是相当具体和明确的,Randy E.Barnett认为,要弄清未列举权利究竟是什么,必须查阅“批准会议”期间有关州送交国会的宪法修正案草案目录,此外,还须查阅制宪者们关于自然权利的理论著述。②SeeRandy E·Barnett,Introduction:JamesMadison’sNinth Amendment,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35—36(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原旨主义方法是认定未列举权利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是,法官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也会遇到某些困难:(1)所谓的“制宪者意图”究竟是什么?在美国宪法 (草案)和“权利法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不管是起草者、赞同者还是批评者——都应当被视为制宪者。但是,只有少数人对于宪法的理解形诸文字而流传下来了,其他人对于宪法的理解是可以被忽略的吗?将少数人的意图当作制宪者意图是合理的吗?(2)语言文字的含义具有模糊性。对于同一段文字,后人会读出截然不同的意思,究竟哪种解读真正地反映了制宪者意图?(3)为什么制宪者们其时对未列举权利的理解对于当代的宪法解释者是有拘束力的?因此,这种方法无法为第九修正案的解释提供足够的指导。
二、文本主义方法
这种方法把宪法看作是正在实施中的社会契约,注重对宪法术语之当下意义的考察,其目的是赋予宪法以当代意义,并赋予第九修正案以权利保障功能。S imeon C.R.Mclntosh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描述:解释一个宪法文本,就是把它置于一个语境之中,并把它理解为某人的、指向某种目的的作品,把它理解为对一个问题的解答,或者用它解决某些“关于存在的问题”(existential problems)。至于把文本置于何种语境中,制宪者宣告的意图当然是有帮助的,但不能把制宪者的话当成是对宪法文本进行解读的结论性的陈述。相反,意图是用“‘行为—描述’术语”(ter ms of action—descriptions)建立起来的,而“‘行为—描述’术语”要么为负责任的行为者本人所采用,要么可以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把这些术语归属于他们,因为制宪者被视为负责任的、有理性的行为者。在理论上,读者和行为者对于“正在做什么”具有相同的理解,因而具有共同的语言即具有共同的“行为—描述”词汇。①SeeSimeon C.R.Mclntosh,On Reading the Ninth Amendment:A Reply to Raoul Berger,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236—237,236,235—236,240—241(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
同原旨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们相比,文本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们特别强调文本对于宪法解释的重要意义。以对待制宪者意图的态度为标准,可以把文本主义方法的倡导者分为两派。一派片面强调宪法文本的当代意义,而不管这种意义是否与制宪者意图相一致,这一派可以称之为“激进派”。比如,Christopher J.Schmidt认为,制宪者们的意图并不优于第九修正案的文本,即便是麦迪逊的意图也是如此。②SeeChristopher J.Schmidt,Revitalizing the Quiet Ninth Amendment:Determining Unenumerated Rights and Eliminating Substantive Due Process,32 U.Balt.L.Rev.169,170,192—194(Spring,2003).为此,他对原旨主义方法进行了批评,并对文本主义方法进行了证成:那些试图对第九修正案作原旨主义解读的法官和学者跳过第九修正案的文本而诉诸第九修正案的历史、宪法的结构以及最高法院的法理学说来探求第九修正案的涵义,他们对第九修正案的理解是政策性的。第九修正案文本能够使对它的解释以及它可能产生的法律拟制受到限制,这使得宪法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第九修正案通过解释而得到进化,这种权力来自第九修正案文本的授予。③SeeChristopher J.Schmidt,Revitalizing the Quiet Ninth Amendment:Determining Unenumerated Rights and Eliminating Substantive Due Process,32 U.Balt.L.Rev.169,170,192—194(Spring,2003).另一派虽然强调宪法解释应当以文本为中心,但也不否认制宪者意图的重要性,可称之为“温和派”。如 S imeon C.R.Mclntosh认为,制宪者意图是宪法解释的首要标准和重要前提,但是,由于对意图的分析在逻辑上都是不明确的,而文本的意图则是所有的解释最终都要处理的问题。因此,在解释中试图揭示的意图,是文本中表达的意图而非制宪者所宣称的意图。④SeeSimeon C.R.Mclntosh,On Reading the Ninth Amendment:A Reply to Raoul Berger,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236—237,236,235—236,240—241(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文本主义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文本基础而使宪法裁判免除了对党派政治和司法机关之一时兴致的依赖。⑤SeeJeffreyD.Jackson,TheModalitiesof theNinthAmendment:Waysof Thinking aboutUnenumerated Rights Inspired by Philip Bobbitt’sConstitutional Fate,75 Miss.L.J.495,518(W inter,2006).但是,在第九修正案的语境中,文本主义方法陷入了某种困境——第九修正案的文本并没有明确指出未列举权利是什么。这种困境,用约翰·哈特·伊利的话说就是:第九修正案的文本给文本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按照文本主义的观点,只能得出第九修正案最好被忽略的结论。⑥SeeJohn Hart Ely,Democracy and Distrust 38—4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为了使对第九修正案的解释走出上述困境,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S imeon C.R.Mclntosh主张对宪法进行整体性解读。他指出,在适用第九修正案时所遇到的问题,涉及的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被解读的宪法的性质问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宪法的性质、结构和历史作出分析,以便从文本中抽出那些能够精确说明文本之意义的特征。⑦SeeSimeon C.R.Mclntosh,On Reading the Ninth Amendment:A Reply to Raoul Berger,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236—237,236,235—236,240—241(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他认为,既然对第九修正案的解释最终涉及对诉讼当事人的具体法律请求进行肯定或否定这一问题,那么,这些请求的有效性问题只能按照我们认为最能揭示宪法之性质的正义理论来回答。换言之,一个法官需要表明,为什么他的宪法理念要求作出那样的判决,为什么那个判决是正确的。⑧SeeSimeon C.R.Mclntosh,On Reading the Ninth Amendment:A Reply to Raoul Berger,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236—237,236,235—236,240—241(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Marsh则主张对第九修正案进行“超文本主义”解读。他认为,文本的意义存在于解读行为中。在解读过程中,读者形成某些“假说”、“博识的推测”或者可能的解释,并根据所有的相关证据——文本证据和超文本证据来确定第九修正案的意义。⑨SeeMarsh,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Understanding 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Damon ed.,1967).按照这种“超文本主义”方法,不仅要将整部宪法纳入考量,而且应当将《独立宣言》等文本纳入考量,以便弄清宪法文本的性质并从中引申出某种正义原则,进而把这种正义原则运用于个案之中。
三、建构性的方法
按照 Randy E.Barnett的描述,建构性的方法是从“历史实例和假设的例子”中以及从“理论素材”中建构一种“融贯的权利理念”,然后把这一理念适用于个案以得出合法的结论。①SeeRandy E·Barnett,Introduction:JamesMadison’sNinth Amendment,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37(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
从 Randy E.Barnett的描述来看,建构性方法的出发点是宽泛的,既包括“历史实例和假设的例子”,也包括“理论素材”,而二者都可以作广义的理解。比如,最高法院的判例,其它政府机构 (如国会、总统等)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惯例等等,似乎都可视为“历史实例”,而对这些“历史实例”甚至是“假设的例子”所作的司法评论、学术评论以及自由、正义等法律价值则可以视为“理论素材”。而从“历史实例和假设的例子”、“理论素材”中得出某种“融贯的权利理念”的过程,无非是运用法学理论对“历史实例和假设的例子”、“理论素材”进行解释并进行权利推理的过程。因此,建构性的方法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方法,不仅可以涵盖屠振宇博士归纳的三种认定方法,而且足以把MichaelW.McConnell所谓的“传统主义的方法”涵盖于其中。
按照MichaelW.McConnell的理解,传统主义方法是一种在解答“何者构成一项基本权利”这个问题时,经过积累而形成共识的方法。他说:经过长年累月而形成的共识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一种分权机制而表达出来。一次投票、一次选举的胜利、一个判决都不足以形成一个传统;传统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经历了公众的赞成或反对之后而在许多不同的决策者之间形成的默认。当法官们根据传统而作出判决时,他们并没有篡夺人民的自治权。②SeeMichaelW.McConnell,The Right to Die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Tradition,1997 Utah L.Rev.665,682(1997).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应当首先承认,按照建国者们的理解,基本权利是先于政治、先于宪法的。这些权利的来源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众多的来源——自然、神法、习俗、普通法甚至理性。但是,这些权利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地进化。要判定这些权利在今天是什么状况,宪法解释者需要回顾分权体制下的代议机构在过去一个时期做了什么并将其共识奉为权威。③SeeMichaelW.McConnell,Textualism and the Dead Hand of the Past,66 Geo.Wash.L.Rev.1127,1136(1998).运用建构性方法的关键是构建融贯的权利理念。Randy E.Barnett强调,运用建构性方法时必须考虑基本权利的双重功能:一是强化政府权力或政府目标的界限,二是对政府追求合法目标时所采用的方法施加额外的限制。④SeeRandy E·Barnett,Introduction:JamesMadison’sNinth Amendment,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44,43(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
四、推定的方法
对于这种方法,Randy E.Barnett是这样描述的: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推定:第一种推定是——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做没有被正当地禁止的任何事情。按照这种推定,宪法所建立的就是“政府权力的岛屿”,这个岛屿被“个人权利的海洋”所包围;第二种推定是——政府可以做没有被明确禁止的任何事情。按照这种推定,宪法所建立的就是被“政府权力的海洋”所包围的“个人权利的岛屿”。第九修正案强烈地支持第一种推定。⑤SeeRandy E·Barnett,Introduction:JamesMadison’sNinth Amendment,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44,43(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
推定的方法成立的前提是,承认宪法是规范政府结构、调整政府——公民关系的法,其基本精神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而将宪法的基本精神付诸实施的任务由法院来承担。因此,推定的方法是一种根据立宪主义原理进行权利推定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中外学者在进行学理分析时广泛采用,而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进行司法审查时也经常采用。
对于为什么要采用推定的方法对未列举权利进行认定,Randy E.Barnett认为,这是“权利先于、优于权力”理念的必然要求。在古典自由主义权利理论中,权利界定了人们对世上的资源 (包括其身体)所享有的道德管辖权的范围,这种管辖权确立了人们自由地做他希望的事情的边界。只要人们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行动,他们的行为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其他人不得强行干涉。按照这种方法,我们的权利之数量就如我们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所能采取的各种行为的数量一样多。虽然我们的行为必须局限于适当的管辖范围,但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的权利如同我们的想象力一样,是各式各样的。按照这种权利观念,要对我们的所有权利进行列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第九修正案建立了有利于个人权利的宪法推定,即个人被宪法赋予了从事“正当行为”的特权,而且这样的行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当然,按照第九修正案进行的宪法推定,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关对普通法权利的所有变更都是为宪法所禁止的。按照普通法的程序,法律偶尔可以用于更正先例原则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错误,确立必要的惯例,使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达成一致。但是,法律必须受到独立而公正的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弄清立法机关是否打着实现合法功能的幌子试图侵犯个人权利。①SeeRandy E·Barnett,Introduction:JamesMadison’sNinth Amendment,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40—41(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
五、未列举权利的判断标准
美国学者认为,以上四种方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法官们需要综合运用上述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运用既能限制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也有赖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发挥,法院运用一种或几种方法而认定未列举权利的做法仍然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嫌疑。因此,有必要构建某些标准,对法官认定未列举权利的过程及结果是否具有相对的客观性进行评判。根据中、美两国学者的研究,存在着两个关于未列举权利的标准:其一是认定未列举权利的标准——法院何以认定某项权利诉求值得予以宪法保护;其二是评价未列举权利的标准——人们何以判断法院对未列举权利的认定具有相对的客观性。
(一)认定未列举权利的标准
根据阿伦·艾德斯等学者的考察,美国最高法院在对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行为 (主要是立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采用两个标准:(1)严格审查标准,该标准着眼于公民的“基本自由利益”的保护。按照这个标准,除非一部法律能够表明它是实现政府的紧迫性利益的最俭省的手段,否则会被撤销。(2)合理依据标准,该标准着眼于“财产”或者其它“非基本自由利益”的保护。按照这一标准,如果立法机关认为一部法律能够增进某一合法的立法目的,那么,该法律会得到法院的确认。②参见[美]阿伦·艾德斯、克里斯托弗·N·梅:《宪法个人权利》(影印本),中信出版社 2003年版,第57页。由于未列举权利属于基本权利,因此,我们可以说,最高法院认定未列举权利的标准应当是“严格审查标准”。
采用“严格审查标准”对未列举权利进行检验时,关键是掌握好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S imeon C.R.Mclntosh指出,要判断一项请求是否值得按照第九修正案予以保护,应当在“提供保护的请求”与“国家拒绝提供保护的道德理由”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国家要否认这样的请求,就必须说明,根据某项原则,该项请求应当让位于其它更重要的考虑。③SeeSimeon C.R.Mclntosh,On Reading the Ninth Amendment:A Reply to RaoulBerger,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241(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在Washington v.Glucksberg案中,戴维·苏特大法官在其协同意见中也认为,在识别未列举权利时,法官应当将该权利与政府利益进行平衡,“只有当立法的证明原则严重背离个人利益以至于这种立法的实施是专横的和无意义的,此时才可以说,申请人具有一项宪法权利。”④SeeWashington v.Glucksberg,521 U.S.702,767—768(1997).
(二)评价未列举权利的标准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认为,司法权能够被限制于合理范围之内的唯一途径在于,法官是否坚持对于自己在政治体制中所承担的角色的性质的理解——通过一个纯粹职业化的过程,他们学会并理解了,他们是裁判者,不是立法者。⑤SeeKen I.Kersch,Everything Is Enumerated:the Developmental Past and Future of an Interpretive Problem,8 U.Pa.J.Const.L.,957,972(2006).那么,置身最高法院之外的人们何以判定,大法官们对于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是一种理性判断而非恣意妄为呢?根据中、美两国学者的观点,法院对某一未列举权利的认定符合下列标准之一即应视为具有相对的客观性:(1)符合社会公众的权利需求。Calvin R.Massey认为,法院应当把“当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要求承认其为个人尊严所固有”的权利请求确认为基本权利。⑥SeeCalvin R.Massey,Federalism and FundamentalRights:theNinthAmendment,reprinted in Randy E·Barnett,ed.,The RightsRetained by the People: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Ninth Amendment 335(George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9).我国台湾学者李震山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权利需求值得由宪法予以保障。⑦参见李震山:《多元、宽容与人权保障——以宪法未列举权之保障为中心》,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5年版,第64—65页。强调当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对未列举权利的认同,或者强调权利需求的普遍性,这强化了权利推定的客观性。(2)为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Cass Sunstein主张,应当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宣言、条约、协定中的权利列举纳入对美国宪法的理解。我国学者王广辉也认为,在判断某种权利请求是否应当被视为宪法上的未列举权利时,要看该权利请求是否为国际性的人权法律所确认。⑧参见王广辉:《论宪法未列举权利》,《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64页。国际人权公约中所列举的权利是自然权利的实证化,法官从中寻求未列举权利也强化了权利推定的客观性。
(责任编辑:周文升 wszhou66@126.com)
DF2
A
1003—4145[2010]07—0113—04
2010-05-18
夏泽祥,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