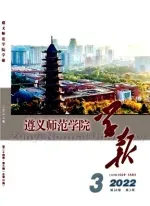清代贵州戏曲的地理分布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
陈季君
(1.遵义师范学院宣传部,贵州遵义 563002;2.西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 400715)
清代贵州戏曲的地理分布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
陈季君1,2
(1.遵义师范学院宣传部,贵州遵义 563002;2.西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 400715)
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和民间艺术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便是戏曲。文章从梳理清代贵州戏曲的地理分布来探求清代贵州文化的结构及其蕴藏的文化背景、社会意义,探究清代贵州的戏曲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及文化特质。这对于打造贵州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特色品牌,促进贵州文化繁荣具有一定的意义。
贵州;清代戏曲;民族;分布;文化;地域性
贵州是一个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民族众多的省份。由于地处云贵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境内重峦叠峰,山高谷深,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18个世居民族共处其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使他们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艺术。清代前期,由于其政治和军事地位的加强以及与外省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中原、江南及邻省文化艺术与贵州本土文化进一步融合,使得贵州戏曲出现“多腔并存”的繁荣局面。对于贵州文化的研究,省内外多数学者多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民族文学等传统视觉去研究,本文旨在从贵州戏曲历史空间角度探究贵州文化的地理特征。
一、“多腔并存,分散集中”的清代贵州戏曲的地理特征
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清政府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清王朝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国库丰盈,文教昌盛,社会稳定,各省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清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乱弹”诸腔蓬勃兴起,民间戏曲兴盛,名伶辈出。清代前期的贵州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展开了他的历史进程。在此百余年的时间内,贵州人口稳定增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生产和水利设施有明显进步,手工业和矿业开发有了新进展,商业也逐渐兴盛起来,税收和财政收入稳步增加,驿道和航运条件有一定程度改善,省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南北戏曲入黔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贵州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出现了汉族戏曲主要流布在贵阳、遵义、安顺等大城市中心地区,而地方戏遍地开花的局面。
1.弋阳腔、昆曲的流布。
明代后期江西弋阳腔传入贵州,出土于遵义县赵家坝的墓葬石刻《演乐图》是明代戏曲在贵州演出活动的历史见证。到清代乾隆年间弋阳腔盛行于贵州,我们从清代乾隆年间查禁戏文的奏折可以得到证实。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代江西巡抚郝硕呈奏《江西巡抚郝硕覆奏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折》:“臣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前因外间流传剧本,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亦未必无碍之处,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兹据伊龄阿复奏:‘派员缜密搜访。查明应删改者删改,应抽掣者抽掣,陆续粘签呈览。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腔,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盛行,请饬各督抚阅看,一体留心查察……’仅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六日”[1]昆曲在乾隆朝有戏班及伶人进入贵州,乾隆三十六年,任贵州贵西兵备道的赵翼(字瓯北)将离任贵阳,在行前酒宴上欣赏了昆曲,也使他伤感,在他的诗中写道:“离人将上洞庭舟,饯别深叨唤主讴。为我红尘留不任,开场先唱岳阳楼。”“当筵忽漫意悲凉,依旧红灯绿酒旁。一曲琵琶哀调急,虎贲重戚蔡中郞。”“解唱阳关劝别筵,吴趋乐府最堪怜。一班子弟俱头白,流落天涯卖戏钱。”[2]从他的诗中估计这个戏班被招来贵阳府已经几十年了,黑发弟子尽为白头老人也。昆曲不但有演出活动,而且产生了《鸳鸯镜传奇》、《梅花缘》等昆曲剧本,出现了傅玉书、任璇两位戏曲家。弋阳腔和昆曲演出活动主要集中在遵义和贵阳。
2.贵州梆子的产生及其分布。
梆子即秦腔,在明末清初由陕西传入贵州,在清初盛行于贵州各个大城镇。乾隆时任贵州布政使的李宗昉在所著《黔记》中,引用《贵阳竹枝词》一首:“板凳条条坐绿鬟,娘娘庙看豫升班。今朝比似昨朝好,《烤火》联场演下山。”在注中讲到:“娘娘庙在指月堂,《烤火下山》,花戏也”,[3]花戏即秦腔,可见当时秦腔在贵阳盛行的场面。黔中艺人向外地艺人学习梆子和各种剧种的声腔和表演,结合贵州民间音乐和语言特点,创造了贵州梆子,并且在乾嘉之后,相继涌现了一批名伶。自乾隆至宣统约170年间,贵州梆子的戏班有隆庆班、豫升班、万和班等,主要分布在在贵阳、安顺。到光绪年间,贵州梆子由于缺乏经济支撑,逐渐衰落。
3.傩戏的发展与地理分布。
傩祭,本是我国古代腊月驱除疫鬼的一种民间宗教形式,是古代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驱邪、消灾纳吉所进行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多伴有傩舞、傩歌,傩戏便在此基础上产生。傩祭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据《周礼》卷25《占梦篇》:“遂令始作傩驱役”又《论语·乡党》卷十“乡人傩,朝服而立于昨阶”。据记载,这种傩祭的方式在汉晋时期中原就十分盛行,唐宋以来,随着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儒学地位的加强,信巫驱邪的风俗日趋简化,傩祭、傩舞和傩歌虽然在民间仍然存在,但是没有与戏剧说唱有机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有影响的戏剧。但在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高山密林深处地区,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疑惑或恐惧,自然就以信巫驱鬼为日常生活的事情,这在贵州地区十分明显。如汉晋时期牂牁郡“俗好巫鬼,多禁忌”[4]朱提郡北部“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4],直到唐宋时期今贵州南部地区仍是“俗尚淫祀”[5]。这种文化环境为傩戏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唐宋时期南方傩逐渐向戏剧化发展,经过了傩祭→傩舞、傩歌→傩戏的发展历程。明清以来,自古就好巫鬼的古夜郎地区成为西南地区傩戏最发达的地区。据记载,清代时期贵州“自城市及乡村,皆有庙宇,土民祁禳,各因其是,以时祭致。有叩许戏文,届时扮演者”[5]。安顺、贵阳四周及毕节、遵义、都匀、凯里、兴义有地戏。黔西北威宁彝族有变人戏(撮泰吉),黔北和黔南流行端公戏。黔北、黔南及省内其他汉族地区流行“阳戏”,也是酬神还愿的宗教性娱乐活动,所祭祀的是川主、土主、药王“三圣”,也有加祀“文昌”星的,带有三教合流的色彩。道光《遵义府志》载:“歌舞祀三圣,曰阳戏。三圣:川主、土主、药王也;近或增文昌,曰四圣。每灾病,力能祷者,则书贴愿,祝于神,许酬阳戏。即许后,验否必酬之。或数月,或数年、预洁羊、豕、酒,择吉,招巫优,即于家歌舞娱神,献生、献熟,必成必谨。余皆诙谐调弄,观者哄堂。”[7]傩戏,是贵州覆盖面最广的一种民间信仰戏剧。主要流行于黔东、黔北、黔南、黔西北等地的土家族、汉族、苗族、仡佬族、侗族、布依族村寨中。其中,尤以德江、思南、沿河、松桃、印江、道真、石阡、务川、江口、岑巩、正安、湄潭等县最为丰富。
4.花灯的产生发展及地理分布。
花灯是在贵州省汉族地区和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流传的花灯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戏曲剧种。正月十五观灯这个风俗很早以来在中原地区流行,是汉民族的一种传统节气风俗,明代建省以后,大量的汉人进入贵州,汉民族的风俗节气亦日渐兴盛起来。清朝初年贵州巡抚田雯作《春灯绝句》,描述了贵州各地花灯流行的情况:“济火祠前试绮罗,奢香驿下舞婆娑。夜郎塞路人如蚁,大半番童僰女多。城北城南接老鸭,细腰社鼓不停挝,椎髻花铃唱采茶”[8]据清康熙至道光年间的地方志记载,福泉、遵义、开阳等地当时已有花灯歌舞流行,每于上元节,扎各式纸灯,由儿童作时新妆,踏歌和乐,谓之“闹元宵”,或男妆唐二,女妆懒大嫂,手持巾、扇,双双起舞,称为“跳花灯”。贵州花灯戏是清末民初在当地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起初,花灯叫采花灯,只有歌舞,后在歌舞中加入小戏,再以后受外来戏曲影响,发展为演出本戏。贵州花灯戏主要流行于独山、遵义、毕节、安顺、铜仁等地,是贵州主要地方剧种,人们习惯地简称花灯。贵州花灯戏在省内有四路花灯调即铜仁东部花灯,安顺西路花灯,遵义北路花灯,独山南路花灯。各路花灯都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
5.文琴戏的产生与流布。
文琴戏,旧称唱洋琴、唱曲子、扬琴戏。演唱形式为坐唱,一般为7-8人,分生、旦、净、末、丑等脚色,并分操乐器伴奏。唱腔清丽婉转,有清板、二板、三板、杨调、苦禀、二黄、二流等七种板式。扬琴为主奏乐器。传统曲本,称为弹词。曲词为7字句或10字句,讲究韵律,工稳典雅,多为文人所作。据清代编修的贵州地方志书记载,唱洋琴在嘉庆、道光年间即已出现,为士大夫、文人墨客自娱的艺术,或在喜庆宴会时演唱,光绪年间最盛。清末落第举子王石青最擅演唱,并能编写脚本,曾吸收贵州梆子的“二簧”、“二流”唱腔和民间曲调,发展了洋琴的唱腔。光绪年间,贵州琴书开始走向民间,扬琴社团和茶社主要分布在贵阳府、安顺府、大定府、遵义府、铜仁府等地的中心城市。
6.川剧在贵州的流布。
清代后期,四川商人来黔经商者不断增多,川剧班也随之流入贵州,主要分布在遵义、贵阳一带。
7.侗戏的产生及分布。
侗戏,侗族的戏曲剧种。最早形成于贵州的黎平、榕江、从江一带,后流传到广西的三江和湖南的通道等侗族聚居地区。侗剧是在侗族民间说唱艺术“嘎锦”(叙事歌)和“嘎琵琶”(琵琶歌)基础上,接受汉族的戏曲影响而形成。“嘎锦”,演员自弹自唱,夹用说白来叙述故事,内容多半为侗族的传说故事。“嘎琵琶”,分短歌和长歌。短歌为抒情民歌,长歌为叙述故事的说唱。侗戏大致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形成。首创者是贵州黎平的著名歌师吴文彩。他借鉴汉族地方戏曲的程式和表现手法,最先组成侗戏班,编排剧目,穿着侗族服装用侗话演唱,这便是侗戏的开始。光绪元年(1875)侗戏从贵州黎平县水口区传入广西三江县高岩村后,流传更加广泛。
8.布依戏的产生和分布。
布依戏是布依族人民用布依语言和音乐演唱的民族戏曲剧种。它最先是从祭祀仪式跳神活动中孕育出来的,在跳神的基础上,先后创立了布依板凳戏、布依彩调(即八音坐弹戏)和布依地戏。约在清代末叶,生活在红水河、南盘江一带的布依族,与广西壮族相邻而居,从清代中叶开始壮剧艺术传入,布依族受其影响,用布依族语演唱布依族的乐曲。一些民间艺人在八音坐弹、板凳戏、土戏布依彩调的基础上再经过改造、融合,使它逐渐演变成为布依族的舞台综合艺术。民间艺人按村寨组成的业余戏班代代相传,每逢民族节日,搭台演唱。布依戏虽吸收了汉族戏曲的部分表演程式,但仍具有本民族的特色。音乐曲调由“八音坐弹”发展而来,有〔正调〕(〔长调〕)、〔京调〕(〔起落调〕)、〔翻演调〕、〔马倒铃〕、〔八谱调〕、〔反调〕、〔二黄〕、〔二六〕等。主要伴奏乐器为尖子胡琴(公琴、牛骨琴)和朴子胡琴(母琴、葫芦琴),配以笛、短箫、木叶和三弦、琵琶、月琴等。打击乐器有大锣、大钹、鼓、木鱼、包包锣、小马锣等。布依戏流行于贵州省黔南、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盘江流域红水河布依族聚居地区。
二、清代贵州戏曲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个剧种的产生、演变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清代贵州戏剧文化的特点与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也与清代贵州的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历史密不可分。笔者认为,贵州戏剧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贵州汉族文化、大山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密不可分。
1.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清代贵州戏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的文化,都应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一种综合文化。历史时期,外来文化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这样,移民来源的籍贯、移民来源的形式、移民来源的行业成分,便与当地文化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9]汉民族形成后对于周边地区影响很大。汉族移民对贵州文化氛围的变化影响是十分强大的。汉族移民浪潮从秦代开始,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民国到现在,在明清时期奠定了移民的基本格局。贵州在明朝永乐年间建省后,大量汉族移民通过屯田、经商、戍边等方式进入贵州,改变了以往贵州“夷多汉少”的局面。贵州的移民结构是基于明代征战留戍和移民屯田形成的。兴义府:“多明初平黔将足之后,来自江南,尚有江左遗风”[10],毕节县“迁自中州诸巨族,皆前明指挥千户”[11],这是贵州屯堡人是东南籍移民的重要历史见证。
清代贵州移民会馆分布表明,黔北以四川会馆占绝大多数,江西会馆和湖北会馆次之,有少量秦晋会馆和福建广东会馆;黔东是江西会馆占绝大多数,湖广会馆次之;黔西是江西、四川、湖广会馆等同,黔南是江西会馆占绝大多数,湖广会馆次之。我们从乾隆《贵州通志》关于明代贵州留寓籍贯统计来看,明代贵州的官员主要是江南籍、江西籍、四川籍、湖广籍组成。这种趋势在清代继续发展,移民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较多的湖广移民在民末清初进入贵州,使清代贵州地区江南人、江西人、湖广人、四川人共同成为贵州最主要的移民,湖广移民和四川移民的比例增大,其活动屡见史籍中。如贵阳是“江右、楚南之人为多”[12]。
明清外来移民的进入对贵州汉族文化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也推动了贵州戏剧的产生与发展。从嘉靖《贵州通志》的记载来看,明代贵阳地区元日祁年、端午饮菖蒲酒、端午吃粽子、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节日,也表明汉文化已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这种文化中呈现出明显的江南、江西氛围。清代初期移民从各省进入贵州后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会馆,会馆文化便呈现出五方杂处的文化氛围。各会馆普遍都搭建戏台,唱着乡音乡曲,这样昆曲、秦腔、弋阳腔、川剧等汉族戏剧就随着会馆舞台上外地艺人的演出传入贵州,并受到贵州人民的喜爱。外来戏剧也催生了贵州地方戏曲的产生和嬗变,如贵州梆子就是贵州艺人吸收了梆子(秦腔)的声腔和其他声腔的优长而创造的。贵州琴书也是从外来琴书的说唱形式演变而来。贵州花灯的传统剧目如《战金山》、《龙凤呈祥》、《盗仙草》等多数为江南民间故事,在贵州的采茶歌中多用江浙方言“侬”字就是证据。安顺府的“屯堡人”即明代征调的江南籍汉族移民,其在衣食住行方面多江南遗风。特别是地戏,明显来源于江南民间戏剧。黔北一带流行川戏,这与清代四川籍移民的大量迁入有关。贵阳城中的四川会馆也常演川剧,这里成为官员们迎宾应酬的主要场所。
外来移民主要分布在交通干道和重要城镇所处的地区,所以汉文化也主要分布在交通干道和重要城镇所处的地区,与外来汉族戏剧分布区域基本重合。
2.贵州戏剧的大山文化特征
贵州地理环境独特,地处云贵高原,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贵州高原山地居多,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有学者认为:“贵州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山地文化。山地文化形成了贵州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形成了贵州人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生活习俗、社会结构”。[13]长期的山地农耕,养成了贵州人强悍尚武的性格;山高谷深、四面闭塞,又使他们较长时间内保留了远古民族豁达善舞的风尚。安顺地戏、侗戏都是大山文化的生动表现。从傩戏的产生和表演来看都具有大山文化的特征,由于贵州地处边陲,山高谷深,文化落后,以致瘴疠之疫,天灾人祸,力所难抵,祁神弄鬼成为日常之事,这种地理和文化环境为傩戏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地戏演出一般在村头旷地上,不上舞台,观众在四周高处观赏。演员把面具顶在头上,扎上靠旗,手舞刀枪等各种道具,边舞边唱,边说边打;表演武打时,往来跳动的动作幅度较大,是为了让高阜处观众能看得见面具听得见说唱。侗戏中侗族大歌是音乐灵魂。“饭养身,歌养心,”这是侗家人常说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他们把“歌”看成是与“饭”同样重要的事。侗家人把歌当作精神食粮,用它来陶冶心灵和情操。他们世代都爱歌、学歌、唱歌,以歌为乐,用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用歌来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歌与侗家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侗族的各种民歌,特别是侗族大歌,便成了他们久唱不衰的一首古歌。大歌的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是其主要特点。模拟鸟叫虫鸣、高山流水等自然之音,是大歌编创的一大特色,也是产生大歌的自然根源。它的主要内容是歌唱自然、劳动、爱情以及人间友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之声,这是山地文化的一朵奇葩,也孕育了侗戏这一民族戏剧的瑰宝。
3.清代贵州戏剧的民族多元性。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世居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满族、羌族等17个。民族的多样性使贵州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使贵州民族戏剧呈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有清一代,贵州境内戏剧十分丰富。汉族地区的戏剧大多数是从外地传入的,较早的有雅部的昆曲,花部的秦腔、弋阳腔,较晚有川剧。黔中艺人吸收各种剧种的板腔,结合贵州的民间音乐、语言特色,创造了贵州梆子。民间流行的有傩戏群(贵州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等民族都有自己的傩戏)、安顺地戏、黔北端公戏、黔东傩堂戏、彝傩面具戏《撮泰吉》,还有各路花灯戏,独具民族特色的侗戏、布依戏等等。在贵州民族歌舞海洋里,许多传入的汉族戏剧都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少数民族的戏剧也吸收了汉族戏剧的表演程式和声腔以及剧目,提升了少数民族戏剧的内涵。所以,贵州民族的多样性使贵州的戏剧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多彩的民族特征。
总之,从清代贵州戏剧地理的研究可以得知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不仅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清代贵州有这样多姿多彩的戏剧演出不是偶然的,她是基于区域文化特殊的土壤孕育的结果;反之,演剧活动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对于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巩固,也必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1]丁淑梅.清代禁毁戏曲史料编年[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124.
[2](清)赵翼.瓯北诗钞[M].上海:商务图书馆,1935.36.
[3](清)李宗昉.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35.
[4](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A].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M].刘琳校注.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196.
[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3406.
[6](清)道光·松桃厅志·风俗[A].成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6[M].巴蜀出版社,2006.511.
[7](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风俗[M]遵义市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556
[8](清)田雯.康熙《黔书·上·二十八》嘉庆十三年刻本[A].民国黔南丛书重排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6.482.
[9]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1997.20.
[10](清)咸丰·兴义府志(卷40)[A].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8)[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6.379.
[11](清)同治·毕节县志(卷8)[A].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49)[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6.419.
[12](清)黄家服,段志洪.黔南识略(卷1)·贵阳府[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5)[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6.266.
[13]黎铎.贵州文化发展概览[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23.
(责任编辑:徐国红)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uizhou Drama and Local Culture
CHEN Ji-jun1,2
1.(Publicity Department,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2.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The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milieu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n Guizhou gestate a lot of colorful ethnic and folk arts,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is drama.After making clear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uizhou drama in Qing dynasty,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structure of Guizhou in Qi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uizhou drama and local culture,which plays a certain part not only in creating distinctive cultural brand of Guizhou with localness and ethnicness,but in facilitating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e in Guizhou.
Guizhou;drama in Qing dynasty;nationality;distribution;culture;localness
J825
A
1009-3583(2010)-06-0005-05
2010-07-16
陈季君,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宣传部部长,历史系教授,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