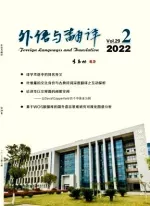论穆旦早期诗歌*
郑艳君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论穆旦早期诗歌*
郑艳君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穆旦早期诗歌艺术价值的缺乏使很多研究者忽略了对它的研究,但笔者认为穆旦的早期诗作就预示了他后来创作的走向,穆旦后来的创作其实就是他早期作品主题的深化和拓展。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穆旦早期诗歌进行解读:哲理化取向;悲观意识与搏斗精神。研究他的早期作品,既是研究其早期作品本身,也是研究他后来作品特色的形成原因。
穆旦;早期;哲理;悲观
如大多数天才一样,穆旦也没有逃脱生前寂寞和死后热闹的命运。穆旦的诗在生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在特殊历史时期,他还被剥夺了公开写诗的权利。他的诗歌在他死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了九十年代,他的位置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1]的编者把穆旦排到了第一位,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诗人。相应的,对穆旦诗歌的研究在这段时期也形成了热潮。但大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穆旦四十年代的作品,而忽略了他早期的诗作。从整体研究的角度而言,穆旦的早期诗作是不能忽视的。虽然这些作品谈不上有很大的艺术价值,但它预示了穆旦后来创作的走向,穆旦后来的创作其实就是他早期作品主题的深化和拓展。对他早期作品的忽视,除了艺术价值方面的原因外,或许还隐藏着另一个理由。那就是大家认为穆旦的艺术成就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而去外国诗人中寻找他的渊源,而忘了从穆旦自身的个性和艺术特性上去寻找其根源。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理论,人与外界的环境的关系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而是以自身的心理构架为依据,经过主动的选择、同化,而后经过调整做出反应的。穆旦之所以在后来接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因为他早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构架。研究他的早期作品,既是研究其早期作品本身,也是研究他后来作品特色的形成原因。
一、哲理化取向
主智是穆旦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这一点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已见雏形。他的早期作品主要集中在两类类型上:一类是在抽象层面对人生的探索,如《梦》、《神秘》、《前夕》就属于此类;另一类则是在具体层面上对人生价值的探索,如《更夫》、《一个老木匠》、《两个世界》。而这两类作品都呈现出哲理化的意味。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作品。《神秘》中,诗人开始探索世界的奥秘:“朋友,宇宙间本没有什么神秘,/要记住最神秘的还是你自己。”十六七岁的穆旦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一切都是那么的“神秘”,他想寻求其中的“高超玄妙”。他认为“世界”充满着变数,而且在命运面前人只能是听天由命的角色。“你要说,这世界真太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我只好沉默,和微笑,”在《梦》中,穆旦则思考着人生:“人生本是波折的,你若顺着那波折一曲一弯地走下去,才能领略到人生的趣味。”穆旦认为人生如梦,不管“美妙”还是“险恶”,只要有“波折”,就有意思。穆旦刚开始写诗就把笔伸向这类抽象的永恒性话题: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可以说穆旦一生就在思考这些人生和世界的奥秘,写出他“发现的惊异”。
哲理化的风格在第一类作品中很容易看出,现在,我们着重来探讨一下第二类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这种倾向。从描写对象上来看,第二类作品主要写了一些小人物:流浪人、更夫、老木匠等,所以很多人对他这些作品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怜悯的层次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然,首先我们得承认,穆旦的确对这些人心怀着怜悯。例如:“仿佛眼睛开了花/飞过了千万颗星点,像乌鸦。/昏沉着的头,苦的心;/火般热的身子,熔化了/棉花似地堆成一团,”(《流浪人》)这些诗句就流露着怜悯之情,对流浪人饥饿感受的描写仿佛感同身受。写老木匠也是如此:“那老人,迅速地工作着,/全然弯曲而苍老了;/看他挥动沉重的板斧/像是不胜其疲劳。”(《一个老木匠》)老木匠工作的样子,看了让人觉得辛酸。但是,穆旦在描写这些人悲惨的生活状况时,表达的主要不是对这些人的怜悯,而是思索这些“芸芸众生”的生命意义和生命状态。在《两个世界中》,作者写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边是一个女人“像一只美丽的孔雀”“高贵,荣耀,体面砌成了她们的世界”,而另一边是“女人的手泡一整天,/肿的臂,昏的头,带着疲倦的身体,/摸黑回了家,便吐出一口长气……/生活?简直把人磨成了烂泥!”两者构成鲜明的对比,流露出诗人对那穷苦的母亲的同情。但在这种描写中,穆旦更多的是在沉思: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同样是人,为何过的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的人?站在这“两个世界”面前的穆旦显然主要是一个生命的形而上沉思者的角色,而不是某一方的控诉者或另一方的怜悯者,虽然他的确是有所倾向。他在这里沉思的正是在《神秘》中所说的“世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的问题。在《流浪人》中这种沉思世界和人生的特色则更为明显。在诗中,作者虽然也写到了“他”的穷困与饥饿,但更多的是表达“他”精神上的流浪和生命的无所归依:“软软地,/是流浪人底两只沉重的腿,/一步,一步,一步……/天涯的什么地方?/没有目的。”他笔下的流浪人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只知道“一步,一步,一步……”走下去,该诗以“一步,一步,一步……”结尾,更加强化了这种不知选择何路,却依然盲目地往前走的意味。很明显,诗人笔下的这个流浪人不是一个“单纯受物质生活的驱使而流浪”的人,“而是一个苦苦寻找人生的目标与方向的精神的流浪者。”[2]如果从对现实的反映的角度看,一个贫穷的流浪人不会去想这些抽象的问题:自己“在天涯的什么地方”,生活有“没有目的”。可见,穆旦在这里是把他当作一个精神、生命的流浪者来写的,他是一个没有人生目的而盲目来到世界上的流浪者。因此,穆旦写流浪人,主要不是为了表达他在街头的流浪之苦,而是为了表现他内心不知往何处去的迷茫心理。同《流浪者》一样,《一个老木匠》中穆旦虽然也写到了他劳作的艰辛,但更多的是孤独寂寞的生活与老木匠自己的内心体验。老木匠“春,夏,秋,冬……一年地,两年地”的劳作,伴着他的却只有“木头,铁钉,板斧”这些毫无生气的东西和永远的寂寞与孤独。在《更夫》中,他这种思考人的生命状态的意味更浓了,“怀着寂寞,像山野里的幽灵,/他默默地从大街步进小巷;/生命在每一声里消失了,/化成声音,向辽远的虚空飘荡;”更夫寂寞的灵魂就如这荒野中的孤独的“幽灵”,在黑夜里默默地行走于人世间的大街小巷。他人“喧闹的/脚步和呼喊”,“人的愤怒和笑靥”,对他来说都如“隔世的梦”,他只听见自己生命消失的声音,听见它飘向辽远处,而辽远处却依然是虚空。他是这黑夜中唯一的清醒者,大家都在“温暖的睡乡”,只有他意识到了“生命在每一声中消失”,只有他明白每走一步既代表生命延续了一步,也意味着生命离消失的时刻更近了一步。
由上可见,穆旦写穷苦的女人,流浪人,老木匠、更夫,都不是把他当作从事具体职业的劳动人民来写,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生命的存在来写。穆旦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他自己对生命、对人生的思索。
二、悲观意识与搏斗精神
穆旦曾写过一首诗叫《悲观者的自画像》,表达了他对人类世界的恐惧与绝望。晚年时,他的诗更是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其实,穆旦的悲观在他少年时期就已显现出来了。前面我们提到,穆旦认为“世界不过是人类的大赌场”,“你会看到一片欺狂和愚痴,一个平常的把戏,/但这却尽够耍弄你半辈子。/或许一生都跳不出这里。”(《神秘》)诗中就充满宿命意识,似乎人只是任命运宰割的绵羊。在他的诗中我们看不到纯真快乐的少年生活,只有对人生、命运的悲观思索:“如果人生比你的/理想更为严重,苦痛是应该”,“不要想,/黑暗中会有什么平坦,/什么融和;”(《前夕》)他早就知道人生远没有人想象中的完美,应该比理想“更为严重”,“苦痛是应该”,“平坦”和“融和”只是想象中的美。
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穆旦在少年时代就似乎看破红尘,心里一片灰色,而这却是他沉思人生的必然结果。当一个人想的不是世俗生活,而是奥秘的人生时,他必然会陷入悲观的境地,悲观主义是个体生命沉思者的基调。穆旦思考的问题是“我在哪里”,“我该往哪里去”等人类根本性问题,而这正是现代主义诗人所有的一种焦虑。在西方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一直信仰宗教,认为人是上帝之子,死了之后可以去天堂。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全部的价值信念都崩溃,所以才有了艾略特笔下“干枯的荒原”。中国人没有这种宗教信仰基础,他们没有精神大厦轰然倒塌的绝望,但少数的精神觉醒者也开始寻问自身生命的缘由和意义。然而同样没有答案,一样的充满着焦虑,所以清醒了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悲观。鲁迅的《野草》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痛苦与绝望。冯至的诗也富于哲理与沉思,他同样走向了悲观。冯至在《北游》中哀叹:“一串串的疑问在我心里想,/一串串的疑问在你唇边唱。/一团团运命的哑谜,/想也想不透,唱也唱不完……”“啊,这真是一个病的地方,/到处都是病的声音—/天上哪里有彩霞飘扬,/只有灰色的云雾,阴沉,阴沉……”命运的哑谜是不能思索的,思索的结果只能是看不到“彩霞飘扬”,只有“灰色的云雾”。穆旦沉思的结果自然也不能逃脱悲观的命运。
但悲观并不是最后的“选择”,冯至在悲观中有超脱,穆旦在悲观中却蕴藏着反抗的激情。在《前夕》中,“我”不愿做“僵尸”“冷水”“死灰的余烬”,反而希望加些“干柴”,再“鼓起风的力量”,即使烧了“你的手”“你的头”“你的心”,“要知道你已算放出了/燎野中的一丝光明;”即使烧完,但至少“你”已经燃烧过,“你”已经“放出了”“光明”,而不是“僵尸”、“冷水”和“死灰的余烬”。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会动摇“我”的信念:“我只记着那一把火,/那无尽处的一盏灯,/就是飘摇的野火也好;/这时,我将/永远凝视着目标/追寻,前进—/拿生命铺平这无边的路途,/我知道,虽然总有一天/血会干,身体要累倒!”我们从他的悲观中没有看到消极的放弃,而是更执着的坚持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许多人在逆境中能够坚持,是因为他相信未来一定会美好。而穆旦的坚持是建立在对未来悲观的基础上的,他知道“那一盏灯”还在“无尽处”,而且也许是“飘摇的野火”,他也要“永远凝视着目标/追寻,前进”,哪怕用“生命铺路”,“血会干,身体要累倒!”在少年穆旦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传统中国人甘于现状、顺从懦弱的影子,我们看到的是血性,是激情,是叛逆。穆旦不是鲁迅笔下沉睡的人,而是被他唤醒的少数人之一。穆旦后来深沉的痛苦和搏斗的特性就来自于他既悲观地看透了一切,却又不甘放弃那“飘摇的野火”的执着。他已知道他一辈子的追寻也许只是无意义的牺牲,但如果他放弃了追寻,他的生命将更无意义。也许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追寻本身,生命本没有意义,而是追寻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意义。他的执著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让世俗的我们灵魂无法安宁。他时常让我想起里尔克的一句名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1]张同道,戴定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2]段从学.论穆旦的早期创作[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1):51.
2010-07-28
郑艳君(1979-),湖南邵阳人,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