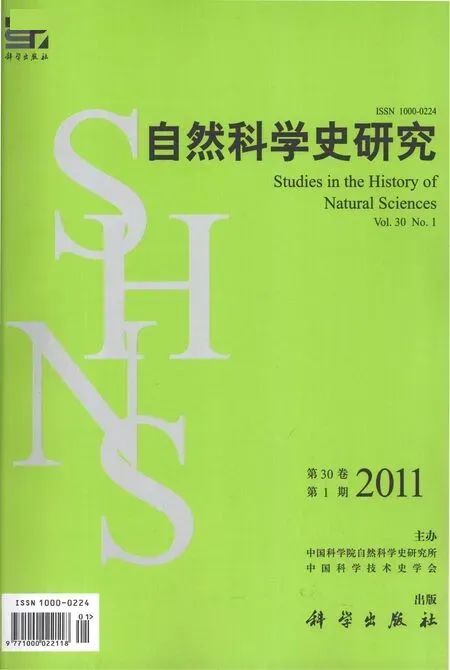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
——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
杜 靖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笔者在《1895—1950年间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教学活动述略》[1]一文中提到,1943年蒋介石曾经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字骝先)研究提高民族素质一案。由于拙作是对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发展状况的回顾,因而当时只对这段案情做了一个简短说明。至于蒋介石在什么情境下饬令中央研究院研究这一问题,以及其如何具体开展和结局之命运,皆未曾详细介绍与分析。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筹备与运作,对于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史来说是一桩非常重要的学科公案,甚至在未来也为我们发展中国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故有必要对其详加介绍与分析。
2009年10月13—17日,笔者重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中央研究院的相关档案。又,2010年7月20—24日,笔者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查阅了吴定良的个人专档。本文就是在这两次阅档以及此前工作基础上对以上两事件的说明。具体包括: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原因、具体内容、开展过程、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筹备情况,以及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与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关系等。
1 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时代背景
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具体包括社会政治因素和由此引发的学术关怀。
南京沦陷以后,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中国中东部地区已不能再作为抗战资源的主要动员地,国民政府不得不倚重西南作为后方。国民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边疆施政纲要,其中说:“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2]当时吴文藻就任中国边政学会的理事兼研究主任([2],221页)。这种情况催生了中国当时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主要从事边政研究,但边政研究主要涉及文化、经济、政治与社会等问题,对于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兵力)等的研究却并不擅长。随着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西迁,体质人类学也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契机。
数年的对日作战,除了少数的如台儿庄战役之胜利外,大部分战役国民政府军都输给了日军,接连丢掉了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大片国土。这有可能使得蒋介石认为,中国军人体质不如日军,因而有必要提高或增强中华民族的素质。因而,欲了解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必须首先放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来理解。
除此以外,似应将这一事件置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之大背景下来加以透观。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全面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在两次中英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和中日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使得中国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为了救亡图存,在近代开展了洋务运动等实业革命,以及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改革。同时,在殖民者对“东亚病夫”的嘲笑声中,一些有志之士开始讨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如,鲁迅等主张从文化上改造民族素质,去除民族的劣根性。
相应地,在中国自然科学界内部也对民族素质改造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由于本文聚焦于利用档案来复原“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和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诞生与运作之历史过程,故就自然科学界有关此方面的研究仅举数端于下。
在体质上较早主张改进人种的学者应该是陈映璜。陈氏在1918年的《人类学》著作里面就专设一章来讨论“人种之改良问题”[3]。后来,潘光旦(尽管潘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但早年在德国却有着系统的体质人类学训练)则比较重视生理改良(从遗传和体质等角度)对改造民族素质的意义。他认为,中华民族存在先天不足,在健康方面有“四大病象”,即“体格的柔韧化”、“科学头脑的缺乏”、“组织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发展”,要整体改良“民族卫生”,增多民族中的优秀分子,淘汰其不良分子。[4]
在生物学意义上主张改善民族素质的人当属张君俊用功最勤,且最为持久。他自民国八年(1919年)起就着手研究民族体质问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如,《中国民族之改造》(1935年,上海)、《战后应否迁都西安——西北建设与民族改造》(1940年,西安)、《中国建军与学生营养》(1942年,重庆)、《民族素质之改造》(1943年,重庆;1944年,上海)、《华族素质之检讨》(1943年,重庆)、《首都地位与民族再造》(1944年,重庆)、《民族健康与营养环境》(1945年,重庆;1947年,上海)。这些作品大多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印刷的。其基本观点是:任一民族如欲保持其优秀地位,必须注意其生物基础、营养环境、文化环境及地理环境诸条件而予以适当配合。①中华民国教育部:《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议记录》,1944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在以上诸背景下,张君俊草拟了一份“增进民族健康计划”呈递给国民党当局②中华民国教育部:《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议记录》,1944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该案的提出,在学术上可谓水到渠成。
2 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具体内容和各相关研究机构对任务的确认
那么,这份“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今把蒋介石的电报原文录下:
中央研究院朱院长骝先兄勋鉴:
查提高民族素质为国家建设之前提。我国民族素质,与并世列强相比较,显形落后,亟应以科学方法做多方面之研究。查民族素质决定之条件,共有四端:一为“生物基础”,包括(子)生物遗传、(丑)血缘与人才之关系、(寅)望族家谱之分析、(卯)人类选种之方法等;二为“营养环境”,包括(子)各地膳食之调查、(丑)各地食物及水土之化验、(寅)维他命B与民族智力、(卯)钙质与民族身长体重等;三为“文化环境”,包括(子)文化与民族素质之关系、(丑)中国文化如何影响民族素质、(寅)何种文化最利于民族素质之改进等;四为“地理环境”,包括(子)民族素质与地理环境之关系、(丑)南北地理环境优劣之研究、(寅)如何作地理环境之调整等。以上各项问题,皆应即交有关各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之动植物研究所、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英庚款会之中国地理研究所,及中国科学社之生物研究所等,分别注重民族改造之有关题材,从事研究,以资改进。除营养问题另交卫生署研究外,希即分别转知各该机关照办为要。中正午元俟秘。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③蒋中正:“侍秘总字第18440号”电报,1943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这份电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标点即由本文作者据原电报稿句读推敲而添加。
显然,在蒋介石眼里,当年的民族素质问题涉及到了生物基础、营养环境、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四个方面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两个维度,即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但这里的“素质”主要指的是“体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以下同)解释为:“素质者,即由父母血统遗传之特性,俗所谓禀赋是也。素质之为善为恶犹自见先天者居多,其受文化环境与教育之影响者甚少。”④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总字第0165号”公函及附件,1944年2月15日(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1373)。
蒋介石的电令下达以后,在具体分工上如何呢?
1929年叶企孙成为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以后曾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名义主持过校务。抗战爆发后,他在西南联大任教。1941年9月至1943年8月,叶企孙赴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蒋介石的这份来电先由叶企孙看过,当时由沙孟海(1941年6月在重庆经陈布雷推荐,在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任职,从事应酬笔墨文字)处转达代电。叶企孙于1943年7月22日在给沙孟海的回函中说:“(除)五个研究所外,弟当在昆明约集西南联大之潘光旦、陈席山、汤佩松等诸教授详细商讨代电中各项目,并拟出几个确实能着手研究之专题,以便呈报。”①叶启孙:“给沙孟海回函”,1943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而当时潘光旦尚在安顺演讲。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于1943年8月12日,以总字第0812.1号电报下达了通知,要求各所(包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动植物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结合自己情况落实相关研究项目和内容,然后就研究计划和内容进行汇报。②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处:“总字第1224.3号”公函,1943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1943年8月16日动植物研究所给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回电,选中了第一端中的“生物基础”的前三项,即,“生物遗传、血缘与人才之关系、望族家谱之分析”。而且,还要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商讨后再确定各自的分工范围。③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总第619号电报”,1943年8月16日(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22422号电报催促动植物研究所进展情况。1943年12月27日,动植物研究所回复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正在进行“望族与人才之关系”一项研究,但还没有什么结果。④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代电总办事处”,1943年12月27日(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1943年8月28日,中国地理研究所回函中央研究院,已指派人员研究“民族素质与地理环境之关系”。⑤中国地理研究所:“总字第667号公函”,1943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在接到1943年12月24日中央研究院“总字1224.3号”公函(该函催问“提高民族素质研究事项”)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于1943年12月31日复函。其答复情况有如下几条:第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已会同中国地理研究所商讨,但并没有产生具体计划;第二,与史语所吴定良私人通函商议,认为短期内恐难竣事,暂拟汇集一些论文印成专刊来响应(原文用“副”)“委座倡导之厚意”;第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卢于道拟先用过去研究结果,就“中国人脑之研究”、“中国青年之身心类型研究材料”草就论文付梓。其基本观点分别是:中国人大脑皮质之显微构造与西洋人比较并无差别;中国青年在身体方面多运动型及瘦长型,在心理方面多外向型。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总字第1096号”公函,1943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1944年元月5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回复年前即1943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2月份之催促函。在这份回函中,社会科学所觉得研究提高民族素质与他们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距离。具体相关回函是:“……,近经本所对此问题慎重考虑后,觉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均极复杂,其于民族素质之影响极为微妙,测验匪易。本所仅可于研究社会经济、行政各种制度或问题时,评骘其优劣,以视其对于民生之影响,至于民生为何影响民族素质,则犹有待生物学之研究,本所无法直接从事探讨。”⑦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总字第0014号”公函,1944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1944年元月22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处又发总字第0122.2号函催促史语所,希望就委座所饬“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初步研究计划尽快回函说明。①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处:“总字第0122.2号公函”,1944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1944年2月15日,史语所在回复电文的附件中认识到:“提高民族素质为人类学与优生学者之主要职务”。考虑到当时史语所内之现有仪器、书籍、设备等条件,就“委座”所示提高民族素质之“生物基础”所涉及的四类问题的性质、重要性及其短期内可以担任的工作进行了汇报。第一,人类遗传研究为素质改良之基本问题,然而当年在国内却尚未开始研究,考虑到工作条件,史语所决定暂时以川南各县为范围、以学校儿童及其家庭为调查对象,开展“普通体质之遗传”、“几种变态体质之研究与其遗传”、“各宗族血液血型之类别与其遗传”、“低能儿童生理与心理之变态及其遗传问题”、“犯罪性之分析与其遗传问题”、“癫狂生理与心理变态之分析与其遗传”、“双生子之研究与其遗传”、“天才生之研究及与祖先之关系”等8个方面的问题。第二,在“血缘与人才关系”方面,他们赞成“杂交”,反对“近亲结婚”,认为:善的素质多因移民与各族杂婚关系而增加数量,恶的素质乃系血族或近族结婚之关系所导致。他们注意到,汉人社会里的女系“表兄妹婚”与边疆地区的近亲结婚均较普遍,这对于后代智力与体力均有莫大之影响,因而急应进行系统调查,就近亲结婚与远亲结婚的后果作一比较,权衡利害,以作人民选择婚姻的标准。具体要开展的内容有“各宗族杂婚与素质改进之关系”、“移民与人种改进之关系”、“近亲缔婚与后嗣品质之关系”、“边疆宗族血族或近族缔婚之结果与其流弊”、“早婚与子女品质之关系”等5个问题。第三,在“望族家谱之分析”中,他们较为注重家谱,因为里面包含了“同族各个人之出生与死亡年月、子女出生与死亡数目及著名人物之事业与著作”等内容,当然也存在不记录女系资料的缺陷。他们打算在各图书馆搜集望族族谱资料,拟从事“各望族著名人物功业之分析及与遗传之关系”、“家族素质之保全问题”、“历代平均人寿之变迁”、“各民族生命表之编制”、“各民族儿童死亡率之比较”、“婚姻年龄与繁殖率之关系”、“异族混合时代之现象”等7方面内容的研究。第四,在“人类选种之方法”方面,当时各国所采用的主要有积极方法与消极方法两种:前者指的是通过提高男女配偶之选择标准以增加优秀分子之生殖率,后者乃对于社会低劣分子实行近婚隔离或消灭生殖机能等方法。鉴于当时人种改良的科学知识对国内民众尚未普及之状况,该所拟先提倡积极方法。为此,需先期开展调查与研究,然后作为实施优生政策之参考,内容包括“各种消极优生方法之抽样实验”、“各社会阶级繁殖率之比较”、“生育节制与优秀分子生殖率之关系”、“抗战与优秀分子生殖率之关系”4个方面。此外,史语所也意识到文化人类学者所关心的自然及文化环境对人类素质的影响,尽管这两个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对人类遗传发生作用。针对本院地理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分别负责这两个问题的情况,史语所“史学组”也打算随时跟进以作“文化比较”研究,探索中国“国民性”的各种问题,并讨论这些因素对于人种选择之影响。约略数端:“历代民族精神之改变”、“各派思想各类宗教如何影响人种选择”、“各时代人民之生活方式”、“魏晋以后文武分途之影响”、“征兵募兵制”5方面内容。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总字第0165号”公函之“附件”及“附记”,1944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上述表明:在1943年7月13日至1944年2月15日这段时间里,“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一事最初由蒋介石下达命令给中央研究院,然后由中央研究院牵头交相关研究机构进一步研讨和落实各自的研究任务和计划。其中,史语所是主力军,其所拟研究内容和计划最为详细可行。
在各相关研究机构意见基础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等待对其加以汇总,提出一份明确的分工研究计划,联合各方面论证并审查之,以便统一协调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
3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及工作开展情况
1924年孙中山北上,倡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聘派蔡元培等筹备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②朱家骅:《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序”,1948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0024)。在总院筹备的同时,与本案研究有关的两个重要研究所也开始筹备。1927年冬筹设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3月正式成立,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平所设立的社会调查所合并,初分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制学4组(蔡元培为民族学组第一任组长,林惠祥1929年为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③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261、229页,1948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0024)。1928年春于广州筹备史语所,同年10月正式成立。初分3组:一为史学组,二为语言学组,三为考古学组(根据该所章程,先后设过8个小组,其中第7组为人类学与民物学组④我在《1895—1950年间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教学活动述略》一文中把“人类学与民族学组”写成了“人类学组和民族学组”。本来一组,因文字输入有误,变成两组。给读者造成了误识,在此予以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伊始,人类学与民物学组没有聘请到合适人选做主任,暂由俄国人史禄国担任组长。1929年5月史语所迁到北平,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归属丙组,李济任组长⑤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经过与组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印,1929年。)。1934年社会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其研究范围包括体质及文化方面)移归史语所为第四组(主要是体质人类学部分移入)。⑥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8页,1948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0024)。
1934年,遵照刚担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的丁文江博士建议,研究所新设了一个人类学组,并聘请就学于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年)生物测量学实验室的吴定良主持该组的工作。吴定良江苏金坛人,1916年考入江苏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后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心理系。1924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1926年8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伦敦大学生物统计学实验室,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生物统计学派创始人、著名统计学家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教授。该实验室源自英国优生学领导人高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年)。生物统计学实验室的早期主持人有卡尔·皮尔逊和费舍尔(Ronald Fisher,1890—1962年),后者也是一位杰出的生物统计学家。学习期间,吴定良就发表了《相关率显著性查表》和《相关系数计算法》等多篇统计学论文,深得卡尔·皮尔逊教授和师兄们的欣赏。1928年他顺利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建立了眉间凸度与面骨扁平度的研究方法,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耶尔(G.U.Yule)教授介绍,被选举为“国际统计学社”社员。1929年《泰晤士报》报道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发现的消息。吴定良甚为激动,并暗下决心钻研人类学。在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补助费后,他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学习人类学。他与导师皮尔逊、著名人类学学家莫兰特(G.M.Morant)合作,有时是独立研究,在英国著名杂志Biometrika和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and Proceedings of Royal Society,以及剑桥大学的Philosophical Magazine上先后发表了《人体内特有骨骼的形态测量学特点的进一步调查》、《对人的面部骨骼扁平度的生物统计学研究》、《依据头盖骨的尺寸对亚洲人种的初步分类》等统计学和人类学方面论文50余篇,以优异成绩再添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经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梅耶斯(J.J.Myers)推荐而加入了“国际人类学社”,并在当年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人类学社”年会。1934年夏天,吴定良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9世纪头骨研究,发表了《对埃及九世纪七十一个头骨的研究》。([5],22—24页)
这个组的工作范围虽包括人类学各不同方面的研究,但分派给吴定良的直接任务则是研究考古组在野外收集并迅速积累起来的商代人骨[6]。1935年夏吴定良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同年,吴汝康高中毕业后到史语所人类学组吴定良手下任计算员。([5],24页)吴定良在1940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二卷上发表了《殷代与近代颅骨容量之计算公式》、《中国人额骨中缝及颅骨测量之关系》、《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与颜訚合著)等著作。但更主要的工作是常年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体质调查。如,1941年6月至1942年9月中央研究院派吴定良等赴黔、甘、新等省考察人体体质及相关文化。①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派吴定良等赴黔、甘、新等省考察人体体质文化有关文书》,1941年6月—1942年9月(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52)。
在吴定良、颜訚等人工作以及史语所人类学组设置之基础上,恰逢蒋介石“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电令之下达,他们遂萌生了欲办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想法。因为,只有成立一个独立的研究所才能完成蒋介石所交办的任务,并发展中国体质人类学。1944年4月,中央研究院依据该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决议案,将史语所下的人类学组独立出来,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②吴定良:《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两年筹备情形之经过》,1944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632)。然后,经呈奉国民政府“本年度五月二十五日渝文字第七一八号指令,准予备案”③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33)乙总字第0602.1号”文件,1933年6月2日(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0—2503)。。但时逢抗战,欲办一个研究所是极其艰难的。
1944年11月15日,朱家骅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草稿中,一方面汇报“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进展情况,一方面要求增加研究经费,同时请示是否让吴定良就研究提高民族素质一事向蒋面陈。兹将这份送达蒋主席的公函全文公诸如下:
案查去年七月奉钧座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侍秘字总第一八四四零号午元代电,为提高民族素质一案,分别项目,提示问题,饬即转知有关部门详事研究,以资改进等因,当经遵电分别转知本院动植物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英庚款会之中国地理研究所,及中国科学社之生物研究所等遵照办理在案。提高民族素质之研究为人类学方面之主要任务,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原设有人类学一组,并已注意研究此项问题,惟自抗战军兴以来,经费数目及增购设备均受不可避免之限制,致此项工作仅能择要进行,未能充分发展。此次既奉交办,自应加强工作,冀有以仰副钧座之期望,但原有之规模太小,设备未充,实难负荷此重大之使命。爰拟依照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之本院组织法,将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人类学组分出,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经提出本院详议会年会通过,并经呈奉,核准备案。一俟设备充实,即正式设所。在筹备期间,加强研究人员,利用原有设备,一切研究工作仍照事继续进行,并已就“生物遗传”、“血缘与人才之关系”、“望族家谱之分析”及“人类选种方法”等问题,更分细目,着手研究。据该处吴主任定良面称,该处现有之设备,故可勉强应付工作计划所列研究事项之需,但为了遵照钧电提示之各项题目一一进行有效之研究,仪器、图书之添置势不可缓。此种仪器、图书均为国内所无,又不得不求诸海外,估计购置研究遗传与优生问题之仪器约需美金肆万元,研究民族生理病理与心理等问题之仪器约需美金叁万元,各种参考书籍等需美金约叁万元,共需美金拾万元。本院经费为数有限,除支付经常用项外,此项设备费既无从挹注。拟请转请政府特准拨发,以利工作等情。查该主任所称确属实情。该主任为目前国内有名之人类学专家,并系本党同志,前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内主持人类学方面之研究,成绩优良,深得国内外学术界之重视,倘蒙核准,发给上述之设备用费,必可缩短筹备期间,早日正式成所,获有更为良好之表现。可否请钧座特赐召见?俾该主任得详陈一切,面请指示?
所有拟请核拨研究提高民族素质各专题设备用费及召见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吴主任定良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具文呈请鉴核,批示祗遵。
谨呈主席蒋①朱家骅:“中央研究院总字第1115.6号公函”,1944年11月18日(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朱〇〇谨呈
三日后,即11月18日,对这份电报又略加修改,将“一俟设备充实,即正式设所”改写为“该筹备处已于本年四月正式成立”;将购置研究遗传与优生问题之仪器约需美金“肆万元”改为“约值国币捌拾万元”;将“研究民族生理病理与心理等问题之仪器约需美金叁万元”改为“约值国币陆拾万元”;将“各种参考书籍等需美金约叁万元”改为“约值国币陆拾万元”;将“共需美金拾万元”一句删除,亦未添写一句“共需国币贰佰万元”的字样。在“一一进行有效之研究”后添写“期获最后之成果”一句。改写后的电报稿之结尾处(即从“现时所能购求之参考书籍约值国币陆拾万元”至“理合具文呈请鉴核”)有较大调整,具体是:“倘蒙政府特准拨发此贰佰万元之设备费,即可诚为规模较为完备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为■(该字暂不能确认)缩短筹备期间早日正式成所起见,可否能为呈请核示等情。查现在抗战期内,用费浩繁,国家之负担已不为不重,又何敢率为额外之请求,致增财政方面之支出?惟该主任所称全系实情,仪器图书之扩充确为开展研究工作之基础所请是否可行?”其他地方虽有个别文字变动,基本意思不变,故未一一指明。
修改后的文稿,在语气上更加婉转,且将吴定良面陈蒋介石一事删除。但修改稿并无正式文件编号,亦无中央研究院印章和院长朱骝先签字。而这三项在11月15日稿上均有出现,故本文详录11月15日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5年1月18日以侍秘字第25932号电报致函教育部:
一月十二日高字第一七一二号呈民族素质改进研究办法可唯照办。至关于此项研究经费希暂就各研究机关原预算内匀支,俟著有成绩或有特殊需要时再行酌核补助可也。①中华民国教育部:“高字第05768号”公函,1945年2月6日(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案:“高字第05768号”公函发于1945年2月6日,可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因内容相近而归在393.2124号档案“中央研究院提高民族素质案”中,封面题写时间为“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此有误。本文还有其他类似情况不再一一说明,读者可自辩明之。
笔者未能找到教育部的高字第1712号函。但从中不难发现,教育部此前曾经于1945年1月12日以高字第1712号函形式,将民族素质改进研究计划、办法和经费等问题报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可是,军事委员会并没有拨钱给他们。
实际上,1944年教育部就过问改进民族素质案了。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教育部组织各有关机关团体及各专家就“民族体质改进研究计划草案”在重庆进行了详细研讨。教育部在1945年2月6日给中央研究院的电函中说:
……关于民族素质改进研究一案,本部曾于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渝召集各有关机关团体及各专家予以详细研讨。
贵院人类学研究所及动植物研究所均派代表出席该项会议。相应随函检送该项会议记录四份及本部原拟民族体质改进研究计划草案一份。即希查照转知该所等将各有关研究问题即行着手研究,并将研究计划先行开送过部,以便统筹办理为荷。
此致
部长朱家骅②中华民国教育部:“高字第05768号”公函,1945年2月6日(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
至于先前由中央研究院具体牵头负责,为什么此时却由教育部来出面。笔者未能找到相关档案给予说明。不过,笔者推测首先与朱家骅个人有关。1931年12月朱家骅调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任部长,1932年连任教育部长(以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4年4月又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1944年再任教育部部长,1945年4月又连任教育部部长。继蔡元培之后,朱家骅自1940年9月至1950年10月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由于这种复杂的工作阅历,当然也是一种便利,使得改进民族素质一事交由他负责。其次,由于涉及中央研究院以外的其他单位,以教育部出面召集更为合适。当然,这尚需具体的档案发掘来印证。
那么,这个筹备处是如何具体开办的呢?其人员组织结构又当如何?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在办公条件方面,中央研究院并没有指定或代觅所址,一切均由吴定良个人来筹办。当时是在南溪李庄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1938年秋迁至昆明北郊之龙泉镇。1940年8月复奉命迁向四川,是年底到达南溪县李庄。,筹备处临时租了一处张姓房产(原为四川省立宜宾中学临时校址)。房子多数已腐朽,门窗户壁业已残缺倾颓。吴定良四处筹挪资金,甚至将个人薪津也垫支进去,先行购买木料。大约了花费了6个月时间,始将4间实验室、2间办公室、9间职员宿舍修理完毕,并且添置了100多件家具。
从1944年12月份领粮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计有12人,分别是专任研究员兼筹备处主任吴定良,副研究员颜訚,助理研究员史济招、王志曾,助理员陈凤梧、杨希枚,技师刘冠生、廖伯梅,技佐陈文永、师伦禄、谢据林,事务员李运昌②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人事、办公费、生活费等文书”,1944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0—2503)。。其时,还有吴汝康。1940年夏,吴汝康学成归国重返史语所,在人类学组做研究实习员。1942年至1944年吴定良受聘贵州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吴汝康追随吴定良至贵州大学社会学任讲师,教授了两年人类学课程。([5],53—55、63—64页)应该说明,此时的吴定良和吴汝康身份仍在中央研究院,去贵州大学只不过是兼职。所以,1944年史语所从昆明前往四川南溪李庄时,吴汝康也随行,并任体质人类学筹备处的助理研究员,负责协助吴定良安排一切筹备工作。([5],64—67页)
在图书购置方面,本来毫无基础,自成立后设法采购必备的中英文书籍。其中,中文资料尽量少购,仅百余册。英文方面一是向中英科学合作馆索取了人类学、优生学杂志四五种,一是订购英美专业杂志五六种和书籍五六百册。当时弄到外汇是极其困难的,吴定良在重庆利用个人关系向战时生产局及中央银行多方设法购买,最后大约只得到12000美金和1600英镑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仪器方面,当时由史语所分出后,仅有2架显微镜、1架双眼镜、3架计算机,其他仪器未转入。另外,卫生署和红十字会捐赠了几种仪器。至于其余的,则由筹备处用木料或金属仿制若干种以应急需。
在标本采集方面,于李庄附近及宋嘴荒地发掘义冢共得近代颅骨与体骨两组,约百余具。
在研究人员训练方面,由于当年所聘助理员及研究助理员多半来自生物学和医学,对人类学未深得门径,故在工作之余,由吴定良开设人类学概要和统计学概要,以及教授测量技术,加以培训。使得其中3人能够担任活体测量和儿童发育测量、能够研究血型者3人、能够测量骨骼者2人。因而,两年筹备期间,完成了4篇调查论文,2篇正在撰写,还有2篇正搜集资料。
在学术成果方面,筹备期间吴定良完成4篇论文并送至国外科学杂志发表,国内已编就《人类学集刊外篇》两册(其中一册已印刷,另一册编好待付印)。①吴定良:《国立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两年筹备情形之经过》,1946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 393.2632)。
另外,当时征兵验兵标准也交由该筹备处负责。比如,对于飞行员与驾驶员的体质指标涉及四肢、体质强弱、皮肤、呼吸、心脏、静脉病、嗳气、吐泻、肾脏、疝气、花柳病、脑、脊髓、神经疼、末梢神经偏疼、眼花、恶心、精神、神经衰弱、色盲等内容。体质人类学筹备处在1944年11月份的《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中所规定的体质标准有“身长一百五十二公分以上”、“体重四十六公斤以上”、“胸围七十六公分以上”、“五官四肢及肺脏正常”、“无重砂眼、痔疾及精神病”等5项指标。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1944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0—2503)。
鉴于吴定良氏在抗战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五年向其颁发了“胜利勋章”一枚:
勋章证书
国民政府为吴定良在抗战期间著有勋绩,特颁给胜利勋章。
此证
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
国民政府典玺官 徐静之③复旦大学“干部档案.吴定良卷”(档案编号:No.479),正本.5类.3号。
在中日战争时局下,不论从办公条件、研究经费,还是研究队伍等各方面看,体质人类学筹备处的工作开展是极其艰难的,尽管当时国民政府给予支持。
4 “民族体质改进研究计划草案”与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议
当年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议的地点设在重庆教育部大礼堂内,具体时间是1943年10月26日上午10时至12时,出席团体代表有中国卫生教育社洪式闿代表、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童第周代表、社会部民族健康运动委员会叶毅代表、行政院民食改进委员会陈世昌代表、社会部谢征孚和刘崇龄代表。另外,个人出席有陈果夫、赖延、吴南轩、洪式闿、欧阳翥、吴功贤、吴蕴瑞、张君俊、江良规、王复旦、吴定良、戴天右、王成发(代表吴宪出席)、郝更生、萧忠国(代表程登科出席)、吴俊开、吴正华、韩庆濂。教育部次长赖延作会议主席。大会首先由赖延作报告,说明为什么召开这个会议以及召集本会议的经过。然后,陈果夫和张君俊分别作大会发言。陈国夫谈论的是对民族健康问题的关心,张介绍了自己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民族体质问题以及向当局呈递“增进民族健康计划”及建议而被采纳一事。
大会发言之后,安排了分组讨论。第一组讨论“体质(包括遗传优生)问题”,吴定良和欧阳翥为召集人,参加人员有张君俊、戴天右、欧阳翥、童第周、吴南轩、刘崇龄;第二组讨论“生理(包括卫生营养)问题”,陈果夫、吴宪(王成发代表)为召集人,参加人员有洪式闿、吴功贤、吴正华、陈世昌;第三组讨论“体格训练问题”,吴运瑞和江良规作为召集人,参加人员有郝更生、萧忠国、叶毅、江良规、王复旦、程登科(萧忠国代)。会上临时动议:第一,建议教育部设立民族素质改进研究委员会;第二,“民族体质研究”以改称“民族素质研究”较为适当。
现把三个小组对于教育部所提“民族体质改进研究计划草案”讨论的结果分别列下:
第一组:遗传与优生
(1)关于优生政策实施方案之研究者,决议:原则通过消极与积极并重。
(2)关于各区域人民体质标准(体格与智力)之研究者,决议:由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中大生物系与心理系、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中央卫生实验院和私立民族改进研究所负责研究。
(3)关于国内各地人民结婚后其子女身心健康之研究者,(4)关于不同民族婚生子女体力与智力之研究者,决议:将此两项合并到第2项中。
(5)关于生物与遗传之研究者,决议:改为“人类遗传之研究”,由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中大生物系、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浙大生物系、民族改进研究所担任研究任务。
(6)关于血缘与人才之研究者,(7)关于望族家声之分析者,(8)关于人类选种之方法者,三项合并到第5项中。
第二组:卫生与营养
(1)关于全民卫生教育实施方案之研究者,(2)关于树立卫生教育机构以普及妇婴及儿童教育、营养教育与健康生活教育者,(3)关于大量培育医药技术人才以完成公医制度以保障全民健康者,决议:以上三项请教育部与卫生署暨其他有关■(一字因纸张腐烂莫辨)卫文化团体商讨进行。
(4)关于树立定期全民体格检查制度以求切合实际之研究者,决议:请教育部商由卫生署主持办理。
(5)关于调查各地价廉质美之日常食品以期拟定合于民族健康之食谱者,决议:请中央卫生实验院主持并请其他有关机关进行调查研究。
(6)关于各地食物及水土之化验者,决议:关于各地食物分析请中央卫生实验院卫生营养实验所负责研究,关于水土化验请中央农业试验所负责办理。
(7)关于食物与民族智力之研究者,决议:由教育部指定各学校暨心理生理营养研究机关试验测定其相关程度。
(8)关于研究并测定中国国民营养需要标准者,决议:请政府指定或成立研究机关专责进行。
(9)关于地方性营养缺乏病与寄生虫病问题之研究者,决议:请中国预防医药研究所、各大学寄生虫研究学部暨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研究。
(10)关于民族体质改进者,决议:由各大学学系研究部门及研究团体分别进行研究,其结果汇由教育部组织民族体质改进委员会综合整理。
第三组:体格训练
(1)关于全民体格锻炼实施方案之研究者,决议:由教育部拟定全民体育训练纲要,使全国国民均有普遍受体育训练的机会,该项计划需与义务教育、兵役制度相配合。其全部训练分三个年龄段实施:一、6—12岁在校儿童,加强小学体育训练,未入学者则由社教机关施以体育学训练;二、12—18岁中学生根据部颁中学体育实施方案实施体育训练,并加强学校童子军活动,未升学者参加社会童子军训练及社教机关主办之体育活动;三、18—20岁兵役阶段,成年以后普遍实施社会体育,由教育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童子军总会兵役部等机关共同负责筹划。
(2)关于不同地带人体发育之比较研究者,决议:先就川、滇、黔三省之小学、中学举办体高、体重、胸围、肺量等有关身体发育项目加以测量及统计,以后再研究其他地区上项工作。由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及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共同负责研究。
(3)关于男女各年龄身长体重之正常比例研究者,决议:由教育部体育委员会中华体育学会及全国体育师资训练机关与有关团体分别测量。先测量10万人,并加以统计。
(4)关于幼童与青年体格之缺点及矫正方法者,决议:青年部分已研究有结果,幼童部分仍由中华体育学会同中央卫生实验院继续研究。
(5)关于营养与运动功能之研究者,决议:归入第二组中讨论。
(6)关于男女体格体能之差异及其适宜之运动的研究者,决议:由中央大学体育系先就解剖、生理、情绪及社会地位四种差异加以研究,然后研究适宜运动项目与方式。
(7)关于工作持久力之训练方法者,决议:改为“运动与工作效能之研究”。由西北师范学院先就工厂工作、空军驾驶及海陆军三方面研究。球类、国术、田径运动项目对于工作效能之影响。
(8)关于体力训练与技巧训练研究者,(9)关于太极拳对于体格训练之功能者,决议:两项取消。
由上述讨论可以了解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民族体质改进研究计划草案”。但关于这份计划草案的拟定者,由于未能找到相关档案暂时尚不能确定(比较后发现,教育部的草案是在张君俊“增进民族健康计划”基础上进行起草的)。显然,这个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议目的在于,由国民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各大学院校有关学系及研究学部有关研究学术机关及专家来表决这份草案,以及提出更加具体的研究计划来。
国民政府教育部“民族体质改进研究计划草案”的最后是一份关于上述研究“进行步骤”的说明,共三点。第一点上段已经阐明;第二点是教育部打算呈请行政院对研究作出成就的大学院校、研究机构及专家拨款给予补助;第三点交代了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负责审议各大学院校、研究机构及专家之研究计划及研究结果。
本小节系根据“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议记录”和“民族体质改进研究计划草案”两份档案①沈灌群、叶佩华:《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议记录》,1944年10月26日(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124)。撰述。不论就其意义,还是就出席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涉及的诸多学科而言,“民族体质改进研究会议”都是百年中国现代人类学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其意义不止于人类学一域,如体育、营养、卫生、地理等等。
5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流产与反思
中日战争结束后,正当吴定良等继续为筹建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所而努力的时候,却迎来该所是否应该继续建立的问题。
1946年1月竺可桢等所作出的评议是:停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业务①竺可桢:“关于停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业务函”,1946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01—1585)。。当时竺可桢等接受谁或哪个机构的命令对此事作出评估?尚未找到具体的档案材料给予落实。不过,笔者推测,不外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两个机构,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可能性极大,原因是上文已经表明,此一段时间,教育部接管了研究增进民族素质案。
那么,为何要停止体质人类学所的筹备呢?《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说:“1946年夏,因经费不充,发展困难,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暂停筹备,器材仍交给史语所接收。”②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8页,1948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393.2—0024)。向史语所移交标本仪器以及有关殷墟骨骼研究资料的时间是1947 年,由杨希枚具体负责。[7]
1946年秋,吴定良离开了中央研究院,接受竺可桢邀请前往浙江大学史地系担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和统计学课程。1947年春,史地所增设人类学组,吴定良任组长。1947年秋,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建立,吴定良任系主任。1948年1月该系师生成立人类学学会。1949年初,吴定良在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研究所,并任所长。([2],303页)
我们从上文的资料看,该所筹备期间的确遭遇经费困扰。吴定良说:
时值抗战期间,图书、仪器均感缺乏,而所获经费为数甚微。三十三年度本处开辟费仅10万元,三十四年度增至90万元,仍为本院各单位经费最少者。两年以还,惨淡经营,不遗余力,规模粗具,不幸奉命停办,致使前功尽弃,以往心血悉付东流,诚科学界莫大之损失,亦良个人所深引为痛心者也。③吴定良:《国立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两年筹备情形之经过》,1946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 393.2632)。
然而,就在上述所引同一份文献中,吴定良披露该所停办的原因似另有隐情:
两年以来,耗尽心血,力图发展,抚衷自问,实无负于本院。而流言中伤,谤毁交至,射影含沙,无所不用其极。良诚百思莫解。是非曲直,有心人当能明了也。④吴定良:《国立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两年筹备情形之经过》,1946年(档案编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 393.2632)。
1947年吴定良辞去了中央研究院的工作。然而,究竟因为什么大家对吴定良产生了流言蜚语?多年来,笔者追查这段公案,终于找到一些线索。其中一条线索是由李济提供的:
日本人从卢沟桥开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批材料的大半都遭到损毁;所幸的是,仍有足够数量的头骨和其他体骨顺利地运往西南,可供充分研究商代中国人民的体质特征。研究所的人都知道吴定良博士是一位有能力的生物测量学家;他对这批殷墟材料连续工作了十多年,配备了战争期间用钱所能买到的最好仪器和他所需要的技术修理和抄写助手,尤其是彼此友好而热情的工作环境。研究所考古组的成员完成了发现和全部采集工作,并担负了全部的保管和运输任务,将这批极有价值的材料毫无保留地交到他的手里,并相信他能完全胜任这项在现代科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工作。可是到1947年,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们期待了13年之后,他在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下辞离中央研究院,并断然拒绝《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主编发表他的研究结果!一直到现在,又过了6年之后,也还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过发表他的结果的打算,即便有过这种想法,在台湾也没有人知道。[8]
从李济的这段文字里隐约可以猜到,当年大家对吴定良在安阳商代人骨上的研究工作存有不满意①安阳侯家庄的人骨材料后来随史语所被运到台湾。无意中在骨骼标本中发现了吴定良的几本笔记,里面记录了161具侯家庄头骨的一些测量数据。之后李济将其整理予以发表(参见李济著,潘其凤、韩康信译,杨希枚校:《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一文)。。也许正是这种不满意才导致了大家并不支持他建立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所。1951年李济在一篇纪念傅斯年的文章中说:“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为整理安阳出土的殷商时代的人骨,这一课题直到1947年吴定良先生辞职时,尚未缴卷,实在是中国科学研究的一大遗憾。”[9]
另一条线索则是由吴定良本人于1950年后提供的,涉及人际关系问题,认为吴定良离开史语所是受傅斯年“逼迫”所致②《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吴定良),见复旦大学“干部档案·吴定良”卷(档案编号:No.479),正本·4类·9号,1952年8月8日。。具体有两段材料对此有详细披露。
材料一:
……反动派朱家骅听任其心腹傅斯年的话,对人类学研究所横加阻碍(人类学研究所系抗战期间,该院评议会通过成立,傅斯年坚决反对,未得逞,遂怀恨在心)。摧残科学,排斥异己,并藉口编缩,停办了人类学研究所。③吴定良:《思想改造材料》,复旦大学“干部档案·吴定良”卷(档案编号:No.479),正本·5类·5号,1956年6月14日。
材料二:
……那时鉴于史语所所长,傅逆斯年对于他的平行科目,大事扩充,其他科目,视如装饰品,诸事掣肘,难于发展。胜利前两年,我拼命企图分出来,单独设所。事前曾和别位接近傅逆的评议员说好成所的理由,自己并在事前预备好一篇演讲稿。评议会开会时,傅逆主张设室,我就立起来说明设所的理由,当经全体评议员通过,傅逆认为大失面子,怀恨在心。这时我心中却很高兴,多年的欲望居然如愿。当时我想脱离傅逆的肘腋,是为了提倡人类学,同时也是受了名心的鼓动。……当时认为我(案:吴定良写检查材料时可能漏掉一个“在”字)史语所的地位,就人类学说,并不比其他所长学术地位低,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并列?傅斯年想克扣公粮,我就跑到粮食部讬留英同学帮忙;他不给经费,我就自己向红十字会友人请求帮忙,给我写设备;他控制经费,我就讬伪院长代为设法;他把伪院长代我向军事委员会请款的计划粉碎了,我就讬重庆市长向电影院募款,拼命与恶势力奋斗。终因没有政治势力,遭到傅斯年假造罪状,把我两年来的经费的一些根基全部收回,整个垮台,并把全部设备,拿到台湾去。①吴定良:《思想检查材料》,复旦大学“干部档案·吴定良”卷(档案编号:No.479),正本·10类·3号,1952年。
从吴定良的上述“交代”中可以看出,他与傅斯年的确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也导致了人类学研究所的流产。除了个人人际关系因素外,我觉得傅斯年之所以反对单独建人类学研究所,恐怕与他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理解有关。史语所最初引进吴定良的目的在于专心致力于安阳殷墟人骨之研究,服务于史语所的考古学。据王道还研究,1934—1935年的两次殷墟发掘获得了一大批人骨需要分析,李济由于担任安阳殷墟发掘的总主持人而无法分身,于是就聘吴定良进史语所第四组主持体质人类学研究。而吴定良进入史语所后所发表的论文,则多偏重技术性的讨论,没有充分利用殷墟出土的材料。[10]这种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设想、安排与吴定良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理解存有出入。
总结上文,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积弱积贫致使在遭遇外敌的情形下,中国文化处于被压抑的地位,遂使得有识之士力倡改进中国民族素质。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作西南迁移,为了动员战争资源,蒋介石高度重视国民素质改进问题,希望借助增强人民体质等来打败日人,赢得战争的胜利。蒋遂饬令中央研究院(后来教育部也介入)等研究机关就“提高民族素质”一事着手进行研究。其涉及生物基础、营养环境、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四个方面的问题。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体质人类学的全面理解,以及对体质人类学之价值的认识。应该说,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具有一种颇为超迈的科学眼光。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因应而生。在吴定良等人的努力下,经两年惨淡经营,致使规模初具。然而,由于战争问题,国民政府无暇将更多精力用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加之资金短缺,以及人际关系等其他因素,致使筹备了两年多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最终流产。
致 谢初稿完成后,我的导师吴新智院士通篇阅读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计划,在此表示感谢。评审专家对拙稿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和建议,使得文章在修改后更加坚实有力。编辑部转来审稿专家意见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道还先生,王先生利用来大陆参加学术研讨会契机将其大作及时赠予我,使得拙作得以修改补充,甚为感动。最后感谢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和复旦大学档案馆的帮助。
1 杜靖.1895—1950年间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教学活动述略[J].人类学学报,2008,27(2):182—190.
2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M].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3 陈映璜.人类学[M].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236—247.
4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M].潘乃穆,潘乃和编.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7—50.
5 李路阳.吴汝康传[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6 LiChi.Noteson somemetrical charactersof calvariaof the Shang dynasty excavated from Houchiachuang,Anyang[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九号)[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39—148.
7 杨希枚.整理殷墟人体骨骼之经过[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九号)[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5—48.
8 李济.安阳侯家庄商代墓葬人头骨的一些测量特征[A].潘其凤,韩康信译.杨希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九号)[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32—138.
9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A].傅所长纪念特刊[C].台北:“中央研究院”,1951.11—19.
10 王道还.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A].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16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