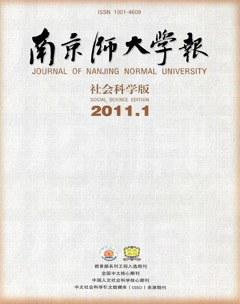论鲁迅“幽暗意识”之表现及由来
摘要:鲁迅有极深的绝望体验和幽暗意识,日本学者称之为“舍斯托夫体验”。在鲁迅具体表现为:死亡意识、忏悔与赎罪意识、“中间物”意识和“过客”精神等。面对人性的幽暗面,鲁迅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担当,浸没于黑暗中开始“呐喊”,严厉批判别人,更严厉解剖自己。他以整个“生命扑过去”,把自己“烧”在里面。鲁迅这种精神气质,主要是受到舍斯托夫等基督教作家和希伯来精神影响所致。
关键词:鲁迅;舍斯托夫;幽暗意识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1—0129—06收稿日期:2010—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06BZW019)、教育部青年课题(EEA090424)
作者简介:齐宏伟,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7
在中国作家中,鲁迅有最深的绝望体验和幽暗意识,但学界对此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学界的研究到了什么地步?幽暗意识在鲁迅人格和作品中有哪些表现?又从何而来?本文将对此展开论述。
一、鲁迅幽暗意识研究之状况
国内学界深知鲁迅的钱理群说:“周作人绝不跟自己过不去,他总要保留一块‘自己的园地,不仅不允许他人轻易侵入,自己也不去怀疑、否定它:这是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容侵犯、不容怀疑、不容否定的精神家园。而鲁迅恰好故意地和自己过不去,鲁迅不仅跟别人过不去,更主要的是和自己过不去,他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周作人有一个底线——‘自己的园地,所以他的日子好过。但鲁迅就不同了,他把自己的后院搞得天翻地覆,不留后路,他不断地进行自我拷打。这样,两个人就有一个区别:周作人的思考是有保留、因而是有限的,永远停留在经验层面上;而鲁迅要打碎这一切,包括自我经验——鲁迅就说过,他本来根据自己的经验而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他又怀疑于这样的经验,‘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于是选择了‘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既重视又不局限于自己的经验,他就有可能进入形而上的超越层面的思考,当然我们可以说,或许这方面的思考并未充分展开,但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与鲁迅的彻底的怀疑精神直接相关的。””
这一说法极有见地,但把鲁迅的绝望体验归结为彻底的怀疑精神显然不确。梅列日科夫斯基批评“从一物皆无中一物也产生不出”,博兰尼(又译波兰尼)认为知识分子来自生命深处的冲动,必须和社会对此冲动的精神价值的支持及和稳定精神资源结合才能开花结果。像鲁迅这样的大家,当然更不例外。
王晓明把鲁迅的绝望体验和幽暗意识归结为个人沮丧和悲观性情及中国文化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传统,刘小枫批评鲁迅因家境败落其心态就染上了怨恨毒素。这些观点显然缺少对鲁迅的“同情性理解”,也过于消极地看待鲁迅的幽暗意识,没看到其在鲁迅精神资源中的贡献。英语学界对鲁迅黑暗面的研究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在1968年于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黑暗的闸门》一书,把鲁迅内在黑暗面看成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沉重压力,没看到是鲁迅主动的选择。这一观点决定性地影响了英语学界的鲁迅研究。
对鲁迅幽暗意识研究最深入的当属日本学界。最先对此发言的是竹内好。他认为鲁迅最深的经验是“宗教的”,他有某种“原罪意识”,也渴望“赎罪”。他认为鲁迅对死亡的自觉意识和对文学的自觉意识纠缠在一起,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仙台“幻灯”事件,而是在“十年沉默”期即1909到1918年间形成的。竹内好认为鲁迅不是启蒙人道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而是以文学为宗教的诗人,他的文学是“赎罪文学”。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向来有“竹内鲁迅”之美誉,他认定鲁迅有类似于宗教性精神资源为支撑才成其伟大,其幽暗意识和“原罪意识”庶几近之。其论点精辟,惜乎语焉不详。继竹内好之后,本多秋五又前进了一小步,他认为竹内好的《鲁迅》其实是以竹内好的方式对鲁迅的“舍斯托夫体验”进行阐释。本多秋五用“舍斯托夫体验”概括鲁迅的幽暗意识,非常恰切,但他只提出概念,没有任何展开与论证。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把这方面研究往前推进。那就先看鲁迅幽暗意识之表现:
二、鲁迅幽暗意识之表现
表现之一:死亡意识。父亲在鲁迅十三岁时病死,这给鲁迅带来了一生都不能愈合的创伤。还有其后陈天华、徐锡麟、秋瑾、范爱农、刘和珍、“左联”五烈士之死等,都给他带来极深痛苦。1916年11月30日,鲁迅请陈师曾刻一枚印章,竟名“俟堂”,即“等死堂”之意,这应是后来《(呐喊)自序》“铁屋子”和《孤独者》“独头茧”比喻之由来。鲁迅曾用笔名唐俟,即从“俟堂”而来。鲁迅对人生剥其华衮,抖落一切价值和意义之附丽,认定其实质不过“等死”而已。由此可知。鲁迅对人作为“有死者”早有某种敏锐觉察,因此才竭力在死之黯淡底色上寻求生之意义,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再从创作看,《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共二十五篇小说,其中竟有十五篇之多写到病与死。到了《野草》,更是笼罩着浓重的死亡阴影,不只《死后》直接写“死”,更有《墓碣文》,写一个人竟“抉心自食”而死。《野草》中《影的告别》这一篇,也被艾伯认为这里“影的所谓告别是一种由创伤所引起的经验,因其告别实则意味死亡”④。晚年,鲁迅在《朝花夕拾》中痴迷于对阴间鬼魂的想象,对女吊、无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浓墨重彩写阿长之死、父亲之死和范爱农之死等。《故事新编》中也写到女娲、伯夷叔齐、眉间尺、王、“黑色人”之死等。
面对这么多死亡事件,夏济安说:“鲁迅看上去是一个专擅刻画死亡之丑陋的能手。在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带有苍白的脸色、呆滞的目光、滞缓的动作,在死亡抓走他们之前就像僵尸一般。诸如葬仪、坟地、死刑,尤其是砍头,甚至疾病这一类题目都一再刺激着他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各种类型的作品。”这一观察和概括是准确的。鲁迅在作品中写到了一些活着的死人,以此来拷问生的意义,也在作品中提及或刻画了多起死亡事件,以此表达对生命如此不明不白、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即逝的哀痛。这一强烈凸显的死亡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未知生,焉知死”观相反,因此不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得到说明。
除死亡意识外,鲁迅还有很强的忏悔和赎罪意识。他算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中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一位。这种意识并非如林毓生所说是因“全盘陸反传统”而带来的心理重压,也不能归入姜异新所言的使“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终于完成蜕变,化蛹而出”的所谓集体性“文化原罪意识”,而本来就是鲁迅在生存层面的基本体验。
早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现象的同时,却不敢肯定自己就没吃过妹子的肉,作为被害者的他,也极有可能是
害人者,哪有什么资格去控诉?请看鲁迅从控诉到反省和忏悔的顺序:第一步,是向所属的整体文化控诉;第二步,想到的是“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一步既有控诉,又有忏悔;第三步,就达到完全忏悔的地步:“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三步层层深入,在控诉和揭露的文本中交织着忏悔的线索,从文化论整体控诉进展到生存论个体忏悔,到最后就不只是对文化劣根性忏悔,也包含对自身人性幽暗面的痛切忏悔,涵蕴极深。
鲁迅最深沉的忏悔之作是《伤逝》。究其实,子君之死不能全怪涓生,他的错误也不过是对于君说了不再爱她的真话。当然,他内心深处责怪过于君的变化,抱怨过生存环境的严酷,也有没能承担责任的软弱。但毕竟,子君之离开他,并她以后的事,及她的死,不能全怪他。然而,涓生却不只为自己的虚伪忏悔,更为自己的真诚忏悔,不只为自己的黑暗忏悔,也为自己的光明忏悔。忏悔沉痛剀切。达到类似于“原罪”意义上的忏悔。自始至终,涓生的罪孽近乎与生俱来无法消除,哪怕再有机会和子君住在一起,他又能怎么办?也无非是“我要骗人”罢了。他和子君的关系也如克尔凯郭尔从一开始的“审美阶段”,经过“道德阶段”,直抵涓生心底的“宗教阶段”。鲁迅和克尔凯郭尔心心相印。
还有《故乡》、《社戏》、《祝福》中的“我”,面对底层民众,忏悔意识不断流露出来,怀疑知识者所有知识之价值。这在中国作品中确系罕见。《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最为鲁迅式的小说中,吕纬甫和魏连殳其实都是鲁迅的精神自画像,鲁迅通过小说主人公对自我的质疑达到顶点,其实,这也可说是鲁迅的深沉忏悔。鲁迅的忏悔是深沉的。连知识分子立身的根基都可以铲除,彻底反省自己生命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所在,并不完全把自己焊接在社会性层面的存在上。
把《狂人日记》、《风筝》、《伤逝》和《墓碣文》等连起来读,邓晓芒认为鲁迅和其他“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们不一样,他的内心不像他们总以为是一片光明,在他是一片黑暗,他的忏悔不只是对知道的事忏悔,对不知道的事也忏悔。对鲁迅来说,忏悔、反省和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他不只是忏悔自己做了不符合既定道德标准的事,更忏悔从前自认光明磊落的行为和道德标准。邓认为这种近乎原罪意识的忏悔精神是鲁迅最大特点。
这也是真知鲁迅者言,只不过这说法尚未把鲁迅的自我否定和忏悔意识上升到明确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角度考察。
幽暗意识第三方面的表现在于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和“过客”精神,这并非明确的哲学体系,而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倾向。这和第二点紧密相关。
《过客》中的“过客”在旧世界找不到意义,而前方的新世界呢,不过是坟地,他也无法寄希望于将来,他更不能在自己的人性中找到坚实的光明根基,他几乎在怀疑一切,连那召唤他往前走的声音,他都在怀疑是不是真有。这种深刻怀疑精神使鲁迅一生都“在路上”。他信奉过进化论,也亲近过共产主义,但都貌合神离,并没彻底投入。他猛烈批判中国文化,但也强烈质疑西方文化。他确有一双在黑夜中还能洞穿一切的“冷眼”。他甚至无力提供所谓“中间物思想”和“过客哲学”,当然更不能形成所谓“过程哲学”这类思想体系。
鲁迅以《写在(坟)后面》提到的“一切都是中间物”思想反对“普遍”、“完全”,又以《野草》中的“过客”精神反对“永久”。钱理群和王乾坤为《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鲁迅卷》写了题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编者序言”,文中提到鲁迅粉碎了一切“普遍、永久、完全”的乌托邦,认为完善存在于不完善,全面存在于片面,不朽存在于速朽,把不圆满、缺陷、有弊端作为万物存在的常态,但又保持对这种常态的批判,用整个生命扑上去进行革新式的破坏与批判,在执着于此岸的同时,又不放弃对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与此同时更是否定了关于自我的“完美”、“不朽”的一切神话,他的怀疑毋宁说首先指向自己,鲁迅是他所说的“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的“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完成了别于祖先思维和人格的革命,贡献了走向未来新文化类型的同时,更公开地否定了自己,也就为新的有限、新的类型无限地敞开了自己,在他人后来者的自由创造和否定中延伸着自己的生命。
我们常把世界和自我看得很完全,对人性可以无限升华的“光明意识”过于信赖。看鲁迅把这一切却“看透”了,又能把“看透”也“看透”,从而又回到人间,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担当,浸没于黑暗中开始“呐喊”,严厉批判别人,更严厉解剖自己。他以整个“生命扑过去”,把自己“烧”在里面。他不是为了光明而战,而是为了跟黑暗捣乱。在大家都为胜利而欢呼的时候,鲁迅则早就看到了失败的阴影。因此,潘知常说:“王国维从发现个体到发现了人生就是痛苦,鲁迅的发现则再进一步,不但认为人生就是痛苦,而且认为痛苦就是人生。王国维发现人生就是痛苦,于是就想办法去解除痛苦。这意味着王国维并没有发现痛苦是‘无缘无故的,因此也是根本无法解除的。鲁迅就不同了。在他看来,痛苦就是人生。意思就是说,这个痛苦是无缘无故的,你不要想解除它,它根本就没有原因,也无法解除。痛苦就是人生本身。每一个人的生存只能是与痛苦同在。这种对于痛苦的发现,应该说是鲁迅的最大贡献。”
但鲁迅不可能只提供了失败。正如鲁迅一再强调过的,那些猛烈批评儒家文化的人,可能是出于最深的信仰和爱,绝非只一味批判和破坏。鲁迅对儒家文化没好感,他批判现有文化现象背后的精神尺度从何而来?看到黑暗和失败的背后不可能是一无所有,肯定得有幽暗意识所赖以依托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是什么?
三、鲁迅幽暗意识之由来
鲁迅的幽暗意识不是泛泛的绝望体验,亦非偶尔流露的思想倾向,而是鲁迅之为鲁迅的根本特质,非从这一角度就不能理解鲁迅精神之精髓。因此,对鲁迅幽暗意识的研究必须上升到鲁迅思想特质和鲁迅精神资源的高度。
英语学界对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的研究大都把他往中国传统文化坐标上靠,有意无意地把他打扮成一个自觉不自觉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大有不把鲁迅说成是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继承者而不罢休之势,对一向反传统文化的鲁迅之解读终究有隔膜。
而国内学界对鲁迅的解读历经单一的社会、历史角度到复杂的个体精神角度这一过程,渐从文化论层面进入到生存论层面。汪晖在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反抗绝望》中把鲁迅思想提炼为“反抗绝望”和“历史中间物”这两点,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这一新视角是什么?王富仁认为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话语和视角。王富仁的看法很敏锐,也很准确。其后,王乾坤、解志熙在汪晖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把鲁迅思想与存在主义哲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使鲁迅的精神内
涵得到进一步挖掘。紧随其后的是彭小燕,她的博士论文更明确地把鲁迅与存在主义视野联系起来,以期说明鲁迅最内在的精神特质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关⑤。然而,存在主义,或更确切地说是存在哲学,又可分为有神论存在哲学和无神论存在哲学,前者以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为代表,后者以萨特、加缪为代表,前者的源头为希伯来精神,后者的源头为希腊精神(或西西弗斯精神),鲁迅的生存体验更接近哪种?国内学界对这两种存在哲学没进一步区分,影响了探讨的深度。
在日本学界,伊藤虎丸在前辈竹内好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地把鲁迅和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内的广义希伯来精神联系起来考察,使鲁迅最深的精神资源得到清晰说明,在学界引起极大影响。
在此学术背景下,参考前文本多秋五的说法,我们认为鲁迅的幽暗意识可用“舍斯托夫体验”来说明,这正来自于希伯来精神的影响,而希伯来精神最显著的特色即其幽暗意识。
鲁迅熟稔希伯来文化资源,一生数次购买不同版本《圣经》。在《摩罗诗力说》中推崇希伯来精神,文末以写哀歌的先知耶利米为“撄人心”的代表。耶稣形象在他笔下反复出现,耶稣受难成为他关注重点。查2005年版《鲁迅全集》,发现鲁迅提及耶稣受难竟达十次之多,尤在《野草》以《复仇》(其二)重述此事为代表。他与果戈理、显克微支、安德烈耶夫、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等基督教作家、思想家心心相印。伊藤虎丸经研究后认定,鲁迅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个”的观念也是经由“托尼学说”而从基督教文化资源中取得②。鲁迅还先后与天主教神父清水安三和基督徒内山完造成为至交好友。
单以鲁迅与舍斯托夫的关联为例来看。查鲁迅日记,鲁迅频繁购阅舍斯托夫著作:“下午买《悲剧的哲学》一本”;“得《创作源自虚无》一本,一元五角”;“下午买书三种,共泉七元七角”。这三种书包括舍斯托夫著《创作源自虚无》。“午后买《舍斯托夫选集》(第一卷)一本,两元五角”;“内山书店送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舍斯托夫、纪德全集各一本,共泉十元”。鲁迅于1934年9月30日写《“以眼还眼”》,又大段抄录舍斯托夫,批评杜衡认为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一剧意在暴露群众的黑暗与堕落的观点。鲁迅深知舍斯托夫“痛恨十月革命”,他自己则亲“十月革命”,为何还一再购阅舍斯托夫的著作?可见,鲁迅确实比我们想的要复杂,他骨子里大概无法否认自己的“舍斯托夫体验”。
鲁迅在《“以眼还眼”》中以舍斯托夫为“哲学家或文学家”来看待,也深以他评论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一文观点为然。就在这篇文章中,舍斯托夫提到了“悲剧的哲学”。而舍斯托夫最先发现“悲剧的哲学”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他认为这篇小说深刻地暴露了陀氏的心灵危机,陀氏在那一刻突然发现自己就是丑陋的地下室人。舍斯托夫还把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放在一起,认为他们尽管有各样特点,但他们在发现“悲剧的哲学”这点上是相通的,因为“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果戈理,他们本身都是最丑陋的人,没有普通的希望”。舍斯托夫通过果戈理、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结出“悲剧的哲学”,以表达他的“舍斯托夫体验”。
他们三位也恰好都属鲁迅最为亲近和敬服的作家之列,这绝非巧合,而有某种内在必然性。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尼采再到舍斯托夫最后到鲁迅,他们的相遇当然不在思想上的一致,而在他们都有某种悲剧性的体验和共通的精神气质。他们都看到了人性最深层次的丑陋与黑暗,这正是深受理性至上思想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这几位作家对启蒙思想都有深深怀疑。舍斯托夫甚至说“知识就是堕落”⑥。他认为生活的勇气和信念并不是源于理性和知识,而是源于对绝望的感知与体验,通向生活的根本途径是信仰,而不是通过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照《圣经》中保罗的说法,人的悲剧不是理性不明、知识不周所以需要启蒙,实则每个人都知道善恶,但人的本性在堕落后却倒向“所知之善反倒不做,不愿之恶却一再去行”的怪圈⑧。这就是首先由奥古斯丁据《圣经》提出来的“原罪说”,后来发展成跟信任人性光明面的光明意识相反的幽暗意识。
对这一幽暗意识,美国思想家尼布尔在巨著《人的本性与命运》中讲得很清楚。他认为从根本来说,这种幽暗意识并不来自东方传统和希腊精神,哪怕是极有力度的希腊悲剧也不过认为人的恶是人的生命力(vitality)与理式(form)之间、日神与酒神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并没有对人性深处根深蒂固之罪性的认识。尼布尔认为来自于希伯来文化的幽暗意识,其实是反对这两种观念:从空间层面看,有限个体的人力图把自己看为无限整体好由此得到意义;从时间层面看,是由希腊精神所体现出的那种为了永恒而力图摆脱现在的观念。
总之,鲁迅正是通过体验绝望和反抗绝望而与希伯来精神相遇,周作人则正是通过刻意规避、抽离其生存体验而获得某种知性乐趣而与希腊精神相遇。周氏兄弟之所以能形成鲜明而深刻的对比,恰恰在于他们以其天才与“双希”精神遇合与碰撞的结果。废名为《周作人散文钞》写的“序”,鲁迅很不满意,因文中充满偏见,但在这点上废名看得倒很准,废名认为鲁迅“对于西方的希腊似鲜有所得”,而周作人“讲欧洲文明必溯到希腊去”。废名和周作人受希腊精神影响,倡导纯粹的知识乐趣,声明“文学不是宣传”而要“为文学而文学”,鲁迅对此大加嘲讽,还著文点名加以批评。这背后其实正是精神取向上的差异。最深刻、最博大、最源远流长的精神资源恰是世人看起来最为偏执和最为激烈的,根本容不得各间调和,如德尔图良所说“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在“兄弟失和”事件中,周作人不愿与鲁迅面谈,急于推开鲁迅的背后,当然不是为了自己一家霸占兄长买来的八道湾,而是对有可能会从鲁迅那边引发的自身黑暗和绝望迅即加以排斥。他其实知道这黑暗根本不是鲁迅带给他的,却急于在认定前把它推开,好使自己可以不必去面对。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不辩解”。他的知性追求甚至把他对“失和事件”的失语化为一场不入流俗者的高见。周作人一生最失意、最痛苦的晚年时光,恰是逃向古希腊文学,其浸淫之深,超乎一般人想像。鲁迅则深深浸没于黑暗中,开始其“呐喊”与“解剖”,对人性探索的深度远超周作人。但国内学界普遍重视鲁迅受“魏晋文章”及启蒙思想这两方面的影响,对他与希伯来精神资源的深层联系则从根本上忽略,这跟日本学界的研究相比显得极为贫乏。本文愿做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学界重视。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