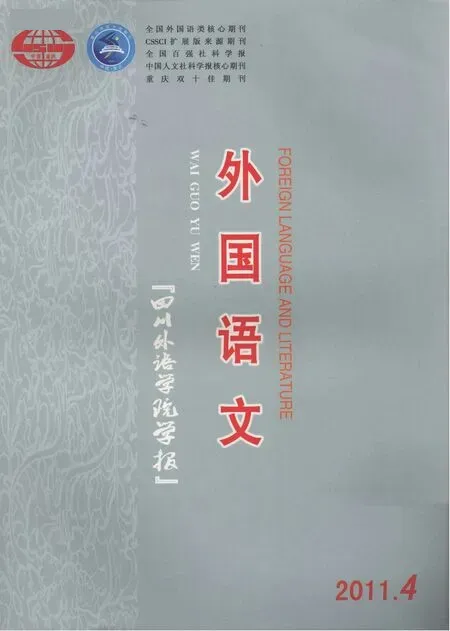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
张德让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1.引言
中国文化会通外来文明有两大高潮,一是自汉魏至唐宋的儒释道“三教融合”,二是由明末耶儒会通发展而成的中西会通。中西会通观的实践和提出分别源自“利玛窦规矩”的适应策略以求耶儒会通①沙勿略是耶稣会士在华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奠基者,范礼安是其组织和策划者,而利玛窦则是其集大成者,经过多年探索终于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利玛窦规矩”。详见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2005年,第2-5卷。,以及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②徐光启崇祯四年(1631)在上疏“历书总目表”中,论及《大统历》和西洋历法时说:“《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亦犹二百年来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见徐光启,“历书总目表”,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74页。的思想。此后,中西会通思想与实践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翻译史上不乏历史回音,如明末李之藻、王徵的西学翻译会通、晚清洋务派张之洞的会通论、维新派严复“统新旧”“苞中外”及林纾“以华文之典籍,写欧人之性情”的翻译会通、新文化运动中贺麟译介西方哲学的“和谐化合”说、钱钟书的学术“打通”论等。其中明清之际、晚清儒家士大夫对西学的翻译会通是儒家文化反思、转型的关键时期,值得专题研究。本文认为明清西学会通是儒家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学术方式,传统文化是明清士大夫会通西学的重要资源,类比联想是其西学会通的认知基础。本研究有助于梳理明清翻译史,确立会通在传统译论中的学术地位,深化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2.翻译会通:儒家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学术方式
翻译会通有着深厚的传统学术渊源和基础,是传统经学会通、儒释道会通的拓展和延伸,指“译者通过翻译把中学和西学进行融会贯通,以求超胜”(张德让,2010:68)。会通首先是“会”,表现为主体对待异域文明的一种文化接受心态和认知方式。对于有自觉反省和文化转型意识的士大夫来说,中西文化之“会”是一种友好的、互补的、对话式的相聚(meeting)、沟通(negotiating)和融合(fusion),否则就容易导致“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Huntington,1996)或“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Faiq,2004)。前者形成了士大夫之会通派,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林则徐、魏源、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林纾等;后者则沦为保守派甚至顽固派,如杨光先、倭仁、晚清清议派等。其次,会通是“通”,是译者选取与原语相似的译语资源以打通原文、反观译语的一种理解和诠释策略。它不是以语言表层的信所进行的“技术化”文字转换,也不是中西学的简单杂糅;不是自欺欺人的强制性附会,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认同,而是译者此在诠释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侧重于两种文化“相会”之后的“打通”,要求译者做到通人通解。最后,会通的目的是吸取异域文化为我所用,并反观传统文化之不足,以求超胜。西学会通不是盲目的西化,相反,明清士大夫在西学会通中的本土文化立场非常明确。表面上看,会通与格义策略类似,但后者旨在“生解”①格义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见(梁)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2页。,而会通更追求以耶补儒、批儒乃至最终超胜西方。这一目的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了翻译的选材和具体会通的策略等。会通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指态度、过程,又指结果;既指理解,又是翻译诠释策略;既是目的论,又是方法论。
以上会通的文化心态、反观译语、超胜目的,共同决定了会通视野下明清儒家文化自我反思和重构的“一个立场、两个群体、三个阶段”。明末以降的西学会通立足于儒家文化反思和超胜的立场,是儒家士大夫探索济世图强的一条学术途径,是传统文化自觉和引进西学的一种文化战略,是士大夫对儒家文化困境的忧思和新出路的探索方式。这些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思想、严复“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严复,1986:560)文化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明末到晚清,翻译会通思想与实践,至少促成了两个明显的士大夫群体,一是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儒者兼天主教“三柱石”,二是晚清桐城派士大夫。前者通过天儒会通以西方天文历算之实补儒家文化之虚,应民用而救世;后者则由曾国藩在桐城前贤“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开创了“经济”之学(曾国藩,1994:442),从而把经世致用与西学会通在实学层面上相结合,通过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大力译介西方科技,并在桐城末代吴汝纶、严复、林纾等翻译中,把西学会通推向新的高潮。
自明末至晚清,翻译会通思想与实践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清初西学中源论下的翻译会通、洋务派中体西用论下的翻译会通、维新派体用不二下的翻译会通。其中会通领域、翻译手段、方式、方法、目的、心理等方面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会通领域来看,由天文历算、科技翻译、制度译介到价值观输入等,层层拓展;从会通方式来看,由合译、广译、转译到独译;从会通方法来看,深深地打上了经学之义理、考据、辞章等治学烙印;从会通模式来看,由“入吾学之型范”到以中会西,再到中西互相会通;从会通目的看,由超胜到自强求富,再到维新救亡;从会通心理来看,由中学西源到中体西用,再到中西道通为一(张德让,2011:215)。一部近代翻译会通史,就是一部近代儒家文化自觉的历史,一部从补儒慢慢地走向保儒、批儒和新文化构建的历史。
自明末中西文化交汇起,走会通超胜之路中国则发展,走闭关自守之路中国则停滞。直到晚清,开放的士人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突破中西语言之间的巨大障碍(季压西、陈伟民,2007:2-10)、会通西学的紧迫性,同文馆第一次把培养翻译人才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中国不培养翻译人才,不会通西学就会被动挨打,就会遭受语言文字所带来的种种不利与损失,从而受制于中西通事设置的障碍,羁绊于语言障碍而难以步入世界近代化行列。
3.传统文化:士大夫会通西学的重要资源
就具体策略而言,会通又是译者选取与原语相似的译语资源以打通原文、反观译语的一种理解和诠释策略,追求通人通解。但由于历史性之囿,会通又只能是译者此在的诠释,即译者自身“前结构”状态下的解释,由其传统文化包括世界观、诗学观、文言等内在积淀和外在社会背景共同促成。明清参与西学会通的士大夫都拥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尤其是深厚的儒学积淀。在会通中,士大夫不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以传统文化为历史记忆和理解资源,从徐光启到严复、林纾,传统典籍和文言笔法在数学、哲学、科技、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翻译莫不如此。
明末代表翻译西书最高成就的译作,无疑是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该书卷一之首“第四求”中论及“长者增之可至无穷,短者减之亦复无尽”(利玛窦、徐光启,1985:15)时,其中“长者增之可至无穷”易懂,而“短者减之亦复无尽”难解。徐光启长期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他信手借用庄子《天下篇》之“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此加以会通:
尝见庄子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亦此理也。何者?自有而分,不免为有,若减之可尽,是有化为无也。有化为无,犹可言也。今已分者更复合之,合之又合,仍为尺棰,是始合之初,两无能并为一有也。两无能并为一有,不可言也。②同上,其中标点为笔者所加。
这样,西方几何中“短者减之亦复无尽”的道理和中国庄子所论的有限、无限的形象比喻,通过翻译达到了会通。
与徐光启同时代的李之藻更是传统文化优越论者,他以传统文化为历史记忆和理解资源,从而在翻译中倾向于儒化策略。他所达辞的《名理探》中术语基本上采用儒学术语加以会通,如该书《五公卷之一》所论及的“诸艺之序”,即西方学术体系的大致顺序如下:
……始穷物理,审如何修身,如何治世,乃创通达形性之学,以成修身治世之用。又加寻思,必更有超于形性者,遂及超形性之学也。
(傅汎际、李之藻,1959:13)
世间诸艺,……皆肇自审形学……而形性学继之,次则克己学,终则超形性学也。
若论各学差等,莫贵于超形性学,而因形性学次之,审形学又次之,而克己,而齐家,而治世诸学又次焉。 (傅汎际、李之藻,1959:13)
这里,政治学(politicus)译为“治世”,物理学(physica)译为“形性学”、神学(theologicus)译为“超性学”,又以“审形学”译数学(mathematica)、“克己”译伦理学(ethica)、“治家”、“齐家”译经济学(economia)等。综合来看,西方这些学科在李之藻的译笔下,很像依据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划分而成的一个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李天纲,2007:167),正如《大学》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样,西方“自审形学……而形性学继之,次则克己学,终则超形性学”,就和中国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克己治世之学,形成了类比和会通。此外,李之藻的《名理探》行文风格也时有传统诗学的身影,总体来说渗透着魏晋玄学名理方法及诸子论辩风格(邹振环,1996:22)。就具体策略来看,中国传统主客问答式的行文方式、晚明讲学风格、译本中杂以经学注解式的夹注等比较普遍。
晚清时期,传统“内圣”之学危机重重,经世实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推崇“外王”之学,尤其是承继晚明会通思潮,广采博纳异域新知,为我所用。张之洞的《劝学篇》可谓代表,特别是其中的《会通》开篇就以“周易”思想立论,倡导中西会通:“《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张之洞,2008:126)张之洞对西学并非十分了解,似乎是传统经典烂熟,面对西学,不自觉就能熟练地从《中庸》、《周礼》、《论语》、《书》、《管子》、《大学》、《汉书》、《左传》等典籍中采摘要义,作为理解西学的种种资源。
严译更以会通中西为治学之“至乐”:“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严复,1981:viii)。严复八大名译中,用以理解西学的传统资源涉及《周易》、《老子》、《庄子》、《孟子》、《大学》、《中庸》、《论语》、《书》、《荀子》、《韩非子》、《诗》等。这些资源在其译著中或显或隐、或宏观或微观、或渗透于正文或独立于按语,通过译名、选词、改写、“易用中事”、桐城笔法等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巧妙地渗透于译文之中。
明清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会通西学有格义、比附之嫌,遮蔽甚至延缓了不少有价值的西学输入,或者误导了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但西学东渐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只要把握好中西会通的分寸,可以产生良好的译介效果。这一点从徐光启到严复的实践足以令人信服。另外,从哲学诠释学视角来看,利用传统资源会通西学既是译者此在解释的应用性(伽达默尔,2007:418)特征,又是获得士大夫读者的有效策略,易使双方通过传统文化进行沟通,产生共鸣。同时在会通中,明清士大夫通过“考据”,发掘出了很多被忽视的传统资源,也创造了大量会通西学的表达方式,包括诸多学科的术语,如几何、上帝、格致、点、线、面、辜榷、名学、计学等。
4.相似性联想:中西会通的认知基础
晚明接受西学的士大夫,一般都深受王阳明及王学前儒陆九渊的熏陶,尤其是陆氏“心同理同”成了会通西学的普遍主义真理观,即:“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陆九渊,1980:483)虽然晚明会通派、晚清洋务派、维新派彼此的文化观不同,但是“心同理同”作为中西会通的认知基础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葛兆光,2004:13)。就操作层面而言,寻找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契合点是会通的首要问题。
徐光启通过与传教士的交往和反思儒家文化,认为传教士“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徐光启,1984:434),“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同上:431-432)李之藻认为西洋之学与“最善言天”的“昔儒”“意与暗契”(同上:272)。作为华夏文化优越论的信徒,李之藻虽然认识到西学的优势,为了调和矛盾,他以中西拟同论来解释西学与华夏文化间存在着一致性(赵晖,2007:26)。
19世纪后期,当异域的新知再度卷土重来,并且挟“坚船利炮”使中国人不得不从“道”或“体”的层面上接受它们的时候,“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再次被人们回忆起来,并被用来理解和解释异域文明或新知(葛兆光,2004:13-14)。维新派严复虽然批评张之洞的中西拟同牵强附会,但他认知西学也同样立足于自己对中西的相似性联想,以嘤求共鸣、“集思广益”(严复,1981:vii)。如 evolution“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谓之天演。”(王庆成等,1998:4)严复通过斯宾塞的“天演”界说“发明”了《周易》中的阴阳“易道”思想,还与《老子》《庄子》的世界观彼此相通:
天演学说滥觞于周秦之间,中土则有老、庄学者所谓自然。自然者,天演之原也。征之于老,如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征之于庄,若《齐物论》所谓“寓庸因明”,所谓“吹万不同,使其自己”;《养生主》所谓“依乎天理、薪尽火传”。谛而观之,皆天演之精义。而最为深切名者,尤莫若《周易》之始乾坤,而终于既未济。(严复,2004:135)
林纾更通过中西文学比较,发现了大量的相似性:“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韩洪举,2005:226),西洋小说“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林纾,1981:序1),如狄更斯小说技法与《水浒传》、《史记》、《汉书》、《石头记》多有类似,“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线处,用法颇同于《史记》。”(林纾,1984:171)林纾还发现拿破仑的形象如同《史记》中的项羽,《歇洛克奇案开场》中的约佛森颇类越王勾践和伍子胥,欧文《拊掌录》之《李迫大梦》中20年长睡的故事与中国“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神话异曲同工等。
中西相似性联想与翻译会通折射了明清士大夫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文化优越感,但也时而流露出他们西学中源的文化心理、对西方文化的历史和优势缺乏深入理解,进而在会通中原著意识不强。
5.结语
本文把翻译会通视为儒家文化自觉和西学引进的学术方式。会通中,传统治学之道、儒家济世情怀不断溢于译文字里行间。从徐光启到严复的翻译会通都以传统文化为历史记忆和理解资源,从而在翻译中倾向于本土化策略。其中的格义、比附之嫌应该为当前西学译介所避免,但其会通中西的精神、充分利用本土文化作为理解西学的资源、译文可读性的打造等,非常值得现今学术译介、文学翻译等领域的借鉴。此外,类比联想在翻译会通中的认知作用和实践价值不可低估,它体现了译者理解的“应用性”特征和诠释学真理追求,是译者融会中西以求超胜的实践智慧,又是医治当前“技术化”翻译的一剂良药。
[1]Dryden,John.The Three Types of Translation[C]//Robinson,Douglas.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172 -175.
[2]Faiq,Said.Cultural Encounters in Translation from Arabic(Topics In Translation)[M].Buffalo: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4.
[3]Huntington,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M].New York:Simon& Schuster,1996.
[4]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名理探[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I)[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葛兆光.一个普遍真理观念的历史旅行——以陆九渊“心同理同”说为例谈观念史的研究方法[J].东岳论丛,2004(4):5-15.
[7]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8]季压西,陈伟民.从“同文三馆”起步[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9]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和神学的相遇[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0]利玛窦.徐光启.几何原本[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林纾,魏易.撒克逊劫后英雄略[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C]//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70 -171.
[13]陆九渊.陆九渊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王庆成等.严复合集(7)[C].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
[15]徐光启.徐光启集[M].王重民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6]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7]严复.进化天演[C]//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34-147.
[18]严复.天演论[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9]严复.严复集[M].王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Z].长沙:岳麓书社,1994.
[21]张德让.翻译会通论[J].外国语,2010(5):66-72.
[22]张德让.清代的翻译会通思想[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215 -221.
[23]张之洞.劝学篇[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4]赵晖.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5]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