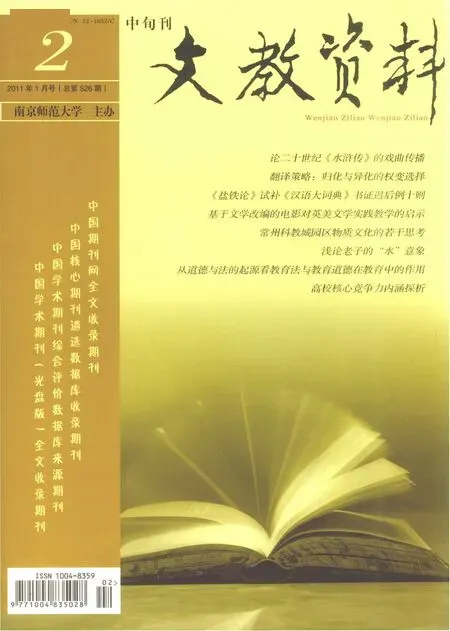论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创作技巧
吴佩芬
(上海商学院,上海 200235)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还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带有明显的前现代特征,但文化的发展既有滞后性又有超前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全球并轨,中西方文化交流,现代化都市纷纷崛起,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使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化城市中会出现了一些超前现象。“新的市井文明、城市文明和中外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带有某些新因素的文明,高校师生中的文化精神或反文化精神,一些受西方文艺影响的当代作家们,构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基础。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和形成也是可能的”。[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文化思潮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涌入国门。袁可嘉主编的《现代派文学作品选》的第三、四卷很多作品,在今天看来就属于后现代的文学范畴。由于“文革”特殊的成长经历和八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传入,西方文明与传统意识就构成了先锋派小说家们的双重文化选择。中国先锋文学在语言、叙事结构、价值取向上,明显出现了语言主体、能指滑动、戏仿、拼贴等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
一、语言主体
在后现代小说中,话语不是事件或进程的表达、反映、象征,它并非与事件或进程一一对应,它本身就是一种事件,具有同样的自主性,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处在同一层次。“语言是在意识和意志之外的,语言是一种非反思的整体整合化过程”,[2]“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3]主体不再是人文科学的中心,语言(话语)已经取而代之。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看来,说话的主体并非把握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4]后现代主义强调人的无意识结构,事实上提出了理性主体消亡的问题。人在语言中并无地位,他只是语言的载体。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相信语言是一个自足自律的系统,竭力强调语言的界定世界、建构现实的功能。
格非的短篇小说《青黄》所表现的就是这种以语言为主体的虚构世界,在虚构平面上的意义是追寻“青黄”到底是不是一部记载九姓渔户妓女生活的编年史。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模糊得近于空泛的历史探询者。在主观性的探询过程中,被探询的对象却越来越具有了一种客观性,与“青黄”有关的历史由村民的印象变成了他人的叙述,最终变成了一部外在的历史,而这部历史仅仅栖身于语言和意义之中。“我”听任自己沿着一条意义的迷途走了下去。《青黄》的第二节出现带有客观色彩的梦游,这里一切都悬置起来,一个故事引向另一个故事,一个事件引向另一个事件,而终结和确定性一样变得不可能了,对某种意义或对历史的确定性的追寻似乎使叙事者“我”如坠云里雾中。叙事的过程像是一种叙事者的自我流放,在叙事的自由发展过程中,叙事者虽有迂回曲折的出现,但却一直在自我消解,语言成为小说的主体,人退居到语言载体的地位,被语言所控制。
现代文艺家彻底打破了小说的亲临感和传统的真实性,在叙事体验过程中加上了那些曾经公认为是读者、接受者所做的事情,这就是元小说的诞生。元小说就是以小说为对象的小说,在元小说中,小说文本赋予了叙事者超乎传统小说家全知全能的叙事能力和魔力,当然这种能力不是传统小说叙事者为达到其叙事的真实性而渗透进去的种种的谆谆教导和训义,而是恰恰相反,在文本中出现了对于小说所叙述事件进行消解的文字和篇幅,马原、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作家就特意瓦解读者索解故事或真实性的企图,甚至连小说的写作过程和小说作法都和盘托出。
譬如,马原的小说充斥着这样的叙述:
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我像许多讲故事的人一样,生怕你们中间一些人认起真。
下面我还得把这个杜撰的结尾给你们。——现在要讲另一个故事,关于陆高和姚亮的另一个故事。应该明确一下,姚亮并不一定确有其人,因为姚亮不一定在若干年内一直跟着陆高。
(作者又注——在一篇小说中这样长篇大论地发感慨是很讨厌的,可是既然已经发了作者自己也不想收回来,下不为例吧。)
正如霍克斯所说:“文学艺术家通过 ‘暴露技巧’,通过使人们注意在写作时使用的‘陌生化’技巧,可能获得所有技巧中最主要的技巧:那种和艺术发挥过程息息相关的异化感。”[5]这种元叙述强调和突出了文学和生活背后的结构。在原来的现实主义那里,这种结构是潜隐的,文学的那种似真幻觉总是驾驭着接受者的意识。先锋文艺就像《皇帝的新装》的小孩,揭露了那种堂皇叙事的“欺骗”伎俩,通过展示“结构”而还原了文学的产生及其虚拟性特征。正如如果说这种文学有什么现实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它能使我们从语言对我们的感觉所产生的麻醉效力中解脱出来。而这种麻醉效力是如此根深蒂固,就像索绪尔所指出的,操本地语者试图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在由“树”一词造成的“音响效果”和真实的树这个概念之间,形成必然的“和谐性”,一种不可置疑的“同一性”。
叶兆言也是一位“元小说”的积极实践者,从《枣树的故事》到《关于厕所》,他让小说的叙述者混杂在故事主人公之间,构成文本中极为活跃的分子。这种叙述不断提醒人们:这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人为的小说。在先锋文学中,叙事不再是与现实具有同等地位的“真实”,在其中,作品转化成为文本,文本的意义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叙事本身,也就是说手法、技巧上升为具有超越现实内容的位置。
二、能指滑动
著名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弗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把语言符号的声音或书写符号称为“能指”,把语言符号指代的观念称为“所指”,而且强调指出,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这“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完全是人为随意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由语言符号的差异所决定,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阐释一个语言符号序列的意义,即寻求与能指符号相对立的“所指”含义的过程,从理论上说,便只能是一个新的能指符号去取代有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一个由一种“能指”滑入另一种“能指”的永无止境的倒退的过程。[6]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从索绪尔语言学这一内在逻辑中引出了“分延”(differance)的概念。他认为,符号并非是能指与所指的紧密结合,符号不能在字面上代表其所意指的东西,产生出在场的所指:一个关于某种东西的符号势必意味着那种东西的不在场 (而只是推迟所指的东西)。 Differance表明符号总是“区分”(to differ)和“延搁”(todefer)的双重运动。确定一个能指的所指意味着无尽的延搁过程,能指的确定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延搁于此的承诺。如此一来,再也不存在所谓的语词和本源的恒定的意义,一切符号意义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地确定,而又不断在区分和延搁中出现新的意义。新的意义进一步在延搁中区分,在区分中延搁。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终极不变的意义,正如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结构一样。语言只不过是分延的永无止境的游戏,终极意义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孙甘露的小说《附近的行星》的开头似乎想说明这样一个定论:小说家“陶列有可能是个终极意义的遁世作家”,但随后的叙述表明,陶列并非是被现实所“逐出尘世”的小说家,不一定想跳入他所描述的死亡之谷。这里,符号的意义被分延,能指继续滑动:“死亡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性关系,是陶列那个时代的小说家所热衷的话题。”但这个命题还未来得及得到阐述,其意义就被“但是我们还能够进入陶列的另外一个世界”所延搁。小说中能指就这样继续滑动,所指总是被延搁,如:“陶列的小说始终洋溢着一种高贵的气氛”—“陶列的祖上似乎在某个朝代做过一回官”—“拜伦爵士或维吉尔的学识深厚广博的风格”—“陶列总是在他的作品中重复描写某些相同的东西”……在这些符号中,区分和延搁避免了意义所造成的在场的中心性。因为文本中语句与段落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网络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小说的终极意义将永远不得而知。
三、戏仿
戏仿(parody)又可称为戏拟、拟仿、滑稽模仿或讽刺性模仿。文艺性的戏拟与文学的永恒演进密切相关,当“陌生的”东西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时,它就需要其他事物来代替。这种戏拟总是以另一部文学作品为背景,“通过暴露那部作品的‘技法’‘背离’那部作品”。[7]戏仿这种艺术方式在中国先锋文艺中屡见不鲜。神话、传说、史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小说、戏剧、通俗文学等都可以成为先锋文艺戏拟或戏仿的对象。在这种戏仿中,原有的故事或隐藏着的叙事被暴露,被放大,被置放于先锋叙事的手术台上,从而把原来隐藏着的叙事秘密揭示出来——这一手法的运用不是将原有的技法全盘抛弃,而是在新的与之不相适合的语境中重复使用,因而使它再一次被滑稽地感觉到。小说和戏剧叙事的历史主义追求在这种戏仿中被解构了。在模仿中加进喜剧的色彩,甚至在表面一本正经中渗透进闹剧的成分,往往借助文本内部的张力把“经典”颠覆。因此,这类文本往往呈现为喜剧化和漫画化。
武侠故事首先成为戏仿式叙事的对象,这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被运用,这是因为在先锋文艺中武侠类故事较少意识形态意味,是一个更纯的文类。更由于武侠故事本来就是中古人最讲究叙事策略和技巧的领域,那种刀光剑影、神仙道士、大侠美女,正是武侠叙事所沉迷的。先锋文本对此充满着解构的恶意和快感。余华的《鲜血梅花》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小说写一个武林复仇故事。守寡的母亲教导儿子阮海阔为十五年前被仇杀的父亲报仇,可是叙事中的儿子却是个无丝毫武功的弱男子,他寻找杀父仇敌的路途扑朔迷离。知道底细的青云道长和白雨潇却并没有告诉他真相。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暗中替阮海阔杀死了他的仇敌刘天、李东,而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在故事的结尾,白雨潇才莫名其妙地告诉了阮海阔。看着溅满梅花样鲜血的梅花剑,阮海阔只是“思索起以前的情景”。复仇本应是行动,而在《鲜血梅花》中只有行走和思索。统篇故事只是一个武侠的戏拟品,在更加随意和不可捉摸的臆想中,完成了一个关于虚无缥缈的武侠叙事。这种戏仿是对武侠类故事的解构,武侠那种悬念迭起的似真叙事和道义承担,在这里变成断断续续的无目的游荡和语言的横冲直撞。
总之,戏仿构成了先锋文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叙事的技巧被引人注目的故事所掩盖,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被故事所遮蔽,同时也遮蔽了我们经历的种种痛苦。而实际上,戏仿文本中我们熟悉的故事、语词、人物等,反而在戏仿之中得到某种还原。
四、拼贴
美国著名文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们“选择并列关系而非主从关系形式,选择转喻面非暗喻,精神分裂而非偏执狂。他们因此求助于悖谬、悖论、反依据、反批评、破碎性的开放性、未整版的空白”。[8]他们认为,世界是由片断组成的,但是片断之和构成不了一个整体,诸片断也并没有向某个整体或中心聚集。为此,后现代主义者不以追求有序性、完备性、整体性、全面性、完满性为目标,面是持存于、满足于各种片断性、零乱性、边缘性、分裂性、孤立性之中。巴塞尔姆认为:“拼贴原则是二十世纪所有传播媒介中的所有艺术的中心原则,是后现代艺术的标志。”[9]
苏童的短篇小说《井中男孩》,从故事层面上看,写的是后现代状况下爱情的毁灭。从叙事形式上看,苏童不再依靠传统的常规性小说手法:冲突、发展和线性情节,而是用零散的、片断拼贴的后现代主义手法编制了一个后现代寓言。这是由丰富多彩的碎片组合而成的文本。小说《井中男孩》出现三个较大的片断,是对德国小说家斯蒂芬·安德雷斯同名小说的戏仿,与小说中的故事发展虽无直接联系,但他的结尾却提供了一个关于毁灭与死亡的寓言式的暗示。作者依靠并置,创作了一幅文字上的拼贴画。诗人水杨门上的写有“写作时间/恕不会客”的小木牌,被作者用方框和黑体字画出来,直接出现在文本中。水杨寄给李彤油印刊物的诗稿“近期诗一首”,形式奇特,耐人寻味,作者如法炮制,将其呈现给小说读者:诗的标题为“无题”,诗在一张单页的页面上分为左右两栏,中间用一条竖画的浪线分开,左栏是三个诗行“产房/在太平间的/屋顶下面”,右栏是两只一高一低、一前一后透过墙窗窥视的眼睛。这首莫名其妙的诗不仅让李彤,而且让所有的小说读者“叹为观止”,但它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为了加强这种拼贴效果,苏童又将音乐简谱写进了小说文本,试图通过读者的再创作,使其产生声音的效果。苏童就是运用这样异质性的小型叙事消解了传统叙事。拼贴引起了文本价值的混淆,将小说的文本带入一个模糊、暧昧的审美空间。小说的叙述不再是唯一的、封闭式的,而是载入多种可能性。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复数式的情节拼贴在一起,将小说的内在维度、认知体系、隐喻世界无限膨胀,小说世界变成一个多维的、立体的审美空间。
[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是福音还是诞语.中国大学生[J].1997,(6):32-33.
[2][3][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第288,281页.杨大春.文本的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0.
[4]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33.
[5]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69.
[6][瑞士]弗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4-57.
[7]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1.
[8][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M].王潮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37.
[9]王岳川,尚水杰.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美学[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