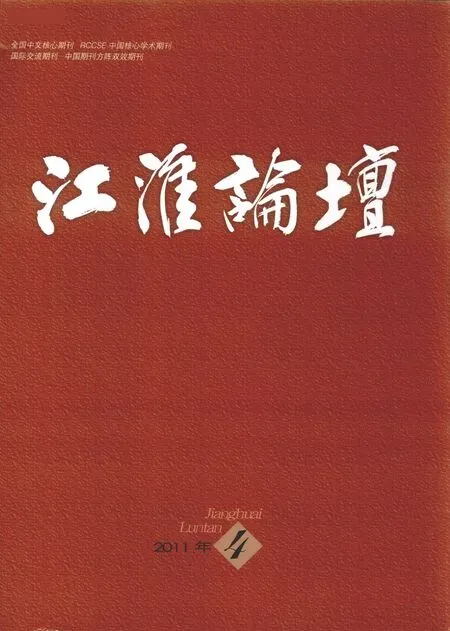谁更关心环境?*
——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检验
王建明 刘志阔 徐加桢
(1.浙江财经学院,杭州 310018;2.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 310012)
谁更关心环境?*
——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检验
王建明1刘志阔1徐加桢2
(1.浙江财经学院,杭州 310018;2.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 310012)
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环境关心之间关系密切。本文基于全国的城市家庭数据(CHIPS)研究了影响环境关心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同时利用城市环境污染数据控制环境关心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收入差异、教育水平高低、性别差异和政党参与是影响个体环境关心的显著因素,年龄则与环境关心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环境关心;经济社会特征;城市环境状况;离散选择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与之俱来的却是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日益突出的环境保护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已成为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环境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也显示出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环境问题的关注,我国环境问题(特别是污染物减排问题)开始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压力。
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研究,即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是否呈现“倒U型曲线”;[1][2][3]二是污染天堂假说研究,即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否造成我国环境的恶化;[4][5]三是考虑环境下的生产率问题研究;[6][7][8]四是环境管制政策或管制工具研究。[9][10]上述文献都以整个国家或某个地区为研究对象,以从宏观或中观视角理解和解决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但这些文献较少关注微观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是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基础,对研究环境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家庭数据(CHIPS)来研究收入、教育和性别等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与环境关心的关系。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主要对收入、教育、性别、年龄等与环境关心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部分阐述本文所利用的数据和建立相关的计量模型,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报告模型的估计结果以及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个体的环境关心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社会基础,本部分主要从个体的收入、教育、性别、年龄和政党参与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环境关心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和评述,为本文计量模型提供理论基础。
1.收入与环境关心
关于收入和环境关心的关系,多数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即收入越高的人越关心环境。[11][12][13]这可以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即把环境看成一种“非必需品”,只有在满足基本需求后人们才会开始关心环境问题。[14]相应地,当收入下降时,人们也会放弃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例如在经济危机时,失业率会相应增加,从而人们的环境关心水平也会下降。[15]Franzen和Meyer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分析发现,不仅一个国家内部高收入人群更加关心环境,而且在国家之间富裕国家的人们也更加关心环境。[16]这更加说明个体层面的问题和经济总体的现象基本是一致的。个体收入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对于某个地区或国家而言,便呈现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2.教育与环境关心
研究个体教育水平与环境关心关系的大多数文献认为:个体的教育水平与环境关心有密切关系,即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比其他个体更加关心环境,[14]并指出这可能由于受良好教育者能获取更多的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知道环境污染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同时教育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素质,从而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更加关心环境。[17][18]同样,在国家或地区研究层面,Dasgupta等的研究支撑了教育和环境关心的联系,他们认为教育水平是环境关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19]
3.性别与环境关心
很多研究都非常关注环境关心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早期的文献没有一致性结论,但新近文献越来越趋于认为,环境关心存在性别差异。Arbuthnot和Lingg[20]、Arcury和Christianson[11]等在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女性更加关心环境,对此解释是男性更加关心政治和集体事务,从而更加关心环境等社会事务。Schahn和Holzer[21]、Mohai[22]、Hunter[23]等提出了相左的观点,他们研究认为女性更加关心环境。对此的解释是父母身份导致女性更加关心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从而更加关心环境问题。洪大用等[24]指出关于性别和环境关心的文献,最新文献研究有趋于一致的倾向。也就是说,越是最近的文献越是报告环境关心上存在性别差异,即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而且这种关心还体现在女性对待环境友好行为上。以至于有学者指出:女性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已经成为环境社会学界日益广泛传播的一个结论。[25]
4.年龄与环境关心
对于年龄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现有的文献观点并未达成一致。Liere和Dunlap发现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负相关,即年轻人更为关心环境质量。[14]并指出这可能由于年轻人更加关心非物质生活,或者由于年轻人更容易接触环境问题的信息。与之相悖的是Hallin[26]、Shen和Saijo[27]的研究。他们认为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正相关,即老年人更加关心环境。而与前两种观点都相异的是,Franzen和Meyer指出,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倒U型关系。[16]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逐渐关心环境(这由于中年人更加关心公共事务,从而更加关心环境),但当年龄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关心环境问题。同时,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年龄对环境态度积极程度的影响呈现正U型情况,即20岁以下的人和40岁以上的人更关心环境。[20]
另外,除了收入、教育、性别和年龄外,是否参与政党也会对环境关心产生影响。[29]这由于参与政党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更加关心环境问题。[16]
在我国,也有一些环境关心的调查和实证研究。有些研究针对特定城市居民环保意识及环保行为研究;[27][30][31]有些研究侧重对农村地区环境关心进行调查研究。[28][32]在已有研究中,基于中国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关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与环境关心的系统分析非常有限,[24]并鲜有排除地区污染程度对环境关心的影响而研究中国的环境关心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从全国来选取样本,而不仅仅一个地区。本文使用中国12个省市的77个城市数据来研究城市居民的收入、教育和性别等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与环境关心的关系,并力图控制地区间环境质量差异对环境关心的影响。
三、数据与基本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个体层面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共同收集的2002年中国城镇家庭调查的相关数据。调查涵盖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四川和重庆等12个省市。和1988年、1995年的两轮数据一样,2002年的调查也是从国家统计局的年度调查样本中抽取的。另外,本文采用的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同年的《中国城市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本研究中,我们设定的离散选择模型(Probit model)如下:
P(environ=1)=Φ(β1lnincome+β2edu+β3gender+β4age+β5age2+β6party+β7pollution)
其中,被解释变量environ表示是否关心环境,若是,则取1;反之则取0。解释变量income表示个体的收入,我们对其作对数处理;edu代表个体的受教育年限;gender代表个体性别的虚拟变量,模型中男性作为参照组,取值为0;age和age2分别代表个体的年龄及其平方;party代表是否参与党派,参与取值为1;pollution代表被调查者所在城市的污染水平。
首先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界定。在本文的研究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环境关心变量,如果被调查者认为“环境问题”是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将其定义为1;如果不认为“环境问题”是当前主要社会问题,我们则将其定义为0。(1)
其次,选择解释变量(具体数据描述见表1)。对于收入(income),我们取被调查者的个体收入,并删除收入缺失样本,通过描述统计分析发现,关心环境组的平均收入(12363元)要高于不关心环境组的平均收入(10856元)。对于教育(edu),我们选择的是被调查者的教育年限,同样也发现来自关心环境组的教育年限要大于另外一组。其总体样本的教育情况如下:初中及以下占比33.91%;高中及大学以下占比39.28%;大学以上占比26.81%。对于性别(gender),我们定义女性取值为1;参照组男性取值为0,总体样本中女性占比53.92%,男性占比46.08%,其中关心环境组的女性比例高于不关心组。对于年龄(age),我们剔除了18周岁以下的样本,然后生成年龄的平方项,总体样本中:30周岁以下占5.08%;30-40周岁占27.81%;40-50周岁占34.27%;50-60周岁占20.3%;60周岁以上占12.54%。对于是否参加党派(party),我们设定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取值为1,其他为0,在总体样本中:参加党派的比例为35.51%,并且关心环境组比例远高于不关心环境组。

表1 分组描述性统计
在模型设定中,我们同时控制了地区的环境差异。我们利用城市层面环境质量数据来控制环境污染对于环境关心的影响。首先,我们选择的是每平方公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来衡量一个城市的污染状况,描述统计显示关心环境组的城市环境质量明显低于不关心环境组;同时,我们选择建成区绿化覆盖率(lvhua)来作为城市环境质量变量的替代。我们假设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越高的城市其环境状况越好,以进行稳健性分析。
四、模型分析结果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如表2中(I)、(II)和(III)列。与此同时,我们将其与OLS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模型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如表2中(IV)、(V)和(VI)列,我们在下文中主要基于probit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分析。
其中,(I)和(IV)是没有控制地区环境差异情况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收入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印证了发达国家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可见,收入水平提高确实可以增加国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从而使环境质量从一种“非必需品”转变为“必需品”。当然,这一结果是否可靠还需要剔除地区间环境质量差异的影响。比如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更高,可是工业化程度更高,环境污染更为严重,从而引致人们更加关心问题。因此,在没有控制地区间环境质量差异时,模型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后面我们进一步分析地区间环境质量差异对环境关心的影响。(2)教育可以增进环境意识,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提高了人们的环境关心。这可能由于教育提供了更多的环境信息,也可能由于教育提高了人们的综合素质,从而使人们更加关心环境问题。(3)女性倾向于更关心环境。在控制收入、教育和年龄等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女性对于环境关心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性别的确是环境关心中的重要因素。(4)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非线性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对环境关心水平不断下降,达到一定阶段又会呈现上升趋势,其转折点大致在50周岁左右。这可能由于老年人接受集体主义教育较多,社会责任感较强,从而更加关心环境问题;[28]同时,年轻人受环境教育较多,同时环境教育对年轻人的“穿透力”更强,从而年轻人也更加关心环境。[31]与之相对,中年人较多关心其个体生计等问题(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较重),相应较少关心环境问题。(5)是否参与党派也显著影响环境关心。参加党派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更加关心环境问题。[16]

表2 模型分析结果
由于模型(I)和(IV)没有控制地区间环境质量差异对环境关心的影响,从而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使得估计结果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接下来本文利用城市层面的环境污染数据来控制地区间环境质量差异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2中(II)和(V)。与(I)和(IV)相比,我们发现:(1)环境污染程度对环境关心存在显著影响,即环境污染越为严重的地区,人们越加关心环境问题,这也说明模型中如果不考虑环境污染程度对环境关心的影响会存在实质性缺陷。(2)在控制地区间环境质量差异的前提下,我们发现,收入、教育、性别等变量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变化,且其回归系数还有所变大,这更进一步支持了上文的结论。
另外,我们又利用城市层面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替代每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地区间环境质量状况对环境关心的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如表2中(III)和(VI)。与(II)和(V)相比,我们发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越高,人们的环境关心越低,即地区间环境状况差异的确会对环境关心产生影响,其他变量系数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也为上文的结论提供了更稳健的佐证。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首次基于全国层面的CHIPS数据考察了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与环境关心的关系,并控制了城市间的环境污染差异。其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环境质量的确影响人们的环境关心,特定城市或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越严重,越能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2)高收入、高教育、参与政党以及女性更倾向于关心环境问题;(3)年龄对于环境关心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年轻人和老年人相对中年人更关心环境。
在归纳出这些基本的结论之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本文研究的基本政策含义:首先,教育能显著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我国应加大对民众环境教育的力度。特别地,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中年人、男性、低收入者更不关心环境问题,因此环境意识教育应重点针对这些目标群体进行,从而促进全社会民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其次,我国应更加重视环境管制,尤其应重视不发达地区的环境管制问题。由本文结论可知,环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应地民众环境意识仍处于较低层次。因此,通过政府驱动的方式,加强政府对环境的管制,这可以更有效地推动地区环境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地区,民众环境意识更弱,更应该重视加强不发达地区的环境管制。最后,我国应促进环境保护中的公共参与(如鼓励民众参与环保协会、进行环保抗议、投票呼吁等)。由本文研究可知,参与政党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环境问题,这说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们更加关心环境问题。当然,公众参与是以信息披露为前提的,只有首先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才可能实施其批评权。由此,我们应在保证环境信息披露基础上,促进环境保护的公共参与,从而使民众更加关心环境问题。
最后,本文不足之处在于,仅研究了影响环境关心的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并未关注环境关心如何影响个体的环保行为和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这将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考察的课题。
注释:
(1)具体做法:在CHIPS数据的城镇居民信息中有个“意向问题”,让被调查者填出当下前三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果被调查者选择了“环境问题”,则认为该调查者更为关心环境,其环境关心变量取1,否则取0。
[1]Shen J.A.Simultaneous Estimation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vidence from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17(4):383-394.
[2]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2008,(6):4-11.
[3]张红凤,周峰,杨慧.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9,(3):14-26.
[4]陆旸.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J].经济研究,2009,(4):28-40.
[5]何洁.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中国各省的二氧化硫(SO2)工业排放[J].经济学季刊,2010,9(1): 415-446.
[6]涂正革.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经济研究,2008,(2):93-105.
[7]胡鞍钢,郑京海,高宇宁,等.考虑环境因素的省级技术效率排名 (1999-2005)[J].经济学季刊,2008,7(3):933-960.
[8]王兵,吴延瑞,颜鹏飞.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10,(5):95-109.
[9]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7-404.
[10]金碚.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5,(4):58-64.
[11]Arcury T A.Christianson E H.Environmental Worldview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ntucky 1984 and 1988 Compared[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0,22(3):387.
[12]Howell S E,Laska S B.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Environmental Coalition:A Research Note[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2,24(1):134.
[13]Scott D,Willits F K.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 Pennsylvania Survey[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4,26(2):239.
[14]Liere K D,Dunlap R E.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A Review of Hypotheses,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0,44(2):181.
[15]Kahn M E,Kotchen M J.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the Business Cycle:The Chilling Effect of Recession[D].NBER Working Paper,2010.
[16]Franzen A,Meyer R.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ISSP 1993 and 2000[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0,26(2):219.
[17]Jones R E,Dunlap R E.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Have They Changed Over Time?[J].Rural Sociology,1992,57(1):28-47.
[18]Marquart-Pyatt S T.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Among General Publics:A Cross-National Study[J].Society&Natural Resources,2007,20(10): 883-898.
[19]Dasgupta S,Laplante B,Wang H,etal.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 (1):147-168.
[20]Arbuthnot J,Lingg S.A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Knowledge,and Attitud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75,10(4):275-281.
[21]Schahn J,Holzer E.Studies of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Concern:The Role of Knowledge,Gender,and Background Variables[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0,22(6):767.
[22]Mohai P.Men,Women,and the Environment:An Examination of the Gender gap in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Activism [J].Society&Natural Resources,1992,5(1):1-19.
[23]Hunter L M,Hatch A,Johnson A.Cross-National Gender Variation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4,85(3):677-694.
[24]洪大用,肖晨阳.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2):111-135.
[25]Tindall D B,Davies S,Mauboules C.Activism and Conservation Behavior in 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The Contradictory Effects of Gender[J].Society&Natural Resources,2003,16(10):909-932.
[26]Hallin P O.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Foley,a Small Town in Minnesota[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5,27(4): 558.
[27]Shen J,Saijo T.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EnvironmentalConcern:Evidence from Shanghai dat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8,69(10):2033-2041.
[28]宋言奇.发达地区农民环境意识调查分析——以苏州市 714个样本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0,(1):53-62.
[29]Dunlap R E,Mccright A M.A Widening gap: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Views on Climate Change[J].Environment: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8,50(5):26-35.
[30]赵爽,杨波.兰州市民环境意识调查研究与对策[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5): 14-18.
[31]王建明.消费者为什么选择循环行为——城市消费者循环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10):95-102.
[32]谭丽荣,刘志刚.山东省农村地区居民环境意识调查分析[J].环境保护,2008,(4):47-51.
(责任编辑 吴晓妹)
F062.2
A
1001-862X(2011)04-0014-006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0C35047);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6110086);浙江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YK2009080)
王建明(1979-),男,江苏靖江人,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营销与政府管制;刘志阔(1987-),男,河北邢台人,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产业经济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竞争战略;徐加桢(1986-),男,安徽池州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业经济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