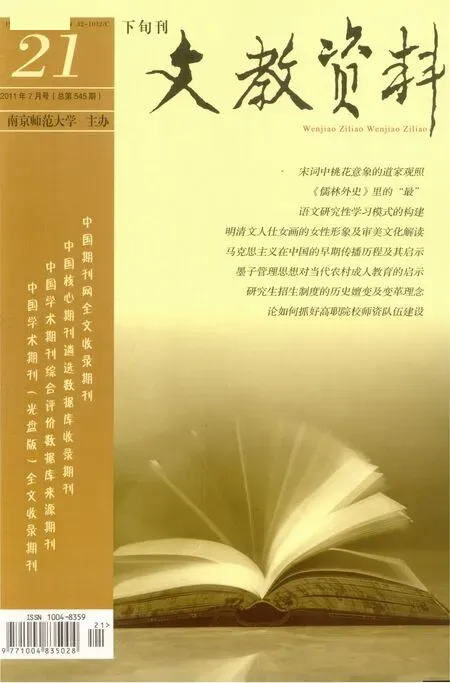明清文人仕女画的女性形象及审美文化解读
李信斐
(齐鲁师范学院 美术系,山东 济南 250013)
中国古代仕女画历史久远,随着不同时代审美需求的差异,仕女画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美人类型。仕女画发展到明清时期,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曰:“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这时期的美女标准逐渐从唐时的丰体肥颊演变为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的仪态。留意一下画作中的女子,如贵妇、名媛、历史人物,多拥有尖脸、削肩、柳腰、莲步的身形体貌和伴以伤感清愁之状态。任何艺术形式及审美标准都离不开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面从几个方面对其审美倾向进行探讨。
一、封建理法的桎梏
明中叶以后,经济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新兴市民阶层逐渐壮大,文化繁荣。但政治腐败的情况日益严重,上层统治集团昏庸腐朽,荒淫无度。官僚地主阶级对广大民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官场的腐败导致科场弄虚作假,世风沉沦,仕途险恶。面对复杂黑暗的社会现实,文人们对政治前途失去了信心,诗人画家开始寄情于山水;出入青楼,纵情风月情场、酒肉声伎,求得心灵的慰藉。“选色谈空”的风气弥漫在文人画家中,各种雅集活动,更常以美人捧砚,声伎佐酒以供消遣助兴。因此,以美人为对象的仕女画引起人们普遍兴趣,也刺激了仕女画的盛行。
在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唯情说”中,情是人类的普遍要求,人在本性上是追求“情”的,是“有情之人”追求“有情之天下”。但现实社会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性论主导着统治阶级的教化策略,“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文人理想就只能在梦中实现,在作品中实现,由此“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文人画家的梦也姑且通过美人画来求得短暂的安慰。在仕女画中,美人的生活多为教子、劳作、文艺、游戏、闲憩等活动,处处尊崇儒家温柔敦厚的教化法则。作为文人思想情感的寄托,在表达思想上也多为隐晦含蓄,用平和恬淡的创作手法表现女性的矜持美,如清人郑绩曰:“写美人不贵工致娇艳,贵在于淡雅清秀,望之有幽娴贞静之态。”所谓理想美人要具“闺阁之态”“贞静之致”,尽量弱化外在感官之美,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
二、文人际遇人格之表征
文人作为臣子,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具有相对的自由和独立性,可以周游列国,选择适合自己的君主,君王也可以普天纳贤。士有各自的志向,君有各自的标准,形成了百家争鸣、楚才晋用的现象。而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在文化领域里,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采取镇压、欺骗与麻醉相结合的政策钳制文人的思想。文人很少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即使被招至宫廷,也是作为附庸,处处谨小慎微,趋炎迎合。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以及失宠女性的凄凉痛楚的心境和封建社会中文人大夫不被君王重用、失魂落魄的心情尤为相似。文人们借用闺中幽怨、孤芳自赏表现自身的失意,揭示人情世态。从反复描绘的美人的柔弱形象中,仿佛看到了文弱书生的样子。华岩《白描仕女图》描绘一娴静娟秀的仕女若有所思地端坐在绣榻上,展现了女子内心的清冷孤寂,将观者的思绪引入了画中之境。唐寅《秋风纨扇图》仕女手执纨扇,在秋风萧瑟的庭院中徘徊观望,展示了仕女的幽怨之情,也倾泻了画家的悲愤之气。风流才子唐寅在《桃花庵歌》里写道:“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1]充分体现了传统文人遭遇坎坷后的心境和风流才子的不甘寂寞。
明清倡导推行女教,官妓业发达,达官文人狎妓之风普遍兴盛。谢肇《五杂俎》记载:“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2]在现实中遭遇不快的文人们,在美人的陪伴下得到暂时的慰藉。而妓在才艺或是情感上的迎合,对文人才情笔墨的效仿,使他们也如同找到了知音,与持才名妓产生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情感共鸣。文人为名妓画像,吟诗题词,为其才情标榜,如吴伟《武陵春图》、《歌舞图》,唐寅《李端端图》、《孟蜀宫妓图》,罗聘《苏小小像》,改琦《元机诗意图》,等等。唐寅《过秦楼·题莺莺小象》词:“潇洒才情,风流标格,脉脉满身倦。”明代潘之恒《金陵妓品》说:“诗称士女,女之有士行者,士行虽列清贵,而士风尤属高华,此诗求之平康,惟慧眼乃能识察,必其人尚素而具灵心……一曰品,典则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色胜。”[3]这也使得女性更注意自身才情技艺的修养,追随文人的欣赏口味。在这样的世风之下,文人也并不以狎妓为不道德,反以与名妓交往赠答为风雅。郭诩的《东山携妓图》便以东晋名士谢安隐居东山的轶事为主题,借历史名人谢安隐居不仕的气度,表现画家自己逍遥豪迈、清高傲世的士人情怀。画中谢安气宇轩昂,三妓女缓步随其后。画家用墨笔勾染高雅清逸,线条刚劲舒放,与画中人物形象气度相一致。郭诩自题诗于画中:“西履东山踏软尘,中原事业在经纶,群姬逐伴相欢笑,犹胜桓温壁后人。”[4]自明代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以来,“南宗”画派作为文人画的正统被大肆宣扬,庄子崇尚淡泊的虚静思想大行其道,推崇阴柔、淡泊、超脱的人格理想,画家追求简逸雅淡的画风,借用园林景色,进行人景搭配,衬托人物的怨情愁绪,将女性单薄、纤弱、哀怨、病态之美推到极致,成为文人审美文化的一种典型风貌。
三、女性地位的弱势显现
封建男权社会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使女性的身份随着周围男性身份的变化而变化,没有独立的地位可言。作为封建女德教化的产物和成果,孝女、贤妇、节妇、烈女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在明清历史文化记录中屡见不鲜。《二十四史》记录的节妇烈女明代就不下几万人,现在仍矗立在安徽境内的那些贞节牌坊,成为封建伦理教化对女性摧残的见证。明清时期对女性的教化是双重道德标准下的身心制裁,一边是教化三从四德的女教纲常,一边又纵容男性狎妓纳妾。许多文人墨客不仅以狎妓为风流韵事,而且淋漓尽致地在文学作品里予以渲染,并搬入绘画之中娱乐玩赏。明清两季,在商贾文人相对集中的江浙地区,流行“养瘦马”之风。挑选“瘦马”有着一套极为严格的鉴定程序,而其中最为客商看重的就是对于“瘦马”小脚的评判。并且人们还为这“三寸金莲”制定出了“瘦、小、尖、弯、香、软、正”等七条标准。缠足使女性在行动体态上表现出严重的柔弱和依附,却迎合了社会的“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欣赏口味。仕女画中那些迈着莲花步,扭着细柳腰,诗心病体,风露清愁的美人们印证着女性的物化和商品化,沦落为男性变态审美与情欲下的玩偶。明清仕女画中的女性,有不少名媛闺秀舞文弄墨的情景,而琴棋书画歌舞技艺的训练,对于闺阁名媛来说,只是作为一种家传教养,而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作的鼓励;对于青楼妓女来说这也是作为迎合士夫文人风雅品味的一种工具。才女名媛即使想施展才华,也会受到“内言不出”“不以才炫”的约束,女性的才智并不能无限制地施展。《金陵琐事》有云:“马氏,名娴卿。善山水白描,画毕多手裂之,不以示人。曰:此岂妇人女子事乎?”姜绍书《无声史诗》云:“傅道坤,貌丽而慧,幼习丹青。范生娶之。居一二载,绝不露丹青。后元夕张灯街衢,灯带偶失绘,众仓皇觅善手。傅闻,援笔绘之。 观者竞赏。 ”[5]
明清仕女画从其内容、形式折射出明清经济社会发展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落后与矛盾,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在社会政治上的失宠与无奈,继而投向风月情场自我沉沦与消解,托美人形象言个人情志,其中不免流露出畸形的审美心态。同时,我们也窥视到女性社会角色的卑弱与无助,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社会,女性成为把玩消遣的艺术品。
[1][4]毕继民.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物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第1版:236-237.
[2][3]赫俊红.丹青奇葩——晚明清初的女性绘画.文物出版社,2008.1,第1版:44-45.
[5]廖雯.绿肥红瘦.重庆出版社,2005.11,第1版:137-138.
[6]中国明清仕女画集(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1,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