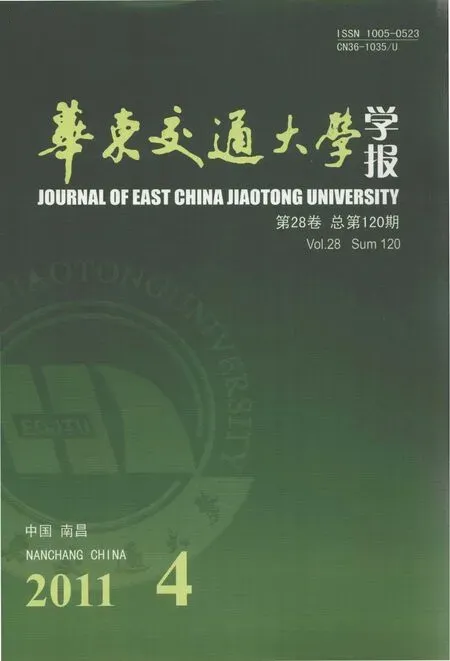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朱执信的历史观
姚卿善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朱执信(1885-1920)学术界多半认为:“即使在后期也没有逾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藩篱”。[1]5对其哲学思想(除历史观外)学术界认为是唯物主义的,本人以为其哲学思想(除历史观外)“含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这基本上构成了他哲学思想当中的马克思主义内核,反映了朱执信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缘关系。这是其哲学思想之所以能超越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从而趋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2]81然而,对他的历史观学术界尚未有专门的著述,本文拟对此作一概括,并从他大体接受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的角度,得出他初步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结论。
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朱执信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他往往能从社会经济基础等社会存在的角度来研究问题。他认为:
1)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的缺陷,而主义的产生绝非思想家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为适应社会改造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时势的产物。他说:“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自来之社会上革命,无不见其制度自起身者也……而今日一般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则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也。今日社会主义,盖由是制度而兴者也,因其制度之敝而后为之改革之计画者也。”[1]56他从经济基础方面找原因,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抽象的人性的观点,道德的观点看问题相比,可以看出他追本溯源的洞察事物的能力,是其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因素的闪光。
2)人的思想由一定的社会生活决定的,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及影响。“我们认罪恶是社会做成的,认犯罪的人是没有先天的犯罪性,”[1]670这显而易见地是否认“性本恶”的思想。人的思想的发展同人的社会生活习习相关,并由社会生活决定,既无天生的奸盗邪淫。同样也没有与生俱来的心端行正,它们都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的熏染下,潜移默化地形成的。他还说:“所有一社会之特殊精神性,一国民之特质,无不有历史之基础。国民特质,每国不同,因其历史不同故也。”[1]356以上两段话可以发现,他认为不仅个体的思想意识的形成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而且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意识也同样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因素,这体现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是典型的唯物史观。
3)他从社会存在如经济基础、社会历史条件等视角出发来考察社会问题,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并非偶然的灵光一现。此外,他还认识到私有制是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女学生李超由于剥夺了继承权被逼致死的“弊害根本,还在私有财产。因为社会一切关系,都放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所以这变相的谋财害命,是随在都有的。”[1]721-722此观点从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考察社会问题,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万恶之源的私有制造成一幕幕人间悲剧,因而他主张“现在社会经济虽然托根在所有权制度上面,到将来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会把这个不必要的躯壳除去。”[1]510看来,废除所有权制度——私有制的革命观点已昭然若揭了。
4)他十分重视思想体系(主义)在指导人们实践中的巨大反作用,思想体系作为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间接的反映,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练出来的有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化的反映形式。因而在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有一主义以定其行动之所趋,则一确定之意志,可以吸集无数未确定之意志,引起其自觉,授与以方向,于是成为有主义之人民意志,”[1]379主义作为系统的政治思想当其深入人心时,可以作为人的行动指南、方向指导、智力支持及精神动力。既然主义对人的活动有如此巨大的调控功能,那就有必要使主义成为人心之所向——大众之意识,主义为大众所接受,成为大众化的东西要靠什么方法呢?朱执信认为空洞而抽象的说教,把它硬塞进人们的脑子里是不会奏效的,唯有“把他们日常生活说起来,告诉他,如此就可以免除痛苦”[1]837的输入方法才能奏效。为了更清楚解释这种方法,他还举了现成的例子说:“现在我们想改造社会,自然要打破经济的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如果能使做工的人,了解了现代社会组织的缺憾,是他们生活上痛苦的原因,自然能够信奉一种主义,为这个主义去拼命了。”[1]838这种方法绝不是教条主义的说教,而是把主义的内容同人们切身利益以及同人们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而其方法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这也是他在看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反作用的情况下,主张把社会主义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体现。
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个原理他没有论述,这是一个遗憾。
2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由于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是,朱执信特别注重人民的力量。他把人民指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细民”。在他笔下,细民、国民、平民、人民等概念虽然不很明确,他界定细民的概念是“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1]60由此看出,细民范畴当包括工人、农民、自给自养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小资产阶级等。他们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生活极其贫困,毫无政治权力,处在政治阶层中的最下层。这使得细民蓄力待时,以求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因而他通过分析大量事实,作出了“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1]64的论断。毫无疑义,这个论断表明了革命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受压迫的细民,劳苦大众是推动历史向前的决定力量。此处他虽未精确说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细民不仅是革命的动力,而且是执政者政权稳固与崩溃的决定力量。他说:“凡共和国执政者,更迭而兴,乃至频繁,莫不据于人民心理。”[1]198人民心理即是人心向背,在这里他看到人心向背是政权更替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推动力,同“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这条唯物史观的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的观点反复出现,如“民意战胜金钱武力”[1]377“天下又岂有立于民意之敌之地位,而可有实力者乎。国家之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1]479-480这里有人会从表面理解,觉得朱执信赞成民意等社会意识决定金钱(社会经济)等社会存在,是唯心史观。殊不知这是望文生义,他指的民意、民心等其实是人民执行自己的意志来改造社会,实施民意的主体是人民自身。这可从如下话语看得出来:“须知此次欧洲战胜武力者,非金钱,非武力,而为民意。非敌国之民意,乃用武力之国自身之民意。俄国政府有武力,人民不满足之,则排去之。德国政府有武力,人民不满足之,亦排去之。”[1]377由此可知,他真正的意思是说沙俄与德国政府是由于本国人民执行了自己的意志即民意,而被人民即物质的力量推翻的,而非民意即精神的力量推翻的。而且结合以上引用的原文来看,他认为凡是违背人民意志的政府,一定没有实力,必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倒。人民才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意思相同。
在人民当中,谁将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有力量者呢?首先,中等社会因“做工特别少,而享结果比较多”,严格说来,不属于细民行列,况且“他的没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必须“把中等社会合并进劳动社会里头。”[1]766-767这样中等社会才能有前途。其次,学界缺乏了农工作后盾,也将没有真正力量。而商界更缺乏打破现有秩序的勇气,所以真正有实力的只有工农。“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力量。中国的商人,实在多半不是商人,多是靠这社会的缺陷来得利益的。我不敢希望他的团体有打破环境的举动。”[1]726最后,在工农之间,工人更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指导,而且工人对于资本家的剥削的感受更深切,痛苦也较早,因而要求革命心理也更迫切,革命性也更坚定。他说:“因为这个主义,生出一个牺牲的决心来……然而恰是在这工人的生活底下,有输进社会主义的可能。世界的工人,都比农人感觉资本制度的痛苦较早,而且也较深切……同时做社会主义的宣传,引起他阶级的自觉”[1]841所以,他断言:“要想改造现在的组织,自然要拿劳工做中心。”[1]800-801然而,何谓中心,按《辞海》解释:“居于中心地位的,起主干作用的。”[3]1583这就是说工人在革命中居核心的地位,其他革命阶级是围绕着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就只差捅破一张窗户纸了。由于世界工人的生活环境,使得工人比农民对于资本剥削有着早而深刻的觉悟,再加之,坚定的革命性,他们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这一切必将导致工人成为推翻资本制度的革命的中流砥柱和领头人。这个观点为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作了铺垫。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工人的阶级自觉问题,有了阶级自觉,工人便能从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进行经济斗争,转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光有工人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也还不够,农民的力量绝不是不可或缺的,“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群众运动“要有一个共同信念,逐渐结晶,到后来就变了无可抵抗的力量,所以最忌是限局于一地方一阶级”[1]878由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比起无主义指导的一盆散沙似的群众要有力量得多,这是十分正确的。为扩大群众运动的影响,他反对群众运动局限于一地方一阶级。这其实提出了无产阶级组织同盟军的观点。这里的群众运动应该看作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朱执信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的分析虽不完全精审,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的问题的分析大体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并为以后不久的国民革命所证实。
3 阶级斗争观点
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导致阶级的产生,自此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消灭一切阶级,并最终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20世纪初,造成社会贫富悬隔,放任竞争的私有制在社会上已根深蒂固,任何改造社会的行为对当时私有制的触动,都将遭受社会的重重阻挠。因而修修补补的改良行为绝不能真正废除私有制,作为先进的中国人之一的朱执信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认为:
1)“革命者,阶级战争也。”[1]60即革命实质上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1]879可见他承认阶级斗争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斗争绝非“野心家可以无因煽动的道理”[1]725产生阶级斗争的最根本原困在于经济基础的问题即“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
2)阶级斗争并非现在才有,是自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就有了,而且最后的消灭阶级还得依靠阶级的力量,没有阶级自然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只是看见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现在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1]879-880
3)阶级斗争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阶级关系又颇为错综复杂,因而阶级斗争的内容是丰富的,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以为用炸弹手枪,是阶级斗争,也不晓得用小册子、用演说台,也是阶级斗争。他以为聚众要挟,杀人放火,是阶级斗争,他不晓得罢工、罢市、怠业,也是阶级斗争。”[1]880这里他承认阶级斗争既有武装斗争,也有罢工、宣传等其他形式。
4)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成不成吃紧的问题不是主观意志能决定的,而由“资本家取得剩余价值多少,和劳动者生活工作条件如何”[1]724来决定,即被压迫者受压迫程度而定。
5)阶级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权,劳动者必须认识到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社会的运动,以阶级斗争为本据。然后持劳动阶级之利害较衡之,以求得之于资本家阶级……故劳动者阶级必为政治上运动者,势宜然也。抑又或迫使不得不然。夫政治上权力既有助于阶级运动,则是欲持而有之者,微特劳动者,富族亦尔矣。王权之摧挫,贵族之倾覆,皆富族之所以为陈勚者,故其持有政权,亦常视劳动者易。苟劳动者不为运动,而令政权纯移于富族之手者,劳动者扼吭坐视已耳,虽并命与争,何所济乎?”[1]40这里劳动者与劳动阶级是同时使用的,且与资本家阶级对比着用,加之他还说过:“劳动者之观念,则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等皆不函之”[1]60据此,文中的劳动者应为无产阶级。朱执信认识到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要由一般的政治斗争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使他超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的阶级斗争理论,达到了列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即“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4]454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的一步,尽管他此处没有说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
6)社会革命成功后,作为经济的阶级将不存在,人人处于平等的经济地位。“社会革命以阶级竞争为手段,及其既成功,则经济上无有阶级。”[1]68朱执信的阶级斗争观点同样走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怪圈,尽管还不完善,乃至于不能象列宁那样对阶级作出精确的界定,对阶级的理解存在偏差,但其核心是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的,而且要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这就使得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具备了科学的内核和切实可行的要素。
4 筑设新制度的暴力革命的理论
在阶级社会里,随着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革命必然爆发。唯物史观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社会革命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新旧社会形态转换的决定性环节。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
作为为革命牺牲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充满了暴力革命的理论。由于他坚持革命就是阶级斗争,而今后的革命动力来自细民,即劳苦大众,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革命中,又以劳工为中心,这使得革命的性质已是一场无产阶级起核心作用,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他看来,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即是革命的目的,他认为“实在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秩序”[1]861当然不可以扰乱的“自然秩序”应不在议论之列;同时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也是革命的内容——“革命虽然不是不要秩序,却不能不推倒现在所有的秩序的一部。要是连这个秩序都保存起来,不许扰乱,这就没有革命,没有改造,”[1]861而且他还把革命的内容同制度联系起来,他说:“凡有一个革命,都是破坏一种不合用的制度。如果不是破坏制度,另行筑设,就不是革命,也不是改造。”[1]861-862这样朱执信就把破坏秩序与建立新秩序同破坏不合用的旧制度与筑设新制度结合起来了,联系他认为的无产阶级必须注重夺取政权的理论,可以得出他赞同无产阶级必须在推翻旧的政权后,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5]434并且他还认定今后的革命决不再是改朝换代的政权更替,而是一场社会分配制度的变革。“把一个政府换另一个政府,把一般官僚换一般官僚不是我们革命的成功,要把我们所主张的生产分配方法来换了旧日的生产分配方法,才可以算是我们的革命成功。”[1]694他所说的生产分配方法的替换实质就是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就使他的社会改造思想含有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合理内核。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缺陷在于他们否定革命实践是社会改造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中肯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草拟出一个从多方面预言未来社会实际发展的图景——这个社会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但是他们认识不到工人阶级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社会,而只是相信通过说服和示范便可以把所有的人,尤其是有产的统治阶级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而此前被人称为主观社会主义者的朱执信在该问题上显然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靠革命手段才能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即破坏不合适的旧制度,创设新制度。他说:“总因为所恢复所创造的秩序,同现有的秩序有冲突的地方,在以要革命才能达到他目的。”[1]861朱执信以革命手段为社会改造开山劈路的社会改造论,反映了其革命思想有超越空想的实质内容。并且足以和许多假社会主义者如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
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武装。朱执信重视建设革命的武装,在他的《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中,他提出以苏俄劳动军法典的“验方”,以“化兵为工”的方式,建设一支为主义而战的“理想军队”。该军队“当兵的就是工人,当了几年的兵以后,可以退伍。退伍以后,倒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人,而且是一个豫备兵,将来可以为主义而战。”[1]841这支由工人组织的军队可在军队教育里头,“同时做社会主义的宣传,引起他阶级的自觉”,在理想军队里,工人兵卒可通过自治组织,“决定这些理想军队的任务和待遇。”[1]845而兵卒在工厂做工时,“建立产业的自治。凡主要工场的管理权,都要叫工人参与。分别专门的、熟练的、非熟练的工人,各选出代表,来管理这些工业。在私有制还不能废止的时候,对于资本的利息,虽然还不能不承认,而决定产额、价格、工钱的权,要分给工人。关于伤病、废疾、老衰、孕产、教育分摊的费用,一定认先取的特权”[1]844通过制度的设计,工人兵卒获得自治的权利,这样在理想军队里“除了作战上的指挥以外,兵卒对于将校士官,是没有区分阶级的必要”,官兵之间,工人之间“虽然工钱饷额有不相同,精神上可以算做平等。”[1]846通过以上分析,理想军队是实施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官与兵,人与人之间民主平等的关系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有着阶级自觉,必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朱执信重视建设工人阶级革命武装的思想,是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一致的。
他通过观察中国的劳动者“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1]724所以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说不成吃紧问题这句话,未免要后悔。”[1]725-726这里吃紧的问题指劳动阶级战争的问题,既然劳动阶级战争是吃紧的问题,他断言“资本制度也不能长久了,还有别种秩序要起来了”。[1]863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思想由此可见。那“别种秩序”是什么呢?他说过:“现在社会经济虽然扎根本在所有权制度上面,到将来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会把这个不必要的躯壳除去。”“现在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据此,一个绝灭所有权即私有制的社会必定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绝灭阶级的社会必定是共产主义社会。
朱执信高度评价了《共产党宣言》的深刻。他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固空想,为可得蕲至也……夫马尔克之为《共产党主义宣言》也,异于是。”[1]11这里他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切中要害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揭示其必然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同空想社会主义是不相同的。另外,他还运用《共产党宣言》作理论武器,对社会上那些害怕共产主义传播的人污蔑诽谤共产主义的言论,进行了驳斥,他质问道:“如果共产社会奖励懒惰,那现在的官、绅、富豪、强兵、悍匪、卖淫、吓诈、鼠窃、狗盗等角色,就应该众口一辞,来欢迎他,为什么还要反对。”[1]755
总之,朱执信历史观中含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核在其思想中都有较为清晰地反映。他思想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自己政权的观点,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的观点,以革命手段铲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等的观点,是其思想中最富革命性的因素。这表明他初步摆脱了主观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实现了由空想到现实的跨越,他至少可被称为“准马克思主义者”。这里需要对“准”的概念作一界定,照《辞海》解释是:“比照;作某类事物看待”[3]420说他是个准马克思主义者,是说他接近于或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主义者,甚至是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待,但是他的思想与1920年的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相比有所欠缺,他不能如李大钊一样,直接明确提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对国家、阶级的概念形成等的分析也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成分,但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建立工人阶级自己政权的思想是他显著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所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6]199来作衡量,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他是个准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没有明确说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但我们应看其思想主流,朱执信初步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是他思想发展的卓越成就,并为中国革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1]朱执信.朱执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姚卿善.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朱执信哲学思想及其特征[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8(2):81-85.
[3]夏征农.辞海[M].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4]列宁.列宁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列宁.列宁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