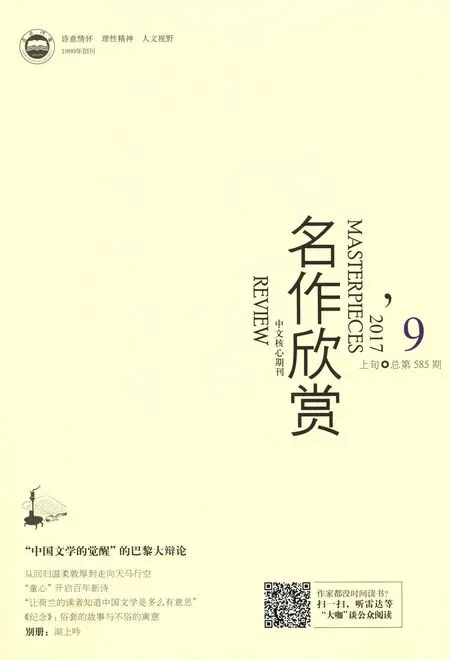钱谷·贪忮(下)
/[北京]李洁非
八
1644年6月7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同时发布《监国谕》。这个文件,诸多史著如《弘光实录钞》《甲乙事案》《平寇志》《明季南略》提都未提,《圣安皇帝本纪》《南渡录》《国榷》《南疆逸史》《小腆纪年附考》等,虽提及,却极简。唯一备其全文(或至少接近于全文)者,盖即《爝火录》。由于诸家的淡漠,我原以为那不过官样文章,但从《爝火录》细读原文才知并非如此,其实是个重要的历史文本,包含许多重要信息。
一般来说,即位诏书之类,确乎都是官样文章,其话语多半不必认真对待。但此番有所不同。这次,是明朝遭受重创、大行皇帝死于非命、国势近于瓦解之际,仓促间扶立新君,为此而发布的文告。它会如何谈论、认识和总结所发生的一切呢?这是我们颇为好奇的事情。
果然,《监国谕》第一条就说:
连年因寇猖獗,急欲荡平,因而加派繁兴,政多苟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则已困穷。今寇未平,军兴正棘,尽行蠲派,实所不能,姑先将新加练饷及十二年以后一切杂派,尽行蠲免,其余新旧两饷及十二年以前各项额征,暂且仍旧,俟寇平之日,再行减却。贪官猾胥朦胧混派,使朝廷嘉惠穷民之意不获下究,诏差官会同抚按官即行拿问,一面题知。如抚按官徇私容庇,并行重处。①
包含三点内容:一、承认多年以来加派过重,民力竭穷;二、宣布停征“三饷”中的练饷,及崇祯十二年以后其他杂派(练饷之征,即起于崇祯十二年),但此前两项饷额,即辽饷和剿饷暂时不能停收;三、承认历年除由国家明确规定的加派外,地方政府或“贪官猾胥”也有自作主张另行加派者,对此中央将派人会同地方官坚决制止。
虽然“大赦天下,与民更始”,从来是新君即位的一个“习惯动作”,我们不必信以为真。不过,将上面这段话从反面读,又自不同,它等于官方的一个自供状:多年来,国家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又坏在什么地方。关于“三饷”保留两饷,附带补充一个材料,《国榷》载:“又议赦书,史可法曰:‘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②尽管如此,但据《监国谕》,谈迁应该是将“辽饷”误写为了“练饷”。
历数下来,《监国谕》欲“与民更始”的条款多达三十条。每一条,我都从反面看,作为明朝所以走到今天的自供状。本文先前涉及的明朝赋税,不论传统的,历来要收的,还是因为“有事”而额外加派的,有两个特点,即:一、都是大宗的;二、都是“合法”的(即由朝廷经过“合法”程序明文规定)。现在,经《监国谕》我们才获知,除此之外尚有许许多多以各种名义由地方或权势者擅自收取的费用,这部分钱物也有两个特点:一、极其琐碎、分散;二、没有任何合法性。
例如第二条中说,在漕粮运输环节,“官旗”(官员、旗校)“向有划会使用、酒席饭食、花红(赏金)等项,民间所费不资”,这些巧立名目的报销入账内容,最后也都“混征”在漕粮之内而由百姓负担,是典型的借饱私囊、挥霍民脂现象,历年由此究竟贪蠹多少,无法统计。着令禁止,“有仍前混征者,官吏、弁旗并行拿究”③。
第三条宣布,崇祯十四年以前“南北各项钱粮”,凡是百姓欠而未缴者,从此蠲免(已解在途者除外)。但特别强调,官吏不许将这一旨意向民众瞒而不宣,而继续“混征”;其次,已解在途的部分,不许官吏“通同侵盗”,亦即借朝廷蠲免之机将民已缴纳、已在运往国库的钱粮窃为己有。④从所强调的这两点,足可想象各地吏治之坏达于何种地步,诚所谓“硕鼠”满地。
第四条说:“江南、浙西之民,最苦白粮一项,合行改折一半。”⑤所谓“白粮”,是明代一种“特供品”,取自苏州、嘉兴等江南五府,以当地所产优质白熟粳米、白熟糯米,经漕运输往京师,供应宫廷、宗人府(皇亲)或作为百官俸禄之用。转用我们当代语汇,就是“特权阶层”之专用物资。除悉数取自江南,它另有一特点,即“民收民解”,农民不单按期按量缴粮,还要自行组织运输。一句话:一条龙服务,负责到底。此项费用极其浩巨,史称“民一点粮解,未有不赔累、破家、流涕、殒命者”,“江南力役重大莫如粮解”。⑥
第五条:“十库钱粮……不许私派扰民。”⑦需要注意的,是“私派”二字。既申禁止,就可知其存在;并且,不到相当程度,显然也无须上谕特申。
第十三条:“近因饷匮,派报营官富户助饷,甚为骚扰。除曾奉明旨酌减外,其余尽准豁免。但寇乱未靖,军兴不敷,各人亦应捐输助国,以励同仇,即照捐数多寡,分别甄录。”⑧此条虽与普通民众无关,却同样逾于法外,我们不因被“骚扰”者是富人,就觉得可以容纳一种非法行径。重要的是,这个朝廷已完全不讲规矩,以致捐款都成为搞钱、勒索的方式。
第十四条:“关税增加太多,大为商民之害。今止照崇祯三年旧额,征解其正税,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等项,尽行除免。如有额外巧立名色,婪行侵肥,大法不赦。至于柴米二项,原无额税,近年自私设立,甚至借名禁籴,索骗多端,殊为可恨,以后俱行裁免。又各关冗员、冗役为害商民,须抚按官严行清察,务令裁就原额,如徇情虚应,定坐通同之罪。”⑨此条所涉,系商业税及财物流通中产生的收费。明朝的苛捐杂税以及因腐败而来的滥收、乱收,于兹洋洋大观。诏书表明,明末之税,除所谓“正税”亦即依法而收的外,还以新加、私派、捐助等方式增设了许多别的税。这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既然是“巧立名色”、乱增乱设,必然不列入财政统计之内,换言之,人民赋税负担实际远远大于官方汇总的数额。这些妄行增设的税收,多少入了国库,多少被地方和官吏“婪行侵肥”,只能是无法确知的谜。这且不论,更有一些费用,连“征收”的名义都没有,而是官吏们假公权直接从事“索骗”。诏书中提到“借名禁籴”,禁籴,是特殊情况(例如灾荒)下实行的粮食贸易管制⑩,却被官吏借以索贿、敲诈商贾。至于“各关冗员、冗役”一句,尤其可怕,它描绘出明末税务机关因疯狂敛财之需而膨胀不已,人员大超“原额”,形成一支“为害商民”的收费大军,这种现象因有巨大利益驱动,似乎已成痼疾,致诏书一面厉命“严行清察”、“务令裁就原额”,一面非常担心旨意被“徇情虚应”,根本得不到执行。
十二天后,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所颁即位诏书又有几条关于减税降赋的内容。如,民间交易(买卖田产、房产等),“先年税契不过每两二分三分,今已加至五分”,现规定“每两止取旧额三分”;朝廷鼓励开垦屯种,但官吏往往“新垦未熟而催科迫之”,致使民间全无积极性,现规定凡新垦之地都待“三年成熟后”再征其赋,且“永减一半”。⑪
两份诏书信誓旦旦的承诺,我们不必理会。以弘光朝的情形,且不说它是否真的准备做到,客观讲,也很难或不可能做到。但透过所列举的那些拟予纠正、拗救的现象,我们对明朝末年的赋税有了更多细节性认识。在这些细节面前,我们觉得“赋税沉重”这样一语话,现在是那样不痛不痒、苍白无力;我们甚至觉得那无法再称为“赋税”,而根本就是洗劫和强夺。
为此,引证一个材料。崇祯十六年(1643),有无知生员名蒋臣者,于召对时建议:“钞法可行,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三千万两。” 什么意思?就是大量印钞。身为国家财政高官的户部侍郎王鼇永,也罔顾常识地附议:“初年造三千万贯,可代加派二千余万,以蠲穷民。此后岁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金。所入既多,除免加派外,每省发百万贯,以佐各官养廉之需。”因缺饷而抓狂的崇祯皇帝,对这种胡言乱语,居然立即采纳施行。“乃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而一贯拟鬻一金,无肯应者,京商骚然,卷箧而去。”⑫
这样的国家,倘若还能维持下去,才是咄咄怪事。
九
所以,南京政权所幻想的延其国祚,根本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不谈贤愚正邪,也不谈君是否明君、臣是否能吏,在弘光朝,这些其实是伪命题。都说“事在人为”,诚有是言,然而当国家信誉彻底透支的时候,这句话只能改做“事不可为”。《明季北略》记:
崇祯末年,在京者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之意,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每云:“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势矣。⑬
并评论道:“当时政敝民玩如此,申酉之变,不察可烛。”“玩民”在先,于是“民玩”随后。国家对人民极尽刻薄,人民对国家也就毫无眷恋。所谓“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是因为相信未来更好,只是知道没法比现实更坏。
“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仅“辽饷”一项,即在原来整个边防费用基础上暴增一倍有余。然而,“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明明有钱,却捂住不用,非转嫁于百姓,盘剥民间,且不断加码,横征暴敛数十年之久。百姓就像取之不尽的提款机,皇帝及其就食者似乎“爽”得不行,居然不知道何谓寅吃卯粮,等真需要钱时,却发现提款机已不能工作。
这便是弘光朝的终极困境。跟二三十年前不同,此番朝廷真正缺钱,真正窘于财政。它最不可能就赋税减这免那,却偏偏在《监国谕》《即位诏》中做出许多保证和承诺。我们与其视为谎言,不如视为笑话。事到如今,明朝已明了其所以落到这田地,根因即在榨民过度,为生存计,它必须停止压榨。
然而事情的荒谬性在于,也是为了生存,它恰恰又必须继续压榨。一开始,弘光朝就处于这种二律背反的焦虑。讨论《监国谕》条款时,向百姓让步的幅度本来更大,提出“三饷”并废,却遭到史可法反对,要求仅废“练饷”,而将“辽饷”和“剿饷”均予保留。这自非别人比史可法更“爱民”,而是史可法比别人更务实,知道实难尽免。
后来,李清《三桓笔记》的一段叙述,等于为我们具体解释了原因:
上(朱由崧)即位后,楚镇及四镇频以匮告……楚镇兵五万余,需银一百八万,四镇兵各三万,需饷二百四十万,本色一百万……京营六万,需饷一百二十万……复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等八镇,共兵十二万,计饷二百四十万,合之七百余万。而大司农综计所入(一年全部财政收入),止六百万。而七百万之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太仓(国库)既无宿储,内帑涸无可发,漕粮改折,此盈彼诎。⑭收支悬殊,根本为负数;一年所入,不谈全部国用,仅供应军队都还差一百万两以上,而六百万收入本身实际却并不能保证,会因灾害等减少。所以说“七百万之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里外出入,岂止是捉襟见肘?
况且李清所列账单,只是“固定支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随机发生的用款。读书中,笔者随手记下一些:甲申五月二十八日,晋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劵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⑮。七月初四,组建以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给银三万两,为山陵道里费”⑯。七月初九,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以及与一千匹骡马等值的银两,“接济山东抚镇军前急需”⑰,同日,御史陈荩奉命募兵云南,给予饷银三万两。⑱八月,太后(弘光之母)由河南迎至,“十四日,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刮万金,以备赏赐’”。十六日,有关内监为安置太后请求给予工科钱粮、宫中陈设用具等“约数十万两”,工部等“苦点金无术,恳祈崇俭”,朱由崧“不听”,结果不详(料不能完全应命)。十七日,工部侍郎高倬报告,为迎迓太后,光禄寺已“费银六千八百六十余两,厨役衣帽工料银九百四十余两”。⑲九月二十日,“给河南巡抚越其杰十五万两,令募兵屯田”⑳。乙酉年春,筹备弘光皇帝大婚,仅采办礼冠一项,“需猫睛、祖母碌,又重二钱珠及重一钱五分者数百粒,又一钱及五分珠千粒,监臣商人估价数十万”,户、工二部和京兆三方,百般努力,措得二万余两,“内府执言不足”,后经圣旨“定为三万”。㉑而据《爝火录》,除礼冠外,还有“常冠一万两”㉒。余如,宫中银作局雇用工匠一千人,“人日给工食银一钱二分,每月支银三千六百两”,全年四万三千二百两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们都不在《三桓笔记》七百余万两兵饷之内。
十
我们曾一再说,南京弘光政权坐拥东南“天下财赋所出之地”,物力充裕。那是相对而言。跟满清或大顺、大西比,它的条件算最好的。不过,此时江南今非昔比,一来战乱年代,生产较承平时大降;二来多年重赋,民力早剥光抽尽;三来上天示儆,《爝火录》载:“大旱,自五月至是(甲申十一月)不雨。”㉔也就是说,从朱由崧登基起,江南春、夏、秋三季无雨,旱情十分罕见。祁彪佳日记也屡次提到大旱,并记下自己作为地方官率民众祈雨的情形。八月二十八日,户科吴适奏言:“旧都草创,一事未举,万孔千疮,忧危丛集。又况畿南各省是处旱灾……”㉕这场大旱对弘光朝确如“屋漏偏遭连夜雨”,历来富甲之江南,在这一年其实是老牛喘汗,力所不支,民生倍艰。吴江诗人潘柽章描述说:“升斗竭所余,满腹辄废卮。”㉖靠乞食和别人周济弄点饭吃,所谓诗酒风雅,是全然谈不上的。
即便朱由崧本人,我们也不能说他铺张奢侈。例如前面引述过乙酉年春他为自己办婚事,花了三四万两银子做礼冠,似乎相当破费,然而跟他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当年相比,却只能称为寒酸。朱常洵的身份不过是亲王,连皇太子都不是,可万历皇帝为了给他办婚事,单单盖房子就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婚礼上再用掉三十万两㉗,真是挥金如土。后来,为朱常洵“之国”,万历皇帝又赏田四万顷为他送行㉘,派出“舟千一百七十二艘、从卒千一百人”㉙的吓人船队,满载而往。所以,朱由崧以堂堂帝尊,结婚有几万两可用,草民虽不免咋舌,在他却已算是克奉节俭、委屈之至了。
当臣工们屡以国用不支提请凡事从简,压低甚至回绝他的某项开销时,朱由崧也不耐烦、也曾甩脸色,不过他的生活确实谈不上花天酒地,那倒不是因为其品质较父亲、祖父为佳,而是实在没有条件供给他那样的生活。他这个皇帝,当得比较憋屈。从登基之日起,财政问题就像绳索一样,始终缠绕着他。《监国谕》《登极诏》里那样的漂亮话,若在过去各朝,都是说说而已,对朱由崧却可不是什么漂亮话,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按李清开出的账单,弘光朝即便紧紧巴巴过日子,一年起码也有一百五十万两左右的窟窿。到处都在伸手要钱。史可法督师扬州启程前,上《请颁敕印给军需疏》,详细开列了大炮、鸟铳、刀枪等“各项军器”造买费用,要求授权他支配“贮淮扬之银”、“泊河湖之米”、“解北之银”,外加“二三十万金,携带前行”。㉚五月二十九日,时任巡抚应天安徽等处御史的左懋第,上疏索要长江战船,说“即以水兵六千计之,亦须少舡三百余只,或募或造”,战船之外,如“水陆士卒、火药器械之类”所费,也应“次第计算,请命施行”。他没有提出具体数额,但想必该是一大笔钱。㉛乙酉年二月十三日,督饷侍郎申绍芳报告,两淮运使所押解的白银一万两,居然被总兵郑彩擅自“截留”。㉜同年三月二十一日,汝宁总兵刘洪起,“以缺饷撤兵还楚”㉝……
说是要“与民休息”,实际容不得“休息”。朝廷第一要务便是搞钱,我们不清楚承诺蠲免的各项是否果行,却看见了不少“开源”、“创收”的新办法、新品种。例如,增设酒税。“马士英奏沽酒,每斤定税一文。”㉞一旦增设,即遭争抢,插手部门多达十一个,户部尚书张有誉反映:“京城糟坊不满百,酒每斤税钱一文,既委府佐,又责五城,凡十一衙门,岂成政体!”㉟又如,增设洋税即出海税:“马士英疏请设洋税,开洋舡每只或三百两,或二百两,设太监给批放行,于崇明等县起税,如临清关例。”㊱又如,“纳银充贡”:“廩生纳银三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㊲几个名词代表明代府州县官学学生的不同种类,廩生相当于正牌公费生,增生是扩招生,此外又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者,称“附生”。古代学而优则仕,诸生将来的前途是拔贡(进入国子监),然后有做官资格。所以“纳银充贡”实即变相卖官鬻爵。又“免童生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溧阳知县李思谟因拒不执行这项政策,竟遭“特降五级”处分。㊳不久,变相卖官变成明码标价:
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二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至乙酉二月,输纳富人授翰林、待诏等官,故更云“翰林满街走”也。㊴
计六奇回忆说,这桩买卖还颇为兴隆:“予在书斋,今日闻某挟赀赴京做官矣,明日又闻某鬻产买官矣,一时卖菜儿莫不腰缠走白下(南京别称)。”㊵中国人普遍有做官梦,朝廷既然肯卖,想过一过官瘾的人也很踊跃。
此外,尚有许罪官输银自赎、命官员佐工(捐款)等招数,不一而足。过去,把“拜金主义”安在资本主义头上,好像只有资本家才掉在钱眼儿里。其实“封建主义”何尝不爱钱?眼下,明朝便毫不掩饰“金钱至上”的嘴脸,为了钱,礼义廉耻全顾不上了。
说来亦属无奈,该收的钱很多收不上来,例如,“两浙巡盐李挺欠课二十六万两”㊶,苏州、松江两府三年欠征三百十一万八千五百两,已征而未上缴九十五万六千多㊷。朱由崧急眼了,和朱家诸先帝一样,他开始疑心大臣办事不利,而派所信任放心的阉奴到地方催要。五月十五日,登基当天,即命太监王肇基前往浙江督催金花银,被高弘图劝阻,朱由崧毕竟刚从监国“转正”,不便坚持,乃“责成抚按严催,不许怠玩”。㊸过了几个月,他不再客气,“遣司礼监太监孙元德往浙闽,督催内库及户工二部一应钱粮”,“凡年额关税、两浙盐漕、备练商价、给引行盐,一概随解”㊹。
事情周而复始。仅数月,曾经以“与民更始”面目出现的弘光政权,便打回原形。有御史名彭遇飓者,在《爝火录》中是个反面人物。他对马士英说:“岳武穆言大 ,文臣若不爱钱,高爵厚禄何以劝人?武臣必惜死,方养其身以有待。”他主动请缨“募兵十万”,别人问他“饷从何出”,答:“搜刮可办也。”㊺我观其言,倒不失坦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是岳飞名言,彭遇飓敢于驳斥,道德上可鄙,证之以现实反而不错。至于“搜刮可办”,更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不搜刮怎么办?敢问有谁能够不搜刮而搞到银子?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后来户部正式奏请,在徽、宁等府“预征来年条银”㊻,朝廷又回到寅吃卯粮的老路上了。
八月,与弘光帝和太后她老人家母子团聚的同时,在内臣亲自坐镇督催钱粮的浙江,“东阳民变”复起。先是,“县令姚孙榘(《爝火录》作“姚孙棐”)借名备乱,横派各户输金”,当地一名叫许都的富户,被坐“万金”,却只拿出来几百两,姚孙榘大怒,“指为结党造反,执而桎梏之,时输金者盈廷,哄然沸乱”,在县衙当场被姚孙榘拖到堂下痛打,后陈子龙与许都友善,以免死说其自首而已,不料浙江巡抚左光先背信,诛杀许都等,复激事变,左光先调兵镇压,致东阳、义乌、汤溪数地民众“各保乡寨拒敌”,而官兵大败。㊼
此事后虽平息,却像一道丑陋的伤疤,刻在弘光朝面黄肌瘦的脸上。
十一
关于明末财政,历来谈得最多的是拮据。无论在当时臣工奏章,还是后人史论中,缺饷、逋欠、灾减之类字眼,随处可见。这些,都突出了一个“无”,令人们把注意力容易放在所谓“困难”上,进而把原因归之于动乱、战争、天灾等“客观因素”或“不可抗力”。
其实,明末财政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比所谓“困难”更严重的,是“乱”。它比较隐蔽,内在于体制之中,缺乏透明性,极易被所谓“困难”所掩盖。战争消耗多少、一年赋税欠收多少、天灾造成粮食减产多少,这些数字可以统计出来,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但是,有多少钱因制度之故暗中化于无形,不单普通民众不知道,甚至连政权及其官僚系统本身往往也不清楚。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甲申五月二十六日,御史米寿图疏论“清核钱粮”。他说:
军兴以来,民间搜括已尽,库藏空虚已极,今加派已荷新谕蠲免,而朝廷之有仍还之朝廷。如先帝发造舡银两,果否造舡若干?费银若干?余银若干?如发兴屯银两,今屯未兴而原银化为乌有。若置之不问,亦可惜矣。诸如此类者,当察明清理,为兵饷之用……今后不论是何衙门,有一官便有一官职掌,不得坐耗储糈,见害则避,见利则趋,须改弦易辙,实心为国雪耻复仇,以尽臣职。㊽
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注意:许多钱下落不明且不被追究,成为无头账。从他的叙述,我们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贪污造成(虽然可能存在贪污),而是制度混乱所致,疏漏百出,支取、投放之后并不随以严格的审计;第二,这里只举了军队造船、屯田用银两个例子,但推而可知必不限于此——制度相同,既然此处稀松,他处也绝无严谨周到的道理。
还有一种情形。例如乙酉年二月二十二日,御史郑瑜纠朱大典先前任漕抚时“侵赃百万”。圣旨批答:“朱大典创立军营,所养士马岂容枵腹?岁饷几何?不必妄计。”㊾郑瑜所纠固然有不属实的可能(不负责任或出于派系之争的纠弹并不少见),但圣旨的批答也实在糊涂得紧。糊涂之一,仅凭推测、未经核实,即假定那笔钱用于军饷开支;糊涂之二,就算用于军饷,漕银是漕银,军饷是军饷,两笔款子应按规程各自收发,岂能随意混淆、处置?这都显示制度本身太过苟且。
现象显现于财政,但根子在别处。如果朝廷能够认识到手中钱一毫一厘都来自百姓——像本文开始所说——国家的作用不过是汇聚民力、代为管理并使之用于国家共同利益,它还会这样玩忽人民钱物吗?问题就在于朝廷把人民的钱,看成了自己的钱,怎么用都是它的自由,糟蹋掉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所以,不足是一回事,浊乱是另一回事;不足虽然堪忧,浊乱却能致命。在浊乱的制度下,钱再多也毫无意义,它们也许花得全不是地方,也许相当一部分被挥霍、浪费和私吞。相反,即便不足但管理有序、使用恰当,却仍可切实办成一些事。
既然浊乱带来巨大弊端,为何不采取健全、严谨的制度加以克服?答案也简单:浊乱,其实是被喜欢和需要的。世上立权为私的制度,往往有意留下一些不周密、潦草、含混之处,给“特权”以回旋空间。专制政体喜欢人治、回避法治,归根到底即因法治会剥夺某种特殊的“自由”,人治则有利于保存这种“自由”,使一小部分人最大限度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因此从经济上讲,专制政体就是通过掌控权力,确保少数人利益集团在社会分配秩序中的优先地位不被动摇。这种循权力大小搭建起来的分配秩序,完全比照着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首先,在自己和人民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形成单独的圈子,来分享比人民大得多的利益。其次,在他们内部,也有一些默认的规则。比如,君权强固时由皇帝及其亲眷攫取最大好处;君权羸弱时,主要利益份额向权臣转移,后者因此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疯狂捞取的黄金时间——历史上,这种时间通常出现在王朝末年。
我们看明朝中期到晚期,便一直保持着两个势头:一是贪欲本身在提速,二是贪欲的主体逐渐交接。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亲王禄赐考”、“各府禄米”、“诸子公主岁供之数”,载有自国初至嘉靖之间,皇族岁贡、赏赐等钱物额度的变化和比对。《明史·食货志》也记载着“仁、宣以来,乞请渐广”,至宪宗“皇庄之名由此始”,大量田亩被皇室、宗藩侵夺的具体数据。㊿对里面的数据略事研究,就可清楚看见贪欲提速的轨迹:大致,中期以前虽一直也在上升,但趋势尚缓,中期起突然加速,历正德、嘉靖、万历三朝,逐浪而高,万历末年登峰造极。万历皇帝一生的聚敛事业,斩获惊人,殊为尽兴。然而达此成就的同时,他也使朱姓皇朝千疮百孔,遍体溃烂,很多史家同意这样的结论:明朝之亡,亡于万历。
崇祯有句名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51]貌似警人耳目,却从根子上便错了。他光顾给自己打分,觉得算不上亡国之君,却忘掉之前几位皇帝都很有亡国天分,早把亡国之事办得差不多。到崇祯这儿,猛然发觉祖宗基业完蛋在即,试图不当亡国之君,却为时已晚。所谓“臣尽亡国之臣”,想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臣属身上,实在并不厚道。
和自然界道理相同,狮子垂垂老矣或力所不支时,次一等的掠食者也就开始大显身手。他们一直垂涎欲滴地等着,眼下岂容坐失良机?这个次级贪忮系统接替皇族贪忮系统开始疯狂运转的标志,是魏忠贤集团出现。魏忠贤犹如一团酵母,汇集了官僚阶层的各种腐败菌群,以最快的速度生长。
明朝从此进入君弱臣强、臣贪甚于君贪的格局,从天启、崇祯到弘光,都是如此。喜欢当木匠的天启皇帝,完全被魏忠贤玩于股掌。崇祯皇帝似乎强势,不断砍大臣脑袋,但这仅为表象而已。别的不说,那位两次入阁拜相的周延儒,“贿来不逆,贿歉不责。故门人亲故,自贿及为人行贿,不拒也”[52]。不光本人受贿,兄弟受贿,连兄弟的亲家翁也大肆招贿:“路礼曹迈,与正仪(周延儒之弟)为儿女姻,复为招摇,候选候考者多趋焉。于是有以七千求词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迈寻改吏部。”[53]索性直接从礼科调到吏部,专司干部人事任用。又如皇家特务机关东厂,其办案人员的方式是“择肥而攀,俟罄掳既饱,然后呈厂”[54]。亦如皇帝心腹锦衣卫,《三桓笔记》记其金吾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下面报来某案,并不直接捕人,“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55]。甚至相互配合,形成“索贿一条龙”。当时一个很有名的言官吴昌时(后被处决),就和东厂达成默契,凡因行贿受贿受到侦缉的,先通报吴,由吴前去索数千金“方免”。更有甚者,吴昌时对此不但不隐讳,反而洋洋得意,屡对人言,李清说他就亲眼曾见。[56]
及至弘光,君弱臣强格局益发明显。此时,权力集团作为一个饕餮团伙,权臣已据主席,君上反而叨陪末座,只是从中取一杯羮而已。朱由崧并非不欲多得,问题是得不到。天下之坏,令他处处须仰仗权臣;皇位得之于此,苟安复得之于此,哪里能讨价还价?九月二十八日,当淮扬巡抚田仰受大帅刘泽清怂恿,额外替后者“请饷”时,朱由崧答:
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田仰着与刘泽清从常措办。[57]
语气不掩怏怏,显出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看看朱由崧迎接母后及为自己办婚事时,在花钱上如何不能畅怀,即不难了解。从头到尾,朱由崧没有当过一天“像样”的皇帝,不论在权力上,还是金钱和享乐上。他留下了不好的名声,然而加以核实,无非是看看戏以及太后莅临前派人到民间“征女”。坊间传说他在宫中如何纵淫腐化,据李清讲皆为不实之词。当然,并非他不想那样。他也曾派人到各省直接搞钱,但实际搞到多少又是另一回事。他最后作为俘虏从芜湖押回南京时,“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58],这寒酸的形象,仿佛又回到一年前作为福王被迎至南京的光景。
反观众权臣,却风光无限。其中,武臣大帅俨然一方诸侯,享受独立王国待遇,赋税独吞,过着帝王般生活。“时武臣各占分地,赋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59]。有人对此提出批评,然而设四镇时却明确宣布,那是强势的将军们“理应”得到的。他们中较好者如高杰,心中还有职责,愿以所积用于军务、积极北进。但这仅为个例,其余武臣,全都只顾穷奢极欲,而且没有止境。最肆无忌惮的是刘泽清,他在淮安“大兴土木,深邃壮丽,日费千金”[60],“四时之室具备,僭拟皇居”[61],规制比照皇宫。甲申年秋收后,各镇臣立即展开疯狂掠夺,御史郝锦奏:“各镇分队于村落打粮,刘泽清尤狠,扫掠民间几尽。”[62]但恰恰此人,偏偏还要哭穷,唆使地方官为他额外“请饷”。
对四镇所拥特权,别的武臣不免妒忌而加攀比。七月十四日,操江(长江防务及水师统帅)刘孔昭上疏要求增加经费,特意详细援引四镇军饷额度,及“田土听其开垦,山泽听其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等优厚政策,加以对照,大谈自己的困难,如何“水师与陆师不同”,又如何“今日防江甚于防边”。总之,担子既比四镇重,兵饷亦应比四镇优,并抱怨此前两次致函有关方面,而“旬日以来,未见议复”。[63]实际上,操江大人并无意于江防,而只是借题捞一把。后来,弘光从南京出奔,想投靠他,他闭关不纳,随即自己逃走,“自太平掠舟顺流而东”,“满载白粮入海”[64]。
文职要员,无军饷可侵吞,亦无收税、“打粮”之特权,却有官爵可卖。关于阮大铖如何“贿足而用”,我们已在别处备说颇详,这里再举一例。有一次,他对人这样说:
考选某某,以二千金相送,推之不去。往我居省桓时,两人各送一卮,皆白物(银质)耳,今则黄(金质)爵,不纳不已。[65]
“推之不去”和“不纳不已”,既画尽阮氏之厚颜,亦极写朝中贿风之炽。阮大铖有一个帮手,亦即赖彼之力当上吏部尚书的张捷:“是时张捷秉铨,部务皆阮大铖一手握定,而选郎以贪黩济之,吏道庞杂已甚。”[66]不过,阮大铖虽称巨贪,却并非弘光朝官风的典型。因为他一面贪忮,一面还搞党争,卷在意识形态当中。典型的弘光官僚,应是马士英一类。官场争斗,一般意在政治,而马士英积极争权,却纯为夺利。他政治野心的脚本上,只写着一个“钱”字,所谓“争权夺利”,到他这儿才真正归于一体。他奋勇出头拥立福王,以重兵胁迫朝廷撵走史可法,与阮大铖结盟等,都没有多少意识形态色彩,并非要搞“路线斗争”,只是抢下权柄以便搞钱。他对政治立场并不关心,祁彪佳被阮大铖排挤辞职时,他托人带口信,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一切人和事,只要不有碍他搞钱就好。他任首辅后,呼朋引类,资源共享,周围迅速形成一个贪贿集团。六月十三日,吕大器下台前告了马士英一状,历数“其子铜臭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阵为总戎,婣娅(即姻娅,婣同姻,泛指姻亲)越其杰、田仰、杨文骢先朝罪人,尽登膴仕(即高官厚禄。这里连同前半句,用《诗·小雅·节南山》典:“琐琐姻亚,则无膴仕”)乱名器”[67]。只要沾亲带故,俱委肥缺,而此时距他得位才不过一个来月。有个小故事:
马士英黩货无厌,贿赂千名百品,日令僧利根次其高下。总宪李沾进带,士英不之重也,嘱利根誉为至宝,士英转以献帝,亦嘱中宫赞其非常,帝每束以视朝。[68]
故事说,马士英因贿物实在过多,就专门聘用一位利根和尚,每天替他鉴定诸物品质。这利根和尚,大概是当时的“鉴宝”权威。左都御史李沾进呈一条玉带,马士英瞧不上,却让利根和尚吹嘘为至宝,转送给朱由崧,让左右太监把利根和尚的鉴定意见转告朱由崧。可怜朱由崧无知受骗,信以为真,经常束着这条带子临朝视事。此事似令人想到“指鹿为马”之类典故,细辨辄不同。赵高戏君出于权奸的骄横,马士英耍弄朱由崧却只关乎钱财,把后者作为“假冒伪劣”受贿品的去处。
任何人稍具理智,都无法理解以朝不保夕的国势,弘光文武大员为何如此疯狂聚敛?而敛来巨额财富又置之何地?但转而一想,身在那种利益集团,权力和制度对他们做出的强烈暗示,原本在此。正像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是“为捞而捞”,这种身不由己、飞蛾赴火般的冲动,必欲一逞而后快。
乙酉五月十一日,马士英从南京仓皇出逃,率卫卒三百从通济门出,“门者不放,欲兵之。乃出私衙元宝三厅,立刻抢尽”[69]。他逃走后第三天,兴奋不已的南京市民,冲入其在西华门的府宅,及其子马锡位于北门桥的都督公署,大肆抢掠。“次掠及阮大铖、杨维垣、陈盟家,惟大铖家最富,歌姬甚盛,一时星散。”[70]其中,马士英家“有一围屏,玛瑙石及诸宝所成,其价无算,乃西洋贡入者。百姓击碎之,各取一小块即值百余金”[71]。
清兵入城,未及逃走或留下迎降的官员们,纷纷解囊讨好新的统治者,“致礼币有至万金者”[72]。礼部尚书钱谦益,刻意不拿钱,只献出一些物品,“盖表己之廉洁也”。然瞧瞧这份礼单,亦知所谓“廉洁”若何: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计开:鎏金银壶一具,珐琅银壶一具,蟠桃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虁龙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珐琅鼎杯一进,文王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进,银镶鹤杯一进,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右启上贡。[73]此件是当时为豫王多铎做登记工作的王佐亲眼所见,抄录后带出,应属可靠。至于这些东西占钱氏家财几何,我们是无从估计的。
十二
乙酉年五月十四日忻城伯、京营戎政总督赵之龙缒城而出,递降表于豫王多铎;次日,大开洪武门恭请多铎入南京。以此为标志,弘光政权结束。同时意味着,明朝作为全国性政权从“国家”意义上消失。
这也是南京首次以中国首都的地位,为外族军队所占领。
在这背景下,发生了既令人震惊又耐人寻味的场景:五月二十五日,弘光皇帝朱由崧被押回,当他所乘小轿穿行于南京街道时,“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74]。这是在外族占领军的注视下,百姓对自己的前国家元首做出的举动。南京人民不欢迎满清占领,但是,他们仍然明确表达了对明朝的唾弃。这是两个单独的问题,它们并不矛盾。
我们也记得,崇祯末年,北京市民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的民谚,用一语双关方式,曲折道出对“明朝”的厌倦。
明朝百姓没有感觉到幸福。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自己受到了过于严重的剥夺。本文耗数万言,细针密缕,罗列和爬梳种种数字,都是为此提供一些实证。
约翰·罗尔斯说:
一个正义制度必须形成自我支持的力量。这意味着它必须这样被安排:使它的社会成员产生相应的正义感,以及为了正义的理由而按照它的规范行动的有效欲望。[75]
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一个被设计来发展它的成员们的善并由一个公开的正义观念有效地调节着的社会。因而,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人都接受并了解其他人也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同时,基本的社会制度满足着并且也被看做是满足着这些正义原则。76
他强调制度设计问题,认为制度是否形成支撑,并非从外部征集和寻求而来,而在于要让正义原则预置于制度内部;只有做到这一点,无须号召和鼓动,社会成员自然能够主动和由衷地拥戴、热爱这一制度。他还探讨了制度间的竞争:
一个正义观念,假如它倾向于产生的正义感较之另一个正义观念更强烈,更能制服破坏性倾向,并且它所容许的制度产生着更弱的不公正行动的冲动和诱惑,它就比后者具有更大的稳定性。77
中国古代社会,不缺乏正义的理念,只是缺乏将理念转化为制度设计的能力。儒家思想体系,虽然尊崇君权,但并不一味充当君权的驯服工具,它的“民本”原则,在古代世界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中,具有相当的先进性。正因此,每当朝代更迭之际,新的统治者都不得不推出若干惠民政策,作为与民更始的表示。
但是,儒家思想体系终究不能前进一步,从理念拓展到制度建设。重“道”轻“器”,止于明道、论道而不辅之以形而下制度层面的精确设计,是吾国文明一大弱项。以为有好的理念,就会有好的现实。这使得儒家伦理最后往往陷于空谈,那些正派、正统的儒家官僚,能够在言论上发表极好的见解,却无法转化、落实于有效的政治实践。
本文中,黄宗羲对于明代田制问题的反思,就暴露出中国最优秀的思想者在制度创新或改进方面,明显缺乏能力。他正确地指出,明朝社会危机根由在于制度不公正,却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只是寄希望于回到古制。我们经常批判古人流行复古主义,指责他们拉倒车,想使历史倒退。其实,那并非他们本意;他们知道现实不正确,认为应对制度加以改良,却又能力有限,想不出比古制更好的办法。
两千多年,中国所以在王朝周期性震荡中徘徊,根子就是不能突破制度瓶颈。由于未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便只好通过旧朝烂透再换新朝的办法加以缓解,如此循环往复、故伎重演。人民所能指望的,无非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苦苦等待当朝贪饱吸足、自取灭亡,然后借着新朝新气象,过上几天好日子。这种节奏从未改变。1644至1645年之间,中国也是如此。
①③④⑤⑦⑧⑪⑰⑱㉒㉔㉕㉛㉜㉝㉞㉟㊱㊲㊶㊷㊸㊹㊺㊻㊽㊾[57][69][60][62][63][66][67][68][72][73]李天根:《爝火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第122页,第122页,第122页,第122页,第123页,第149页,第271页,第367页,第444页,第367页,第309页,第202页,第400页,第419页,第345页,第375页,第346页,第361页,第395页,第396页,第243页,第344页,第345页,第443页,第190页,第403页,第332页,第236页,第332页,第418页,第279页,第372页,第237页,第366页,第476页,第366-367页。
②㉙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083页,第5072页。
⑥此外参引鲍彦邦《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其于“白粮”问题研究深入,文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⑨李天根:《爝火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版,第124页。附注:此段引文中“征解其正税,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等项”,点校者断为“征解其正税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等项”,笔者以为不当而改之,特说明。
⑩参叶向高:《论本邑禁籴仓粮书》,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一百一卷,荒政部,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
⑫[64]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页,第369页。
⑬计六奇:《明季北略》,北都崩解情景,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0页。
⑭㉑㉓[52][53][54][55][56][65]李清:《三桓笔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8-109页,第110页,第109页,第188页,第183页,第4页,第4页,第5页,第108页。
⑮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⑯⑳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第4页。
⑲㊳㊴㊵[58][61][69][70][71][74]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3-84页,第98页,第98-99页,第99页,第224页,第31页,第214页,第216页,第214页,第224页。
㉖潘柽章:《和陶乞食诗赠乞食诸君》,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明遗民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79页。
㉗㉘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49-3650页,第3650页。
㉚史可法:《请颁敕印给军需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㊼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463-464页。
㊿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86-1889页。
[51]彭孙贻:《平寇志》卷之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75][76][77]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第440-441页,第441页。